打破日本性侵的沉默,她教會我們太多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40527-2019-12-19 15:26
判決後,伊藤詩織在法院外接受採訪時落淚
昨天,東京地方法院對一起備受關注的案件做出了判決,認定原TBS電視台華盛頓分社社長山口敬之的駁回無效,並賠償給被性侵受害者伊藤詩織330萬日元(21萬人民幣)。
法官鈴木昭洋表示,伊藤事發當日就到醫院求診,並有朋友及警察證明性行為違揹她的意願,相反山口的證詞與他發送的電子郵件內容矛盾,故判斷伊藤較為可信。
**伊藤手持寫有“勝訴”的牌子,在法院外哽咽地説:”真的太久了,勝利並不意味着我不曾受到過傷害。“**而山口則稱判決內容令人難以信服,將提出上訴。
日本推特上有記者稱,這個賠償數目約等於新人記者7個月的工資。
至此,這場訴訟歷時長達四年的“日本 MeToo 第一案”,終以受害女性的勝利結果而告終。
雖然 MeToo 風潮在此刻已然平息,但不影響這個判決結果的振奮人心——“進一寸,自有進一寸的歡喜”。
這份需要用四年才收割來的“歡喜”,我們應該如何冷靜地去消化?難道一切真的都會好起來?想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要先回到原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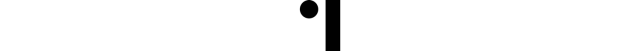
那是2015年東京春天的一個週五夜晚。畢業於紐約大學新聞系的伊藤詩織相約和一位著名記者在東京惠比壽吃飯。
這位記者是當時東京廣播公司 TBS(Tokyo Broadcasting System) 的華盛頓分社社長山口敬之,也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御用傳記作者”。
山口敬之
在約見的前一週,經朋友牽線搭橋,伊藤詩織給山口發去自己的簡歷,諮詢“能否去華盛頓當記者”。山口則回郵件稱:“只要簽證沒問題,以TBS的力量不是不可以,我會考慮。我下週臨時回國,如果有時間的話,一起吃飯。”
見面吃飯當天,二人吃了烤雞,喝了啤酒,還去了一家名叫喜一 (Kiichi) 的壽司店吃晚餐,伊藤詩織對當晚的最後印象,是感到頭暈目眩,起身去了廁所後,頭便靠着馬桶水箱,昏迷了過去。
等到伊藤詩織醒來時,她發現自己全裸躺在酒店牀上,被壓在山口身下,乳房和下身有明顯的疼痛感。
詩織很快從山口身下掙脱出來,跑到了衞生間,很有力氣的山口想把她推倒在牀上,掙脱不過,詩織便衝着她尖叫,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及山口是否使用了避孕套。
此刻的山口勸告伊藤詩織冷靜下來,並提出會給她買一粒事後避孕藥。**伊藤詩織很快離開了酒店,匆匆趕回家洗澡。**後來她才知道,這樣的處理是完全錯誤的,“我應該直接去警察局”。
關於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麼,至今沒有一個統一的版本。
在回應伊藤詩織民事訴訟的法庭文件中,山口説,他脱掉了詩織的衣服,幫她清洗乾淨,後來詩織醒了,還跪在他牀邊道歉,然後,山口要她躺回牀上去,並和她發生了關係。
山口強調説,她當時是清醒的,沒有抵抗。
然而在雙方同年4月18日發送的消息中,山口敬之卻講述了略有不同的另一個版本,暗指是伊藤詩織爬上了他的牀。
“所以,我完全沒有在你意識不明的時候,跟你發生性關係。我當時也喝得酩酊大醉,像你這麼迷人的女人半裸着來到我牀上,結果我們就那樣了。我想我們都應該檢討一下自己。”
其實在案發後的第5天,伊藤詩織就去東京警視廳的高輪警署報了案,最初接受報案的警察勸她不要起訴,還對她的故事表示懷疑,因為她講述的時候都沒有哭。
但是在伊藤詩織施壓,敦促警方查看事發地喜來登酒店的安全監控錄像後,警方最終開始認真對待她的案子。
事發地東京喜來登都酒店
警署的人找到了當時從壽司店送二人去酒店的出租車司機。司機回憶説,伊藤當時處於昏睡狀態,是被山口抱上車的。上車後,伊藤一直在喃喃地説“我要去車站”,山口則説“先去酒店,我們還有事情沒有談完”。
警方根據伊藤昏睡的狀況,和在酒店監控中看到詩織是被抱着走進房間的,合理懷疑山口在伊藤喝的酒水中加了睡眠藥,並強姦了她。
隨即高輪警察署發出了逮捕令,準備在成田國際機場設下埋伏,等山口回國走出機場時,就實施逮捕。
但是,**就在山口剛剛落地的時候,搜查員突然接到警視廳總部的指示:****停止逮捕行動。**這件事不了了之。
山口敬之不是普通的記者,他跟了安倍晉三整整16年,是安倍身邊少有的可以進入安倍家一起喝酒論事的御用記者。
2016年,山口敬之出版了一本近距離觀察安倍的書《總理》,封面的照片是山口親自拍的:安倍靠在自己的首相辦公桌上打電話——這是日本社會第一次公開安倍首相辦公室的模樣。
證據不足的伊藤詩織,很快就成了日本第一位公開姓名和長相控訴性侵的女性,但她想把山口這樣的人繩之以法,無疑是艱難的。
既在她意料之中、但也令她幾近崩潰的是,比起在公開場合一遍遍講述自己性侵經歷,一次次複習自己遭遇的傷痛,來自日本社會的敵意和藐視才是最痛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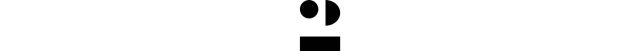
日本社會向來視性侵議題為禁忌,伊藤詩織公開指控被山口迷姦的做法,很快引起了各界注意,也開始審視對性侵受害者的支援不夠及司法制度不足等問題。
就文化根基而言,在日本的漫畫和色情作品中,**強姦常常被描述為性滿足的一種延伸,**而這類作品往往是多數日本人獲得性教育的重要渠道。
日本的強姦法沒有提到“同意”,約會強姦本質上是一個陌生的概念,私底下關於性暴力的教育和警醒也非常少。
根據日本法律,受害人須在遭性侵期間呼救和反抗才可被定性為強姦案,伊藤詩織這種因喝了酒而失去意識、無力抵抗的案件,則只會被視為“準強姦”。
因此,**警方和法院也傾向於狹隘地定義強姦,通常只在同時出現了強制暴力和自衞的跡象下才會追查案件,**至少這證明了受害者“並不享受這個過程”。這也就是伊藤詩織報案時沒有痛哭流涕,便被警察質疑的根基所在。
在伊藤詩織的案件引起了全國關注後,日本眾議院在2017年6月通過了將百年未改的「強姦罪」修改成「強制性交罪」,加重了有期徒刑,但施暴和脅迫等仍是構成罪行的關鍵因素。
日本政府修改強姦法
而且,如果施暴方或受害者確定喝過酒,或者沒有留下“證據”的話,警方也不鼓勵受害者起訴。
負責對伊藤詩織的指控進行跟進調查的少數記者之一——望月衣塑子 (Isoko Mochizuki) 表示,她就面對了來自整個新聞編輯室裏的男同事的反對。
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因伊藤詩織沒有即刻去醫院“取證”,推斷“她的理智大於憤怒”,因此心中可能有其他顧慮,或者是謀取職位不成便把山口拉下水進行“報復”。
早稻田大學 (Waseda University) 的性別法律講師谷田川知惠 (Tomoe Yatagawa) 便説道:“這個社會對女性的偏見是根深蒂固的,而且非常嚴重,人們根本不把性犯罪的危害當回事。****”
當時,在位於大洋彼岸的美國,由哈維·韋恩斯坦引發的 MeToo 運動愈演愈烈,震撼着國會、好萊塢、硅谷和各家新聞媒體。
哈維·韋恩斯坦
然而在日本國內,伊藤詩織卻慘遭冷遇,有日本女網民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這樣的評論:
“詩織小姐別有用心地與上級男士吃飯,想用走後門的方法去獲得職位,心裏面難道不明白會發生什麼?又沒錢又沒勢,別人怎麼可能不對她做點什麼?”
你或許會驚訝於日本女性對“性侵”的“寬容”,但根據御茶水女子大學 (Ochanomizu University) 的性別研究榮休教授戒能民江 (Tamie Kaino) 説,很多遭到性侵的日本女性“都會怪自己,她們會反省,‘剛剛那樣應該沒問題,那麼,這很可能是我的錯或者誤解’”。
根據內閣府2017年的調查,只有4%曾遭強姦的女性會報警求助,超過三分之二人表示未曾向任何人訴説有關經歷。相比之下,美國司法統計局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的數據顯示,在美國大約三分之一的強姦案會被報告給警方。
基於定罪門檻高、懼怕社會污名及警方冷待案件等問題,不少受害人寧願保持沉默。法務省的數據表示,去年有410宗強姦罪進入起訴程序,相較前一年增加了35宗,但在國際標準而言,起訴率依然偏低。
就在前天,世界經濟論壇發佈了最新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日本在153個國家中排第121位,和去年相比下跌了11位,是代表着發達國家的“七國集團”(G7)中排名最低的一個。
本就是個諱莫如深的話題,更別提像是伊藤詩織這樣,一開始就有求於人的“野心家”和“不完美受害者”,是多麼令日本社會不齒了。
另外還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法律很難懲治強姦犯,雖然國會前年修訂了條例,加重了強姦罪的刑法,將最低刑法由入獄三年提升至五年,同時擴大了性侵受害者的定義,將男性也納入法網**;**但不變的是,檢查官必須證明強姦案涉及暴力或恐嚇,或受害者無力反抗。依然是個死循環。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法務省的數據顯示,在日本即使強姦犯被起訴和定罪,有時候也不會入獄服刑,大約十分之一的人只獲得緩刑宣判。
上智大學 (Sophia University) 政治學教授三浦麻裏(Mari Miura)説:“所以我認為,日本民眾對到底什麼是‘同意’ (consent) 缺乏認識,而日本男性恰好從中獲利。”
就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伊藤詩織對業界前輩山口敬之提起了民事訴訟,並做了絕大多數日本女性絕不會做的事情:關於性侵的經歷出書、拍紀錄片。
她説:“我知道,如果我閉口不談這件事,這種可怕的性侵犯大環境永遠不會改變。”
2017年的10月, 伊藤詩織的《黑箱》問世了,她在其中詳述了案件的調查經過,其中包括警方冷淡曖昧的態度、取證過程的不完善、已簽發的逮捕令被緊急收回、調查人員的突然撤換等種種耐人尋味的細節。
但是在日本媒體和電視台,這本書只獲得了極少的關注,卻也從側面印證了“黑箱”這個書名。
伊藤詩織還拍攝了BBC紀錄片《日本之恥》(Japan’s Secret Shame),片中不乏日本議員對此事的公開表態:“懷疑裁決的公正就是對日本司法體制的侮辱”“對於此事,我認為男性才是受到巨大傷害的一方”,不少人稱伊藤詩織是“日本之恥”。
紀錄片《日本之恥》
更有一些日本網友痛罵伊藤詩織是“賣國賊”,不過是藉此事為跳板,牆外開花以求博得其他國家同情,趁機搬到英國去生活罷了。
但究竟是誰之恥呢?
在色情產業發達、性意味濃厚的日本,可以在報刊看到哪裏的 oral copulation 服務最好,風俗街上看得到誰的價位最高,去情趣小店也能打聽到哪家店的 sex massage 做得最棒。
但是一旦涉及到約會強姦、性侵這種話題,媒體輿論很少提及,很少看得到這方面的公開指控,像伊藤詩織這般更是聞所未聞。
便是已經有了這樣的發聲和推進難度,在今年4月,山口敬之甚至還對伊藤詩織進行了反訴。
山口敬之表示,伊藤詩織通過書籍和紀錄片的方式,將此案公之於眾和持續曝光的行為,導致了他在名譽和經濟上的雙重損失,所以要求伊藤詩織賠償1億3000萬日元,並在全國的報紙和媒體上公開道歉。
伊藤詩織説,自己恐怕這輩子都賺不了這麼多錢。
本以為今年結束之前都不會看到什麼好消息了,但伊藤詩織勝訴的新聞終於還是來了,和落淚的詩織本人一樣,我們:
“現在看到的景色,已經和之前完全不同了”。
算起來,從 MeToo 運動鬧得沸沸揚揚開始,已經是第三個年頭了。
在這個從“大快人心”到“矯枉過正”的三年時間裏,我們聽到了太多的故事和信息,卻很少停下來認真地反思這些生命的血肉擦痕,到底給我們帶來了怎樣的功課。
伊藤詩織為了工作機會去見山口敬之,遭遇性侵,稱得上是 Metoo 運動裏“職場權勢派”的典型案例,自然也會引發多一些的爭議和疑慮。
雖然我們不能粗暴地給這件事馬上下個定論,但是最近的熱播美劇《早間新聞》,倒是對職場環境下的 MeToo 有一些比較有趣的探討,值得我們借鑑和參考。
男女主角在新聞直播間錄節目
曾經的金牌早間男主播米奇,因為 MeToo 運動被拉下馬,還被自己的老東家迅速拋棄和封殺,在劇中超過一半的時間裏,他都在想如何走到台前,告訴大家這一切都是因為社會縱容名流和台里長期的silencing culture,讓他自己也習慣了這種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文化,所以才會去捕獵更多的女人,享受着成功的明碼標價。
男主角米奇享受生日派對
當其中的一位受害者漢娜來電台老總面前控告米奇時,老總僅是問了下這位受害人的職位,在得知是 junior booker 後,便馬上給她升職,“補償”的同時也乾淨利落地解決了一起公關危機,徒留這個初出茅廬、對世界充滿好奇、對工作充滿熱情的女孩,在原地懵圈和掙扎,又在不知所措中接下這樣的“天降好事”。
揭發性侵的漢娜意外獲得升職
這當中到底是誰在包庇誰?又是誰的羞恥心讓誰放不下?應該都不太無辜,因為人性的複雜。世上愈是黑白分明的事情愈是要出錯的。
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因為遭遇性侵而獲得的“好處”,並不能給性侵這個行為本身去污名化。
就像韋恩斯坦在前天接受《紐約郵報》採訪,對自己的罪行閉口不談,大概是覺得“瑕不掩瑜”,不斷強調自己的成績。
哈維·韋恩斯坦
“**我想要這個城市承認我過去是什麼樣的,而不是我後來變成了什麼樣子。**我感覺自己像是一個被遺忘的人,女性執導的電影和關於女性的電影,我比任何電影人做得都多。我説的是30年前,不是説現在。現在這件事已經變得流行,我是第一個那麼做的人,我是先鋒。”
我們不會否定韋恩斯坦曾經在藝術上做出的成就,但是這些成績也不能被當成惡行的“保護傘”,一個懂得電影藝術、馳騁商界、在世界級名利場上居高臨下的他,也的確曾對女性説出了“你把浴袍脱下,你過來,你要是不願意我會讓你惹上麻煩”這樣的話。
兩種樣子都會被記住的。
不管多麼位高權重,那麼做是錯了,錯了就是錯了,整個社會不僅需要認識到這一點,也該尋求一些“伊藤詩織式”的改變吧。
或許比高喊“發聲就會有力量”更有用的,是受害者們不再沉溺於羞恥,不再對這樣的痛苦諱莫如深的自我折磨,而施暴者們多一些共情,多一些對痛苦的想象力。
這讓人想起《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裏的話:
社會對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強暴一個女生,全世界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連她都覺得是自己的錯。罪惡感又會把她趕回他身邊。**罪惡感是古老而血統純正的牧羊犬。**一個個小女生是在學會走穩之前就被逼着跑起來的犢羊。
《房》作者林奕含生前照
學着放下吧,這樣想這樣做的人多了,大概也就能成為常態了。
“我是餿掉的柳丁汁和濃湯,我是爬滿蟲卵的玫瑰和百合,我是燈火流離的都市裏明明存在卻沒人看得到也沒人需要的北極星。”
像這樣被性侵後還自我貶低的句子,這個世界不需要更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