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照耀中國的理想主義者,我很懷念他_風聞
乌鸦校尉-乌鸦校尉官方账号-2019-12-26 13:18
大家好,我是烏鴉上尉。
今天是12月26日,毛主席的誕辰,我們就來聊聊**“他”**——張牧之。
在張牧之來之前,鵝城是一個黑暗的地方。
富人和地主在城裏為所欲為,而人民羣眾是他們的奴隸,打碎牙齒往肚子裏咽。
老百姓只知道當地的黃四郎,不知道有什麼縣長。
縣長敢反抗黃四郎,他們也不敢反抗,因為縣長是流水的縣長,黃四郎才是鐵打的老爺。
有一個叫埃德加·斯諾的美國記者到了中國,民國的交通部長孫科給他安排沿着鐵路旅行,希望他能寫一寫中國的風景。
然而,斯諾卻忠實地記下了,他沿途看到的這個古老國家的落後和苦難:
道路兩旁種滿了罌粟,陝西軍閥們為了賺錢,強迫農民把最肥的地拿出來種鴉片,一旦出現乾旱,糧食就不夠吃,在西北大饑荒的時候,幾年時間就餓死了三百多萬人;
西北是各種流行病的重災區,在上路之前,為了安全,天花、傷寒、霍亂、鼠疫……斯諾把自己能打的預防針通通打了一個遍;
饑民為了換一點吃的,心甘情願賣兒賣女,讓自己能多活幾天;他們餓死了以後,屍體還沒有下葬就消失了,因為在一些村莊裏,人肉是公開售賣的……
1936年四川饑荒的時候,四川靖化縣縣長於竹君頭一次看見吃死屍、吃活人的慘像,從小讀四書五經的於竹君被嚇得精神失常,覺得魯迅寫的《狂人日記》痛斥吃人現象,簡直是小題大做。
於是,這位學法律出身的縣太爺寫了一篇奇文,説“食人者不食人,則時刻有被人食之危險! ”
所以,食人者不犯殺人罪,應正名為“正當防衞”。
四川人籌了141萬賑災的錢,但國民政府貪腐成性,連這點錢也不肯給到災民頭上,蓬溪縣一個小小的公安局長陶子國,就貪掉了一萬多元賑災的錢。
四川省政府三番五次邀請慈善家尹昌齡主持川省賑務,卻被對方屢屢嚴詞回拒。
因為尹昌齡認為,四川之災實為“人災”,而非“天災”,他一直在掏錢救自己身邊的百姓,卻始終不願和國民政府合作。
“終是人災一日不去,賑務一日難言”。
誰能拯救鵝城?這是一個當時很多人都在找,卻沒有人能回答的問題。
從洋務運動開始,這個國家的精英們探索了很多次,卻沒有一次能夠成功。
1
1918年,李大釗介紹了一個學生去北大當圖書管理員。
這個當圖書管理員的人很不安分,不光在圖書館裏讀了很多經典,還見到了許多新文化運動中的領袖來圖書館借書,有不少還是他的偶像。
每次他看見了自己的愛豆,都要湊上去想要和愛豆討論學術問題。
可惜,沒有大佬有時間聽一個操着福南口音的年青人講話。
“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
有一次,他去課堂旁聽,壯着膽子向講台上的胡適提問。
結果,得知他不是正式學生時,胡適****直接拒絕回答。
這個到處碰壁的小透明,就是毛澤東。
在當時的中國,“胡適”這樣所謂要救中國的民國大師比比皆是。
但是靠“胡適”這樣的人,是推翻不了黃四郎的,因為****他們嘴上説自己是麻匪的命,但實際上卻懷着一顆師爺的心。
毛澤東在中共三大上説,要把農民作為革命的必要組成部分。
但是,黨內的學院派知識分子們,守着本本不放,不理睬他。陳獨秀就説:“農民是小資產階級……如何能做共產主義的運動?”
覺得農民重要的,只有他一個人。
沒辦法,青年毛澤東只能再次回到湖南。
從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他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跑到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攙着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什麼,問他們要些什麼,仔細聽他們講話。
他很快就發現,很多漢口、長沙的知識分子説的道理,其實都是瞎想的,真實的農民説出來的和他們完全相反。
他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寫成了一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但是,他是黨內的少數分子,人微言輕,沒有人接受他的主張。
1927年,中共五大,他提出“建立農民武裝”,但再次遭到強烈反對,還被取消了投票表決權。
除了他,沒有人真正意識到,廣大的人民羣眾才是這個國家真正的主人。
正是這一年,蔣介石、汪精衞相繼叛變革命,在全國大肆殺共產黨。
秋收起義雖然如期舉行,但還是失敗了,爾後各大城市的起義也接連失利。
連續的失敗終於讓共產黨明白了,在重兵防守的城市,共產黨沒有一點機會。
唯一的出路,是農村。
前面説到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後來在張學良的安排下,去了紅軍的根據地,他用自己在紅軍這裏的真實見聞,寫了一本《西行漫記》。
在《西行漫記》裏,斯諾寫道,自己見到了根據地一羣年幼的孩子,就問那些還在玩耍的孩子:
“什麼是共產黨?”
“是幫着紅軍打白匪和日本的人。”一個八九歲的小孩脱口而出。
“還有呢?”
“他幫着打地主和資本家!”
“那什麼是資本家?”
“資本家就是不自己幹活,而讓別人給他幹活的人。”
“這裏有地主或者資本家嗎?”
“沒有!”孩子們齊聲一起大喊道:“他們都跑了!”
“跑了?幹嘛跑了?”
“怕咱們的紅軍唄!”
一個小孩子,卻説紅軍是**“咱們的”**軍隊,斯諾對此感到無比好奇。
斯諾又去問根據地的戰士,為什麼參加紅軍?喜歡紅軍嗎?
戰士説:“紅軍教我們讀書和寫字,教我們操縱無線電和怎麼用步槍瞄準,紅軍是幫助窮人的。”
“紅軍待我們好,我們一回也沒捱過打,這裏人人都一樣,不像在白區,窮人是地主和國民黨的奴隸,這裏人人打仗都是為了幫助窮人,為了救中國。
紅軍打地主,打白匪,紅軍打日本,怎麼會有人不喜歡這樣的隊伍呢?”
紅軍每到一地,就會把土地分給窮人,減輕賦税,大規模興辦集體企業。
僅僅是1933年,江西一個省就有一千多個蘇維埃合作社,在這裏,妓女不再需要當妓女,農民不再需要種鴉片,兒童也不需要去地主家當奴婢。
紅軍的戰士有來自四川的,有來自湖南的,有來自江西的。
這些戰士要麼是被地主剝削的農民,要麼是被師傅虐待的學徒,要麼是被國民黨害死雙親的孩子。
戰士沒有衣服穿,毛澤東就把自己的衣服給他穿,戰士沒有鞋子,毛澤東就自己也不穿鞋子……
有個福建蘇區的年輕戰士,跟着紅軍走完了長征的全程,卻一點都不把長征當回事,還説**“如果紅軍再長征的話,我就再走兩萬五千裏!”**
這是受壓迫的窮苦百姓第一次自己站起來,建立了一個屬於自己的軍隊。
正是在紅軍這裏,他們才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被當做一個平等的人看待,能夠有尊嚴地活着。
在紅軍剛到井岡山上的時候,井岡山上其實有兩支農民武裝。一個叫袁文才,一個叫王佐。
他們是當地的綠林好漢,佔山為王。
一開始,有人覺得,需要消滅這兩個人,他們覺得這就是兩個土匪。
然而,毛澤東不這麼認為,他調查過了,這個袁文才是客家人,因為反抗土豪劣紳的壓迫參加了當地的馬刀隊,是被世道逼得落草為寇的,佔山為王期間也是多次劫富濟貧。
於是,毛澤東親自去見了袁文才,和他聊了聊天,肯定了他反抗豪紳地主階級的革命精神,然後告訴他光是佔山為王是不夠的,革命需要有組織有目標,最後還給他送了100多支槍。
袁文才當了多年的山大王,還是第一次碰到一個真正理解他苦衷的,瞭解他心意的人。
這一談之後,不費一兵一卒,袁文才就主動歡迎紅軍來井岡山,願意接受改編,從此跟着毛澤東。
毛澤東打心眼裏把自己當成人民的一份子,人民也就心甘情願地追隨他。
斯諾採訪的戰士,一説起自己參軍之後的故事都會興高采烈,可以侃侃而談每次戰役的日期和過程。
但是一旦讓他們講述自己參軍之前的事情,他們就需要回想好一陣子才能想起來。
用斯諾的話來説就是:
“他們傾向於把這段歲月視為黑暗年代,他們真正的生命,是從成為共產黨人開始的!”
這樣的一支隊伍,在戰場上無比堅韌。
飛奪瀘定橋的時候,對岸的國民黨軍早已架好了機槍,第一批衝過去的人一定會被掃射而死,但是紅軍每一個人都知道,全軍的生死都繫於鐵索橋上,這仗打不下來,自己和戰友都要死。
於是,紅軍戰士紛紛主動請戰,揹着手榴彈和毛瑟槍,攥着鐵索一點一點往前挪。
第一個戰士被打中,掉到急流中就沒有了,緊接着是第二個第三個,但剩下的人還在不斷順着鐵索前進,明知是死,也要奪下鐵索橋!
對岸的川軍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打仗的人——這些光着腳,衣衫襤褸,只有十幾歲的年輕人,當兵不是為了錢,不是為了混碗飯吃,而是為了勝利願意捨生忘死。
打着打着,連對岸的川軍都在默默盼望這些紅軍成功,紅軍衝過去朝國民黨陣地進攻的時候,對岸有的國民黨軍立馬扔下槍就投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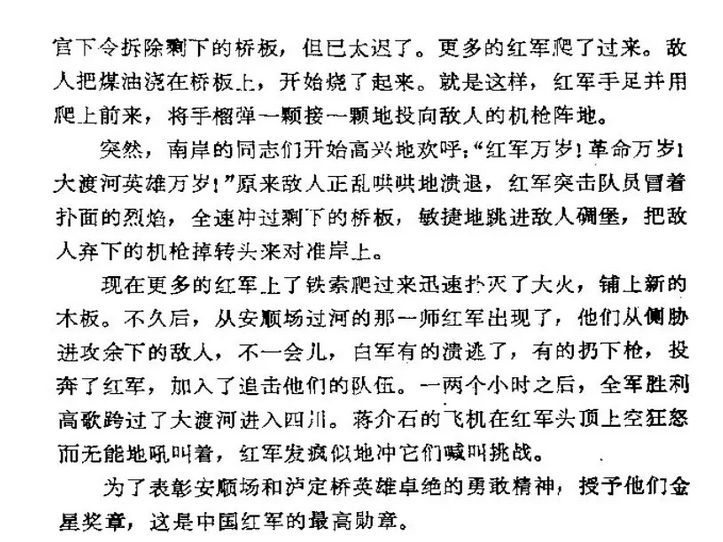
斯諾《西行漫記》截圖
四渡赤水的時候,紅軍對國軍是3萬對40萬,國軍有飛機偵查,紅軍在當地沒有原來根據地的羣眾基礎,沒有依靠。
國軍對紅軍是壓倒性的優勢。
但是在毛澤東的指揮下,紅軍卻能在國軍的眼皮底子下晃點國軍,把蔣介石騙得一愣一愣的。
美國作家索爾茲伯裏曾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這麼描寫當時的場景:
“毛澤東故伎重演,而蔣介石卻像巴甫洛夫訓練出來的狗一樣,毛澤東要他怎樣,他就怎麼樣。****”
毛主席用自己的實踐,給出了那個無數前輩都沒解決的問題的答案:
要拯救鵝城,推翻騎在人民頭上的黃四郎,需要的是人民自己的力量,是一支由人民羣眾先鋒隊組成的軍隊。
在此之前的數千年,中國的執政者一直都解決不了中央權力到不了縣、鄉一級的問題,而在此之後,中國的十多億人終於可以團結一心做大事。
在1925年,毛主席寫下《沁園春·長沙》時,對於革命的前途還有點迷茫,雖心憂天下,但還是寫道:
“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但僅僅到了1936年,他寫《沁園春·雪》時,卻已然成竹在胸,彷彿天下大勢,盡在掌控: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2
在張牧之成為領導核心之後,打黃四郎的革命隊伍就幾乎再沒有出過大戰略判斷上的失誤。
如果有的話,可能是他覺得解放戰爭需要5年,但是蔣委員長鬼斧神工的操作把時間縮短到了3年。
無論是抗日戰爭還是解放戰爭中,革命隊伍都面臨過無數驚濤駭浪。
但你總能從毛澤東的詩句中感覺到,在****一個充滿光輝的理想主義者筆下,革命中那種血與火交織的浪漫感,會讓一切風花雪月都黯然失色: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新中國成立之前,從鴉片戰爭到日本侵華,隨便一個工業國就可以騎在中國頭上作威作福。
但是新中國剛剛成立,就可以在朝鮮半島硬剛全世界最強大的軍隊,把對手一路逼退回三八線!
在前三十年裏,印度、蘇聯、越南、美國都像以前的列強一樣試探過中國,但新中國用自己的實力證明了,再強大的對手,也無法打斷中國發展的腳步。
在革命的過程中,很多人都犧牲了,毛澤東的家人也不例外。
他的弟弟、他的妻子、他的妹妹、他的侄子,都是英烈,20多歲、30多歲就犧牲了。
毛岸英是毛澤東和楊開慧的長子,從小就吃過無數的苦,楊開慧被湖南軍閥逮捕的時候,只有8歲的毛岸英也一同被抓進監獄。
後來,幾經輾轉,毛岸英被送到蘇聯學習。1941年,蘇聯和德國開打之後,儘管中蘇之間有不讓孩子服兵役的規定,但毛岸英還是主動要求參戰。
1946年回到中國之後,毛岸英只跟在他的身邊吃了兩天飯,就被要求去機關食堂吃大灶。
後來,毛澤東又覺得兒子不僅要學知識,還要和工人一樣參加勞動,“補上勞動大學這一課”。
毛岸英就按照父親的要求,去解放區搞過土改,做過宣傳工作,當過秘書,跟着李克農當過翻譯,後來又去基層工廠當工人。
可以説,作為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從來沒有享受過任何一點特權,反而總是戰鬥在最艱苦最危險的第一線。
朝鮮戰爭爆發後,毛岸英又主動要求,去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
但不幸的是,1950年11月25日,在美軍飛機的一次轟炸中,毛岸英犧牲了,成為了197653名志願軍烈士中的一個。
1951年,彭德懷回北京彙報第二次戰役的時候,非常內疚地想要對毛主席道歉。
但是毛主席打斷了彭德懷的話:“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志願軍戰士死了成千上萬,岸英就是屬於犧牲了的成千上萬革命烈士中的一員,一個普通的戰士。
不要因為是我的兒子,就當成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不能因為是我的兒子,就不應該為中朝兩國人民共同的事業而犧牲,哪兒有這樣的道理?”
但其實,在剛得知毛岸英犧牲的時候,毛主席一度悲痛得吃不下飯,睡不着覺。
彭德懷離開之後,他站在窗前,默默地看着庭院裏的松柏,無不傷感地念起了南朝庾信****的《枯樹賦》:
**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
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毛岸英對自己的要求非常苛刻,即使自己已經付出了很多,已經非常優秀了,毛岸英還總是對自己不滿意,想要做得更好。
毛岸英總是在日記裏一遍一遍地問自己:“我做毛澤東的兒子合格嗎?”。
在去朝鮮戰場上之前,毛岸英又拿這個問題問了毛澤東一遍,但他只是説:“等你回來,爸爸給你個答覆。”
誰成想,這次分別,就是天人永隔。
毛岸英犧牲之後,有無數的人往毛岸英的身上潑髒水,用各種各樣編出來的“蛋炒飯”段子抹黑毛岸英,説毛岸英去朝鮮戰場是去“鍍金”的。
在很多影視作品裏,毛岸英這個角色一出現,往往都被塑造成一個唯唯諾諾跟在父親身邊的木偶,完全不是真實的鮮活的人。
反而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總是被拍成一個風度翩翩又能力超羣的公子哥,什麼“台灣民主之父”。
一個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獻給了這個國家,每每戰鬥在最前線的人,被人説是鍍金,要搞世襲。
一個正兒八經子承父業搞世襲的人,卻被奉為“民主先鋒”。
這簡直是天大的諷刺。
可能在某些人的眼裏,身為“他”的兒子,就是一種罪過,哪怕把心掏出來把肺掏出來,也是罪過。
毛岸英犧牲之後,毛澤東瞞着所有人,把兒子留下的兩件棉衣、一雙襪子、一頂軍帽和一條毛巾,疊得整整齊齊,悄悄地收在了一個小箱子裏。
這個箱子,他一直帶在身邊,珍藏了20多年,從來沒有丟掉過。
也許,夜深人靜的時候,毛主席還會拿出這些東西細細地看,想象着自己的兒子還活着,還在自己身邊。
一直到1990年,在整理他的遺物時,工作人員才發現了這些東西。
我想,如果能重來一次,毛主席肯定想以一個父親的身份,好好對毛岸英説上一句他心裏想了很久,卻始終沒有機會説出口的話:
“兒子,爸爸為你感到驕傲。”
3
鵝城和平了,張牧之趕走了黃四郎,也在朝鮮打跑了十八國聯軍。
但這並不代表革命就此結束,反而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的開始。
天底下沒有人不會犯錯,一個隊伍壯大了,總會被腐蝕,總會出現有別的心思的人。
打倒了黃四郎,張牧之還想回山裏,繼續當他的革命者,可是張牧之的手下不幹了。
老三老四不想回到山裏,他們想去上海,他們想拿着師爺那裏來的委任狀,去當新的縣長。
《讓子彈飛》的最後,老三拉着和電影開頭湯師爺一樣的列車,奔往上海,留下了張牧之一個人。
而穿着湯師爺衣服的黃四郎,又坐在了列車後面。
歷史的車輪還在滾滾前進,黃四郎的身影依然盤踞在革命者身邊,陰魂不散。
歷朝歷代的故事,免不了都要落入同一個宿命:
屠龍的勇士守着如山的財寶,自己也逐漸變成了惡龍,然後等待下一個屠龍者來終結自己,數千年的封建王朝歷史,都是如此地循環往復。
革命者始終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是——代表人民羣眾的先鋒隊被腐蝕了,該怎麼辦?
1965年,已經闊別井岡山36年的他突然提出:“我老了,經常夢到井岡山,很想回去看看……”
5月22日,他沿着當年秋收起義的路線,重新回到了那個讓他魂牽夢繞的地方。
真正的革命者,始終要一把槍對着敵人,另一把槍對着自己。
在井岡山上,他揮毫寫下了一首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
久有凌雲志,重上井岡山。千里來尋故地,舊貌變新顏。
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雲端。過了黃洋界,險處不須看。
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
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張牧之又一次背叛了自己既得利益者的身份,再一次站到了人民這一邊。
那時的他,還是那麼豪情萬丈,意氣風發。
在他眼裏,只要自己想做,這世上就沒有什麼事,是自己做不成的!
哪怕這次的對手,是亙古不變的興亡鐵律。
它看不見、摸不着,它盤亙在人心裏,比國民黨,比斯大林,比美帝,比他面對過的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敵人都更強大、更可怕!
但他依然敢説,“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
其實,從參加革命的那一天起,毛澤東就是其中的“異類”。
革命的路上危險重重,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堅定無比的信仰,大多數人都沒有能夠堅持走到最後。
一大一共13名代表,其中有4人犧牲,有3人叛變投敵,有2人成為漢奸,有2人脱離革命後又迷途知返。
從那條小船上堅定不移地走到新中國成立的人,只有他和董必武兩個人。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去世。
董必武去世的當天,毛主席把一首送別詞,反覆聽了一整天,是南宋張元乾的《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
夢繞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
底事崑崙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
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老易悲如許。更南浦,送君去。
涼生岸柳催殘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斷雲微度。萬里江山知何處,回首對牀夜語。雁不到、書成誰與。
目盡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舉大白,聽金縷。
也許是覺得最後“舉大白,聽金縷”兩句太過傷感,他忍不住提起筆,把這兩句改成了**“君且去,休回顧”**。
**目盡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君且去,休回顧。
這次也一樣,張牧之依然是少數,他要淨化被腐蝕的先鋒隊,老三和老四並不同意。
不止老三老四,當初一起上山的人,有的人已經忘了自己本也是窮苦人的出身,又開始騎到窮苦人身上作威作福。
從革命隊伍誕生那一天起,這個問題就如影隨形。
紅軍時期有個戰士叫肖玉璧,窮苦人出身,給地主放馬的,參加紅軍以後是有名的戰鬥英雄,戰功赫赫,身上有90多處傷疤。
他受傷住院的時候,毛主席曾去醫院看望他,當看到這個戰鬥英雄骨瘦如柴的時候,毛主席眼眶濕潤,把自己特批的半斤牛奶全部送給了他。
然而,後來他居功自傲,當税務分局局長時貪污受賄,還把根據地很緊缺的糧、油偷偷倒賣給國民黨,從中牟利。
事發被捕之後,按紅軍法院陝甘寧高等法院的判決是死刑。有很多戰士給肖玉璧求情,説他是戰鬥英雄,希望網開一面,但毛澤東表示堅決擁護法院的判決,一定要槍斃他。
有的人沒有忘,但“革命者內心潛藏的黃四郎”看不見摸不着,張牧之以往讓他們打誰,他們説一不二。
但這次的對手,他們一輩子都沒有碰到過,即使想打,他也不知道這樣虛無縹緲的對手,要從哪裏打起。
只有老二,始終站在張牧之的身邊。
不少曾經的戰友,成為了自己的敵人,他支持的人民羣眾也不理解他。
在《亮劍》裏,1967年,李雲龍的部隊換了一個新政委,叫馬天生。
讓李雲龍覺得奇怪的是,這個馬政委1955年還是上校,怎麼才過了12年,就爬到了正軍級的位子?
結果一出事,李雲龍就明白了。
這個馬政委最大的本事,就是挑動其他人不要“文鬥”,要去“武鬥”,不要光寫口號寫大字報,要拿槍拿炮去“鬥”,最好拼個你死我活。
**明明本來是要自我淨化,有些人卻把事情擴大化,**拿戰友和人民的血換自己的前程。
馬天生正是這種人,才會升官升得這麼快。
《亮劍》原著截圖
人民羣眾的力量是偉大的,但是需要引導,沒有引導的羣眾力量失控,就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混亂。
“革命”可以,但是不能只會“革命”不會“生產”,只會“造反”,不會“建設”。
原先的戰友不再和他站在一邊,新起來的人有很多也不是真的理解他的本意,只是找到了一條升官很快的大路,只是想做一個“馬天生”。
有好人被打成了壞人,有壞人被洗成了好人;有人公報私仇,有人趁機上位;有人只想“文鬥”,有人醉心“武鬥”……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已經徹底脱離了他原來的初衷。
他不得不重新拿起了筆,寫了很多文件,告訴人民要怎麼在“革命”的同時不要忘記生產,不要忘記建設。
但是他老了,他太勢單力薄了,那些文件推行不下去,成了一張又一張的廢紙。
張牧之舉目四望,發現自己無比的孤獨。
“四海龍王”水淹陳塘關
1975年,他已經垂垂老矣,做完白內障手術沒多久,一隻眼睛剛剛能看東西,他就去看書。
有一天,眼科大夫陪他看書,卻發現看着看着,他突然發出一陣嗚咽聲。
大夫趕忙抬頭,他不知為何,捧着古書哭了出來。
大夫趕緊起身去勸:“你不能哭,千萬不能哭,眼睛要壞的!”
但是他還是控制不住自己,抱着古書,一時間哭得老淚縱橫,肝腸寸斷。
大夫靠近去看,他讀的是南宋陳亮的詞《念奴嬌·登多景樓》:
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鬼設神施,渾認作、天限南疆北界。
一水橫陳,連崗三面,做出爭雄勢。六朝何事,只成門户私計。
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憑卻長江管不到,河洛腥羶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疆場。
六朝何事?只成門户私計。
那一刻,歲月塌了下來,重重地壓在了他的身上。
他老了,他的時間不夠了,他一個人的肩膀再也無法扛起這片天了。
他努力過,戰鬥過,和數千年的興亡鐵律殊死搏鬥過,他真的如同太陽一樣,把自己的生命都燃燒殆盡,只想要為天下蒼生驅逐黑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但是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在頑固的人性面前,他一敗塗地。
尾聲
1976年9月9日凌晨10分,他與世長辭。
他誕生的時候,這個國家積貧積弱,人均壽命只有35歲,全國80%的人都是文盲,有鋼廠也找不到能勝任的工人。
隨便一個帝國主義就可以逼得中國像饑民一樣賣兒賣女,最繁華的上海灘,年年都是餓殍遍地,人們的眼前一片黑暗,看不到未來的出路。
他離開的時候,這個國家已經有了一整套完整的工業體系,人均壽命達到了65歲,文盲率降低到了20%,有數以億計的產業工人。
大家能吃飽穿暖,能有尊嚴地活着,再沒有國家能夠欺負我們,後來的開放和飛速增長都有足夠的基礎,前途一片光明。
他引以為傲的兩件大事之一雖然失敗了,卻提醒了後來的執政者,要在內部建立有效的自查自省的機制,時時注意自我糾正,防止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腐蝕變質,不要走歷朝歷代的老路。
很多人年少的時候讀不懂他,但時間越久,懂他的人就越多;時間越久,懷念他的人就越多。
沒有黃四郎,對鵝城很重要。
在他死後,有無數宵小之輩又換了一身裝束,重新粉墨登場,想要再在這個時代再當一次黃四郎。
他活着的時候,這些宵小都被治得服服帖帖,唯有在他死後,這些人才敢出來對他指指點點,陰陽怪氣。
但是這些人也知道,他在人民羣眾心中的地位很高,直接攻擊不成,這些人就編出各種各樣的段子,旁敲側擊,抹黑他的戰友,污衊他的兒子,這些謠言七拐八拐,最終都會拐到他的身上。
但是,是非曲直,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
他活着的時候,一直反對個人崇拜,老百姓對他喊萬歲,他卻總是回答説**“人民萬歲!”**
如果沒有他,今天的中國很可能會是另外一個模樣。
但他卻時刻提醒我們,功勞屬於全體人民,雖然我們一個人的力量無比渺小,但是隻要我們團結起來,那誰也無法欺負我們。
無論身前身後,全世界都有無數他的粉絲,景仰他、崇拜他的人數不勝數,無論是敵是友,對他的評價都極高。
但他卻時時提醒我們,對誰也不要跪,這世上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每一年的這個時候,都會有數萬民眾不惜坐十幾個小時的火車,不惜翻山越嶺,從全國各地自發趕去湖南韶山紀念他。
****真正一心為民的人,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
主席,生日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