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骨柔情陳丹青:小學畢業,一幅畫3200萬,怒辭清華教授,陪木心終老……_風聞
最人物-最人物官方账号-记录最真实的人物,品味最温暖的人间2019-12-26 13:23
作者| 北方女王
來源| 最人物
每一代人的批評與掙扎都不該被浪費。
從五十年代走來的陳丹青身上,最為可貴的是歷經多半個世紀的沉浮與滄桑後,仍舊擁有獨立的人格與魏晉之風骨。
陳丹青總是身穿一襲黑色長袍,留着利落的平頭,戴着眼鏡,抽着煙出現在公眾面前,看上去温文爾雅。
他一貫地似乎帶着點微笑,又似乎面無表情,一雙鋭利的眼睛冷冷地看着這個世界,目光如炬折射出一身傲骨。
木心總結的好:陳丹青有點英氣,有點秀氣,有點流氓氣。
有人曾説陳丹青是連耳朵背後都乾淨的人。乾淨與剋制,對於一箇中年人來説,可謂是最高的修為。
這些年大家基本上已經淡忘陳丹青的畫家身份了,看客們對於他的“公知身份”更感興趣,只是在他怒吼批評的背後,總有種極深的落寞。
在別人眼中,他是個傲慢的知識分子,嬉笑怒罵皆成文章。
只是陳丹青從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公知,他不過是認清自己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後,漸漸在泥沼裏學會了自救:
“自救就是忠實自己的感覺,認真做每一件事,不要煩,不要放棄,不要敷衍。”

保持着知識分子具有的批判本性,敢説真話這件事,一度讓陳丹青成為眾矢之的。
2000年,陳丹青離美回國,載譽而歸的他當即就被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聘請為教授,且具有招收博士生的資格,學校還專門以他的姓名成立了純藝術教學研究室。
但是這所有的形式,看上去都形同虛設。
這一年5月,陳丹青開始招收博士生。報考清華美院博士生的24位考生中,有5名入圍,但最後因外語而全部落榜。
清華美院考慮到陳丹青是首次招生,讓這5名考生以博士課程訪問學者名義成為陳丹青的學生。第二年,這5人再次因英語而失敗離校。
陳丹青長達3年招不進一名碩士生。甚至有一位女學生,連續兩年繪畫專業成績位居第一,第一年英語政治各差一分,第二年英語仍未及格,依然被無情地拒之門外。
陳丹青説:“我不想慫恿她考第三次。對一位想當藝術家的青年,這樣的考試是不折不扣的荒謬和侮辱。”
在他的內心,就算這些孩子畫得和梵·高、畢加索一樣好也沒用。藝術學院應該招一些瘋子,而不是那些成績優秀的好孩子。
陳丹青憤怒不已,這種憤怒不是為自己,而是為這羣學生:
“專業前3名的永遠考不進來,由於外語達不到那個分數,因此他們的畫形同廢紙。我們不能單憑英語分數就把一個孩子粗暴地拒絕在門外。”
而在1978年,陳丹青自己就以外語零分、專業高分被中央美術學院錄取。
他惜才,對這種有天分的學生進不了高等藝術學府的情況,陳丹青多次與校方爭論不休,拍桌子瞪眼,再三手寫上書,跑各種辦公室,可是每次都是完全沒結果。
僵化、教條的管理導致人才流失,這讓陳丹青倍感惋惜,也很失望:
“我不相信現行考試製度,不相信教學大綱,不相信目前的排課方式,不相信藝術學生的品質能以課時與學分計算,但是我不得不服從規定。”
終於在2004年10月15日,陳丹青向清華大學遞交了辭職報告,憤然離職,他不想再委曲求全了。
同事們一支支香煙遞過來,對其進行勸阻,可是陳丹青去意已決,後來在訪談中,他自嘲道:“他們當然不願意我走,少了個心直口快的傻逼。”
他辭職時很平靜,媒體卻風波四起。
這件事掀起了中國現行教育制度的討論高潮,陳丹青在公眾眼中也從一位畫家變成了一位批評家。
自那之後,他成了記者熱衷於採訪的對象。媒體叢林中出現的陳丹青,像一把尖鋭的刀,鋒利而不羈。

弗裏德曼筆下加速的世界,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喧囂,一切看上去都是徒勞和無意義的,在這種語境下生存的我們,漸漸走進屬於陳丹青的那個時代。
1953年,陳丹青出生於上海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陳兆熾是民國知識分子,因崇敬文天祥,用“留取丹心照汗青”給他取名“丹青”。
陳丹青自幼喜歡繪畫。上世紀六十年代畫畫的少年,頂多玩玩水彩,畫不起油畫。
1967年,機會來了,全國工廠農村要畫巨幅領袖像,他跟着中學美術老師四處幹活兒,每接一單,剩餘的顏料畫筆就歸他所有。
陳丹青白天畫人像,晚上就臨摹達芬奇、米開朗琪羅的素描作品。
年輕時的陳丹青
然而那是一個對知識分子缺乏善意的年代,陳丹青深受其苦。
1970年,只讀了兩年初中的他就被註銷掉上海户口,流放到偏僻的贛南農村插隊落户。
那是很絕望的一段記憶,16歲的陳丹青覺得自己的天全部黑下來了。他茫然離開曾經打架、畫畫、鬥蟋蟀、爬屋頂的上海石門一路老弄堂。
城市長大的孩子,被迫流放到鄉下,房間裏只有那麼一個油燈。
他跟兩個男孩子擠在一張牀上,陳丹青至今仍然記得前幾天晚上自己幾乎是醒着的,幾斤重的老鼠,整夜在被子上竄來竄去。
連綿不斷的陰雨,籠罩住整座深山。陳丹青聽着雨打在瓦片上的聲音,抽着煙,望着漫無邊際秧田,內心茫然絕望,腦子裏是空的。
20歲那年,陳丹青又輾轉到了蘇北農村插隊。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裏,他蹲在村辦的骨灰盒廠畫了近千個骨灰盒。心情極其壓抑之下,所幸有紙筆可以讓他畫畫。
在極其惡劣的生活、勞動中,陳丹青一直自主學習繪畫,是當時頗有名氣的“知青畫家”,期間他還被當做人才借調到西藏搞創作。
1978年,“文革”的陰影逐漸褪去,國家恢復了高考。這一年,陳丹青以專業第一、外語0分的駭人成績考進了中央美院油畫系研究生班。
當時他在英語卷子上寫:“我是知青,沒上過學,不會英語”,然後站起來就走了。
人家讓他填寫學歷,他只填了小學畢業。美院的老師説不可以這樣填,但25歲的陳丹青表示自己初中還沒畢業就下鄉去了,為何要作假。
後來他被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聘用,又要填學歷,陳丹青仍然堅持説:我小學畢業。
他説:“無論繪畫還是寫作,我儘量不説假話。”
1980年,對西藏倍感懷念的陳丹青再次進藏。
高原的風土人情、樸實無華的藏民,給了這個年輕人震撼與觸動。他創作了別開生面的《西藏組畫》。
“我記得在七平方米的小房間裏畫那些畫,光線差,黃昏就挪到門口,就着過道的光繼續畫……”
陳丹青的《西藏組畫》,以高度的寫實主義描繪出真實的西藏生活,避免了泛英雄主義的悲壯,作品公開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自那之後,陳丹青被賦予為劃時代意義畫家的頭銜,聞名海外四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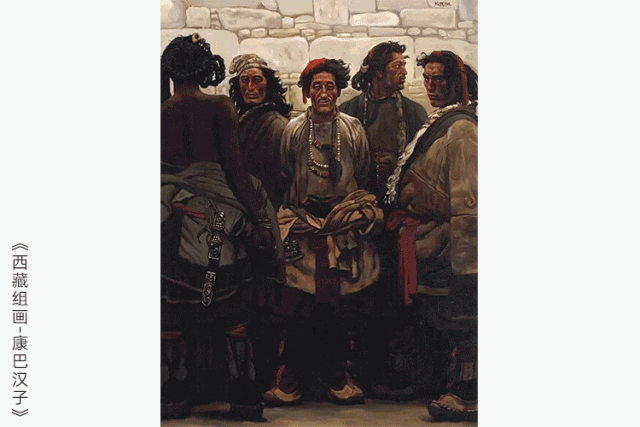
2007年,陳丹青西藏組畫之一的《牧羊人》拍賣價格高達3200萬。
多年前的他,一定不曾想到自己在西藏畫的這幅作品,會在日後拍賣出如此高的價格……
陳丹青畫作《牧羊人》

自成一派的陳丹青,因而得到了留校任教的機會,面對這隻人人羨慕的鐵飯碗,他卻無動於衷。
1982年,陳丹青從中央美術學院辭職,去往紐約創作油畫與生活。
“從紐約機場走出來,整個人自由了,但關鍵是,接下來,你拿自由做什麼?並且,你失去了與國家的關係……”
這年,他29歲。
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人類歷史上的藝術珍寶鋪天蓋地呈現在陳丹青面前,他得到了莫大的啓發。
後來,他説:“我沒有讀過高中、大學,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就是我的大學,30多年了,我至今尚未從中畢業。”
1983年6月,陳丹青辦了自己的畫展,成為中國當代畫家在美國舉辦的第一個個展,他在創作上漸入佳境。
最為幸運的,是他遇到了影響自己一生的精神導師木心。這兩個流浪異國的藝術家,如久旱逢甘雨,他們相談甚歡。
在木心身上,陳丹青看到了一個文人的尊嚴,也讓他開始重新審視自己。
只要木心在講話,當年聽課的陳丹青就記錄。聽課五年,累計筆記八十五講,大概四十萬字,這便是後來的《文學回憶錄》。
木心和陳丹青
陳丹青是個有情有義的人。
木心曾在講學中一再強調哈姆雷特身邊那位霍拉旭的重要,陳丹青無疑就是木心的霍拉旭。
木心先生回到故鄉烏鎮後,他為木心安頓在烏鎮的晚年生活,悉心照料陪伴,兩人亦師亦友。
2011年,木心先生去世後,陳丹青將木心的作品帶到了國內讀者面前,在大陸出書,建造了木心美術館。
他説:“我想把《文學回憶錄》裏提到的‘老哥們’都給木心請過來。”
他將自己定義為木心美術館的建設者,一度虔誠求問:“我怎麼能夠做的更好一點?”
他如此不遺餘力地推介木心,讓人倍感温暖,他曾經慨嘆:“珍貴的關係,是不可替代、不可複製的。”原來憤青的陳丹青也有柔軟的一面。
木心和陳丹青
2000年,陳丹青在朋友的勸勉下,回到了國內,首先感受到的是某種不適應。
一切都來得太快了。當一個曾經落後的民族強大之後,人們的意識卻沒有跟上來,集體性地進入一個現代人格。
在陳丹青看來,物質層面日漸富強的今天,人卻遲遲沒有醒過來。
太好的房子,太豪華的消費,但是聽聽人們在説些什麼,他們內心到底怎麼想的,這一切都讓剛剛回國的陳丹青感到巨大的沮喪。
為了抵抗刻板的教育體制,他從清華美院憤然離職,可是這並未意味着結束。
作為海歸藝術家,他説:“我身為海歸,感到羞恥!”
因為在他看來,海外經歷最可貴的財富不是所謂的前沿專業知識,而是羞恥之心、獨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由此體現的一系列價值觀。
但是,他在不少海歸那裏看到的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而毫無羞恥之心。
從清華美院辭職後的陳丹青可能會有兩種結局 ,一種是完全放棄繪畫,轉而走進與媒體的共謀和狂歡,另一種就是整個人認了,縮進畫室,做規規矩矩的體制內的一員。
但兩者都不是,最終陳丹青選擇了一條近乎不可思議的路,那就是做一個跨界的、穿梭的發言者。
本意是來做些抗爭,説些真話,結果最後變成一個被消費的“媒體明星”。
後來的他更為人所知的身份是作家和公共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的“邊緣人”,他沒有單位、沒有職稱、沒有官銜。
陳丹青曾經批判中國的美術教育,如今在他看來,一切有過之無不及:
“不光是藝術教學,整個都是荒謬的,包括我的批評也是荒謬的,一點用也沒有,什麼都不能改變。”
活到這把年紀,陳丹青再也沒有心力去控訴這個時代,他表示只要別弄錯自己,把自己擺清楚,不要做一個失業者就好了。

陳丹青今年66歲了,他從未想要順應這個時代,也從未覺得自己在這個時代中。
在這個互聯網環境下,他至今不會上網,也不承認自己是個當代藝術家,在他看來,畫畫本身是一件出局的事,不必和外界扯上關係。
陳丹青這些年總是會感到莫名的沮喪,他承認自己當下的作品確實畫的不如年輕的時候。所以他一直以年輕的自己為師,期望能達到二十幾歲的創作水平。
回國十幾年,陳丹青相繼出版了《退步集》、《退步集續編》、《荒廢集》,他與外界總是保持着一種適度的距離。
他沒有像梁文道、韓寒等人那樣,對談論公共事務持有濃厚的熱情,而是以自己的節奏寫作、出書。
陳丹青自畫像
陳丹青是個悲觀的人。他的寫作和發言,常常伴隨着一種深刻的絕望感和憂患意識。
關於未來他沒有任何計劃,他説老年人沒有未來,自己的未來就是殯儀館。也不想去了解任何新興事物,時間不多了,要趕緊多畫幾幅畫。
關於“人生70才開始”這種話,他説這都是騙人的話,自己從來不相信。
他不相信任何確鑿的答案,也不喜歡在安全的地帶慷慨激昂,只想做着自己的事情。
這一切,註定使陳丹青面臨着眾多非議。
記憶是個累贅。如今66歲的陳丹青將自己年輕時的記憶,放進了《退步》畫展之中。
此次個展命名為“退步”,多少是修辭遊戲,也是他試圖回應世人對自己藝術觀念落後的質疑。
在偌大的時代洪流中,他始終是一個文化追問者。
對於外界討論自己的言論,陳丹青一直表現得很坦然:“我一點不想宣稱我的畫具有觀念,更不認為我是當代藝術家,我就是個傻逼。”
在歷年捲入的洪流中,他已漸漸沉入話語的泥潭。陳丹青曾講過少年口無遮攔,如今的他依舊如此,對此他説:
“性格改不了。我一家人都是直性子,不會説假話客套話。我少年混江湖,算是家裏最為圓滑的一個,口是心非,跟人敷衍。”

每一代人的批評與掙扎都不該被浪費。
從五十年代走來的陳丹青身上,最為可貴的是經歷多半個世紀的沉浮與滄桑後,仍舊擁有獨立的人格與魏晉之風骨。
他是個不合作的妙人,妙在敢説真話,敢做自己,從不屑於偽裝,他作為一個藝術家,是最自得其樂的一種高級動物。
“沮喪”是陳丹青常常提及的一個詞彙,這何嘗不是因為他是一個悲天憫人的文人畫家,寧願冒天下之大不韙,也不願説假話。
他本可以在先鋒藝術的探索上走得更遠,然而卻止步不前,選擇了另外一種表達自我的方式,這是他作為普通人的選擇。
十年前的一次採訪,有記者問陳丹青:“您是如何在畫家和作家這兩者身份之間切換的?”
陳丹青笑了笑,回答道:“我不是畫家,也不是作家,人當了‘家’就走到末路了。”
記者窮追不捨:“那應該怎麼介紹您呢?”
“這個人叫陳丹青,有個名字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