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大學生命科學院新任院長於洪濤:我相信年輕人的看法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19-12-26 10:45
採訪 | 丹麗
近日,西湖大學發佈官方消息,生命科學學院迎來了首任院長於洪濤。在海外科研半生,成果卓著,於洪濤為何做出回國的決定?為何來到西湖大學出任院長?他又抱有怎樣的理念和願景?12月13日,《返樸》受邀參加了西湖大學安排的見面會,我們見到了這位低調、謙和的科學家。
近日,西湖大學發佈官方消息,生命科學學院迎來了首任院長於洪濤。於洪濤1995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長期致力於細胞週期及基因組穩定性領域的研究。他曾任美國得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藥學系終身講席教授、美國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HHMI)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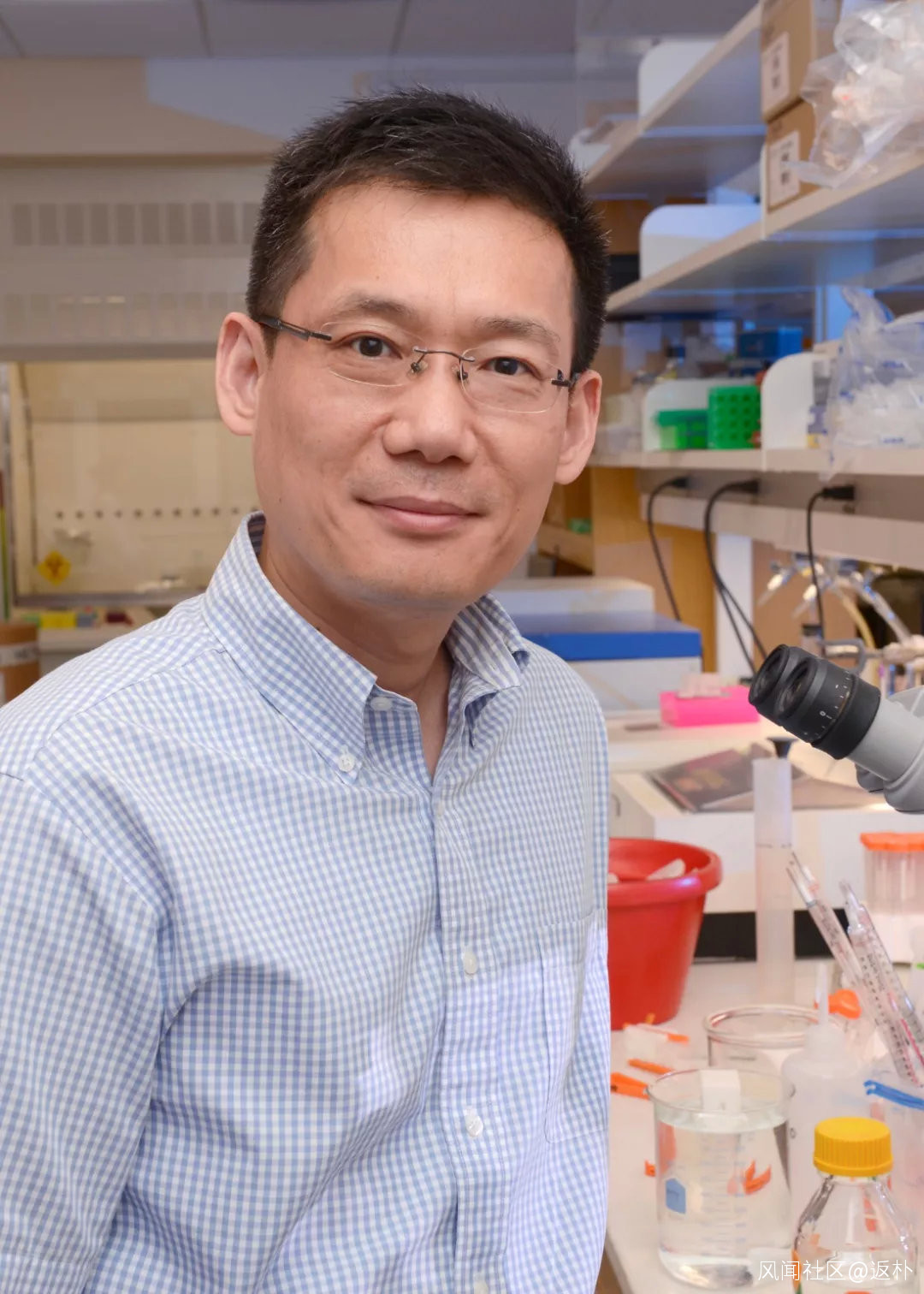
在這次矚目的受任之前,於洪濤的名字並不廣為大眾所知。網上能搜到的信息少之又少,而如果打開生物醫學搜索引擎PubMed,相關論文有150多篇,谷歌學術則顯示他的論文被引總共近1萬7千次。他曾獲Burroughs Wellcome藥學新研究員獎、Packard科學工程獎、白血病及淋巴瘤學會學者獎等諸多獎項,並於2012年當選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會士。
1990年,於洪濤從北京大學化學系本科畢業後赴美留學。1990年至1995年在哈佛大學師從有機化學名家Stuart Schreiber獲得博士學位,期間用核磁共振的方法解析了SH3蛋白的三維空間結構。博士後期間跟隨細胞生物學大家Marc Kirschner,從事細胞週期調控機理的多手段多學科研究。1999年至2019年二十年間,他受聘於美國德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藥學系,歷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再到Serena S.Simmons講席教授。由於在細胞週期的調控機理和基因組穩定性等研究領域的一系列重要成果,2008年他入選了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擔任研究員。
在海外科研半生,成果卓著,於洪濤為何做出回國的決定?為何來到西湖大學出任院長?他又抱有怎樣的理念和願景?12月13日,《返樸》受邀參加了西湖大學安排的見面會,我們見到了這位低調、謙和的科學家。
“我相信年輕人的看法”
去不同的地方做講座時,於洪濤常被人問到有沒有意願要“動一動”,也就是向他發出新工作的邀請。但他堅持認為,在一個地方持續工作,具備一定基礎之後,“動”一次起碼要浪費半年的時間。加之對西南醫學中心的環境還算滿意,於洪濤一直沒有選定要去什麼地方。
2002年,在温哥華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於洪濤與施一公相遇。兩人交換了對科學的看法,談得很投機,成為朋友後也常常關注對方的發展。2008年,兩人同時入選HHMI研究員,施一公放棄名額,選擇全職回到清華任教,這件事在圈內引起了不小的震動,但於洪濤覺得,回國的時機還不成熟。
近10年來,於洪濤經常參加國內的評審工作。每隔一兩年回來看一次,他都能明顯地感受到國內生命科學領域的迅速發展,他自己的一些博後回國後也做得非常成功。“這給我一個很大的激勵。”
2018年11月,於洪濤再次與施一公相遇,施一公向他伸出橄欖枝,請他擔任西湖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於洪濤詢問周圍的同事、朋友,大多數人都覺得去西湖大學風險太大;而和學生、研究生聊天,年輕人卻覺得西湖大學是“可以做成”的。於洪濤説:“我相信年輕人的看法。年輕人最有希望。”今年8月,他參加了西湖大學的開學典禮,目睹195位學生入學,看到這麼多家長“把孩子交到西湖大學”,於洪濤終於下定了決心,完成人生中繼出國留學之後的第二次大“動”。
於洪濤今年50歲了。他還有十多年的時間,可以精力充沛地為國內學術界、為這些孩子們做些什麼。
選人“不問出身”
於洪濤是山東淄博人,祖輩代代務農,直到父母這輩才成為知識分子。他從小和奶奶生活在一起,小學三年級後被父母接到城裏。“我小時候在一個很小的村裏面長大,當時上學,班上同學有些跟我的水平是相像的,大家考試也考得差不多。但是三年級離開後,過三五年之後再回去看,其他那些同學的發展機會要少得多。”於洪濤説,這對他而言是一次重大的人生感悟,“我現在看,大家都是有天分的,關鍵是有沒有機會。我覺得應該給學生提供一個機會。”他感謝父母為自己創造了最早的機會,這也讓他對社會和公平有了特殊的思考。
於洪濤招學生一般不看學生的成績、院校背景、在哪個實驗室做過輪轉、導師的評價等等,而是直接找學生面談。“五分鐘、十分鐘可能聊不出來,但半個小時、一個小時一定可以談得出來。”於洪濤説,“我相信自己的判斷。”雖然也有選錯的時候,但大多數時候證明,他在實驗室選人上都選對了。
實驗室的學生快畢業了想進一步深造,於洪濤給他們寫推薦信,發現自己不知道學生原先是從哪個學校畢業的,有時候一問,發現是一個沒聽説過的學校。原來他在招學生時往往不看對方的簡歷。“我不去看這些條條框框的東西,是因為有時候這會造成一些先入為主的偏見。”儘管於洪濤自己一路名校畢業,但是他覺得出身好學校不是做學問的必要條件,“我擅長考試,但是做學問要的不是思維快捷,實際上做學問真正要的是想得深遠。兩個小時內可以做一張卷子,但是做學問誰能在兩個小時之內要出答案?都是十年二十年。”絕大多數情況下,做科學實驗要經歷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如果沒有足夠的毅力和心理調節能力很難走到最後。因此於洪濤認為,做學問更是一項綜合能力。
到西湖大學之後,於洪濤開始籌備實驗室,並於不久前發佈了博士後招聘廣告。他覺得,現在很多學生家長還是更希望孩子去國外或者國內一流大學比如清華、北大,如何説服這些家長,讓他們相信自己的孩子可以在西湖大學同樣獲得優質甚至更適合的教育,成了西湖大學辦學過程中要面對的一個重要命題。他認為,正是因為西湖大學小,才意味着每個學生受到的重視會更多。

於洪濤參加“鐵人三項”
科研評價怎樣“去量化”
國內的學術評價體系一直是近幾年為人關注的焦點。學術評價依賴量化指標,既推動了國內學術在國際範圍內的發表和傳播,也引發了一些負面效應。對此,於洪濤的看法是,比起沒有任何標準,有一定的標準顯然是好的;但標準完全是硬性的、定量的,比如要求學生髮多少分的雜誌、多少文章才能畢業,帶來的壓力會誤導一些學生主觀意願上去忽視與結論不符的證據。
中國科研人員每年的發論文總數在世界上位居前列,但撤稿比例遠超過世界上其他地區撤稿率,這似乎暗示着同一項政策的正反兩面。“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科學要沒有誠信的話,整個事業就完了。所以這是我們最重要的底線,就是我們不能保證不出錯,但是不能主觀地去出錯。” 於洪濤不贊成量化指標帶來的壓力,在他看來,無論得出的結果是否顯著,只要是認真做的,都是好的,這樣才能夠讓大家誠實地彙報結果,學問才能做得好、做得下去。
“學生不光是做工作,也要完善自己。”做實驗是一部分工作,但做完實驗之後,得到了成果,還要出去講這個成果,學生是不是能夠像一個科學大家一樣去給別人解釋自己的研究?“能力不是在實驗室天天做就能有的,要跟導師去談,跟同行去談,最後會培養出全面的能力。”於洪濤告訴大家,最終評比的時候,西湖大學會有一個學術委員會——通常是三位PI來聽取學生的科學進展,再做出評價。
於洪濤進一步解釋:一個做了許多實驗工作的學生可能面臨兩種結果,一是證明了自己之前的假設是正確的,那麼可能會出很好的文章;但也有可能發現假設是不正確的,這可能就沒有文章,或者將陰性結果發表在次一些的雜誌上。“這種情況下學術委員會就會考慮,如果這個學生做得很細緻,確實證明出這個假設是錯誤的,那麼至少在我這裏他同樣可以畢業。這樣就會淡化量化的(負面)作用。”
除了盡力排除量化指標的負面作用,於洪濤也毫不諱言地談及他對各類“排名”的反感。他笑説,排名總讓他想起《隋唐演義》的兄弟排行榜。實際上,在科學界,許多學校都在同一層次上,不可能分出一二三四;即使是不同檔次的學校,也有不同專業、不同特色。學生排名、教授排名、對頭銜的崇拜,都對科學發展毫無用處——説到底,諾貝爾獎是對一個人工作成果的肯定,而不是對獲獎者本人的肯定。
因此,西湖大學的追求,不是引進多少千人、院士、諾獎得主,而是實質性的科研和教育工作。畢竟,國際上對一個學校的評價,不是看它有多少個某某獎得主,而是看獲獎者的工作是不是在這裏做的。
興趣、創新與平等
談科研,總繞不開創新的問題。與許多科學家一樣,於洪濤也一再強調興趣的重要性。從個人的角度來説,只有確實對一個課題感興趣,才能享受科研的過程,才可能會有重大的突破;從宏觀的角度來説,如果所有人都做同樣的領域,會產生不必要的競爭,浪費很多人力和物力。如果大家都按照自己的興趣來,一羣人就能廣泛涉獵各個領域——在大面積的深耕之後,必然會出現重要的新發現。
於洪濤非常強調科研的“自由度”。這不僅僅是對每個人學術興趣的尊重,更是出於科學發展本身的性質和特點——有些時候,“我們無法評價這個工作到底有多麼重要”。在他看來,唯一的要求,就是“潛心地做原創的東西”,至於這個原創到底有多重要,可能需要時間的檢驗。於洪濤舉了Avram Hershko的例子:這位以色列科學家研究泛素十幾年,開始人們都覺得這項研究沒有意義,泛素的角色不過是個垃圾清理工,去除不要的蛋白,然而時間表明,泛素極其重要,幾乎參與調控所有重要的分子機制和細胞活動,最終Hershko的工作獲得了2004年的諾貝爾化學獎。於洪濤非常敬佩Hershko的“潛心”:“我就做這個東西,別人覺得不重要,但是我覺得重要。”
由此,西湖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方針,就是營造“正確的”學術氣氛,讓年輕人自由發展,讓他們“自下而上”地做科研,而不是由院級校級規劃好課題。每個人跟隨自己的興趣,就相當於一個小公司的CEO,按照自己的想法來發展,學院要做的是提供資源、平台和環境方面的支持。同時,對年輕學生的培養目標也需要“更個性化、更人性化”,“我們要培養的是下一代科學家,是人才,而不是下一步的技術員。”於洪濤坦言,這些目標完成起來“肯定比較困難”,但這也是國外比國內做得好的地方,他希望把國外“更能沉得住氣、更能夠潛心”的氛圍在國內帶起來,讓大家潛心做一件事情——而不是追着熱門的東西跑——做幾年、十幾年,做出真正的原創。
要做到這些,需要創建自由平等的環境。於洪濤希望,生命科學學院從院長到PI,再到學生、到工作人員,大家都能平等相處,互相尊重。平等,意味着尊重年輕科學家的選擇,而不是讓他們遵從學院的決定。於洪濤説:
“我們senior PI唯一的指導就是來自更多的經歷,更多的經歷帶來不同的判斷,但不一定是好的判斷。因此,當一個年輕學者或學生來問我:這個東西能不能做?我會講出我認為的好處、壞處和可能出現的結果。至於最終他做出什麼選擇,那是他的決定。我們當然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願望,但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幫對方把事情分析清楚。”
在於洪濤看來,科學和工程有很大的區別:工程是可以訂立目標的,技術是現有的,人力物力和資金到位,就可以在既定的時間內達成目標;而科學是無法佈局的,誰也不知道重大的創新會發生在何時何地,真正的原創不可預測、無法規劃。因此,西湖大學需要年輕的PI敢想敢做,再冷再偏的領域,5到10年後很可能轉變成熱門的領域,有重要的發現。他樂觀地估計,如果有八九十個PI的體量,每個人都有原創的東西,那麼一定會從中湧現出重大的科學發現。
未來:“兩條腿走路”
任職西湖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之後,於洪濤的期待是“兩條腿走路”,基礎研究是立足之本,只有重視基礎科學才會有真正的重大突破;另外一條腿是“轉化”,將研究成果推動到臨牀應用,促進大眾健康。他表示,具體哪個方向能做出突破是無法預估的,他們能做的是招最好的人,給予平台支持,給予自由發揮的空間。在一個有風險、但有可能改變整個生命界現狀的研究,和一個比較平穩的可以發文章的研究之間,他們會鼓勵學生選擇做有風險的研究,“即使你做不成,但有可能做出一半、20%、10%的成果,也會比你跟在別人後面跑,還是要更值得尊重。”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於洪濤認為,教育和科研都是長期的工作,和別人比不是目的,做出對社會有貢獻的東西才是目的。如果只是模仿他人的研究,即使發表了很好的文章,也未必能獲得學術界的尊重。
比起國外的科研環境,中國的優勢在哪裏?於洪濤認為,中國人動手能力強、刻苦務實,國家投入多,經費支持力度大,這都是不可多得的優勢。現在缺乏的是長期的積累,是科研質量的提升。他希望,若干年後,説到西湖大學做了什麼事情,大家能夠舉出兩三個例子——即使外行人也瞭解——這就是一個成功了。

特 別 提 示
1. 進入『返樸』微信公眾號底部菜單“精品專欄“,可查閲不同主題系列科普文章。
2. 『返樸』提供按月檢索文章功能。關注公眾號,回覆四位數組成的年份+月份,如“1903”,可獲取2019年3月的文章索引,以此類推。
版權説明:歡迎個人轉發,任何形式的媒體或機構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和摘編。轉載授權請在「返樸」微信公眾號內聯繫後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