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力:充實與空虛-朱蘇力
隨着中國的進一步崛起,中國與世界、東與西、古與今的複雜關係也日益清晰地呈現出來。時移勢易,基於中國立場與視角的去學術殖民的話語體系的建立變得有必要,也有可能。
近代以來,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百年以來西方話語的強勢傳入,以及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西方話語在新興社會科學領域的大規模引進,在在值得我們回顧反思。同時,如何深入中國文明的內在肌理,從大的歷史尺度看待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的歷史連續性,建構中國話語體系,更加有機地表達中國並與世界其他文明交流對話,這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時代使命。
第十六屆開放時代論壇於2018年11月3日至4日在武漢大學社會學系舉行,本屆論壇的主題為:“中國話語”,旨在聚焦於建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自覺意識,展開跨學科探討,立足中國文明及國史經驗,從歷史進程、思潮濫觴、概念傳播、話語流行、社會變遷、文明覆興等諸方面深入挖掘,從中領略中西古今的碰撞交融。
本專題根據現場發言整理而成,並經發言人修訂。篇幅所限,部分內容未能收入,內容編排並未完全按照發言順序。

蘇力教授演講現場(圖/開放時代雜誌)
【文/蘇力】
“當我沉默着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魯迅先生的這句話準確描述了我的此刻。
就本屆開放時代論壇的主題而言,我好像一直有準備,可以説些什麼。我一直有這一學術追求,追求中國經驗的自我表達。我也一直認為,中國學者完全可能對此有所貢獻,不僅能解説中國的本土經驗,其中有許多還一定具有普遍意義,可用來理解和解説外國的經驗現象,發展出具有一般性的理論。
自打1992年我回國任教北大以來,我的所有研究和發表,好壞另説,也不論學界尤其是我置身其中的法學界的辯駁批評,始終貫穿了這一追求,自覺且堅定。這一追求也一直推動我關注和研究的問題及領域,瞭解和嘗試着不同的學術傳統、思想資源和方法。我也翻譯了不少英文著作,目的就是為了推進法學研究的中國立場和視角,客觀上則促成了我的基於中國經驗的研究和表達。
中國話語問題,在我看來,是要許多學人對於各自的日常經驗始終保持基於熱愛而發生的深刻關切和高度敏感,並以此為基礎做出好的研究。這裏説的熱愛,不是讚揚,而是一種割不斷的情感聯繫,甚至是冷靜。就像對自家孩子,你可能揍他幾巴掌,卻無法捨棄,你會為之仔細謀劃和盤算。這根本就是一個沒法抽象概括談論的問題。説句不好聽的話,抽象討論這個問題,有社會意義,卻幾乎沒有學術意義。這是我感到空虛的原因之一。
如今有不少中國學人出於種種原因在學術上是看不見或看不上中國經驗的,無論是古代的,還是當代的中國經驗。在他們的眼中,中國就是一堆積澱的錯誤,包括我們自身也全都是錯誤,其唯一的意義,只是為了證明他們今天瞭解的某些東西和他們信口開河的批評是遠見卓識,證明他們已經接近甚至接觸了上帝或真理。針對這一點,從宏觀上在中國學界提一下“中國話語”,提一下包括學術在內的文化自信和理論自信,強調一下中國立場和視角,敦促學人尤其是年輕學人關注一下自己身邊的經驗,在輿論宣傳上對抗文化虛無主義,有一定的社會意義。
但是,這只是社會意義。這種提倡或強調,或討論,也許會改變一些學人的説法,但沒法真正改變他們的觀點或成見。
有些人,由於種種原因,幾乎從一開始接觸西方的某些概念、理念或命題,就覺得外來的和尚會念經,然後就不斷重複,一輩子都在這般重複,還自以為是對真理“忠貞不渝”。如果有學人到了我這個年齡,即便就是更年輕一些,還一直固守那些所謂正確的或高大上的抽象語詞、概念或命題,將之當成終結了歷史的學術和研究,就不可能指望他們還能理解歷史中國的學術理論表達,也不可能指望他們理解當代中國的偉大變革和經驗,更不可能指望我們在此的討論,可能説服或激發他們以中國經驗為基礎,來發展中國的學術和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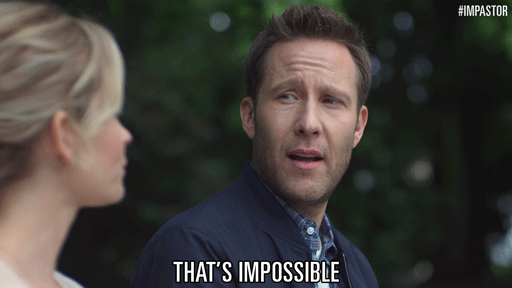
其他學科可能稍好一點,法學界問題會更大一些。因為法學界從一開始基本就研究法條,研究規範,並且是抽象研究,自然可以甚至就應當一心追求高大上,而且也沒有經驗的研究工具和方法來挑剔規範可能隱含的問題。
只有將規範置於具體社會歷史語境中來研究,有了一系列看得見、摸得着的約束條件後,才可能感知規範的社會實踐會有收益,會有成本,才能察覺其中的所得和所失,才能察覺規範實際的效果是在不同的個人、羣體之間分配收益和成本。這種分配,你認為公平,卻一定會有爭議,因為有切實的利害關係,人們很難達成和分享共同的規範。注重規範研究的法學一直不是這種傳統。琢磨和死磕規範的字眼、含義本身不會有直接可見的重大利害得失。這個學術傳統導致法學者不習慣、不願意或沒有能力仔細地分析問題。

資料圖來源:視覺中國
還必須看到,中國的頂尖大學才開始從教學型大學轉向研究型大學。此前,學術發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直很低。因此,有許多法學前輩基本一輩子都沒有機會做經驗性的研究,最好的只是編教科書,主要就只是複述和闡述中外先哲或經典作家的論斷。
“文革”後至少一代甚至兩代法學人的學術起步都是以複述前人或他人為主的,不好聽的説法就是“抄”,抄外國的,抄台灣地區的,“天下文章一大抄”,好一點的也就是改動個別字句。前些天南京大學的梁瑩事件,真不是偶然的。如果要較真的話,即便我們這一代學者中,這類情況也不少。必須歷史地看中國學術的發展,當時這類“抄書”就算學術,就算研究了。
20世紀90年代之前文科基本是沒什麼科研經費的,沒錢,自然沒法提倡問題導向的經驗研究。即便比較聰明、有想法的老師,又能如何去研究寫作?因此,不少人幾乎一輩子就是重複他們在35歲前後瞭解的一些概念或命題。人一旦形成了這種寫作風格以後,到中年,還要讓他們改換話語,這實在有點強人所難。
因此,在我看來,即便作為學術追求或理想,強調中國立場和視角,強調關注中國研究,強調接地氣,強調中國話語,當然應當,也必須。但務實地看,卻不大可能真的改變我們這一兩代甚至更晚些的絕大部分法律學者的學術路徑依賴。若過度強求,弄不好還會出現兩種更糟的結果。
一是偽裝的中國話語,在其研究成果中增加一些諸如此類的名詞或命題,作為標籤,作為裝飾,但其中並沒有任何基於中國經驗的智識產出。如今有好多對策研究,甚至有一些專門追求“領導批示”的“研究”,就屬這一類,基本是毫無學術價值的,不可能有學術生命力,不可能真正形成中國話語。
二是一些自稱反對學術意識形態化的人把中國學術和話語追求作政治意識形態的理解,給你貼上種種標籤,什麼思想保守,不同世界接軌,反對普世價值之類的。我回國任教以來一直受到這類指責。能忍也就忍了,忍不住了,我就槓到底:你找找,法學界有誰比我翻譯的英文學術著作更多?2018年我出版了《大國憲制》,實際上十年前我就想做,可是那時我太忙,連睡覺都沒空;如果當時出版的話,更難被理解,引發的批評和造成的學術環境,可能更不利於學術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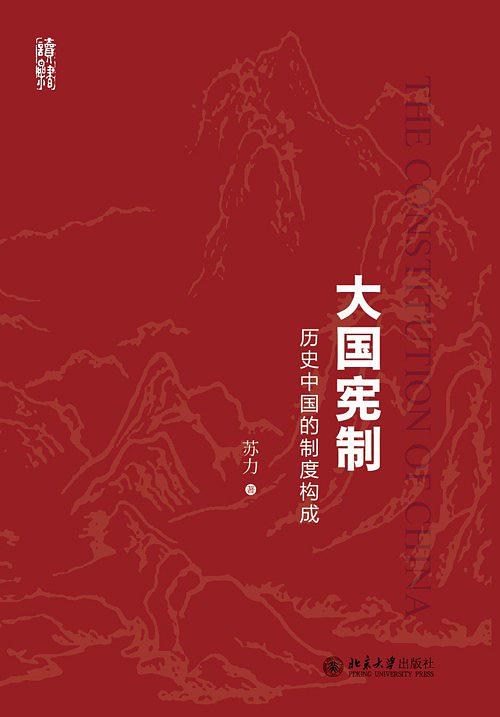
在我看來,這個中國話語問題,需要研究者有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上的自信,認真關注中國的經驗。但也必須清楚,關注中國經驗,不能只關注或急於回應一些社會熱點事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將其置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歷史甚至地理語境中,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語境中,來梳理其發展演變的脈絡,理解、發現其中的道理。
這種自信,在我看來,就是要相信,我們綿延了數千年的文明,不像其他古代文明在時光中湮滅了;尤其是在近現代歷史中,中國正經歷着偉大的社會和文化轉型,正成功將一個傳統農業中國轉變為一個擁有現代工業製造、科技和工商的中國。確實,就像毛主席1954年在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式上説的,“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我們一定有些經驗對別人也有意義,具有普遍的實踐意義,同時也具有智識意義和理論意義。
這些經驗和實踐就在我們身邊,就在我們的傳統中,其中的理論和學術意義可以為人類共享。其中有些,甚至許多,是我們以前沒有關注的,或者根本就沒重視、不理解或理解片面的,甚至可能是長期誤解的。今天,我們有必要,也有可能重新理解。“一切是熟悉的,一切都是初次相逢;一切都理解過了,一切又都在重新理解之中。”我們至少在理論上有最便利的渠道來研究和理解它,也更容易首先在中國社會語境中經受經驗的挑戰和智識的挑戰。
關注中國經驗,不能僅僅關注中國歷史和當代中國的社會實踐,一定得有開放的眼光。
説實話,我對中國許多問題的理解恰恰是我在美國學習了多年之後,才有了一些判斷,或是重新有了判斷。人必須常常換個場景或情境,才可能有真切的感受。隨着視野的擴展,我們就一定會有,也一定要有中國道路和中國話語問題。沒有比較,就沒有鑑別。真正有價值的學術研究,肯定要有一個國際比較的學術參照系。只有從比較的差異中,研究者才可能察覺哪些是中國的經驗。
當然,真正的天才可以不關心別人,他自己就能把他想説的説清楚。真正偉大的自信,也許就是我活着,沒有哪種力量能殺死我,但我也無需表達,也根本不在意什麼表達,我的存在就是我的表達。但是,我們一定要到外面看看,才知道哪些是我們能做的,才能在自己身邊發現一些有價值的東西,才能更有效地表達自己,把自己説清楚。一個開闊的國際學術視野,是學術必備的,不是“可以有”,而是“必須有”。
説到具體的“國際學術視野”,又必須警惕。任何學人對國際學術的瞭解都一定有侷限,沒有人可能全知全能;任何一國的學術也一定有侷限,它通常只針對本國的問題在本國語境發生的。有主見的研究者千萬不能讓自己先前瞭解或其他學人瞭解的,其實註定是狹隘的所謂“國際學術視野”遮蔽或壓抑他感受的中國問題,尤其是不能壓抑或遮蔽中國問題促成了那些中國創造。要避免用歐美的經驗來評判中國的經驗,視其為“異端”,視其為必須革除的弊端。
真正困擾我乃至令我感到空虛的還有,文化自信和理論自信的問題,這個中國話語問題,根本就沒法通過説道理來解決。不可能有人一提醒,他人就能確立或提升這種自信。這需要個人的覺悟,明白道理後,做出勇敢的選擇。但真做出了選擇,也未必就能解決。高度關注中國經驗,也不一定取得很好的成果。
學術研究的事是沒法計劃的,“一將功成萬骨枯”也是常事。我不時也會有研究結果與學術直覺、預期全擰的經歷。即便你做出了優秀的成果,也要清醒地看到,學術世界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知識權力的宰制,因此你可能在一定時期內不能獲得恰當的評價,甚至被淹沒,不是被批評淹沒,就是被無視湮滅。這會是很悲劇的。真正的學人必須想透了,看透了。
由於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特點,庫恩理論也早就暗示了,在學術世界中,依據現有範式的常規(重複性)研究,通常會比那些真正有智識和學術貢獻、挑戰的研究,更可能獲得認可,這意味着許多人不可能不考慮一系列實在的利益損失。

資料圖來源:視覺中國
由於更關注發表的數量和在什麼刊物上發表,中國目前的人文社科學術資助和發表機制客觀上是趨於支持常規研究的。還不能排除,編輯和學界都可能認為那些沒有引福柯、哈貝馬斯、施密特的話,僅僅分析中國經驗的研究不高大上,因此無意中用《法門寺》裏賈桂的眼光來看待這類研究成果。基於這一學術格局,出於對趨利避害的人性的理解,不大可能指望有多少人願意,也不可能有很多人真有能力,來從事這類基於中國的研究。
還有一個大問題是,現在太多中文的人文社科學術作品,無論是否研究中國問題,包括引介西方的研究,都缺少真正的理論解説力。無論是倫理的,還是經驗的,都很難令人感到智識的挑戰和樂趣,很難讓人有舉一反三、觸類旁通,或茅塞頓開的感覺。與此相關但並不等同的是,許多研究成果的敍述太不吸引人,語言不生動,味如嚼蠟。
一個突出的標誌是,在中國銷路比較好的社會科學著作,幾乎全是翻譯作品,中文的人文學術著作還有不少暢銷書,但中文社科學術著作幾乎沒有暢銷書。我不認為暢銷書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但如果中文的社科著作寫得不生動,這就是作者有問題。研究中國問題,如果沒有很好的表達也不行,無法獲得足夠的受眾,在中國都沒有“中國話語”,又怎麼參與國際的學術話語競爭呢?這是堅持“中國學術理論話語”的中國學人必須高度關注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法學界問題更大。部門法往往集中關注法條的規範分析和演繹。他們不大願意也沒有能力進行政策性分析,更少將中國的法律問題放在中國的歷史、社會、人文語境中來考量,甚至不時會把這些考量視為對法律、法學自主性的不正當干擾。
總體而言,當今中國法學研究更多受教義學研究傳統支配,而隨着法律學人日益從校門到校門,這種傾向甚至有可能加劇。此外,受教科書語言的影響,也受台灣學人的影響,很多法律學人一直把法律語言的精確表達誤解為枯燥、生澀的語言表達。這些因素也都不利於法學研究的中國話語,使其面臨更艱鉅的挑戰。
真正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自己去做,我們身邊人更多地去做一個一個的研究。我認為,在這類學術問題上,號召、告誡、相互鼓勵、督促甚至獎勵、懲罰,用處都不太大。真正好的研究,要靠研究者自身的覺悟,尤其是持續自覺的實踐,這樣不僅能及時發現有學術理論意義的中國問題,更重要的是能體察和理解中國的實踐經驗中隱含的道理,自覺改變自己研究和表述問題的方式,追求一種更生動、有效、接地氣的語言表達。

資料圖來源:視覺中國
最後,“中國話語”這個概念也需要界定,要避免各種非智識的誤解。關注中國問題,注重並描述中國歷史以及當代實踐和經驗,並不必定意味着中國學術理論話語的成功和有效的實踐。這只是基礎,真正的中國話語至少是在學術世界中有競爭力的學術理論話語,不能僅僅是自説自話。學人要追求具有一般性的學術表達,更多基於經驗和實證的研究,要有普遍解説力,不能只是缺乏理論意義的對中國現象的特別解説。
儘管在一定程度上我們仍然可以借鑑中國古人的簡約表達,不加或很少論證,更多以敍事和斷言,直擊古代文化精英的直覺和智慧,但由於時代和文化的變遷,文化下移導致今天人文社科的預期讀者與古代很不相同了。中國學人必須學會分析和論證,能以樸素、生動的語言講出道理,否則就不可能有真正強健和有普遍意義的學術話語和理論。
上面這幾點恰恰意味着,我們真正需要的其實不是一個抽象的可欲目標——“中國話語”,而是一批令人信服和讚賞的具體研究,有些還應當稱為範本,供人以某種方式效法、模仿。它們必須概括了某些中國的經驗,提煉出或隱含了某些具有一般意義的理論命題,或是藉助中國人的歷史、文化視角,啓發了人們對某些老問題更深刻的理解。這就註定了我一開始説的那個“空虛”是真實和實在的——這是一個矛盾修辭!我們要討論的“中國話語”真不是個有確定答案的智識問題,而是一項由學者自我選擇並通過學術踐行來構建的事業。
這一事業基本沒法在社會層面規劃,然後推進,它只能靠學者自我規劃、自我努力、自我追求、自我超越,不僅不關注什麼得獎,甚至有時——弔詭的是——也不關注自己是否選擇利用了中國經驗,是否追求中國話語,重要的是有真正有意思且為他自己的經驗、知識、能力和追求把握的問題。
如果他真的是一位中國學者,長期生活在這塊土地上,對中國歷史傳統、現當代的偉大變革和轉型有一定了解和感受,我相信,這些會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他的立場和視角,他一定會更多取材於中國經驗,一定會更關心中國經驗。隨着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隨着“一帶一路”的建設和發展,許多中國問題都可能成為有國際意義的問題。
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基於中國經驗的各類研究會逐漸增多。對於絕大多數中國研究者來説,這類經驗材料必定是他最容易獲得和理解、分析的。
其他重大社會變量也會推動人文社科領域內中國的學術理論話語的增長。
伴隨着中國的高速發展,中國的崛起已經改變了國外許多人對中國的理解。即便是敵對,也將促進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和關注。僅僅中國的存在,對西方世界意識形態就構成了挑戰,因為中國經驗動搖了三百年來西方文明的根基。與我同齡的這一代乃至更年輕一代的“公知”,在中國民間和學界的影響顯著衰落,年輕一輩學人的民族和文化自信心顯著增強,這也反映了中國人的認知和自信。
概言之,中國的經濟文化實力一定會促使中國話語的發生和成長。中國年輕一輩的學者,不僅因為其學術能力的增強,更可能因為中國的崛起而在學術和文化心態上,更自然而從容地反思西方學術話語,也更可能基於歷史中國的經驗和現當代中國的偉大變革和社會實踐,努力建構有更強理論解説力的中國話語體系,創造當代中國的學術表達。
這更多是對於明天的期待。好的研究和好的作品,幾乎永遠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一旦有了更多可效仿的好作品後,就一定會有更多範式上依葫蘆畫瓢,照貓畫虎的作品,即所謂的常規研究。
這也意味着,我在此談論中國話語意義真的不大,需要的只是個人的不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