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先秦諸子都在爭論什麼?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上一篇寫道,周朝早期通過宗法分封和武裝殖民,在中原大地上實現了第一次的定居農耕文明大一統。這應該被確定為世界政治發展史的一個跨越,因為與同時期世界其他文明大為不同的是,周朝大一統局面的形成,依靠了一種“德治天下”的政治策略。
“德治”的由來
文明各有起源,起源於“多元一體”的定居,還是起源於單一部族的遷徙或征戰,區別重大,因為這直接決定了後世關於其部族始祖的類型想象。中華始祖的類型很特殊,雖然也照例被尊為戰神,但另一個更重要的面貌,則是指導萬民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聖王。
中國人作史,按“三皇五帝三王”的順序,始祖是“三皇”,曰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有熊氏。“皇”字的古義是“德冒天下謂之皇”,本身就含有全天下至德之人的意思。據傳説,伏羲氏教人民作網罟以佃以漁,養六畜以充庖廚,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神農氏教人民因天時,相地宜,制耒耜,蓺五穀,嘗百草,立醫道,列廛於國,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黃帝有熊氏教人民探五行之情,佔鬥綱所建,造曆法,作算數,為文章以表貴賤,作舟車以濟不通,畫野分州,設立井田,左右大監監於萬國,遠夷之國莫不入貢。【1】
 :
:
河南新鄭軒轅黃帝像
考察聖王們這些事功,可以看出,無不是定居農耕區內的農業革命活動,今天的話叫“改善民生”,而且是關於全天下人的民生。這當然就是一種至德。對比一下,古代以色列人的聖經敍事講述的是部族的大遷徙,古代希臘人的荷馬史詩講述的是特洛伊戰爭,都屬於前定居、非定居文明中的行為,充斥着遠征、燒殺、搶奪、復仇之類的情節,看不到“天下平”“萬國和”的景象,當然也就談不上德行、德治的問題。
那時世界不通,中國和地中海世界之間沒有交流,如果有的話,無論是古希伯來還是古希臘,也必定逃不出蠻夷戎狄的定位,有多少華麗的長詩流傳也沒用。因為率領部族遷徙或率領軍隊征伐的英雄,在古代世界隨處可見,大地上無數的蠻族遊團,每個都有自己的亞伯拉罕、摩西、阿伽門農和阿基琉斯,故事甚至更精彩,區別僅在於有沒有留下文字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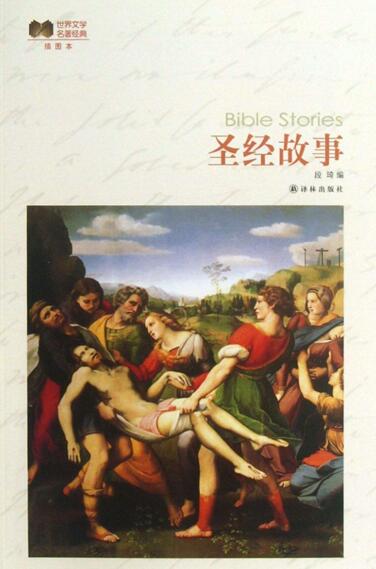
聖經故事
但可以斷定,並不是每個部族都能出現自己的伏羲氏、神農氏和有熊氏,因為這些最早的農民領袖和農業革命帶頭人,都是大有功於天下萬民的聖王,只屬於“天下”型定居文明,只可能在中華大地上出現。
德治,中華政治的這個核心概念,就是從這裏出來的。換言之,中國人所謂“德治”,其實是專屬於定居農耕文明的一種道德化政治,不能説最好或最高,但卻是最適合於“天下”型定居文明的早期發展的。
中華大地上最早的定居農耕文明區,猶如大海中散佈的羣島,被無數蠻夷遊團所包圍。而之所以能夠像星星之火一樣,不僅生存了下來,而且終成燎原之勢,發展成世界上最大的“天下”型定居文明,一整套適合於定居文明的“德治”,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周朝的早期歷史就是一部“德治”的成功史。據《周本紀》,周人先祖后稷“好耕農,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則之”,本是一個定居農耕部族中的聖王。但是兒子不窋不務正業,放棄了農耕,“竄居戎狄之間”。好在第三代孫子公劉很有作為,又率領部族在戎狄之間的豳地復修后稷的稼穡舊業。然而農耕事業並不順利,因為周圍的“薰鬻戎狄攻之”。結果不用説,彎腰種地的肯定是打不過騎馬打獵的,就這樣進進退退糾纏了有一千年。到了古公亶父當政,為了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終於下決心舉國離開豳地,渡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

今日岐下週原
審看這段歷史,從戰術上講,肯定是周人敗了,薰鬻勝了,因為前者被後者趕跑了,丟了豳地。但是從戰略上講,卻正好相反,因為周人撤離時,“豳人舉國扶老攜幼,盡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賢,亦多歸之”,最後不僅重建了新的根據地、擴大了地盤,而且盡收民心。到了古公之子王季、之孫西伯,“修古公遺道,篤於仁義,諸侯順之”。周家八百年王業,自文王始。
在公元前一千紀的那個世界,其他地方有沒有可能發生類似的故事,大可懷疑。軍事上的失敗者反而成了文化上的勝利者,憑着仁義二字最終贏了全天下,這樣的“德治天下”敍事,遍讀其他民族的史詩,恐怕找不到第二家。
後人紀念文王,全都是動人故事——敬老慈幼,禮賢下士,耕者讓釁,民俗讓長,修德行善,發政施仁,澤及枯骨…蓋人心至是已去商而歸周矣,“德治”大勝。但這裏似乎有個問題:周人這些道德觀念和行為到底是如何產生的呢?真的是頭腦中聰明智慧靈光一閃的產物嗎?設想一下,假如周人沒有離開豳地南下關中平原,“德治”能夠在北方的薰鬻戎狄當中產生同樣的效果嗎?能夠讓周圍的蠻族遊團像中原的殷商諸侯一樣紛紛歸附嗎?
絕無可能。不要説當時的薰鬻戎狄,從那時起到後來的匈奴、五胡、突厥……直到兩千多年後蒙古諸部,這些北方遊牧-遊獵民族只要不進入中原的定居文明圈,就不知“德治”為何物。他們不僅不會因“德治”所歸順,反而毫不猶豫且理直氣壯地一次次越過長城碾壓整個中原乃至南方。為什麼?歸根結底,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道德標準,周朝的“德治天下”只能在定居農耕文明為主的區域內起作用,而在遊牧遊獵文明為主的區域內,基本沒用。
敬老慈幼在定居文明中是美德,但在遊牧文明中卻不是,因為根本沒條件,整個部落必須不斷地長途遷徙甚至快速奔走,不可能因為要照顧少數老人,影響整個羣體的機動性。恭敬守禮在定居文明中是美德,但在遊牧文明中也不是,在馬背上生活的所有男人必須以好鬥、殘暴、貪婪和好色為基本品質,才能讓整個羣體獲得更多的獵物並且更快地繁衍。
一條條考察下來,在定居文明中一直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那些道德行為,在遊牧文明中也許恰恰是非道德,因為不能促進羣體的生存發展利益。周文王禮賢下士,尊八十歲的呂望為太公,因為賢士們頭腦中的一個良策,就可能大大推進治國平天下的事業。但遊牧民族的世界就是茫茫大草原,散落着無數的野獸羣體和異族部落,要想生存下來就要儘可能多地消滅它們,因此,計謀遠遠頂不上勇猛,智力不能代替臂力,與其禮賢下士還不如錘鍊戰士。
就是這樣。若沒有大面積定居農耕區、大規模定居農民人口,再出一百個周文王也沒用。周人從豳地舉國遷徙到岐下週原,從地理上看就是跨越了農-牧分界的400毫米降水線,融進了定居農耕的核心區;從歷史上看就是匯入了當時的農業革命浪潮,順應了定居農耕區的大一統趨勢。“德治天下”政治策略的成功,當然要歸功於文武周公這些開國者的偉大政治實踐,但背後的深層歷史運動,卻是那個歷史時期定居農耕區域的迅速擴大和對周圍遊牧-遊獵蠻族遊團的大量吸收。
先秦諸子都在爭論什麼?
與定居農耕區大一統趨勢發生的同時,是一個堪稱政治奇蹟的新事物的出現——原本作為地理概念的“天下”,通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制度安排和“德治天下”政治策略的實行,成了一個地理、政治和倫理的“三位一體”。
天下,同時意味着全部土地、全體人民和全局秩序,天道、人倫和天人相與之際三合一,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個類似的“三位一體”。
早周其時,封王所到之地,新城拔地而起。以周文王為源頭,在全天下制邑立宗,每個城市自始封者開始別子為祖,建立宗廟,下一代則按嫡長子繼承製再繼別為宗。一切都井然有序,各就各位,各得其所。
重要的是,當人為制定的宗法制度遍行於全天下,各地的宗廟都只祭人祖不祭鬼神之後,關於天的觀念也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研究者們注意到,在講述周人遷徙故事的《詩•皇矣》等篇章中,天還是一個被稱為“帝”的人格神,“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像極了希伯來《舊約》中的耶和華;而到了較晚的《書•呂刑》等篇章中,天即變成了“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於四方”的抽象物,與人為秩序合二為一了。梁啓超對此總結道:
其所謂天者,已漸由宗教的意味變為哲學的意味。而後世一切政治思想之總根核,即從比發軔。【2】
天,不再是任意的、絕對的、超越於人的,而成了規則的、相對的、與人合一的。如《詩•烝民》的表達,上天與萬民直接聯繫在了一起: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對這句話,孟子的解釋是:“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彝指法度、常規;懿是美好的意思;萬民只要遵從天的法則,就是好的德行。梁啓超的解釋是:
凡一切現象,皆各有其當然之法則,而人類所秉之以為常也。故人類社會唯一之義務在“順帝之則”(《皇矣》)。【3】
中國人研究六經,往往帶着一種想當然,認為天就是天,民就是民,不用多解釋,全世界都一樣,基本上可以等同於人類社會。其實這是個大謬。在中國人開始將“天”與“民”連在一起,甚至有了“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這類思想的當時,在世界其他民族當中,無論是天的觀念,還是民的觀念,都還遠遠沒有成型。

《千里江山圖》局部
在中國的“天下”型定居文明之外,滿眼荒蠻:歐亞內陸的遊牧民族長期掙扎在生存線上,為尋找水草和獵物而四處奔走,觀念上擺脱不了野獸崇拜的矇昧階段。地中海一帶的城邦民族則永遠被不同的敵國所包圍,相互攻伐,從不知“天下”的範圍有多大,自然不會形成“天下”觀。印度有較大規模的定居農耕區,但卻始終沒能形成一個與中國類似的“同心圓”或“同心方”地緣格局,無法讓定居文明成為一個整體以抵抗北方蠻族的頻頻入侵,當然也就不成“天下”。至於西歐,作為一個文明它在這個時期還根本沒有出現。
所以,當中國的先秦諸子們使用“天”和“民”這兩個概念時,兩者本質上是一對,是一枚硬幣之兩面。硬幣就是“天下”型定居文明本身,這個文明的一面是生養萬物的天,另一面是順天之則的民。那些不在“天下”型定居文明中的民,要麼是蠻族暴民,要麼是小城寡民,要麼是奴隸草民,皆非“天民”。
“天民”觀念最圓滿的表達,在《書•皐陶謨》中:
…天工,人其代之,天敍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至此,從“多元一體”定居文明開始,到“天道”哲學的確立,一個獨立的、完整的、自洽的天-地-人體系終於出現在中華大地上,並且從此屹立千秋。
獨立的,因為一切都起源於中華大地上獨一無二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完整的,因為正是基於這種文明,才有了集合在“天下”概念之中的地理、政治和倫理“三位一體”;自洽的,因為“天下”中的天是哲學意味的天,所以“順帝之則”就成了“順天之則”,繼而通過“天生德於予”又進一步融化成為人的道德義務,完成“天人合一”。
其他文明中不可能誕生類似的體系。僅僅從人格神到抽象的天這一步,就都沒能完成跨越,更不要説“天下”觀念的“三位一體”和“天民”的“一體兩面”。

儒家六經
然而,凡事都有兩面,正如近現代學者反思中華文明時普遍認為的,這個文明的確過於超前和早熟。回看中華歷史,無論是“三位一體”的“天下”還是“一體兩面”的“天民”,其實更多的只是士大夫們頭腦中的理想,而非真正的社會現實。周初“協和萬邦”“德治天下”策略的實行,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就建成一個理想社會。雖説從理論上講,當時的中國農民已初步具有了辜鴻銘所説的“良民宗教”精神,但實際上,在當時的中原地區,遊牧的蠻族暴民、城邦的小國寡民、底層的奴隸草民,也都大量存在,與其他文明無異。人畢竟是人,性惡就是性惡,不可能因為《詩》《書》中幾句虛無縹緲的哲言,全體農民就都集體昇華成了與眾不同的“天民”。
歷史見證,短暫的“成康之治”過後,“周道衰廢”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昭王伐楚不返,厲王侈傲弭謗,再經驪山之恥、平王東遷,諸侯並起禮崩樂壞的局面已成。讀書人們心目中那個空中樓閣般的“天下”自此土崩瓦解,於是喧譁四起,眾聲鼎沸,中華文明最為光彩奪目的思想文化之花大綻放時期隨之到來。
70年對話5000年,今天的人們在重讀先秦經典時,既不能將它們僅僅看成是聖賢們高人一等的聰明智慧,也不能盲目認為其中的名句格言一如既往地英明正確。大體而言,它們只是“天下”型定居文明這個特殊文明的產物,且生髮於這個文明遭遇到理想與現實、超前與滯後、早熟與晚成之間巨大沖突的那個特殊時代。而諸子百家的不同學説,就其實質而言,就是面對這些衝突的諸種不同回應。
進行了這個界定之後,再看先秦諸子的學説,脈絡就清楚了。
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抱負最宏大,對於“三位一體”的信念最堅定,天道、人倫和天人相與之際三端缺一不可,所以立志要修舊起廢,從正面匡扶周道。如太史公所言:周道衰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論詩書,作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王道之大者也。【4】
對於天人相與,儒家給的是完整解。《禮記•禮運》中表達得很清楚: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淆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淆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5】
以商鞅、韓非等為代表的法家,與儒家同出孔學,兩派的區別在於:儒家的理想更高遠,追求昇平世到太平世之間的“大同”;而法家的關注點在當下,致力於據亂世到昇平世之間的“小康”。所以,法家對於“三位一體”能否恢復其實半信半疑,雖然也相信天道,但執意將其中的道解成“法”和“紀”。《管子•形勢解》: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蒞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6】
《韓非子》: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7】
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屬於所謂“南派”,偏於逍遙,對於“三位一體”的信念最淡漠,不認為聖賢們能夠做什麼。於天道、人倫和天人相與之際這三端,只信天道,只解無為,根本不相信人倫。所以老子會主張“絕聖棄智”、“絕仁棄義”: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8】
莊子也説: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9】
以墨翟禽滑釐為代表的墨家,屬於北南之間的“宋鄭派”。但墨子魯人,習孔子之書,業儒者之業,在匡扶周道的事業上與儒家算是同志,對於“三位一體”的信念同樣堅定。墨家於天道、人倫和天人相與之際這三端,比儒家更為相信人倫的力量,也相信天人相與。對於天道,執意要解出“天志”。《墨子•法儀》曰:
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為法,動作有為,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慾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10】
所謂諸子百家,就其“大宗”而言,就是以上幾家,其他諸家都是“大宗”之間混合衍生而成,不再一一詳述。本文對此進行梳理,旨在特別強調這些產生於那個特殊時代的古典學説與“天下”型定居文明本身以及這個文明內在困境之間必然的和因果的聯繫。今天的中國,正在大步跨入新時代,面對傳統思想和文化的繼承和借鑑問題,更需要對這些聯繫進行清晰的辨識。
70年對話5000年,新時代所達到的高度越高,前景越遠大,對於歷史的追溯和探究也越深越遠。筆者才疏學淺,力有不逮,在此拋磚引玉,誠邀學界同仁共襄此舉。下一篇“三千年來中國人的政與商”。敬請關注。
參考文獻:
1、見《史記》、《資治通鑑》等
2、梁啓超《先秦政治思想史》
3、同上
4、見《史記•太史公自序》
5、見《禮記•禮運》
6、見《管子》
7、見《韓非子》
8、見《道德經》
9、見《莊子》
10、見《墨子》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