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乘旦:歷史學研究離不開“體系”
【文/錢乘旦】
本文針對當前史學界一個流行的傾向,這種傾向不僅在中國史學界,也在世界史學界散發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史學研究發展迅猛。幾十年中,史學研究最大的進步之一,就是研究越做越細,課題越做越小、也越做越深,和 “文革”之前的 “假、大、空”形成鮮明對照。這種越做越細、越做越小、越做越深的現象本身很好,歷史學確實應該做細、做小、做深——不深、不細、不小,大而不當,不接地氣,從空到空,這樣的歷史學是沒有出路的,也看不到發展的前景。所以,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年歷史學在這方面的變化是一個進步,這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在這個總體發展的趨勢中,有一個苗頭也日益明顯,非常值得史學界注意。這個苗頭就是歷史學界——包括已經成熟的學者以及正在學習之中的研究生 (碩士生、博士生) 和正在成長中的年輕一代,自覺或不自覺地滋生出一種傾向,認為歷史學研究是不需要體系的,應該擺脱體系的束縛;歷史學研究是不需要理論的,理論無助於歷史研究。題目小就是好,越細、越小越好。小題目無需框架,更不需要體系。至於為什麼做某個題目?做一個題目要不要理論?這些問題無足輕重,為題目而題目就可以了。
更有甚者,有人聲稱有了體系反而不好,有了理論就礙手礙腳。因此,一種 “反體系”思潮廣為流傳,碎片化現象因而坐大。我認為,這種傾向如若繼續發展,對歷史學研究一定造成傷害。關於碎片化問題,史學界——甚至整個學術界——已經討論了很長時間。七八年前,《歷史研究》曾召開一個會議,我當時就提出了碎片化問題,在場有不少學者並不在意。但是,七八年過去了,碎片化現象卻愈加明顯,不僅在中國,在全世界都成為問題,碎片化已經是一個世界性的學術現象,不得不引起人們的注意。
歷史學研究要不要體系? 答案是肯定的。體系是歷史學研究的一個本質特徵,或者説是最重要的本質特徵之一。有了體系才有對史料的選擇,才有對歷史的梳理與書寫,這是做歷史研究的人都能體會到的。做歷史研究的人都知道,史料本身是碎化的,是散亂的,需要歷史學整理,把散亂的史料整合起來,讓它們成為 “歷史”。歷史學家的工作,第一是尋找史料,第二是整理史料,如果還有第三,那就是 “書寫歷史”,由此而闡釋史料中所包含的歷史意義。無論是尋找史料,還是整理史料、書寫歷史,“體系”始終在發揮作用,比如,就史料而言,它存在於很多地方,各種各樣的史料多極了,也很混雜。
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把他自己認為有價值的史料挑選出來,梳理成 “歷史”。可是哪些史料有價值、值得寫進“歷史”呢?不同的學者會有不同的判斷和不同的選擇標準。通常出現的情況是: 有些學者挑選這些史料,有些學者挑選那些史料,其他學者又挑其他的史料,這種情況在歷史學家們看來是非常正常的事,毫無奇怪之處。可是,為什麼不同的學者會挑選不同的史料、然後使用不同的史料呢?這就涉及到體系問題了,是體系為篩選提供了標準,也為書寫制定了框架。
歷史學家這樣做也許是不自覺的,但體系確實是客觀存在的,不管歷史學家有意識還是無意識,沒有體系就無法篩選史料,也無法書寫歷史。從體系出發,某個歷史學家會覺得某些史料有價值,於是挑選它們,寫進他寫的 “歷史”;其他歷史學家則根據他們的標準挑選他們認為重要的史料,並書寫他們的 “歷史”。因此,體系不以歷史學家的主觀意志而存在,它本身就是存在;如果沒有體系,史料就永遠只是史料,不能成為 “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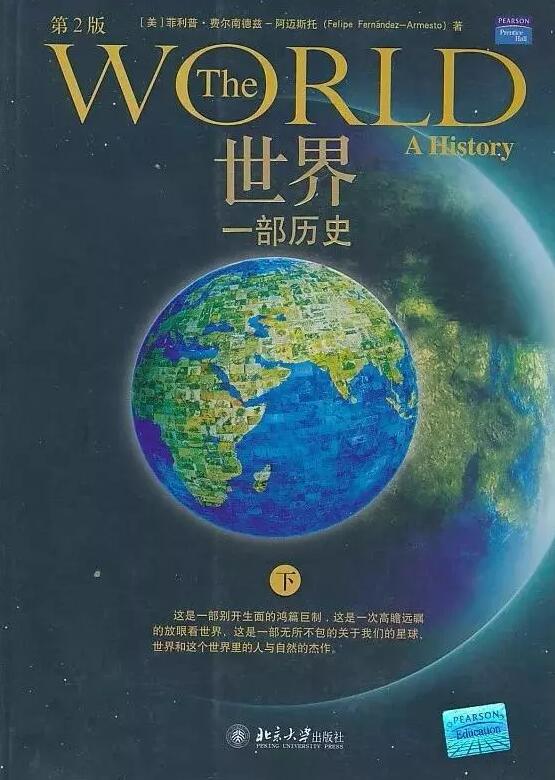
舉一個不要體系的例子。北京大學出版社前幾年出過一本書,中文書名是 《世界: 一部歷史》,作者是美國人費爾南德茲-阿邁斯托。這是一部全球通史性質的書,也是一部典型的不要體系的書。作者在前言中就説,他這本書不要體系,也絕對沒有任何體系。他試圖把整個世界從古到今各個地方、各種人羣、所有文明、一切能夠找得到的東西都寫進書裏。書寫得非常精彩,也很耐看,但我們發現,他——作為一位沒有受過專業史學訓練的記者作家,雖然把書寫得很精彩,但素材都是信手拈來的,並未精心挑選;如果他碰巧拈到了另外一些素材,那他就一定會寫出另外一部歷史了。讀者看完了這本書,腦子裏仍然是一堆碎片,而沒有成為 “世界”。所以我説,體系是歷史學研究的本質特徵之一。
中國史學傳統和世界史學傳統都非常重視體系,無論自覺或不自覺,都把體系看得很重,而且有成型的體系。比如,中國史學傳統從形式上説是紀傳體,從《史記》開始就是這樣;從理念方面説,自孔子以來,經過司馬遷、司馬光等,一直到現在,都強調經世致用、知古鑑今,強調史學的借鑑意義——“資治通鑑”就是用古代的東西警示現今,這是中國史學的一大特點。中國史學重視史料鑑別,因此,考證、考據在中國史學傳統中佔有重要地位。但是考證、考據不是中國史學研究的根本目的,鑑別史料是為知古鑑今服務的。考據之學到清代發展到頂峯,形成所謂乾嘉學派,但那是有時代背景的,就是清代愈演愈烈的文字獄。關於這個問題,史學界各位同仁都很清楚。
西方史學傳統同樣有體系,但它的體系更加多樣化,並且隨着時代變動而不斷變化。從形式上説,西方敍事方法和中國的紀傳體敍事有很大區別,我把它稱為“時空敍事”,也就是講故事,沿着時空一層層鋪敍;另一種形式是編年體,按年、月、日記錄所發生的事,這種形式在中世紀相當普遍。從理念上説,西方歷史學強調求知,也就是以追求知識為目標,想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把求知作為非常重要的理念。但即便如此,它仍舊重視對歷史教訓的探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修昔底德寫這本書,試圖找到戰爭中的教訓,尤其是雅典失敗的教訓。可見,求取教訓在西方歷史學的源頭就已經是傳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
進入中世紀,中世紀的史學基本上是一個神學的體系——《聖經》的框架,教會的體系。各種史學書籍、著作等,都跳不出《聖經》的規範,以《聖經》作為解釋與理解歷史的框架。到了近代,近代前半段,從15世紀 (或更早) 到大約 18 世紀中葉,是一個文藝復興的體系,它逐漸突破中世紀的神學體系即教會體系,打破了《聖經》框架,而形成一個人文主義的框架,無論從伏爾泰的《路易十四時代》,或者從意大利的一些人文學者書寫的史學著作中,都可以看到這個特徵,即文藝復興的體系、人文主義的框架。
近代的後半段,從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西方史學又出現新的變化,這和那個時代的背景密切相關:科學技術、工業革命等影響到歷史學,就形成一個“科學的”體系和蘭克的框架。蘭克標榜他的歷史是 “科學的歷史”,這個影響非常大。歐洲其他地方也出現類似情況,比如説英國阿克頓勳爵牽頭寫作的多卷本鉅著 《劍橋近代史》,差不多也是這種性質。
到20世紀,某一個主流體系獨大為宗的情況慢慢消失了,而越來越趨向於多樣化和多元化。進入21 世紀,多元化的傾向就更加明顯了,各種 “體系”越來越多,最後多到了雜亂無章,不得不用一個“後現代”的大口袋把它們套進去。儘管如此,審視20世紀西方歷史學的發展,史學家們對體系的探索一直在持續,他們一直在嘗試構建新的體系,並試圖將其構建成主流的體系。
比如,20 世紀上半葉,有湯因比、斯賓格勒為代表的文明史觀,西歐很多國家及美國則出現經濟史和社會史,英國的屈維廉就是早期社會史的著名代表。再比如,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美國出現邊疆理論,這也是一種體系,帶有強烈的理論色彩。20世紀下半葉英國形成西馬學派,這是一個有很大影響力的學派,它有獨特的理論,有自己的體系。法國的年鑑學派也是這樣,有自己的體系,有自己的理論。差不多同時,社會史在西方蔚然成風,但二戰以後的社會史和 20 世紀早期的社會史不同,它是一個“沒有政治史的”宏大歷史,包括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看起來非常瑣碎,但是有它的框架和理念。再往後,全球史出現了,這是一個龐大的歷史框架,它那種“橫向”構建歷史的方式,在歷史學研究中顯然另闢了蹊徑。而最近這段時間,在史學研究碎片化甚囂塵上的時刻,又有人試圖去構建新的體系,於是就出現了“大歷史”:大歷史把宇宙萬物、天地人神全都寫進歷史書,並且説這才是真正的“歷史”。由此可見,在西方史學傳統中從來就不缺乏“體系”,只是“體系”太多、又不斷髮生變化而已。
但是從 20 世紀下半葉起直至現在,碎片化的現象卻愈演愈烈了,許多人越來越傾向於不要體系,拋棄所有框架,而把歷史等同於神話,把寫歷史看成講故事。歷史學受到後現代主義的巨大沖擊,變得越來越碎片化。後現代主義的基本特徵就是解構,它解構一切。歷史學正遭遇後現代主義,它的體系正在被解構。這就是歷史學正在面臨的重大危機。
説到這裏,必須回答什麼是體系? 這當然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關於“體系”的理解顯然很多。我認為歷史學的 “體系”就是在歷史學研究中確認一個思維框架,把研究放在這個框架裏進行。思維框架當然和歷史研究的理念相聯繫,因此必定有某些理論的指導。如此回答也許太簡單,但我認為是有道理的。**就體系而言,框架是關鍵,框架的邊界就是理論。就具體研究工作而言,題目不在於大小,而在於有沒有框架:一個很小的題目也可以“以小見大”,關鍵在於有沒有體系。沒有體系、沒有框架,再大的題目也只是碎片。所謂碎片化,並不是説題目小,而是不存在理論框架。**小題目也可以做出大歷史; 相反,很大的題目,無數的史料,一百萬、兩百萬字的篇幅甚至更多,也可能寫出一大堆碎片。所以,題目不分大小,篇幅不分多少,關鍵在於有沒有體系。
現在有很多研究生論文就存在這個缺點:沒有體系,沒有框架,只是一批史料的堆積。如果這只是寫作技巧或處理不到位的問題,那還情有可原。但現在很多人其實從思想深處就反對體系,認為史學研究不需要體系,甚至應該有意識地擺脱任何體系。儘管出現這種思想傾向是有原因的,但歷史學研究確實不可能沒有體系,因為體系是客觀的要求,是歷史學研究的本質特徵之一;離開了體系,歷史學研究便無從下手。
由此説到大眾史學問題,它和體系問題有關聯。葛劍雄先生近期發表一篇文章 《大眾史學未嘗不可以碎片化》。我覺得他的提法不是沒有道理,因為通過大眾史學這樣一種傳播方式,讓更多的人瞭解歷史,瞭解各種歷史知識,提升全民的歷史知識水平,確實非常重要。但大眾傳播畢竟不是系統學習,於是就很容易出現 “碎片化”,也就是一般民眾得到的歷史知識很零碎,難以形成整體的歷史觀。
現在,在中國國內,歷史學已經從谷底慢慢升起,從冰點升温,越來越熱,對於專業史學工作者來説,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是一件振奮人心的事。但需要指出的是:**作為專業的史學工作者,不僅要向大眾傳播歷史的知識,也要向大眾傳播歷史的價值理念。而歷史的價值理念是什麼?它體現在體系中。專業的史學工作者在向大眾傳播歷史知識的同時,尤其要注重傳播歷史的價值和歷史的理念,否則,大眾史學就會變成全民娛樂。**現在,很多東西都變成全民娛樂了,各領域都出現娛樂化現象。一旦大眾史學也成為全民娛樂,變成了飯後茶餘的消遣對象,那麼大眾史學也就變成笑料了,變成了“戲説乾隆”。所以,專業史學工作者應該引領大眾史學的方向,從史學研究的本質特徵出發,注重傳播歷史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