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戰略是刀尖上的哲學
【文/ 張文木】
我的研究方法多不源自國際流行的理論,而是依據被人們稱之為“常識”的經驗事實,特別是最簡單、最平常、人們天天要重複的像衣食住行這樣的經驗事實。理論畢竟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1。
小時候給人幫忙,人家留下吃頓飯。開始只認為這是天經地義,後來悟出“幹活吃飯”是一種在盡責後應有的民主權利;而尊重別人的勞動,則是民主原則的重要體現。這用於觀察國際事務,我們發現,現在中國成長了,還進了WTO,給世界幹了不少活,但結果我們得到的回報卻遠不足以補償我們的勞動和資源支出。我們用自己已十分稀少的資源和辛勤勞動為世界提供了豐富的產品和龐大的市場,這個時候我們就會聽到西方人表揚中國人“勤勞勇敢”;但當我們的國內資源已使我們的發展難以為繼,從而需要更多的資源進口的時候,西方人就説“中國威脅”。這就不公平了。幹活吃飯,這是天下最民主的道理。可就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放到中國人身上就不行了,西方人的“自由貿易”理論就不見“普世性”了。
其實,中國也不是受到這種不公正待遇的唯一國家,當年英國就是這麼對待美國的。正是英國壓迫才造成早期美國那麼多有生命力的國際政治理論。現在美國人又學着當年英國人的樣子不公正地對待中國人,教訓中國人。説千道萬,意思無非是讓中國儘量多地在外邊幹活而儘量少地在外邊吃飯或不吃飯,他們説這樣對中國最“安全”。這也是很不講道理的。因此,在發展問題上,我們學者就應當為中國説話。為中國説話,就是為公平正義説話。
尋求公平正義是需要手段的,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與早年美國的經驗一樣,當代中國也意識到,為了國家統一,為了能保證穩定的能源進口,中國迫切需要擁有強大的制海權。可已從英國人手中奪得制海權的美國人這時卻忽悠咱中國人説:中國並不需要制海權;如需要,中國可以依託美國的海上力量尋求海外安全;中國應向西部內陸發展,那裏才是中國“最安全”的地帶。遠的不説,單就日益臨近高危期的台灣問題而言,這種理論就包含着巨大的陷阱。因為台灣問題實質就是中國製海權不足的問題。1943年斯大林就開闢第二戰場地點的分歧,告訴丘吉爾:“正因為俄國人相當單純,因此就認為他們沒有識別能力,看不見眼前的事物,那是錯誤的。” 2斯大林這裏説的“識別能力”是指用英國人所擅長的以地緣政治理論判斷世界事務的能力。這話轉用於回答上述説法就是,正因為中國人相當單純,因此就認為他們沒有識別能力,看不見制海權之於中國發展的深遠意義,那也是錯誤的。這裏我説的“識別能力”,是指英美人擅長而中國人剛起步的用地緣政治和海權理論分析世界事務的能力。本書不僅研究這一理論,而且還要與中國人民一起提高用這些理論分析和處理世界政治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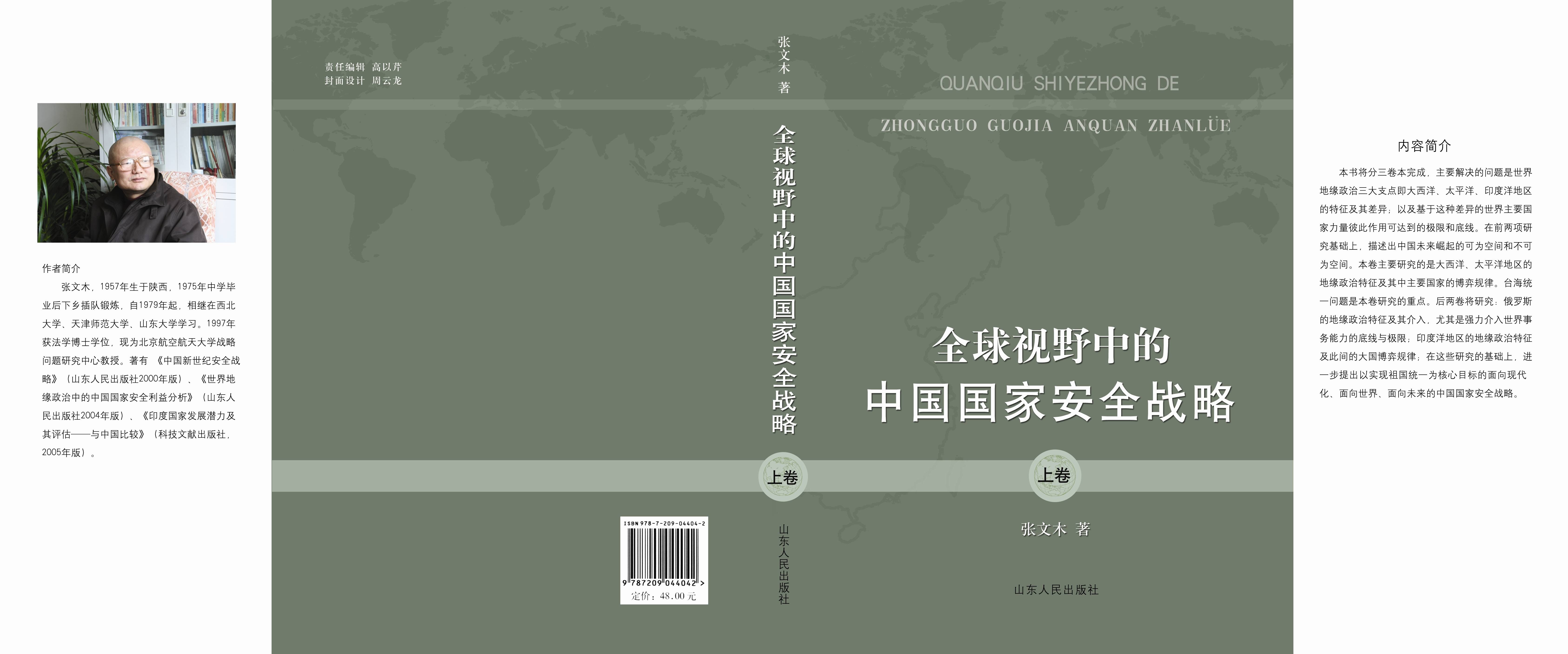
小時候記得最清楚的事,是出遠門時要多帶些乾糧。後來明白有多少乾糧就能走多遠的路。這種來自餓肚子的經驗,使我形成了現在學術研究中關於國家發展規模必須與資源規模相匹配的理論,以及在本書中反覆強調並運用的國家力量伸縮極限與底線的理論。小時候愛看世界地圖,那時以為國家邊界是像電影上那樣談出來的,邊界線是像寫描紅一樣畫出來的。後來看了歷史書才知道,國家邊界是打出來的,邊界線是血染出來的。不然為什麼資源豐富地區的國家邊界就犬牙交錯,而資源貧乏地區的國家邊界就多是直線?
國際政治多是資源政治的倒影。正如樹木本身的高低決定其倒影的長短一樣,不管各國外交多麼變化莫測,也不論各國戰略研究報告説得如何振振有詞,國家資源總量決定了國力伸縮終有其不可超越的底線和極限。基於特定資源支撐的一國人民對其生存權的捍衞態度決定該國必須堅持的戰略底線,國家主權邊界大體就是這條底線的終極反映。國家的資源佔有水平及基於並運用這種資源實踐其發展權的國家戰略能力,決定國力伸展的戰略極限。戰略底線,事關國家生死存亡,公民對此比較容易形成共識;而戰略極限,事關國家發展,則往往容易被渲染誇大並由此導致許多國家其興也勃,其亡也忽。歷史上的帝國多在捍衞國家戰略底線中崛起,在無節制地突破其戰略極限中敗亡。毛澤東同志告誡中國人民不要作超級大國,不要稱霸世界,所以才有新中國可持續的高速發展;明治天皇告訴日本國民要征服整個亞洲,要稱霸世界,結果卻使日本不僅成了世界唯一經歷核打擊的國家,其近代“成就”也隨之灰飛煙滅。因此,在戰略底線和極限間,後者是戰略學研究的重點,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小時候常玩“勾皮筋”遊戲,那時能將一個根皮筋圈翻勾出12個花樣,最後解不開對方花結的是輸方,當然前提是不能將皮筋拉斷。長大了才知道,國際政治也是一個萬變不離其宗的遊戲,不管各國外交如何花樣翻新,其極限就是不能將“皮筋”拉斷。不然,國家博弈的成本就會被推向極端,那就是世界大戰。國力收縮的底線是不能受到嚴重入侵。只要研究出極限和底線這兩個點,我們就會對這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做到心中有數。
遊戲規則猶如國際體系,近世有拿破崙之後的維也納體系、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凡爾賽體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雅爾塔體系。其中,法國拿破崙、德國威廉二世、希特勒、日本的東條英機等,都是硬將“皮筋圈”扯斷的人;而梅特涅、美國的兩位羅斯福、斯大林、丘吉爾等則是另建遊戲規則的人。打破遊戲規則多需勇氣,而建立這種規則卻需要哲學。打破遊戲規則的多是在這場遊戲中所獲甚少的國家,也有的是野心過大的國家。對於前者,國際社會尚可包容,比如蘇聯,它既是凡爾賽體系的打破者,又是雅爾塔體系的建立者;對於後者,則往往因其失道寡助而終成國際和平力量團結一致鎮壓的對象,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德、日法西斯的結局就是這樣。基辛格説:“可惜自俾斯麥去職後德國最欠缺的就是節制。”3
資源的絕對有限性與發展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決定了現實的世界只能是一個各國在“丟手絹”遊戲中不斷博弈的世界。在20世紀末那場遊戲中,“手絹”輕輕地丟在了戈爾巴喬夫的後面,大家都不告訴他,西方人還用諾貝爾獎章忽悠他,結果蘇聯很廉價地被忽悠倒了。蘇聯倒下後,西方人在一片“快點快點捉住他”的叫喊中乘亂將北約邊界推到東歐並乘科索沃戰爭的勝利繼續向中亞挺進。此後西方人又擺好了第二輪“丟手絹”遊戲,並在開始時將“手絹”輕輕地丟在中國的後面。當時中國人還真相信“與國際接軌”可以救中國。科索沃戰爭,尤其是伊拉克戰爭後,中國人明白了,沒有上當。後來歐洲人又順其“反恐”高調將“手絹”輕輕地移到小布什的後面,等美國深陷中東沼澤後,歐洲國家紛紛從伊拉克撤軍並由此獲得新的機會。國際政治,不管其變化如何詭譎,説到底還是一種在總量守衡中此消彼長的力學結構。
戰略是刀尖上的哲學,是國家為生存和發展與他國博弈的學問,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是要帶刀子的;同時戰略又是研究國家發展能力邊界即底線和極限的學問,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沒有哲學是不行的。刀子容易煅造,而哲學卻不能一蹴而就。古今國家的失敗多不是沒有刀子而是沒有哲學,其創傷恢復的速度更是取決於該國公民哲學素養的深淺。同樣的戰敗創傷,在黑格爾的故鄉就容易平復,而在富士山腳下迄今仍在頻頻作痛。尼克松是美國少有懂哲學的領袖,為了撫平越戰創傷,他來北京説要與毛澤東討論哲學問題。柏拉圖對此説得精闢:
除非是哲學家們當上了王,或者是那些現今號稱君主的人象真正的哲學家一樣研究哲學,集權力和智慧於一身,讓現在的那些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學或者只研究哲學不搞政治的庸才統統靠邊站,否則國家是永無寧日的,人類是永無寧日的。4
哲學是關於邊界的學問。朝鮮戰爭中,美國在時間和空間上均越過其國力極限,因而敗得既沒面子也沒裏子。1962年10月古巴導彈危機中赫魯曉夫將手伸出了其國力不可承受的空間極限,但這一失誤很快以時間上的收縮而受到矯正,儘管失了面子卻保住了裏子。在同年發生的中印之戰中,毛澤東恰當地把握了國力伸縮的時間和空間:我方長距高寒的空間劣勢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大張大合的時間優勢彌補,等到爭執於古巴的蘇、美和國會爭吵不休的印度三家醒過神來,毛澤東已全勝收兵。一仗下來,既贏了面子——中國人打出了威風和氣勢,也贏了裏子——中國人在西南對印自衞反擊戰中打出了近半個世紀的和平與安定。
邊界既是對自己的規定也是對對立面的規定。不懂自我規定的國家,其戰略家眼中要麼盡是敵人,要麼全是朋友。尼克松與前任兩位羅斯福一樣知道哪裏是美國國力的邊界,由此也知道沒有中國的合作,美國力量不足以應付全球的,甚至是地區的挑戰。尼克松告誡美國人“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此後美國才得以復興。今天的一些美國政治家不大懂得“有多少乾糧就能走多遠的路”的道理,他們視國事為兒戲,也拿出了當年麥卡錫和凱南“反共”的勁頭,以“反恐”劃線。他們幾乎將南方世界的所有大國都列為必須打擊的“邪惡軸心”,結果弄得美國國力透支和天怒人怨,其外交猶如一場鬧劇。黑格爾説,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都出現兩次;馬克思補充説,“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 。5美國兩個布什總統與法國歷史上兩個拿破崙皇帝所扮演的歷史角色相似,前一個是悲劇即正劇人物,後一個在政治家圈中絕對是世界級的笑劇即滑稽人物。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後者因不學習而失去了哲學。但是,美利堅民族是有智慧的,尤其在困難的時候美國人往往會迸發出大戰略的思想光芒。想必美國人會通過尼克松前後的歷史經驗,很快認識到尼克松哲學對於美國的巨大意義。
哲學也是關於立場的學問。立場是主體的基礎。立場不排斥學習,但失去立場的“學習”是要捱打的。19世紀下半葉,中國人先是有限地向歐洲學習,結果我們因拒絕輸入西洋人的鴉片而捱了“老師”的打;轉學東洋日本,結果又蒙受甲午國恥。後來人們誤解是學得不夠,還不夠開放,還要全盤西化,中國主體意識由此受到全面衝擊:個體消融主體,本能消融個體,“客觀中立”説消融民族立場説,最後中國意識形態被分解得散沙一片,這為20世紀初開始,30年代末達到高潮的更大的國難在中國內部作了思想鋪墊。《辛丑條約》簽訂和日本全面侵華,大大激發了中國人的主體意識,這種意識在外敵不斷入侵的刺激下在中國迅速成長並在延安經歷了革命的洗禮,最終形成了以毛澤東思想為旗幟的主導中國前進方向的有民族風格和民族氣魄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再次凝聚起中華民族打敗日本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並在朝鮮戰爭中教訓了美國的驕橫,此後便是全民族依託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復興。這段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立場是戰略哲學的根本:失去立場,尤其是失去國家立場的戰略,在國際鬥爭中就會異化為那種被恩格斯批評的“為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只圖一時的成就而不顧後果”6的機會主義式的“學術技巧”。這種貌似“中立客觀”和“普世性”的哲學,如引導中國戰略學研究,那就會使我們既分不清“誰是我們的敵人”,也不知道“誰是我們的朋友”,而沒有對手的戰略哲學,導致出的只能是沒有根本利益訴求的戰略。這對國家而言,無異於又一場國難的開始。
哲學與刀子是不能分離的,中國宋朝傾國就是從哲學與刀子分離開始的。毛澤東批評宋太宗“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敵手”;批評亡國之君宋徽宗“既能寫詩,又能繪畫”。前者不善用刀子,後者乾脆丟掉刀子,結果在宋朝哲學日益發達的同時,國難卻日益逼近;毛澤東説:“一些老粗能辦大事情,成吉思汗、劉邦、朱元璋。”7毛澤東讚賞的這些“粗人”都是一些將哲學與刀子結合得很好的政治家。
**好的國際政治學研究應當是一個雙向經驗互證的過程。一方面不僅要認識世界主要國家的戰略需求,更要認識這些國家實現其戰略需求的能力及支撐這種能力的資源極限。另一方面,在知彼的基礎上,不僅要認識本國的戰略需求,更要認識本國實現這些戰略需求的能力及支撐這種能力的資源極限。**歷史上許多政治人物多不敗在戰略邏輯的嚴密性,也不敗在戰略意志的堅定性,而是敗在缺乏對本國國力底線和極限的經驗性的認識和了解。21世紀初的美國小布什外交戰略的失敗,便是這一原理的最近説明。導致1905年俄國在東北亞失敗的別佐布拉佐夫的經營遠東的理論(我將在第二卷中對此提出並深入分析),以及導致美國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失敗的凱南遏制理論等,其失誤多不在戰略邏輯是否合理——事實上它們在學理邏輯上非常完美,而在於這些戰略理論提出者對當事國的國力底線和極限缺乏經驗性的瞭解,他們以充足的理由推導出的卻是隻有上帝才能完成的目標,其結果使他們的國家不是慘敗就是為這個目標疲於奔命。這種戰略研究就是那種於事無益、於國無補的研究。
青年時為學,曾誤將才氣當學問。讀書到一定年紀,方知能講出新穎觀點,那只是才氣,而能證明這種觀點,那才叫學問。學問之難,難在證明。才氣和聰明是學問形成的必備條件,而經過證明,尤其是實踐經驗證明的見解,才是學問的最終完成。人年青時往往以才氣先聲奪人,那是由於他還有證明問題的時間;年紀大了就不能這樣,就要以儘可能豐富的經驗事實來證明你提出的觀點,並由此取得大家的共識。現在奉獻給大家的這部著作就是我這種學術理念的結晶。
中國國家安全戰略是我學術研究的主線。2005年下半年起,我確定了下列研究計劃:
(1)世界地緣政治三大支點——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地區——的特徵及其差異,以及基於這種差異的世界主要國家力量彼此作用可達到的極限和底線。
(2)在前項研究的基礎上,從大國博弈及其興衰歷史中尋找當代主要國家力量伸縮的實際而非僅僅戰略文件上提出的極限和底線,並在其間找出符合實際經驗而非僅僅符合紙面邏輯的中國崛起的可為空間和不可為空間。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以完成祖國統一為核心目標的基於全球視野的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
我們知道,國家制定國民經濟計劃的前期準備工作是資源普查。知道資源可能供給的總量,就能確定國民經濟可增長的規模。我們還知道,達爾文進化論研究的準備是從在世界各地收集人類化石標本開始的。當時,化石是支撐進化論觀點的最硬的證據,拿出這些證據,也就拿出了進化觀點的基本論據。從某種意義上説,本書前兩卷就是為第三卷的主題即“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研究在全球範圍內開展的前期“資源普查”和國家戰略能力“化石”標本的收集、鑑別、比較工作。我要盡力從世界範圍找出“最硬的證據”來支撐第三卷的結論。
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全書的第一卷,主要研究的是大西洋、太平洋地區的地緣政治特徵及在這一地區主要國家的博弈規律。太平洋地區及其中的台灣問題是本卷研究的重點。後兩卷將研究:(1)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特徵;沙俄帝國和蘇聯的興亡經驗及其中反映出來的俄羅斯介入,尤其是強力介入世界事務能力的底線與極限;(2)印度洋地區的地緣政治特徵及此間的大國博弈規律;(3)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基於全球視野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
人的生命是有目的的存在,而寫作則是知識勞動者實踐生命意義的重要方式。我寫這部著作的目的是為了中國人不再經歷剛剛擺脱的百年屈辱、為了中國獲得與其他大國平等的政治和貿易地位、為了中國可持續的和平與發展。
2008年1月於北京
註釋:
1.本文是為拙著《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上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所作的序言。刊發於《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年第4期。
2.轉引自[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啓迪、馬寧、鄭昭彬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下冊,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617頁。
3.[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149頁。
4.[古希臘]柏林圖:《國家》,引自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卷,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118頁。
5.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頁。
6.[德]恩格斯:《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4頁。
7.轉引自薛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44、347頁。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