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新史學、帝國興衰與古典教育
【本文是作者在湖南師範大學教育學院舉辦的“古典教育研討會”(2018年11月)上的主題發言,經擴充後以“世界史意識與古典教育”為題刊於《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9年第1期),本版經作者重新擬題及稍有增訂。】
值此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之際,親身經歷過這一偉大歷史變革的學人撫今思昔,都會對我國學界經歷的史無前例的巨大變化感慨萬千。**1978年的“我們”在讀什麼書、能讀到什麼書?當時尚且年輕的“我們”在想什麼問題,腦子裏有怎樣的知識儲備和學術視野?如今,“我們”在思想學問和政治覺悟兩方面有了多大長進?**晚近20年來,我國學術景觀變化之快,即便已經成為學界中堅的“70後”和“80後”學人,恐怕也有跟不上時代步伐的感覺。
自1840年代以來,為了應對現代列強的進逼,深入認識西方文明的來龍去脈迄今仍是我國學人無法卸下的時代重負。一百多年來,國家接連遭遇共和革命、內部分裂、外敵入侵和封鎖圍困,數代學人很難有安靜的書桌和沉靜的心態面對紛然雜陳且蜂擁而來的問題。

五四運動
“改革開放”以來,隨着國家生存狀態逐漸改善,學界也在不斷拓展學術視野。儘管學術熱點數次更迭,教育面貌不斷更新,但“西學熱”始終是主流。僅舉犖犖大者,自1978年以來,我們至少經歷過“經濟學熱”“現代哲學熱”“社會理論熱”“後現代哲學熱”“古典政治哲學熱”。晚近10年來,隨着我國在國際政治格局中面臨新的挑戰,又迅速出現“世界史熱”(晚近5年來尤為明顯)。
**這會是最後一波“西學熱”嗎?很難説。但這個問題不重要,重要的是,任何一波“西學熱”都會對我國人文-政治教育的品質產生影響。**與其想象我國學界還會在哪個學問領域開放自己的學術視野和學問意識,不如審視一下正在興起的“世界史熱”與人文-政治教育的關係,或者説審視我們正在形塑什麼樣的世界歷史意識。畢竟,與其他學科的“西學熱”相比,“世界史熱”與我們的人文-政治教育的關係更為直接。
1874年,時年30歲的尼采(1844 - 1900)作為巴塞爾大學的古典學教授出版了第二篇“不合時宜的觀察”(寫於1873年)。這篇題為“史學對於生活的利與弊”的小冊子一向被視為尼采關於史學的論著,其實,它的真正主題屬於如今的教育學,因為其問題意識是新生的德意志帝國應該形塑什麼樣的人文-政治教育。[1]

尼采(1844—1900)
尼采寫下這篇文章時,德語學界的“世界史專業”已經發展成熟,而且與巴塞爾大學史學教授布克哈特(1818 - 1897)開設的三次“史學研究導論”課(1868 - 1872)直接相關。[2]尼采對這位前輩和朋友十分敬重,但他仍然忍不住提出警告:
我把這個時代有權利(mit Recht)為之驕傲的某種東西,即它的史學教育(historische Bildung),試着理解為這個時代的弊端、缺陷和貧乏,因為我甚至認為,我們所有人都患上了一種折磨人的史學熱病(den historischen Fieber),而且至少應當認識到我們還有這種病。[3]
儘管這話在今天會讓我們難堪,但我們要理解這一刺耳之言的含義卻並不容易:尼采為何認為新興的史學教育對國家的人文-政治教育會帶來致命危害?
“世界史”誕生的地緣政治含義
渴求來自身體的需要,晚近的“世界史熱”明顯出自國家身體變化的需要。隨着我國在經濟上成為世界大國,重新認識中國在世界歷史中的位置,自然會成為我國學界的身體需要。
**在我國大學的文科建制中,世界史專業迄今相當纖弱,明顯不能適應國家成長的需要。2011年,教育部將世界史專業從二級學科提升為一級學科,但這個專業顯然沒可能短時間內變得強健。**我們值得問:推動晚近世界史翻譯熱的有生力量從何而來?
在大學任教並從事研究的世界史專業人士大多在國別研究或區域研究的海量材料中辛勤耕耘,憑靠現代社會科學的各種新派方法積累實證成果,不大可能成為這股世界史翻譯熱的有生力量。反過來説,由於專業劃分明細,且受人類學/社會學方法支配,世界史專業人士未必會感覺得到,自己的學問意識、研究取向乃至學術樣式正面臨嚴峻挑戰。
在18世紀啓蒙時代的歐洲,“世界史”作為一門現代學科才初見端倪。德意志哥廷根學派健將施洛策(August Ludwig von Schlözer,1735 - 1809)40多歲時,為了讓自己的女兒成為受過教育的“有學養的女士”(gelehrte Dame),在1779年出版了《為孩子們準備的世界史:少兒教師手冊》(第一卷)。[4]該書算不上西歐學人的第一部“世界史”,但它可能算得上第一部德語的為青少年編寫的世界史教科書。兩年後(1781),捷克的天主教修士、教育家帕瑞切克(A. V. Parizek,1748 – 1822)也出版了一部德文的《給孩子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 für Kinder)。由此可見,現代文教剛剛形成之時,世界史就成了重要內容之一。[5]
施洛策首先是研究德意志帝國史的專家,同時也是德意志學界研究俄國史的開拓者。這意味着,“世界史”作為一門學科在其誕生之時就與歐洲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衝突有內在關聯。
希羅多德(約前480 - 前425)在西方有“史學之父”的美譽,他的《原史》儘管在今天的實證史學家看來有些不靠譜的“八卦”,卻因探究“希波戰爭”的成因和過程而成了今人能夠看到的人類有記載以來的第一部“世界史”。[6]這提醒我們應該意識到,“世界史”的含義首先並非指編年通史,而是探究人類不同政治體之間重大地緣衝突的成因、過程及其影響。不用説,隨着歷史的演進,這樣的事件越來越多,與此相關的紀事性探究也越來越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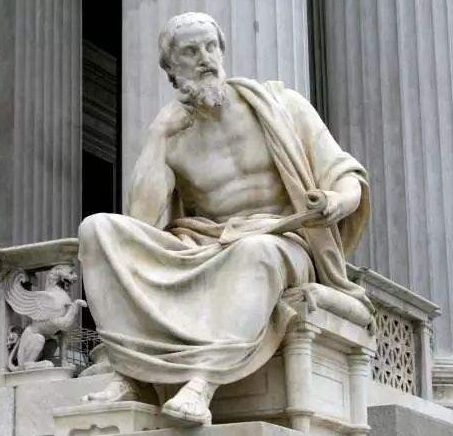
希羅多德
儘管如此,並非每個經歷過重大政治衝突的政治體都留下過這類“史書”。記住這一點,對我們眼下關切的問題不能説無關緊要。
18世紀的施洛策既研究本國史,又研究他國史,難免會對“世界史”形成一套自己的理解,這樣的史學家在歐洲並不少見,而在我國學界迄今屈指可數。這並非不可理解,因為,“世界史”作為一門史學專業的形成與兩件歷史大事相關,而我們對這兩件大事的反應都過於遲鈍。
首先,歷時三個世紀的地理大發現(15世紀末至18世紀末)給歐洲學人帶來了整全的世界地理視野。[7]19世紀的法國有個獻身少兒教育的作家叫凡爾納(1828 – 1905),他的好些作品最初發表在《教育與消遣雜誌》(Magasin d’éducation et de récréation)上。筆者上高小時讀到過他的《海底兩萬裏》(中譯本1961),但直到接近退休年齡才知道,他還寫過給孩子們看的三卷本《發現地球:偉大的旅行與偉大旅行家通史》(Découverte de la terre: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grands voyages et des grands voyageurs,1870 - 1880),讓法國人從小就知道公元前5世紀至19世紀的兩千多年間那些著名旅行家和航海家的事蹟,凡爾納也因此被授予榮譽軍團騎士勳章。[8]該書中譯本與原著相隔足足一個多世紀之久,在今天看來有些不可思議。

《海底兩萬裏》劇照
第二件世界歷史上的大事更為重要:在施洛策身處的18世紀後半期,爭相崛起的幾個歐洲強勢王國之間的地緣廝殺已經越出歐洲地域,蔓延到新發現的大陸——不僅是美洲大陸,還有我國身處的東亞和內亞大陸。若要説施洛策的世界歷史意識與他所屬的政治體的地緣政治處境有內在關聯,並非臆測。畢竟,對歐洲各國人來説,他們各自所屬的政治單位一直處在激烈而且錯綜複雜的地緣衝突之中。嚴酷的生存處境讓他們類似本能地懂得,“世界”從來不是和諧的“天下”,所謂Weltgeschchte[世界歷史]不外乎各種政治體之間的地緣衝突史。
在寫於1929年的一篇世界史短論中,施米特開篇就説:
我們身處的中歐生活在sous l’œil des Russes[俄國人的眼皮底下]。一個世紀以來,他們內心緊盯着我們偉大的文化和制度。他們強大的生命力足以掌握我們的知識和技術,使之成為自己的武器。他們所秉有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勇氣,以及他們正教的善惡力量無可匹敵。[9]
認識自己的遠近鄰人的稟性,是希羅多德所開啓的世界史認識的基本原則。施米特所説的“一個世紀以來”,正是施洛策的《為孩子們準備的世界史》出版以來的150年。當施米特寫下這篇短論時,我國讀書人大多還沒有充分意識到,由於西方列強的煎逼,日本人很快學會了模仿西方帝國主義,積極掌握西方人的知識和技術,使之成為手中的武器用來征服中國。[10]
《新史學》呼喚新的教育意識
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為爭奪對我國遼東半島的控制權,日本與俄國在我國土地上打了一場典型的“世界史式”的戰爭。因為,這並非僅僅是日俄兩國之間的戰爭,背後還有英國和法國在遠東的角力,實際上是英日同盟與法俄同盟之間的戰爭。德國和美國正在崛起,為了各自的利益,美國支持日本,德國則支持俄國,即便當時德國與法國在歐洲仍處於敵對狀態。
兩個異國在我國土地上爭奪地盤已經不是頭一回。1622年6月,荷蘭人在東印度羣島站穩腳跟後,曾攻擊葡萄牙人佔據的我國澳門,以圖奪取通往日本和我國台灣的海上交通線的控制權,遭葡萄牙的澳門守軍用火炮給予重創。儘管如此,就戰爭規模而言,歷時長達一年半的“日俄戰爭”仍算得上我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大事。直到今天,我們對這場戰爭的成因、過程以及歷史影響的探究遠遠不及日本史學界,頗令人費解。[11]
戰爭爆發之前兩年,流亡日本的梁啓超(1877 - 1929)在報紙上發表了名噪一時的《新史學》(1902),史稱我國現代史學意識的開端。[12]梁啓超痛斥中國傳統史書有四弊,根本理由是傳統史學無助於中國“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
**在筆者看來,這篇文章也理應被視為呼喚我國現代新式教育的標誌性之作。**畢竟,梁啓超對“舊史學”的指控明顯帶有改革傳統教育的意圖。他指責説,我國曆代積累的史書已經“浩如煙海”,讓人“窮年莫殫”:
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讀應讀之書,而苟非有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不能別擇其某條有用,某條無用,徒枉費時日腦力。(《新史學》,頁9)
梁啓超並沒有無視我國古代史書中藴藏着政治智慧,問題在於,並非只要是讀書人都能汲取這些智慧,遑論普羅大眾。從古代史書中汲取政治智慧需要“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而這樣的人古今中外任何時代都數不出幾個。如今,非動員全體國民不能救國於危難,徹底更改史書的寫作方式,編寫全新的歷史教科書勢在必行。
結束對中國傳統史書的針砭時,梁啓超發出了迄今傳誦不衰的呼籲:
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新史學之著,吾豈好異哉?吾不得已也。(《新史學》,頁9)
這不也是在呼籲“新教育”嗎?史界革命與教育革命是二而一的事情。首先,必須重擬史書內容;第二,必須為國民而非為少數人寫史,這意味着必須普及史學教育,“以激勵其愛國之心,團結其合羣之力,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於萬國者。”
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國民”,要讓“臣民”成為“國民”,就得憑靠新式教育塑造“國民”意識。因此,梁啓超有理由認為,新式教育的第一要務是改變史書內容和書寫方式施行“國民教育”,否則,“聲光電化”之類自然科學知識只會培育出“世界公民”。
接下來的問題是:重述歷史應該依據何種史學原則呢?
梁啓超概述了他從西洋人那裏聽來的人類“進化説”,即人類進化之公理在於“優勝劣敗”。在任公看來,這種公理已經得到世界歷史的證明,而中國史書卻從未涉及這樣的公理:
歷史生於人羣,而人之所以能羣,必其於內焉有所結,於外焉有所排,是即種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結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繼焉自結其鄉族,以排他鄉族,繼焉自結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終焉自結其國族,以排他國族。此實數千年世界歷史經過之階級,而今日則國族相結相排之時代也。夫羣與羣之互有所排也,非大同太平之象也,而無如排於外者不劇,則結於內者不牢;結於內者不牢,則其羣終不可得合,而不能佔一名譽之位置於歷史上。(《新史學》,頁16)
在今天看來,梁啓超所表述的“進化論”史觀太過粗糙,也太過質樸。但他受時代的知識語境侷限,我們不必苛求。我們倒是值得注意這裏出現的“世界歷史”這個語詞,因為它表明梁啓超的頭腦已經有一種世界史覺悟,而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沒有對他的這一覺悟給與足夠的關注。[13]
在《新史學》中我們可以讀到:
何謂世界史的?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僅在本國之境域,不僅傳本國之子孫,而擴之充之以及於外,使全世界之人類受其影響,以助其發達進步,是名為世界史的人種。吾熟讀世界史,察其彼此相互之關係,而求其足以當此名者,其後乎此者吾不敢知,其前乎此者,則吾不得不以讓諸白種,不得不以讓諸白種中之阿利安種。(《新史學》,前揭,頁19)
梁啓超沒有意識到,按他對“世界歷史”的這一理解,他所宣揚的人類“進化”説其實很難站得住腳。既然世界歷史就是“國族相結相排”的歷史,何以可能説“今日則國族相結相排之時代”,人類有史以來不就一直如此嗎?如果所謂歷史“進步”即一國之“文化武力”能“擴之充之以及於外”,那麼,古代中國堪稱相當“進步”。問題僅僅在於,中國古人的地緣視野有限,不知道真正的世界地域有多大。但西方古人的地緣視野即便比中國古人大得多,同樣不知道整全的世界是什麼樣!
基於林則徐(1785 - 1850)組織翻譯的英人慕瑞(Hugh Murry)所著《世界地理大全》(1836,中譯名為《四洲志》,約1839),魏源(1794 - 1857)編著的《海國圖志》(1843)才不僅讓中國智識人而且也讓日本的智識人與西方人在“地理大發現”後獲得的世界地理新視野接榫。
在此三百年前(1517年),葡萄牙艦隊駛入珠江口,進佔我國東莞屯門島,沿途“銃炮之聲,震動城廓”(《明武宗實錄》)。整整4年之後,中國換了一位有血性的皇帝(明嘉靖皇帝),才發兵將葡萄牙人逐離屯門島。那個時候,葡萄牙人也還不具有整全的世界地緣視野,誤打盲撞而已,與三百年後英國人的入侵不是一回事。[14]
梁任公接下來的説法更有意思——他説,並非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有“歷史”,有的民族是“非歷史的人種”:
能自結者,為歷史的;不能自結者,為非歷史的。何以故?能自結者,則排人;不能自結者,則排於人。排人者,則能擴張本種以侵蝕他種,駸駸焉壟斷世界歷史之舞台。排於人者,則本種日以陵夷衰微,非惟不能擴張於外,而且澌滅於內,尋至失其歷史上本有之地位,而舞台為他人所佔。(《新史學》,前揭,頁16)
在如今後現代的任何一派史學家看來,這話恐怕都屬於政治不正確。但我們能夠理解,當梁啓超這樣寫的時候,他一定想到中華帝國曾是“能自結者”,但也隨時可能變成“不能自結者”。畢竟,曾經“能自結者”而後變成“不能自結者”,歷史上不勝枚舉:羅馬帝國就是再顯赫不過的例子。梁啓超並沒有讀過黑格爾的《世界史哲學講演錄》,但他憑靠天生“極敏之眼光”懂得:
在世界史中,我們首先必須涉及那些曾經知道自己是什麼和想要什麼的民族,那些在自身之內和超出自身得到發展的民族。[15]
由此看來,我們的確需要有世界歷史意識,否則,我們未必會對此有清醒的自我意識。梁啓超由此得出他所理解的作為史學的世界史基本原則:
故夫敍述數千年來各種族盛衰興亡之跡者,是歷史之性質也。敍述數千年來各種族所以盛衰興亡之故者,是歷史之精神也。(《新史學》,前揭,頁16)
這裏的“歷史”一詞的含義當指“史學”(英文history包含兩種含義),因為,梁啓超説的是“敍述”各種族盛衰興亡“之跡”和“之故”,而這樣的“敍述”只能由所謂紀事作家來承擔。
由於時代的知識語境的侷限,梁啓超沒有認識到,“敍述”盛衰興亡“之跡”和“之故”並非“進化論”引出的史學原則,毋寧説,這一原則堪稱史學的古典傳統。梁啓超沒有提到,古希臘以弗所城邦的赫拉克利特(約公元前535 – 前475)的一句名言曾培育了古希臘紀事作家“極敏之眼光”:
爭戰既是萬物之父,亦是萬物之王,這既證明了神們,亦證明了人們;既造就了奴隸,亦造就了自由人。(殘篇53)
這段著名箴言讓我們看到,古希臘自然哲人已經懂得,萬物之間的生存原則是爭戰性的,任何一物唯有通過與彼物的對抗、牴牾、爭鬥才成其為自身。每一存在者之成其為自身、保持自身、伸展自身,憑靠的都是爭戰的敵對性,由此自然會引出“優勝劣敗”原則,無需等到19世紀的“進化論”來總結經驗教訓。
歐洲的思想史家提醒我們,赫拉克利特有如此“極敏之眼光”,乃是因為他所身處的希臘城邦毗鄰戰爭頻仍、帝國不斷更迭的近東大陸:“伊奧尼亞人擁有大量機會去體驗天下時代的暴力。”[16]
另一方面,面對如此殘酷的“天下”現實,古希臘哲人也致力於建立一個言辭上的“世界城邦”,指望有一天能終結“國族相結相排”的歷史。亞歷山大的帝國雖然曇花一現,畢竟為“世界城邦”的現實可能性提供了一線希望。由此可以理解,正是在馬其頓崛起之時,古希臘出現了一批“世界史”作家。[17]
現在我們值得問:中國古代史書真的像梁啓超痛斥的那樣無視“國族相結相排”的歷史?從《史記》《漢書》乃至以降的歷代官修史書來看,當然絕非如此!問題僅僅在於,中國所處的世界地緣位置不僅不同於希臘人和羅馬人,甚至也不同於阿拉伯人,這意味着“國族相結相排”的地緣狀況不同。
即便如此,在“地理大發現”之前,無論古希臘人-羅馬人還是中古時期的阿拉伯人,他們的史書同樣受自身的地緣視野限制——大名鼎鼎的赫勒敦(1332 - 1406)的《歷史緒論》就是證明。[18]
梁任公所説的“今日則國族相結相排之時代”,實際指“地理大發現”之後出現的“國族相結相排”的時代。不過,即便在19世紀晚期,普魯士王國的偉大史學家蘭克(1795 - 1886)的《世界史》仍然沒有把東亞地區納入自己的視野。[19]儘管如此,“敍述”各種族盛衰興亡“之跡”和“之故”,是蘭克史學的基本原則。
還要過上一個世紀之後,準確地説,直到中國已經重新“站起來”之後,記敍晚近兩百年“國族相結相排”時代的“世界史”才會把中國納入其中。比如説,肯尼迪和西姆斯記敍“歐洲爭霸之途”五百年的大著相隔三十多年,看起來就像是蘭克《世界史》的續篇。[20]
《新史學》後三節專論中國舊史筆法和體例(“論正統”“論書法”“論紀年”),似乎在梁任公看來,新的中國史書當以世界歷史意識為前提,凡此都得改變。在今天看來,梁任公的確有“極敏之眼光”,問題在於,我們應該具有怎樣的世界歷史意識,或者説應該有怎樣的史學教育。
這讓筆者想起比梁任公早一個世紀的德意志史學家施洛瑟(Friedrich Christoph Schlosser,1776 – 1861),他早年在哥廷根讀神學,畢業後轉向歷史研究,以撰寫中世紀的人物傳記名家。1815年,施洛瑟出版了《連貫敍述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 in zusammenhängender Erzählung)卷一,名噪一時,隨即受聘為海德堡大學史學教授(1818)。5年後,他以兩卷本的《18世紀史》(Geschichte des 18ten Jahrhunderts,1823)進一步證明了自己的史學功夫,隨後不到3年又出版了《舊世界及其文化的歷史的普遍史概觀》(Universalhistorische Übersicht der Geschichte der alten Welt und ihrer Kultur, 1st part, 1826; 2nd part, 1834)。接下來,施洛瑟用12年時間將《18世紀史》擴展成《18世紀和19世紀史:直到法蘭西王朝崩潰》(六卷),[21]晚年又花費13年時間為德意志人寫了一部普及性的《給德意志人民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 für das deutsche Volk,1844-1857)——那個時候,還談不上有一個統一的德國。
梁任公從經學轉向史學與施洛瑟從神學轉向史學看似相似,實則不可同日而語。毋寧説,兩相比較,發人深省之處在於,梁任公並未充分認識到,深入認識西方人所理解的“世界史”對重述中國史究竟有何意義。
“新史學”與西方的古典史學傳統
《新史學》發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我們的文教面貌已經徹底換了新顏。梁任公一夢醒來後首先會問:我們中國人今天具有了怎樣的世界歷史意識?在新的歷史意識支配下,中國古史重述有了怎樣的“風景”線?梁任公關心自己當年的祁夢是否已經實現,完全可以理解。
我們會對梁任公説,他的史學觀受19世紀末流行的達爾文主義影響,實在可惜,“優勝劣敗”的世界觀早就是學界的不齒之論。梁任公伸直腰板爭辯説,晚近十多年來,歐美史學的新動向據説與震驚全球的“9.11事件”直接相關,“優勝劣敗論”不過換成了僅僅説起來好聽得多的“文明衝突論”,難道我的看法過時了?看看西洋人自己怎麼説吧:
20世紀90年代波黑戰爭後,人們才認識到自由主義的侷限性,並重新建立對地圖的尊重。冷戰結束後,人們逐漸喪失地理意識,似乎理想主義的時代已經開始,但在“9.11”之後的10年裏,一系列災難性的事件將這種幻想擊得粉碎。[22]
我們還看到,某些西方人的世界歷史意識會讓他把晚近的“優勝劣敗”的世界衝突溯源到2500年前——也就是所謂“人類有史以來”:
基地組織和西方的戰爭不過是曠日持久的東西方對抗的最新表現而已,雙方的衝突經年累月,其起始之日已不可考,只能歸入傳説的範疇。衝突很可能始於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場戰爭,對陣雙方分別是阿凱亞人(伯羅奔半島東北部的希臘人)和屬於半神話的小亞細亞民族特洛伊人,戰爭的起因是斯巴達國王墨涅拉俄斯的尊嚴受辱,他的妻子海倫被一個名叫帕里斯的放蕩的特洛伊花花公子拐走。
……
但是,在後來那些通過荷馬詩歌構建自己的身份認同和文化歸屬感的世代看來,特洛伊的陷落標誌着兩個民族爭奪霸權的鬥爭的歷史的開始,而且隨着時間的流逝,他們之間的區別變得越來越明顯。[23]
從地緣政治學角度看待世界歷史的政治史學家承認,“民族國家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要在達爾文主義法則下求生存的自然現象。”[24]事實上,所謂“達爾文主義法則”不過是16世紀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另一種表達方式而已。
據説,梁啓超在《新史學》中表達的歷史觀其實與蘭克學派的教科書有關。[25]《新史學》篇幅很短,與梁啓超的其他同類文章一樣,涉及西學的地方往往蜻蜓點水,要確認他的觀點是否來自蘭克並不容易。《新史學》發表之前,梁啓超的一些文章倒顯得帶有蘭克的政治史學色彩。比如,《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1899)以及《論民族競爭之大勢》《現今世界大勢論》《歐洲地理大勢論》(1901)等等,至少從篇名來看,也會讓人想到蘭克著名的《諸大國》(1833)。
蘭克雖有“實證史學之父”的美譽,他要求成為史學家必須在考辯文獻和史料採集方面接受嚴格訓練,但他自己的史學樣式大多是文學色彩濃厚的敍事,沒法與注重識讀和辨析史料的實證史學樣式對上號。蘭克的史學楷模是修昔底德,在他看來,史學家的基本職責是,憑靠史料以敍事方式探究人世間政治衝突的成因、過程及其影響。畢竟,史學的最終目的是政治教育。僅僅注重識讀和辨析史料,很難説有什麼積極的教育作用。
修昔底德算得上希羅多德之後的又一位世界史家,因為,雅典與斯巴達之間長達30年的希臘內戰期間,波斯帝國始終是在場者和參與者。修昔底德有比希羅多德更為自覺的“修史”意識或者説“實錄”精神,從而贏得了現代實證史學家更多的敬重。儘管如此,在現代的實證史學家眼裏,修昔底德的《戰爭志》所提供的“史料”仍然不足以讓人們看清這場戰爭的歷史“真相”。[26]
何謂戰爭的歷史“真相”?搞清這個問題並不全然取決於“史料”,而是取決於看待歷史事件的眼力,即梁啓超所説的“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蘭克從修昔底德那裏學會的“極敏之眼光”體現為,關注具體的人性和共同體稟性在政治體的衝突中的表現,而不是專注於人世生活中的某個方面:比如經濟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換言之,蘭克史學實際上更多具有古典史學品質,而非現代式的實證史學品質。直到今天,西方史學界仍然有人不相信,修昔底德式的古典史學過時了。[27]
無論如何,從《新史學》來看,梁啓超並不熟悉蘭克。即便他從某個日本學人那裏輾轉得知蘭克史學的某些觀點,他也未必意識到蘭克的古典史學對中國新史學的意義。否則,“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會帶他深入認識蘭克史學,説不定還會循此追根溯源瞭解西方史學的古典傳統。[28]
事實上,不僅梁啓超沒有,整個“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中國智識人都沒有致力於認識西方的古典史學傳統。1930年代,我國曾有專攻史學的學子從德國留學回來,而且據説十分服膺蘭克學派。然而,也許由於聽信了胡適(1891 - 1962)的那個關於“方法”的著名説法,他掉進了“史學方法論”的泥沼,蘭克史學就混在這潭泥沼之中。[29]
今天的我們不難理解,儘管蘭克在史學史上聲望很高,但他的要著的中譯本直到晚近才魚貫而出。[30]因為,與蘭克的政治史學幾乎同時,歐洲學界正在形成如今所謂的經濟史觀,即關注世界歷史中各文明單位曾有過的經濟生活方式。[31]這並非不可理解,畢竟,18世紀末以來,歐洲正在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工業化革命”。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所帶來的巨大社會變動促使整個19世紀的歐洲文教不斷創新,現代社會科學式的史學路徑逐一登場: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迅速取代了直到吉本(1737 - 1794)和蘭克都還葆有的古典政治史學樣式。
在19世紀後期湧現出來的新派史學中,關注經濟生活方式的社會變遷史研究路向影響最大。畢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讓世界歷史可以被截然劃分為古今兩截。[32]直到20世紀末,我國學界還在為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問題費腦筋,並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堅持不懈地翻來覆去尋找“資本主義萌芽”。
顯而易見,19世紀出現的相互競爭的種種政治觀念支配了人們看待世界歷史的眼光,資本主義如何形成和衰亡成了世界歷史意識的中心問題:考茨基(1854 - 1938)的洋洋1800頁的兩卷本世界史(1919 – 1927)堪稱這方面的最早嘗試之一。[33]
當“改革開放”取得顯著成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治目標成功“超克”資本主義,人們馬上就感覺到:資本、科技乃至“自由”“人權”“民族”“獨立”“自主”之類的觀念,都不過是“國族相結相排”必不可少的武器。“冷戰”結束之後,這一點顯得更加清楚。借用施特勞斯的説法,人們現在不得不從“第二洞穴”爬回“第一洞穴”。[34]
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我們便很難理解,為何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儘管我們的人文-政治教育中並非沒有世界歷史課程,或者説並非沒有確立起一種世界歷史意識,我們如今卻突然感到需要從頭學習世界史。
新“新史學”與民主化的世界歷史意識
此一時,彼一時也。梁啓超寫下《新史學》時,他的首要關切是中國能否“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一百多年後的今天,經歷數代人的艱難奮爭,中國不僅“站起來”而且也“強起來”。[35]恰好在這個歷史時刻,坊間再次出現了史學熱。1840年以來的屈辱和抗爭的歷史,一直是我國政治教育中的重點,現在我們需要更為整全的世界歷史視野,完全可以理解。
置身“新時期”的我們張望西方史學界時,那裏已是一派繁榮的後現代景象。人們看到,當代歐美學界的史學景觀比19世紀後半期更讓人眼花繚亂,但其基本取向仍然是不斷求“新”。[36]儘管如此,如果我們無需在意史學這門學科的種種所謂新方法和新路徑,而是着眼於西方智識人的世界歷史意識的嬗變,那麼,我們便不難看到,從魯濱孫(1863 - 1936)的《新史學》(1911)到勒高夫(1924 - 2014)的《新史學》,[37]最為引人注目的史學現象非世界歷史意識的“民主化”莫屬。
若要問什麼叫“民主化”的世界歷史意識,著名的西方古代史家芬利(1912 - 1986)會樂意第一個站出來為我們解釋。這位劍橋大學的古代史講座教授告訴我們,古典史家大多不可信,比如説,修昔底德就偽造歷史,因為他污衊伯利克勒斯時代的民主人士為蠱惑家,雅典人民被這些“公知”牽着鼻子走。芬利讓我們相信,雖然直到現代都還有學者不斷重複修昔底德的觀點,但在他的實證考據筆下,這一謬論已經不攻自破。
芬利自稱古代史研究的“復原派”,即反對用現代的觀點來研究古代。奇怪的是,他的《古代世界的政治》(1983)讓我們看到,他自己恰恰是現代民主觀念的囚徒。中譯本“導言”敏鋭地指出:
對於希臘化世界的君主國、羅馬帝國,以及古代埃及和兩河流域的各類由君主統治的政治機體,他[芬利]抱持幾乎鄙視的拒斥態度,直接將它們從自己的討論中剔除。[38]
在這位實證的史學家眼裏,古代世界的政治單位只要不是民主政體就“沒有政治可言”,因為,按照他的理解,唯有民主政治才稱得上“政治”。倘若有人覺得這種説法匪夷所思,那麼,他就應該理解:1960年代末,歐美髮達資本主義大國出現了新一輪民主運動,“民主化史學”即這場社會民主運動的伴生物。據説,“民主化史學”有力而且有效地推動了隨技術革命誕生的新型中產階級的民主運動,而這場激進的社會民主運動又反過來促進了史學的激進民主行動,即後現代史學讓我們看到的“解構”和“權利訴求”景象。[39]
芬利的《古代民主與現代民主》出版於1973年,當時,激進社會民主運動的“狂飆突進”勢頭一時受阻。為了替激進民主助力,芬利用自己的古代政治史研究告訴當今的精英主義者們:雅典的全民參與式直接民主從未導致所謂的極端主義。[40]
要知道後現代的“民主化史學”激進到什麼程度,劍橋大學的羅馬史專家比爾德(1955 - )的《羅馬元老院與人民:一部羅馬史》(2015)為我們提供了最新範例。[41]這個書名中缺少古典史學中的一個主要角色:皇帝。出於自己的激進民主信念,比爾德認為,研究古羅馬史不必關注“皇帝的品質和性格”,甚至不必理會古羅馬史書中記敍過的那些偉大人物,因為,在民主化的眼光看來,“偉人未必偉大”(《一部羅馬史》,頁410)。一個史學家如果有正確的政治觀念的話,他/她就應該致力於重新發掘史料,以便“讓我們直抵古代街道上的男男女女生活中的具體問題和焦慮的核心”(《一部羅馬史》,頁472)。
**用“民主化的史學”眼光來看,古羅馬史家留給後人的“歷史”充滿了重構、誤解和自相矛盾,因此,民主的史學家的“重要工作便是批判地梳理這些糾結的線團”。**當然,由於歷史年輪的堙沒,很多歷史事件或普通人的生活狀況,如今的史學家即便想要知道也沒有可能,更不用説“重構”。儘管如此,比爾德相信,只要抱持堅定的自由民主信念,很多“幾乎被歷史埋沒(hidden)”的普通羅馬人的生活故事,仍有可能像碎片一樣“被複原”(pieced together)(《一部羅馬史》,頁528)。
從中譯本推介語中我們能夠看到,英美主流報刊紛紛評價説:這部書代表了“革命性的全新古代史寫法”,“極富開創性……令人振奮……”,因為,作者“讓我們習以為常的觀點變得可疑”,“向我們揭示出,古羅馬人與許多個世紀後與權力、公民權、帝國和身份這些問題鬥爭的人息息相關。”
如果我們記得《埃涅阿斯紀》序歌的開首句arma virumque cano[我歌唱戰爭和一個人],而這個人顯然不是古代街道上的某個普通人,那麼,人們的確有理由説,比爾德用重述羅馬史的方式顛覆了歐洲的傳統政治德性。我們應該知道,比爾德不僅是劍橋大學第一位女性古典學家,她還是“自豪的女權主義者”,長期“活躍於各類網絡、電視、電台等公眾平台”。出版民主化的羅馬史兩年之後,比爾德又發表了《女性與權力宣言》(Women & Power: A Manifesto,2017),這本小冊子與她的羅馬史不僅交相輝映,而且相互發明。
除“年鑑學派”之外,在我國“新時期”最有影響的當代西方史學恐怕非伯克(1937 - )的“新文化史”莫屬。坊間已經譯介了伯克的不少著述,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新文化史”如何從世界歷史中發掘民眾趣味。[42]比爾德的“民主化”羅馬史敍事完美地體現了“新文化史”派旗手伯克的主張:動用所有史學手段致力於從普通人的視角重述西方歷史。
“新文化史”置換了世界歷史的政治敍述,形塑出一種所謂“平民化”的世界歷史意識。用第一部研究伯克的專著的書名來説,這種意識準確地表達了西方國家教育品質的“每況愈下”。[43]因為,“文化史”的開拓者是19世紀的布克哈特,而我們很容易看到,布克哈特的世界史敍事追求精神的高貴,看重“歷史中的偉人”,與“新文化史”派的世界歷史意識絕少共同之處。[44]
我們甚至可以設想,布克哈特要是得知自己的世界史研究所開創的“文化史”取向變成了“文化雜交”,[45]他恐怕會不得不承認,尼采當年對他提出的警告完全正確:
人們可以設想,無藝術氣質和藝術氣質薄弱的人被紀念式的藝術史學武裝起來,有了防禦能力,他們的槍口現在會對準誰?對準他們的宿敵,對準強大的藝術英才,即對準那些人,只有他們才能夠真正為了生活從歷史中學習、並把學到的東西變成更高的實踐。(《觀察》,頁157)
總之,民主化史學意識的“槍口”對準了西方文明的高貴傳統,對準了某些個人天生要傳承高貴文明血統的心性品質。“新文化史學”的原則據説是“從下向上”,發掘歷史中的普通人乃至另類羣體的趣味訴求,憑靠歷史上被忽視、被排斥、被歪曲的種種社會異類力量,對過去的精神貴族們所塑造的文明史施行“去中心化”的革命,給已有的世界史敍述貼上要麼“歐洲中心主義”要麼“男權主義”的標籤,進而徹底掃蕩和顛覆“既定”的西方文明“主流”傳統。
著名的左翼史學家霍布斯鮑姆(1917 - 2012)正確地看到,“自下而上”的史學意識其實源於法國大革命之後的19世紀。[46]布克哈特其實已經預感到,“大革命”之後,西方文明的高貴傳統岌岌可危,他本來指望通過“文化史式”的世界史敍事來挽救這一傳統,卻沒有想到會事與願違。[47]
為了推行激進的民主化教育,“新文化史”的世界史十分注重敍事,以講故事的方式重述世界史的各類主題,作者既有大學中的史學專業人士,也有傳媒寫手——或者身兼兩者。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推出的“古代史上的轉折點”大型叢書的“總序”説,叢書的作者們“既是會講故事的學者,又是在其專業領域有着最新研究成果的敍事好手”,因為這套叢書“既關注上層精英,又關注普羅大眾”。[48]這意味着,“民主化史學”不僅要塑造普羅大眾的世界歷史意識,改造精英們的世界歷史意識更為重要。
由此可以理解,為何後現代的激進民主史學要摒棄學究式的實證考據,轉向“敍事體史學”(narrative history)。[49]敍事史學注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文筆生動活潑,對年輕人尤其有吸引力。可是,敍事同樣是古典史學的基本特徵,因此我們不能説“敍事體史學”本身有問題。畢竟,要更好地教育年輕人,就得用講故事的方式講道理。問題僅僅在於:誰教育誰?講什麼樣的人世“道理”?
現在我們能夠理解,為何尼采在《史學對於生活的利弊》的“前言”中會憂心忡忡地説:現代之後即19世紀以來急速生長的“歷史感”(der historische Sinn)是“一種發育不良的德行”(eine hypertrophische Tugend),它不僅敗壞個人的靈魂,而且敗壞民族的政治生存,更不用説敗壞一個民族的精神健康。
在這篇“不合時宜的觀察”中,當時還不到30歲的尼采禁不住激烈抨擊德國的教育。他以年輕人的名義“抗議現代人在年輕時期[所受]的史學教育”,因為,這種教育會讓一個“真正的文化民族”喪失自己本有的“教養品質”。出於愛護年輕一代的精神健康,尼采憤然指責“自下而上”的史學把年輕人快速訓練成“那種人們到處都在追求的利己主義的成年期”:
人們利用歷史感覺,為的是通過美化、亦即通過魔幻般的科學光芒照亮那種成年男性和非男性的利己主義,損害年輕人的自然反感。的確,人們知道,史學憑靠某種優勢能做到什麼,人們對此知道得太精確了:即根除年輕人最強有力的本能——熱忱、執拗、忘我和愛,降低他們正義感的熱度,用快速完成、迅速見效、速見成果的相反渴望壓制或遏制慢慢成熟起來的渴望,使[年輕]感覺的正直和勇敢染上病態的懷疑。
史學甚至本身就能騙取年輕人最美好的特權,騙取他們以充盈的信心為自己培養起偉大的思想並讓自己向更偉大的思想成長的力量。只要有某種程度上的過分,史學就能夠做到這一切,這我們已經看到了,而且原因就在於:史學通過不斷推移地平線的前景,通過清除周圍氣氛而不再允許人非歷史地感受和行事。這時,人就從地平線的無限中撤回到自我,進入最小的利己主義領域,不得不在其中腐敗、乾枯:他也許會成就了小聰明,卻絕對達不到智慧。(《觀察》,頁227 - 228)
説得多好、説得多麼透徹!我國不少愛讀書的年輕人喜歡尼采,卻不會有像尼采那樣的年輕目光和自覺。我們應該問,何以尼采會對“自下而上”的史學教育有良好的免疫力?僅僅憑靠他的天生素質能夠倖免於難?尼采在《史學對於生活的利弊》中告訴我們:他的免疫力來自傳統的古典教育——來自柏拉圖(《觀察》,頁136,233)。我們可以説,若不是接受過古典教育,尼采這樣的高貴天性同樣可能因史學教育的致命損害而要麼腐敗要麼乾枯。
由此看來,我國坊間晚近大量湧現的各色世界史譯著,未必都出於所謂“大國崛起”的問題意識。毋寧説,出版界的盈利考核同樣能夠驅動這樣的翻譯熱。在一年一度的國際書展上,外商必定會推銷自己的“民主化史學”暢銷書,而出版界商家更關切盈利而非關切我們的人文 – 政治教育的品質,並非不可理解。
梁啓超號召我們走向“新史學”,除了要我們具有世界歷史的視野和意識,還要求我們改變我國傳統史學的品質:他身體力行親自動手改述中國的傳統史書。隨着伯克的“新文化史”著述大量譯介,在民主化的世界歷史意識啓發下,我國的古史重述也的確出現了可喜的新景象。[50]
梁啓超若看到這樣的“新史學”景象,他會心生憂慮還是欣喜,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應該會意識到自己在《新史學》開篇所説的話未必妥帖:
於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然則,但患其國之無茲學耳,苟其有之,則國民安有不團結,羣治安有不進化者?(《新史學》,頁3)
今天梁啓超還能這樣説嗎?他只能説:歐美自由民主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激進民主,“新文化史學”等後現代式的解構史學之功居其半焉。接下來他恐怕會説:但患我之有茲學,苟其有之,則國民安能團結,羣治安有不退化者。
西方文明史如何既連貫又斷裂
隨“民主化”的世界歷史意識而生的是“全球化”意識:“全球史”式的新“世界史”與“民主化史學”相伴而生。據説,民族國家式的世界史敍事壽終正寢了。[51]
所謂民族國家式的世界史與“歐洲中心主義”的世界史幾乎是同義詞,即便在“全球史”學的創始人麥克尼爾那裏,世界歷史的主線仍然是古希臘羅馬 – 中世紀基督教歐洲 – 現代歐美的三段式。因此,人們有理由把民族國家式的世界史視為歐洲霸權主義的世界史。隨着地緣政治格局的改變,如今得叫做美國霸權主義的世界史。[52]
對於美利堅帝國式的世界歷史意識來説,西方文明從古希臘到美利堅的歷史是連貫的歷史,美國理應是“西方文明”傳統的承繼者和擔綱者。對於美國學界的民主化世界歷史意識來説,則不僅西方文明具有多重傳統,甚至“英美文明”也具有多重傳統和內在多元性。[53]用梁任公的話來説,民主化的世界歷史意識必然使得帝國內部從“相結”走向“相排”。
一百多年前,梁任公已經認識到,自希臘羅馬以後,世界史之主位,既全為阿利安人所佔,及於羅馬末路,而阿利安族中之新支派,紛紛出現。除拉丁民族(即羅馬族)外,則峨特(Celtic,[引按]今譯“凱爾特”)民族、條頓民族、斯拉夫民族其最者也。峨特[凱爾特]民族在阿利安中,以戰勝攻取聞。(《新史學》,前揭,頁22)
在今天的民主化“全球史”學者看來,梁任公上了“歐洲中心主義”的當,因為他完全忽略阿拉伯民族和蒙古遊牧民族。梁任公會爭辯説,史學不過是“敍人種之發達與其競爭而已”(《新史學》,頁16)。對法蘭西帝國舊夢念念不忘的法國史學家會對這一説法點頭稱道,卻不會對拿破崙帝國之後法國接連敗走麥城的歷史多看幾眼。[54]
相反,預感到法蘭西帝國已經一蹶不振的史學家,早就回過頭去細看羅馬帝國瓦解的歷史。換作當今仍然掌握着世界霸權的帝國的史學家,則會細看羅馬帝國如何擴張和防禦的經歷,從中獲得維持世界霸權的經驗和教訓。[55]
梁任公會願意承認,他看到“人種之發達”及其競爭隨時勢而變,絕對沒錯。他只是沒有想到,在他離世後僅僅半一個多世紀,“競爭”就出現瞭如此出乎他意料的變局。[56]但是,誰能夠預料世事的變局呢?
其實,有些事情與世事變局無關,梁任公有“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難道不應該想到並思考這樣的事情?既然梁任公關切中國在“國族相結相排”的時代如何重構史學和施行新的史學教育,他就應該花費心力深入認識“國族相結相排”的世界歷史。
梁任公沒有看到,所謂“西方”是一個充滿歷史斷裂的文明概念。“西方”與“歐洲”這個希臘人命名的地理名詞一樣,“是個浮動的、可修改的,而且有彈性的概念”——霍布斯鮑姆因此認為:
從來沒有“單一”的歐洲這回事。差異永遠不可能從我們的歷史上消除。事實就是如此,不管是將歐洲換上宗教的外衣還是地理的外衣,都不會有所不同。……基督教是歐洲史上不可磨滅的一部分,但是,它就像“民族”及“社會主義”一樣,都不可能成為統一歐陸的力量。[57]
對比半個多世紀前(1928)施米特的説法,我們一定會覺得深有啓發:
“歐洲”這個詞在今天更是一個難以清晰可辨的觀念。在關於歐洲的不同設想和概念中,即便確定一個令人信服的地理範圍也是困難的。英國屬於歐洲,還是它與其自治領域和殖民地構成一個封閉性的帝國?這個帝國與歐洲大陸建立聯繫既是可能的,也是有害的。西班牙屬於歐洲嗎?它與拉丁美洲國家的聯繫比與德國和斯堪的那維亞國家的聯繫不是更密切嗎?俄國屬於歐洲嗎?設想在斯拉夫民族的主要國家與西方斯拉夫人之間存在着一個差別是正確的嗎?法國應該與它的全部殖民地和整個軍事力量一起參與進來嗎?這就是説,它應承擔軍事和政治的統治嗎?德國由於它日益增長的債務不是更加依賴美國而不是它敵對的或者持不信任的鄰國嗎?最終,整個歐洲問題只歸結為德法諒解?甚至只歸結建立一個包括德國西部、法國北部和東部、比利時和盧森堡的經濟綜合體?所有這些問題都尚未解決。[58]
羅馬帝國曾不可一世,但帝國東西分治後,兩個羅馬帝國相互拆台,隨之先後被由東向西入侵的兩家蠻族顛覆。東羅馬帝國被突厥人的政治單位更替後,如今除了剩下所謂的物質文化遺產,就是地緣政治學上的破碎地帶。[59]
西羅馬帝國則比較幸運:由於入侵的蠻族在1492年後承繼了其“文化武力”,以至於迄今仍然可以見到西羅馬帝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梁任公已經看到:
羅馬位於古代史與近世史之過渡時代,而為其津樑。其武力既能揮斥八極,建設波斯以來夢想不及之絕大帝國,而其立法的智識,權利的思想,實為古代文明國所莫能及。集無量異種之民族,置之中央集權制度之下,為一定之法律以部勒之。故自羅馬建國以後,而前此之舊民族,皆同化於羅馬,如蜾蠃之與螟蛉。自羅馬解紐以後,而後此之新民族皆賦形於羅馬,如大河之播九派。(《新史學》,頁21 - 22)
即便在今天看來,我們還不能説梁任公的“世界史觀察”錯了。1854年初秋(9月),蘭克應邀為巴伐利亞國王講世界史,他開場就説:
為避免在歷史中迷失方向,我們將從羅馬時代講起,因為這個時代匯聚了極為不同的重要因素。[60]
哪個“羅馬時代”?羅馬城邦崛起時,憑靠“拉丁同盟”形成的“國力”與迦太基城邦爭奪伊比利亞半島和西地中海的控制權,曾險些遭遇覆亡;隨後的地緣擴張節節勝利之時,羅馬城卻又陷入共和政制危機。若非“天降大人”屋大維(公元前63 - 公元14)花費20年時間完成從共和向帝制轉型,世界史上是否有“羅馬時代”還真難説。[61]
“羅馬時代”到來之時,羅馬人如何看待此前的“希臘化時代”呢?
拉丁語詩人維吉爾(公元前70 – 前19)生活在“羅馬時代”來臨之時,他經歷過愷撒(公元前102 - 前44)的改制和隨後屋大維創立帝制,可謂生逢其時。然而,《埃涅阿斯紀》把羅馬的崛起與荷馬筆下的特洛伊神話粘在一起,用埃涅阿斯取代奧德修斯,無異於刪除古希臘的文明“霸權”,打造出新的帝國神話。[62]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提醒我們:
維吉爾是外省人,而不是羅馬人;就算對他而言,羅馬城邦畢竟有意義,意義也不大。在他的史詩裏,作為共和時代歷史的行動者的羅馬人民不具有任何作用。《埃涅阿斯紀》不是作為城邦的羅馬及其人民的史詩,而是作為帝國秩序之工具的羅馬和執掌這個工具的皇帝的史詩;《埃涅阿斯紀》製造的不是一國人民的神話,而是一個帶來和平黃金時代的救主的神話。[63]
因此,《埃涅阿斯紀》並非是羅馬城邦英雄的史詩,而新的“羅馬帝國”想象,這個正在興起的“無限帝國”(imperium sine fine)有權接過從亞歷山大身上滑落的希臘人的天命。維吉爾釜底抽薪,通過改寫荷馬筆下的特洛伊故事,用羅馬人的經歷覆蓋希臘人的經歷,在沃格林看來,體現了拉丁民族對希臘民族的“深切妒恨”。甚至在西塞羅這樣的崇尚希臘文明的羅馬政治家身上,“對高級的希臘文明的歆慕與蠻族的驕傲和妒恨”也交織在一起(同上書,頁167)。
在後來的諸多歐洲帝國身上,我們不是也可以看到這樣的愛恨交加嗎?
儘管如此,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實現了一種偉大的文明綜合:讓野蠻的拉丁人穿上高度發達的希臘文明傳統的外衣,希臘和羅馬由此疊合為一個統一的文明政治單位。
另一方面,並非所有被羅馬人征服後的希臘智識人都抱着自己的“高貴文明傳統”不放:羅馬剛剛崛起之時,珀律比俄斯(公元前200 – 前118)就已經對羅馬的“大一統”(μίαν ἀρχὴν)心悦誠服。哈利卡納蘇斯的狄奧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公元前60 – 公元7)是極有學養的希臘人,比維吉爾僅小大約10歲。他在奧古斯都時代低下高傲的頭顱遷居羅馬,不僅花時間學粗糙的拉丁語,還撰寫《羅馬古史紀》(Rōmaikē Archaiologia)替羅馬人樹碑立傳。在這位修昔底德傳人筆下,羅馬人的祖先被説成從歐洲遷徙到亞平寧半島的希臘人部落維諾特利亞人(Oenotrians)和卑拉斯哥人(Pelasgians),從而將羅馬人的歷史溯源到了特洛伊戰爭之前。[64]
今天的我們應該意識到: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不是實證史學式的史書,而是動人心魄的詩歌,否則它不會有如此神奇的歷史功效。反過來看,隨着現代實證史學的出現和人類學-考古學的田野發掘進展,尤其是隨着民主化“全球史”學的興起,《埃涅阿斯紀》對西方人的文明政治教育作用難免岌岌可危。
沃格林還提醒我們,被愷撒征服後的高盧人同樣接受了維吉爾的敍事,讓自己的出生與特洛伊神話扯上關係。甚至日耳曼裔的法蘭克人入侵高盧後,也加入維吉爾敍述的特洛伊世系,讓自己變成希臘人的後裔。直到1545年,法蘭西人還用自己的特洛伊出身神話來證明,法蘭西王國的歷史比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的歷史悠久得多,法蘭西國王的地位因此絕不輸給帝國皇帝。[65]
德意志人就不同了,他們有自己的起源神話。畢竟,日耳曼族人不是羅馬人,也不是羅馬人治下的地中海周邊的族裔,而是與羅馬軍團在歐洲東部長期對峙並膠着廝殺的敵對族裔。查理大帝執掌法蘭克王國後東擴,以血腥手段將德意志人併入王國,並共同披上拉丁基督教的衣缽,儘管查理自己本屬德意志族裔。[66]
但是,查理大帝的帝國與亞歷山大的帝國一樣曇花一現,分裂後的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從未成為一箇中央集權式的大一統帝國,日耳曼各部族王國的發展終有一天會挑戰“羅馬帝國”這個俗世的“普遍歷史”的理想標準。[67]“地理大發現”開始以來,隨着日耳曼族的幾個王國成長為爭霸歐洲乃至全球的政治大國,“歐洲人”與希臘羅馬的所謂“文明關係”始終非常曖昧:承繼與背離交織在一起,讓人難以分辨。
意大利人文主義者庇安多(Flavio Biondo,1392 - 1463)史稱最早具有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史學家,他生前出版的著作顯得意在恢復意大利與古羅馬的聯繫。庇安多喜歡在羅馬城轉悠發掘古蹟,他的《修復的羅馬》(De Roma instaurata,1444 - 1448)似乎想要喚起意大利人對羅馬城古貌的記憶,這讓庇安多成了現代考古史學的先驅。《意大利名勝》(Italia Illustrata,1474)考察意大利各地與古羅馬的歷史關係,史稱現代西方歷史地理學的開山之作。[68]與之配套的《獲勝的羅馬》(Romæ Triumphantis,1479)講述羅馬帝國的文官制度和軍事制度,據説透露了庇安多的意大利系列著作的真實意圖:希望意大利能夠成為一個像英格蘭和法蘭西那樣正在走向統一的獨立王國。[69]
庇安多還留下一部遺作《羅馬帝國衰亡以來史》(Historiarum Ab Inclinatione Romanorum Imperii,1483),他離世20年後才由後人整理出版。這部史書記敍的是人們後來所説的“中世紀”時段,即從公元410年羅馬遭哥特人洗劫到1440年的意大利,無意中打造出“中間世紀”這個歷史時段,為隨後出現的古代與現代劃分作了鋪墊。
這部大著才讓人們恍悟到,庇安多著作的真實意圖其實是向羅馬帝國告別。或者説,這位意大利人文主義者身上正在形成民族國家式的世界歷史意識。離庇安多的寫作年代不到半個世紀,為意大利的命運操心的大政治家馬基雅維利(1469 - 1527)就用義疏李維(公元前59 – 公元17)的羅馬史的方式與羅馬告別。他的《李維史論》(1519)看似在通過李維學習羅馬人的政治德性,其實是在依據日耳曼各王國晚近的“相結相排”經驗塑造新的政治德性和新的競爭方式。[70]
如果沒有隨後出現的一場自然知識革命,那麼,馬基雅維利塑造的政治德性和競爭方式還算不上完全是新的,毋寧説,他更多是拋棄了古典的政治德性而已。“優勝劣敗”的政治原則的更新在於競爭“工具”的更新,就此而言,培根(1561-1626)的《新工具》才真正具有劃時代意義。[71]
法蘭西王國崛起之時,心儀商業化生活方式的孟德斯鳩(1689 - 1755)寫了《思索羅馬人的偉大和墮落的諸原因》(1734)。這是一部政治史學式的羅馬簡史,在今天看來,它不僅論證歐洲因英國革命而有了新的政治標本,也為現代之後的“民主化史學”埋下了種子。
“世界公民”的全球史與中國文明史的危機
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1770 - 1787)與孟德斯鳩的“羅馬史”相隔不到半個世紀,它顯得像是為歐洲人心中葆有的對羅馬帝國的“歷史想象”唱的一曲綿長而又哀婉動聽的輓歌,與休謨在此前不久出版的《大不列顛史》(1754 - 1762)放在一起來看,讓人覺得意味深長。用聲譽卓著的古代世界史家鮑爾索克(1936 - )的話來説,它“註定要為古羅馬坍塌的紀念碑灑上幾縷陽光”。
在鮑爾索克看來,從史料角度講,吉本的這部用15年時間寫成的大著並沒有提供任何新東西,而他“處理古代史和中世紀史原材料的方式,很像是一個小説家處理情節線索的方式”。儘管如此,這部輓歌卻養育了19世紀的德意志詩人瓦格納、20世紀的希臘詩人卡瓦菲斯乃至美國劇作家拉爾。換言之,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與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遙相呼應,把分屬不同民族國家的西方詩人的心靈連結在一起。
鮑爾索克還提到,注重掌握史實的羅馬史大師蒙森(1817 - 1903)對吉本崇拜不已,他的《羅馬編年史》第四卷沒有寫完,不是因為沒時間,而是因為他“害怕與吉本競爭”。因為,吉本“站在哲人而非博學家隊列”,而“哲人史學家應該以一種既讓人愉悦又能給人教益的形式呼應時代的需要”。[72]
鮑爾索克的這一説法讓筆者想起,尼采的《悲劇的誕生》(1872)不也是註定要為古希臘廢墟灑上幾縷陽光嗎?德意志人與古希臘有什麼文明血緣上的關係呢?《悲劇的誕生》的寫作明顯具有世界歷史意識,但在20世紀的英國日耳曼學者巴特勒(1885 - 1959)看來,德意志人的古希臘崇拜不過是帝國心態在作祟。[73]
的確,尼采出版《悲劇的誕生》時還不到30歲,一年之前(1871)的元月18日,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在凡爾賽宮加冕為皇帝,德意志帝國宣告成立。正是在這一年,德意志富商、考古學家施利曼(Heinrich Schlieman,1822 - 1890)在土耳其西部的海港城市恰納卡萊(Çanakkale)南面成功發掘出特洛伊遺址,證實了荷馬的記敍不是憑空編造。
施利曼8歲那年(1828),他從父親手上得到一份聖誕禮物:梅尼爾(J. H. Meynier,1764 - 1825)用筆名耶爾(G. L. Jerrer)出版的《給孩子的世界史》(Die Weltgeschichte für Kinder)。這本書在施利曼幼小的心靈裏埋下了尋找特洛伊遺址的願望,而他自己也沒有想到,這一願望居然實現了。不難設想,倘若沒有找到特洛伊遺址,多少文人學士會拿來説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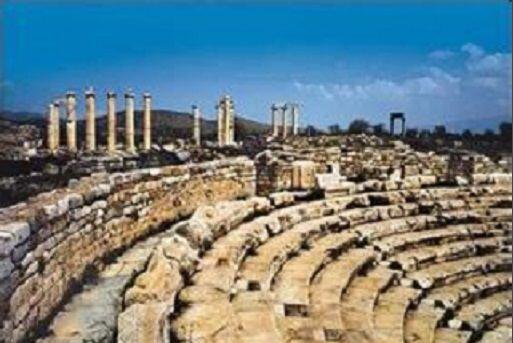
特洛伊遺址
《悲劇的誕生》與施利曼的考古發掘有什麼關聯嗎?當今的西方古典學家告訴我們,“在19世紀為自己創造的關於古代希臘和現代的理想化形象上,施利曼象徵着某種污跡或血跡,模糊了歐洲當時希望用來看待自己的方式”:
施利曼只是佔據了歐洲長期以來關於自己的身份所具有的幻想中的一個預先存在的位置。施利曼大膽地步入斷裂,這是無比勇氣和膽量的一個標誌。但是,創造這一斷裂,這完全不是施利曼的功績:斷裂早已是歐洲幻想的構成要素。[74]
17世紀末,倫敦和巴黎幾乎同時出現激烈的“古今之爭”,“荷馬問題”成為論爭焦點,似乎英法兩個西歐王國的崛起促使某些歐洲智識人不認可古希臘是歐洲文明的地基。畢竟,泛希臘城邦並未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治單位,以至於詩人荷馬的身份也十分模糊。憑靠人類學的史學方法,20世紀的民主化“口傳詩學”派的古典學家們將養育西方靈魂的碧玉打碎成民間歌手口頭創制的碎片,不會讓人感到意外。[75]
如果梁任公知道在他那個時代本來能夠知道的這些事情,他很可能會改變對中國史書的看法。畢竟,在世界歷史中,唯有中國史書和經書具有內在連續性和一元性,即便北方異族曾兩度入主中原並統治整個中國。[76]梁任公萬萬不會想到,在他開啓的“新史學”風氣引領下,説不定中國文人在不久的將來也只能像吉本或尼采那樣為漢唐遺址“灑上幾縷陽光”。
對我國的人文- 政治教育來説,梁啓超的《新史學》發表近115年之際的2016年是個不尋常的年份。因為,在風靡全球的民主化“全球史”風潮裹挾下,史學界在這一年出版了兩部文集,都與古代中國曾遭遇異族統治的歷史時期相關。[77]無獨有偶,台灣學界的《思想》輯刊在這一年也出了一期專號,討論“歷史教科書與國家主義”一類問題。與錢穆(1895 - 1990)在我國“改革開放”那年(1978)所作的著名講演對比,可以説,我國的史學教育已經面臨嚴重危機。[78]
事情原委得追溯到此前的“新清史”風波。據説風波來自美國研究東亞和內亞史的史學家,其中不乏“全球史”學的倡導者。這些史學家“強調清帝國與眾不同的滿洲元素及其獨特性質,傾向於把清王朝描繪為一個有意識的多民族帝國,從早期近代和殖民主義的角度去探索清朝,從邊緣的觀點審視清朝的發展”。中國學者雖然對這樣的史學觀點作出了回應,但“肯定”這一研究取向為清史研究在“方法上注入了新的活力”。於是,在“從周邊看中國”的史學目光帶動下,“中國”的歷史觀念不得不開始“移動和變化”。[79]
人們以為,“新清史”風波是幾個美國的“全球史”學家在1990年代末挑起的。事情恐怕並不那麼簡單,我們不能忘記鄰國日本的“全球史”學家。平野聰的《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2007)基於其博士論文《“皇清的大一統”與西藏問題》(2002),作者並非美國的“全球史”學家的學生,而是日本本土培育出來的史學新秀。
該書憑靠大量文獻史料以敍述史學方式講述了這樣一個新版本的“清帝國”史故事:東北亞梟雄努爾哈赤(1559 - 1626)率領滿洲國人越過長城征服漢人,建立了大清,這個“帝國”的疆域雖然廣大,但它起初並非儒家的“中華文明”的代表,而是藏傳佛教的代表。因為,若不是獲得藏傳佛教支持,大清帝國不可能統治西藏和蒙古。因此,大清帝國不是“中國”,而應稱之為藏傳佛教的“內亞帝國”。
據説,19世紀西方列強抵達東亞後,為了應對西方的挑戰,大清帝國才演化為憑靠經世儒學自救的“近代東亞帝國”。儘管如此,大清帝國仍然不能自救,在清末的混亂中,漢人興起排滿思想,而清帝國也面臨必須轉變為現代“主權國家”的壓力,才最終走向一個叫“中國”的民族國家。
作者的敍事以大明帝國作為歷史背景,從天安門和萬里長城等文明符號開始其歷史敍述。言下之意,就算大明帝國之前有一箇中華帝國,清帝國也中斷了這個帝國傳統。由於清帝國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帝國,所謂“東亞”概念也含混不清。據説,如今東亞國際社會的矛盾和緊張關係,都來自這個叫做“中華帝國”的“混迷”。
關注邊陲政治單位對中心地帶的顛覆,看似所謂“全球史”的史學方法,其實,作者憑靠日本史學界的某種內在傳統也能構造出他所需要的“新清史”敍事。毋寧説,“全球史”學的興起為日本的政治史學家提供了看似整潔的學術外衣。在為中譯本繁體字版寫的長篇序言中,作者刻意説,台灣也很難納入“東亞”概念,因為台灣在歷史上一直具有“邊陲”特性,即“原本就處於馬來 – 玻里尼西亞文化圈的‘邊陲’”。[80]作者心裏當然清楚,他這樣説對今天的“台獨分子”意味着什麼。
1937年,日本軍部曾組織日本東方文化研究所東京分部和京都分部的史學家們編寫過一部《異民族統治中國史》,試圖為日本吞併中國尋找歷史依據。[81]如果我們沒有忘記這件事情,那麼,我們就不難看到,平野聰的“新清史”不過是讓皇軍史觀穿上“全球史”這件新衣。它應該讓我們想起,1939年,日軍進佔武漢和廣州之後,流亡西南的中國學界曾有過一場關於“中華民族是一個嗎”的激烈論爭。[82]一旦國家的“自結”和“主權”岌岌可危,這樣的問題自然而然就會出現。
我們值得注意到,平野聰的這部大著屬於有一百多年曆史的日本講談社組織編寫的“興亡的世界史”系列。這套“世界史”的寫作主旨是:既要擺脱西歐中心論史觀,也要擺脱中國中心論史觀,重新思考世界史的興衰,為日本的出路尋找歷史的內在動能。引進這套“世界史”的台灣八旗文化出版公司則不諱言,其目的是要讓所謂“台灣史”成為一個“全球史”概念,培植“新一代台灣人”產生“渴望融入世界”的願望——“全球史”成了“台獨”政治行動的工具。
康拉德的《全球史是什麼》有兩個中譯本,繁體字版的“中譯本導讀”題為“當代世界公民的全球史閲讀指南”。[83]我們的“全球史”學者看到這樣的標題,他們會認為自己已經是“當代世界公民”了嗎?
偉大的古典紀事作家珀律比俄斯在《羅馬興志》一開始寫到:
不僅就政治事務而言,最真實的教育和訓練是學習歷史,而且就培育高貴地忍受機運之無常的能力而言,最好且唯一的教師就是關於別人命運突轉的記述。[84]
我們不應該忘記,珀律比俄斯是亡國奴:希臘人最終未能“自結”,亞歷山大駕崩之後,帝國內部“相排”讓羅馬人漁翁得利。我們的世界歷史意識應該讓我們珍惜自己的無數先輩給今天帶來的“命運突轉”,並警惕“別人的命運突轉”始終可能落在我們自己頭上。
餘論 “超歷史的”眼光與古典教育
任何一個文明大國的教育都離不了史學,民主化的“全球史”學則讓我們看到,史學也最容易敗壞一個文明大國的教育品質。
在今天看來,梁啓超當年呼喚“新史學”沒有錯,但他忽略了一個根本問題:誰來施行新的歷史教育,史學家應該具備何種精神素養?梁啓超沒有意識到,作為實證學科的西方現代史學讓搞“史”的人以為,他們掌握史料、知道歷史的“真實”就等於有了“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
在《史學對於生活的利弊》中,尼采一再強調的根本論點是:雖然對個人和民族的健康來説,“非歷史與超歷史的東西”和“歷史的東西”同等必要,但相比較而言,“非歷史與超歷史的東西”更為重要。
我們將必須把在一定程度上非歷史地感受的能力視為更重要的和更原初的能力,因為,在這種能力中才有能夠讓某種正當的、健康的和偉大的東西,某種真正人性的東西在它上面才有生長的基礎。(《觀察》,頁142—143)
嚴格來講,尼采這篇時論的標題當讀作“史學對於教育的利弊”。前文提到,尼采的這篇時論寫於普法戰爭結束之後兩年。在普魯士王國及其鐵血宰相俾斯麥(1815 - 1898)帶領下,德意志人顯得相當輕鬆地打贏了這場戰爭,以至於德意志知識人滋生出一種樂觀情緒:德意志帝國的崛起指日可待。[85]在尼采看來,這種情緒是歷史意識短視和膚淺的體現。德意志帝國的崛起更應該體現於德意志人的教化,而非僅僅是一場戰爭的勝負。否則,在下一場戰爭中,德意志人可能會一敗塗地。
可以説,尼采與梁啓超一樣看到,德意志的新生需要新的國民教育,而這種教育離不了史學:
毫無疑問,我們需要史學,但我們需要它,卻不同於知識花園裏那愛挑剔的閒逛者,儘管這種人會驕傲地俯視我們粗卑的、平淡無奇的需求和急迫。也就是説,我們需要史學來生存、來做事,而不是舒適地脱離生活和行動,或者甚至美化自私自利的生活,美化怯懦而醜陋的行動。(《觀察》,前揭,頁133 - 134)
要理解這段話,我們就得知道,尼采是在勸誡布克哈特試圖讓古典史學“非政治化”並轉向文化史學。尼采相信,只有在史學為生活服務這一前提下,人們才應該為從事史學。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了理解“生活和行動”,我們需要史學,但史學能夠理解“生活和行動”嗎?“生活和行動”的根本問題涉及何謂“正義”,史學能夠為我們提供判斷理解“生活和行動”是否正義的標準嗎?
德意志人正在形成統一的民族國家,但有助於德意志人正確理解“生活和行動”的是古典史學,而不是作為一門實證學科的現代史學。古典史學(其代表是修昔底德)通過考察歷史上的事變探究人世的根本問題,旨在培育人的德性品質,而非通過收集具有“客觀性”的歷史材料,尋找所謂歷史的“真實”。
四篇“不合時宜的觀察”分別論及德意志學界當時的神學、史學、哲學和藝術。換言之,這四篇時論都事關德國的人文 – 政治教育,與尼采在此前(1872)所做的“論我們教育機構的未來”的六個公開報告相呼應。神學是拉丁基督教歐洲文教體制中的傳統“王者”,自17世紀以來,新的哲學篡奪了“王者”地位,而19世紀以來,現代史學正在從哲學手中奪取王位。尼采指望通過恢復古典的“藝術感”來阻止現代史學的僭越行動,因此,在《史學對於生活的利弊》中我們看到,尼采大談“藝術感覺”。
第四篇“不合時宜的觀察”專論“藝術感覺”,而我們在開篇卻讀到:
一個事件若要成為偉大,必須匯合兩樣東西:完成者的偉大意識和經歷者的偉大意識。就事件自身而言,無所謂偉大,即便是整個星座消失、各民族毀滅、創立疆域遼闊的國家,爆發巨大力量而又損失慘重的戰爭:凡此種種事件,歷史的微風輕輕吹過,猶如吹過遊絮。然而,碰巧也有這樣的情況:一個強大的人朝一塊堅硬的石頭擊出一拳,卻毫無影響;一聲短暫而尖鋭的迴響之後,一切都過去了。對於這樣一些彷彿沒有稜角的事件,史學幾乎不會注意任何東西。(《觀察》,頁142 - 143)
所謂“完成者”和“經歷者”的“偉大意識”,就是梁任公所説的“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專注於實證史料或史實客觀性的史學不可能培育出這樣的眼光和學識,相反,辨析歷史事件乃至識讀史料,卻需要“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因此,在尼采看來,現代史學的所謂“科學要求”只會敗壞古典史學的品質。
真正的史學教育應該以悉心研讀歷代有“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之人所寫下的作品為前提。史學教育與古典教育在品質上是兩回事:古典教育以研讀經典作品為主。生活經歷本身並不能給人真正的德性教育,必須經過靈魂高貴之人的咀嚼和反哺,對經歷的歷史(敍事)才會成為對生活有益的東西。否則,面對永遠混亂的人世,一個人永遠看不到“智慧以及一切稱之為美的人性”。
讓你們的靈魂飽餐普魯塔克吧!在相信他的英雄們的同時,要敢於相信你們自己。有一百個如此非現代地教育出來的人,即已然成熟、對英雄事蹟已然習慣的人,現在這個時代的整個鬧哄哄的偽教育就會永遠銷聲匿跡。(《觀察》,195)
沃格林是20世紀研究世界歷史與政治實在之關係最有成就的哲人,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説過的一段話讓我們看到,他如何獲得看待世界歷史的“極敏之眼光”和“極高之學識”:
就對人的理解而言,柏拉圖和莎士比亞明顯比雜牌大學的某個瓊斯博士更清晰更全面。因此,研習古典作品是自我教養的主要工具;而且,若一個人帶着愛的關切(with loving care)去研習……他突然會發現他對偉大作品的理解(還有他傳達此種理解的能力)有所長進,理由很充分:學生通過學習過程得到長進……若是在高度(在個人侷限這個範圍內)上不朝最好那個級別的[人物]長進,就不可能有什麼參與;還有,除非一個人認可權威,並向其輸誠(surrenders to it),否則就不可能有什麼長進。(轉引自沃格林,《記憶》,“編者導言”,頁19)
古典史學從不追求所謂客觀的歷史知識,而是培育“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畢竟,正因為人世永遠混亂,我們才需要有把握人世生活的“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尼采稱之為藝術家式的感覺。
誰不曾比[其他]所有人都經歷一些更偉大、更高尚的事情,誰也就不懂得解釋過去的任何偉大和高尚的事情。(《觀察》,194)
不難設想,一旦民主化的“全球史”取得了對中學和大學的歷史教育的領導權,尼采的預言就會應驗。現在我們可以對梁啓超説:離棄經學的史學是無本之木,遲早腐朽斷爛,而經學離棄史學成為理學或心學,則必然因自絕血脈而枯死。
註釋:
[1]參見莫利,《“非歷史的希臘人”:神話、歷史與古代之利用》,彼肖普編,《尼采與古代:尼采對古典傳統的反應和回答》,田立年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31 - 46。
[2]洛維特,《雅各布·布克哈特》,楚人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頁36 – 37,49 - 50;施奈德爾巴赫,《黑格爾之後的歷史哲學:歷史主義問題》,勵潔丹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頁58 - 66。
[3]尼采,《不合時宜的沉思》,李秋零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135。以下簡稱《觀察》,隨文注頁碼。凡有改動,依據《尼采全集》德文版第一卷,參考楊恆達等譯,《尼采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4]August Ludwig von Schlözer,Vorbereitung zur Welt Geschichte für Kinder. Ein Buch für Kinderlehrer,M. Demantowsky / S. Popp校勘箋註本,Göttingen,2011。
[5]科瑟勒克,《“歷史/史學”概念的歷史流變》,劉小楓編,《從普遍歷史到歷史主義》,譚立鑄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7,頁350 - 354。
[6]比較考克斯,《希波戰爭:文明衝突與波斯帝國世界霸權的終結》,劉滿芸譯,北京:華文出版社,2019。
[7]比較阿諾德,《地理大發現》,聞英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龔纓晏,《西方人東來之後:地理大發現後的中西關係史專題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費爾南多-阿梅斯托編,《1492:[現代]世界的開端》,趙俊、李明英譯,北京:東方出版中心,2012;阿布-盧格霍德,《歐洲霸權之前:1250 - 1350年的世界體系》,杜憲兵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本特利,《舊世界的相遇:近代之前的跨文化聯繫與交流》,李大偉、陳冠堃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5。
[8]凡爾納,《地理發現史:偉大的旅行與旅行家的故事》,戈信義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15。
[9]施米特,《中立化與非政治化的時代》,見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劉小楓編,劉宗坤、朱雁冰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頁121。比較赫坦巴哈等,《俄羅斯帝國主義:從伊凡大帝到革命前》,吉林師範大學歷史系翻譯組譯,北京:三聯書店,1978;土肥恆之,《搖擺在歐亞間的沙皇們:俄羅斯羅曼諾夫王朝的大地》,台北:八旗文化出版公司,2018。
[10]比較堀幸雄,《戰前日本國家主義運動史》,熊達雲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0;豪斯霍弗,《太平洋地緣政治》(1925),馬勇、張培均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9。
[11]比較大橋武夫,《戰略與謀略》,古月譯,北京:軍事譯文出版社,1985;井口和起,《日俄戰爭的時代》,何源湖譯,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公司,2012;原田敬一,《日清、日俄戰爭》,徐靜波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6;和田春樹,《日俄戰爭:起源和開戰》,易愛華、張劍譯,北京:三聯書店,2018。
[12]林毅點校,《梁啓超史學論著三種》,香港:香港三聯書店,1980,頁3 – 40(以下隨文注頁碼)。比較米什拉,《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啓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黃中憲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13]比較楊念羣/黃興濤/毛丹編,《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宋學勤,《梁啓超新史學的當代解讀》,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2013。
[14]比較克勞利,《征服者:葡萄牙帝國的崛起》,陸大鵬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
[15]黑格爾,《世界史哲學講演錄》,劉立羣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頁12。
[16]沃格林,《天下時代》,葉穎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8,頁254。
[17]斯科菲爾德,《廊下派的城邦觀》,徐健/劉敏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6;努涅茲,《公元前4至前2世紀出現的普遍歷史寫作》,劉小楓編,《西方古代的天下觀》,北京:華夏出版社,2018,頁167 – 188;比較H.C. Baldry,The Unity of Mankind in Greek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
[18]赫勒敦,《歷史緒論》,李振中譯,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5;比較歐文,《天才的一生:伊本·赫勒敦》,苑默文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8;R. Simon / K. Pogátsa,History as Science and the Patrimonial Empire,Académiai Kiadó,2002。
[19]蘭克,《世界史:從最古老的種族到前現代過渡時期的西方歷史》,陳笑天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7。
[20]肯尼迪,《大國的興衰》(1988),蔣葆英等譯,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西姆斯,《歐洲:1453年以來的爭霸之途》(2011),孟維瞻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21] Friedrich Christoph Schlosser,Geschichte des 18ten Jahrhunderts und des 19ten bis zum Sturz des französischen Kaiserreichs,1836-1848;英譯本: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ill the Overthrow of the French Empire,)
[22]卡普蘭,《即將到來的地緣戰爭:無法迴避的大國衝突及對地理宿命的抗爭》,涵樸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頁9。
[23]帕戈登,《兩個世界的戰爭:2500年來東方與西方的競逐》(2008),宇方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8,頁7 – 8;比較莫里斯,《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麼會落後,西方為什麼能崛起》(2010),錢峯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24]帕克,《城邦:從古希臘到當代》(2004),石衡潭譯,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頁3。
[25]黃克武,《百年以後當思我:梁啓超史學思想的再反省》,見楊念羣等編,《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前揭,頁58 - 59。
[26]霍恩布洛爾,《希臘世界》,趙磊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5,頁50 – 54。比較卡根,《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曾德華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卡根,《伯羅奔尼撒戰爭》,陸大鵬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
[27]卡根,《雅典帝國的覆亡》,李雋暘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頁3 - 5。
[28]莫米利亞諾,《現代史學的古典基礎》,馮潔音譯,北京:三聯書店,2009。
[29]李孝遷編,《史學研究法未刊講義四種》,上海:上海古籍書店,2015,頁258 - 285;比較李孝遷編,《中國現代史學評論》,上海:上海古籍書店,2016。
[30]蘭克,《歷史上的各個時代》,楊培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蘭克,《世界歷史的秘密》,易蘭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蘭克,《拉丁語日耳曼民族史:1494 - 1514》,付欣、劉佳婷、陳潔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蘭克,《近代史家批判》,孫立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蘭克,《德國史稿》,王順君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6。
[31]莫米利亞諾,《19世紀古典學的新路徑》,見劉小楓編,《古典學與現代性》,陳念君、豐衞平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5,頁3 - 44。
[32]比較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四卷),郭方等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3;沃勒斯坦,《變化中的世界體系:論後美國時期的地緣政治與地緣文化》,王逢振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貝克特,《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徐軼傑、楊燕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
[33]考茨基,《唯物主義史觀》(共六分冊),《哲學研究》編輯部編/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 1984;比較庫諾,《馬克思的歷史、社會和國家學説》,袁志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34]劉小楓編,《西方民主與文明危機:施特勞斯讀本》,北京:華夏出版社,2017。
[35]徐中約,《中國近代史:1600 - 2000,中國的奮鬥》,計秋風、朱慶葆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
[36]孫江,《後現代主義、新史學與中國語境》,見楊念羣等編,《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前揭,頁659 - 677。
[37]魯濱孫,《新史學》,齊思和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1989;伊格爾斯,《歐洲史學的新方向》(1975),趙世玲、趙世瑜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勒高夫/諾拉,《新史學》,姚蒙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希梅爾法布,《新舊歷史學》,餘偉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多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鑑》到“新史學”》,馬勝利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38]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晏紹祥、黃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頁xix。
[39]彭剛編,《後現代史學理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帕特納/富特編,《史學理論手冊》,餘偉、何立民譯,上海:格致出版社,2017。
[40]芬利,《古代民主與現代民主》,郭小凌、郭子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比較阿祖萊,《伯利克里:偉人考驗下的雅典民主》,方頌華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5。
[41]比爾德,《羅馬元老院與人民:一部羅馬史》,王晨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8(以下簡稱《一部羅馬史》,隨文注頁碼)。
[42]伯克,《歐洲近代早期的大眾文化》,楊豫、王海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伯克,《法國史學革命:年鑑學派,1929 - 1989》,劉永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伯克,《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與社會》,劉君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伯克,《歐洲文藝復興:中心與邊緣》,劉耀春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伯克,《什麼是文化史》,蔡玉輝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伯克,《歷史學與社會理論》,姚朋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伯克,《文化史的風景》,豐華琴、劉豔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伯克,《法國史學革命:年鑑學派,1929 - 2014》,劉永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43]蔡玉輝,《每況愈下:新文化史學與彼得·伯克研究》,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
[44]布克哈特,《世界歷史沉思錄》,金壽福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199 - 238;伯克,《什麼是文化史》,前揭,頁7 – 16,119 - 120;比較亨特主編,《新文化史》,姜進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岡恩,《歷史學與文化理論》,韓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45]伯克,《文化雜交》,楊元、蔡玉輝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6。
[46]霍布斯鮑姆,《來自底層的史學》,氏著,《論歷史》,黃煜文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頁305 – 324。
[47]比較吉爾伯特,《歷史學:政治還是文化:對蘭克和布克哈特的反思》,劉耀春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48]克萊因,《文明的崩潰:公元前1177年的地中海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頁i。
[49]霍布斯鮑姆,《論敍事體的復興》,見《論歷史》,前揭,頁279 – 290。比較彭剛,《敍事的轉向: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考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2017(增訂版)。
[50]比較伯克,《製造路易十四》,郝名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辛德勇,《製造漢武帝:由漢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資治通鑑>的歷史建構》,北京:三聯書店,2015。
[51]伊格爾斯/王晴佳,《全球史學史:從18世紀至當代》,楊豫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比較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趙軼峯、王晉新等譯,北京:中華書局,2006;柯嬌燕,《什麼是全球史》,劉文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康拉德,《全球史是什麼》,杜憲兵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康拉德,《全球史導論》,陳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52]本德,《萬邦一國:美國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孫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53]比較卡根/奧茲門特/特納,《西方的遺產》,袁永明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卡贊斯坦,《英美文明與其不滿者:超越東西方的文明身份》,王振玲、劉偉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54]布瓊主編,《法蘭西世界史》,張新木主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比較羅格瓦爾,《戰爭的餘燼:法蘭西殖民帝國的滅亡及美國對越南的干預》,詹涓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7。
[55]比較羅特,《古代世界的終結》(1931),王春俠、曹明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塞姆,《羅馬革命》(1939),呂厚量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布蘭特,《古典時代的終結:羅馬帝國晚期的歷史》,周鋭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8;勒特韋克,《羅馬帝國的大戰略:從公元一世紀到三世紀》,時殷弘、惠黎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奧唐奈,《新羅馬帝國衰亡史》(2008),夏洞奇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勒特韋克,《拜占庭帝國大戰略》,陳定定、王悠、李希瑞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8。
[56]卡贊斯坦主編,《中國化與中國的崛起:超越東西方的文明身份》,魏玲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57]霍布斯鮑姆,《耐人尋味的歐洲史》,見氏著,《論歷史》,前揭,頁330 – 333。比較熱爾貝,《歐洲統一的歷史與現實》(1983),丁一凡等譯,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1989;哈貝馬斯等,《舊歐洲新歐洲核心歐洲》,鄧伯宸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施勒格爾,《鐵幕歐洲之新生》(2013),丁娜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
[58]施米特,《論斷與概念》,朱雁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分社),2016,頁115。
[59]希瑟,《羅馬帝國的隕落:一部新的歷史》,向俊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布朗沃斯,《拜占庭帝國:拯救西方文明的東羅馬千年史》,吳斯雅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諾里奇,《拜占庭的新生:從拉丁世界到東方帝國》,李達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8;菲德勒,《幽靈帝國拜占庭:通往君士坦丁堡的傳奇旅程》,洪琛,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9;貝爾福,《奧斯曼帝國六百年:土耳其帝國的興衰》,欒力夫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羅根,《奧斯曼帝國的衰亡:一戰中東,1914 - 1920》,王陽陽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麥克米金,《奧斯曼帝國的終結:戰爭、革命以及現代中東的誕生,1908 - 1923》,姚志宏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60]蘭克,《<世界史上的各個時期>導言》(谷裕譯),見劉小楓編,《歷史主義及其克服》,特洛爾奇等著,陳湛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9。
[61]歐康奈爾,《坎尼的幽靈:漢尼拔與羅馬共和國最黑暗的時刻》,葛曉虎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8;戈茲沃西,《奧古斯都:從革命者到皇帝》,陸大鵬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
[62]阿德勒,《維吉爾的帝國:<埃涅阿斯紀>中的政治思想》,王承教、朱戰煒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2;托爾,《<埃涅阿斯紀>與羅馬的建構》,刊於婁林主編,《羅馬的建國敍述》(“經典與解釋”第54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9。
[63]沃格林,《希臘化、羅馬和早期基督教》,謝華育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182 - 183。
[64]羅布古典叢書中的Earnest Cary譯本共七卷(1936 - 1950);比較E. Gabba,Dionysius and the History of Archaic Rome,Univ. of California Press,1991;C. C. de Jonge / L. H. Richard編,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and Augustan Rom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
[65]沃格林,《希臘化、羅馬和早期基督教》,前揭,頁185 – 186。
[66]沃格林,《中世紀(至阿奎那)》,段保良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39 – 51;P. T. 金,《查理大帝》,張仁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67]盧兆瑜,《三國時代:查理大帝的遺產》,長春:長春出版社,2012。
[68] Biondo Flavio,Italy Illuminated(拉丁文 – 英文),Jeffrey A. White 編/譯,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比較伯克,《文藝復興時期的歷史意識》,楊賢宗、高細媛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7;頁28 – 30;32 – 35。
[69]Ottavio Clavuot,“Flavio Biondos Italia illustrata. Porträt und historisch-geographische Legitimation der humanistischen Elite Italiens”,J. Helmrath / U. Muhlack / G. Walther編,Diffusion des Humanismus. Studien zur nationalen Geschichtsschreibung europäischer Humanisten,Göttingen,2002,S. 55 – 76.
[70]曼斯費爾德,《新的方式與制度:馬基雅維利的<論李維>研究》,賀志剛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
[71]魏因伯格,《科學、信仰與政治:培根與現代世界的烏托邦根源》,張新樟譯,北京:三聯書店,2008。
[72]鮑爾索克,《吉本的歷史想象》,見氏著,《從吉本到奧登》,前揭,頁3 - 10。
[73]巴特勒,《古希臘人對德國的暴政》,林國榮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7;比較湯因比,《希臘精神:一部文明史》(1959),喬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歐洲自我意識的轉折點,17至18世紀》,劉瑞洪譯,廣州:花城出版社,2012。
[74]波特,《尼采、荷馬與古典傳統》,彼肖特,《尼采與古代》,前揭,頁29 - 30。
[75]陳斯一,《再論“荷馬問題”中的口頭與書面之爭》,刊於《古典學研究》(第二輯:荷馬的闡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頁1 - 19。
[76]周春健,《元代四書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周春健,《宋元明清四書學編年》,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2。
[77]葛兆光等,《殊方未遠:古代中國的疆域、民族與認同》,北京:中華書局,2016;張志強主編,《重新講述蒙元史》,北京:三聯書店,2016;比較王晴佳/李隆國主編,《斷裂與轉型:帝國之後的歐亞歷史與史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78]王曉漁,《歷史教科書與國家主義》,刊於《思想》(第31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錢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
[79]劉鳳雲、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2;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葛兆光,《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有關“中國”與“外圍”概念的再澄清》,香港:香港中文出版社,2017。
[80]平野聰,《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帝國的遺產》,林琪禎譯,台北:八旗文化出版公司,2018,頁43;比較張昆將,《東亞視域中的“中華”意識》,台北:台大人社高研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2017。
[81]日本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統治中國史》(1943),韓潤棠、張廷蘭、王維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82]馬戎編,《“中華民族是一個”:圍繞1939年這一議題的大討論》,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
[83]康拉德,《全球史的再思考》,馮奕達譯,台北:八旗文化出版公司,2016。
[84]珀律比俄斯,《羅馬的興起與天下一統》,劉小楓編,《西方古代的天下觀》,前揭,頁2。
[85]比較施蒂默爾,《德意志帝國:一段尋找自我的國家歷史:1848 - 1918》,李超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諾恩,《俾斯麥:一個普魯士人和他的世紀》,陳曉莉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8;斯特恩,《鐵與金: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王晨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