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裏克·皮耶魯齊 :所有案子在美國司法系統裏都是一場交易,比如我-弗雷德裏克·皮耶魯齊、馬修·阿倫
【5月27日,一名彭博社記者在社交媒體上傳兩張照片稱,華為創始人任正非的辦公桌上,正擺放着一本中文版《美國陷阱》。
在這本書中,法國電力巨頭阿爾斯通前高管皮耶魯齊以身陷囹圄的親身經歷,不僅展現阿爾斯通被美國企業“強制”收購過程,也展現了美國如何利用“長臂管轄”、《反海外腐敗法》等司法武器打擊美國企業商業競爭對手的內幕。
這多少和今天華為面臨的境遇有些相似。而在早些時候,皮耶魯齊在接受新華社的採訪時呼籲:“昨天是阿爾斯通,今天是華為,那麼明天又會是誰?現在是歐洲和中國做出回擊的時候了。”
觀察者網摘編部分內容,與讀者共享。】

《反海外腐敗法》
《反海外腐敗法》這幾個字一直縈繞在我的心間。它們給我帶來了牢獄之災(此後還須繼續服刑4個月),而我對這部法律卻知之甚少。斯坦和莉茲已經給了我一些信息,儘管我一再要求,他們也只給我發了一份非常籠統的文件。克拉拉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美國律所長達800頁的研究文件,其中統計了所有因腐敗而被指控的案件。自從拿到這份文件後,我就一直在仔細研究所有案例,並將它們和我的案子進行對比。在這幾個月,我基本上就只做這一件事,幾乎快成為一名真正的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專家。但是在2013年春天,我還沒有達到專業程度,那時我才剛剛接受美國《反海外腐敗法》的教育。
我發現,這項法律頒佈於1977年著名的水門事件之後。在調查導致理查德•尼克松下台的政治醜聞的過程中,美國司法機關揭露了一個暗地資助和賄賂外國公職人員的龐大體系,涉及400家美國公司。負責調查的美國參議院委員會在調查報告中透露,美國大型軍火公司洛克希德為了向他國出售戰鬥機,其董事會成員已經支付了數千萬美元的賄款給意大利、聯邦德國、荷蘭、日本和沙特阿拉伯的政界人士與企業高管。此外,洛克希德還承認向荷蘭女王朱麗安娜的丈夫貝恩哈德親王支付了超過100萬美元的賄款,以便銷售他們與法國幻影5競爭的F-104戰鬥機。這一家醜外揚之後,作為應對,時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通過立法規定,立即禁止美國公司向“外國公職人員”(包括公務員、政治領導人、受託管理公共事務的人)支付佣金。
這項法律由兩個機構負責執行:在刑事上,由美國司法部控告違犯這項法律的公司和個人;在民事上,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起訴涉嫌篡改賬本(進而誤導投資者)來掩飾行賄的公司。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原則上只會干預在美國證券市場(紐約證券交易所、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
然而,《反海外腐敗法》自從20世紀70年代末生效以來,就一直受到美國主要行業巨擘的質疑。他們認為這項法律可能會使他們在出口市場(如在能源、國防、電信、製藥等領域)處於不利的地位,這或許並非完全沒有道理。
事實上,其他經濟大國,特別是歐洲國家(法國、德國、英國、意大利等)尚未通過類似的法律。相反,這些國家的公司在許多腐敗猖獗的國家繼續求助於中間人服務。一些國家,比如法國政府甚至為公司制定了向財政部申報賄賂款項的制度,以便將這些款項從公司應納税款額中扣除!這項制度在法國一直持續到2000年。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規則。美國政府沒有打壓自己企業的傾向,也不想懲罰美國的出口產業,並沒有大力實施《反海外腐敗法》。1977—2001年,美國司法部只懲罰了21家公司,而且通常都是二線企業。這樣算下來平均每年懲罰的公司還不到一家!
然而,美國僱主協會並不希望這項法律“進入睡眠狀態”。美國的行業巨頭很清楚他們能從這項法律中獲得多少利益。為了達到目的,只需讓他們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對手卷入同一麻煩。1998年,他們終於如願以償:美國國會修改了法律,使其具有域外效力。此後,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同樣適用於外國公司。美國政府自認為有權追訴任何一家公司,只要它用美元計價簽訂合同,或者僅僅通過設在美國的服務器(如谷歌郵箱或微軟郵箱)收發、存儲(甚至只是過境)郵件,這些都被視為國際貿易工具。
這項修正案就是美國人的一個把戲,他們把一項可能削弱自身企業的法律轉變為干涉他國企業、發動經濟戰的神奇工具。美國司法部和證券交易委員會從2000年中期開始不斷地試探這種域外法權的底線。例如,毫不猶豫地審判外國醫生——因為他們被委託從事公共服務,就像審判“公職人員”一樣,從而對國際製藥公司提起訴訟。
企業因違犯美國《反海外腐敗法》而支付的罰款總額在2004年僅為1000萬美元,到2016年則猛增至27億美元。“9•11”事件後頒佈的《美國愛國者法案》使這一大躍進成為可能。該法案賦予美國政府部門可以藉助反恐的名義,大規模地監視外國企業及其員工的權利。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在公共採購合同公開招標的範圍內是完全不適用的。顯然,腐敗的受益者首先是受賄的公務員或者政黨,而不是達伊沙或基地組織。2013年“稜鏡門”醜聞爆出,愛德華•斯諾登揭露了美國的秘密監控計劃。世界各國這才意識到美國的主要數字企業(谷歌、臉書、微軟、雅虎、美國在線和蘋果等)也和美國情報機構分享信息。

美國數字企業和美國情報機構共享數據
這還不是全部。美國政府不僅用違規的手段獲取情報,還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內發動攻勢,督促該組織成員也在國內或區域內進行反腐立法。法國在2000年5月通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頒佈《反腐敗公約》(9月正式生效)。只是這些歐洲國家沒有頒佈域外法律的手段和野心,它們最終都掉進了陷阱。一旦某個國家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經合組織反賄賂公約》,它實際上就授權美國可以起訴該國的企業,而它卻沒辦法使用法律手段報復美國企業!這些事情環環相扣,是一個居心叵測的大陰謀。很多人都被騙了。
我從未想過不應該反腐敗,恰恰相反。比起落進受賄高官、有權勢者或統治家族中有影響力成員的口袋裏,這些鉅額賄賂對貧窮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來説更加有用。是的,腐敗是一種禍害。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01—2002年,有1萬億美元被用於賄賂,佔同時期全球貿易總額的3%。當然,這筆錢本來可以而且應該被用於在很多國家建學校、醫院、診所或大學。當然,我們必須同這種惡行進行鬥爭,但是不應該搞錯鬥爭對象。
首先,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在道德的掩飾下成為一種非同尋常的經濟統治工具。況且,2000—2017年,腐敗是否顯著減少?我們對此嚴重懷疑。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這項法律對美國財政部來説是一件喜事、一座真正的金礦。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罰款總額都不是很高,但自2008年開始呈現爆炸式增長。其中,外國企業的貢獻最大。1977—2014年,只有30%的調查(474項)是針對非美國公司的,但是它們支付的罰款佔總額的67%。在26個超過1億美元的罰單中,有21個涉及非美國公司。包括德國公司西門子(8億美元)、戴姆勒 (1.85億美元),法國公司道達爾(3.98億美元)、德希尼布(3.38億美元)、阿爾卡特(1.38億美元)、法國興業銀行(2.93億美元),意大利公司斯納姆普羅蓋蒂(3.65億美元),瑞士公司泛亞班拿(2.37億美元),英國航空航天系統公司(4億美元),日本公司松下(2.8億美元)、日本日揮株式會社(2.88億美元)。請記住,這張令人印象深刻的“狩獵表”就是仰仗於一項美國法律。
當然,美國公司也是被調查對象,但令我驚訝的是,在實施《反海外腐敗法》的近40年裏,美國司法部從來沒有在石油業巨頭(如埃克森或雪佛龍)或國防業巨頭(如雷神、聯合技術公司、通用動力)的交易中挑出什麼毛病。我們該如何想象,為何這些美國巨擘無須支付鉅額佣金,就能成功簽訂處於高度敏感領域的合同呢?我從事這個行業22年了,我不相信,這的確不可能。
我們必須睜大雙眼看清楚,美國司法部不是獨立的,而是長期處於美國強大的跨國公司的控制之下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後,我還意識到,絕大多數時候,美國司法部都是在美國的大型企業被他國法院起訴之後,才會對它們提起訴訟(萬幸,這一幕還是發生了)。隨後美國收回調查權,讓它們“回家”受審,然後它們就可以為所欲為!
美國哈里伯頓公司的凱洛格•布朗•魯特公司事件就是一個典型例子。20世紀90年代中期,凱洛格•布朗•魯特公司是美國哈里伯頓公司的子公司,當時由未來的美國副總統理查德•切尼領導。該公司和法國德希尼布、日本日揮株式會社,以及丸紅株式會社(即塔拉罕事件中的日本公司)聯盟,為尼日利亞的伯尼島油田提供裝備。為了贏得這個價值20億美元的合同,凱洛格•布朗•魯特公司為賣方聯合體找到一個倫敦律師,通過他向尼日利亞的官員支付1.88億美元賄款。
此案被公開後,被送到了法國一個預審法官的桌上。該法官在2004年5月收審了這個倫敦中間人。美國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啓動調查。最終法國和美國達成一項協議:法國法官放棄追究哈里伯頓公司及其子公司凱洛格•布朗•魯特公司的法律責任,因為美國政府對該案進行過調查。
美國檢察官隨後發現,凱洛格•布朗•魯特公司的董事已經收取了大量回扣,因此不可能不對他們提出指控。但相對於涉案金額,判決實在太輕了。最終,組織支付了1.88億美元的賄款,領取了1000萬美元回扣的凱洛格•布朗•魯特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艾伯特•傑克•斯坦利卻只被判了30個月的監禁。凱洛格•布朗•魯特公司總共被罰5.79億美元,而德希尼布卻是3.38億美元。在一位法國法官揭露的案件中,一個法國公司被判處向美國政府而不是法國政府支付3.38億美元的罰款!這就叫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而我在達成塔拉罕交易的時候只是一名小職員,出現在一份涉案金額比凱洛格•布朗•魯特公司案小得多的項目中,沒有拿一分錢的回扣,卻有可能被判15年有期徒刑,因為柏珂龍(前阿爾斯通首席執行官)從一開始就不想配合美國司法部的調查。這種完全不成比例的處罰是如何變得合理的?我看的資料越多,就越感到沮喪和厭惡。
同樣,我發現在美國司法系統裏,不僅僅是關於我的案子,所有案子都是一場交易。美國司法部一旦懷疑企業行賄,很快就會與涉案企業首席執行官取得聯繫,然後給他提供幾種可能的情況:要麼同意合作,並自證其罪,然後開始漫長的談判(99%的案子都是這種情況);要麼選擇反抗,走訴訟程序(在我研究的幾百個案件中,只有兩例是這種情況);要麼用拖延戰術(就像阿爾斯通案),但要自擔風險。
因此,所有公司都傾向於與美國司法部或證券交易委員會談判,最終達成交易。此外,有誰聽説過阿爾卡特、德希尼布或是道達爾先後簽署過和解協議?
不幸的是,我的案子進展不是這樣的。顯然柏珂龍試圖讓美國司法部相信他進行了內部清理,但他其實是在玩火。於是擁有雄厚實力的“美國聯邦調查局碾壓機”開始啓動了。美國政府其實將反腐敗作為排在打擊販毒之後的國家第二優先任務。有超過600名聯邦官員在執行反腐敗任務,其中有一個特殊小組——國際腐敗組——專門負責調查外國公司。
例如,美國聯邦調查局會毫不遲疑地設計圈套(釣魚執法)使公司上鈎。這種行為在法國是被法律禁止的(除非是為了打擊販毒活動)。同樣,2009年,美國動用了幾名卧底特工(其中一個是法國人保羅•拉圖爾),讓他們假扮成代表加蓬國防部長的中間人。然後,這些假中間人上門向20多家企業推銷,用合同引誘其支付佣金。一切都被記錄在案。
美國人還會招募企業內部人員作為眼線。我這個案子就是這種情況,他們想讓我做線人,幫忙蒐集證據。美國聯邦調查局已經做好準備,打擊目標企業或瓦解棘手的公司。那些試圖抵抗的公司都會遭遇不幸。
雖説如此,就算美國警察是一台殺人機器,但這不妨礙我繼續研究。研究越深入,蒐集的資料越多,我就越覺得我的情況十分特殊。柏珂龍的戰略錯誤讓我進了監獄,即便如此,我所受的處置也是前所未有的,不同於其他任何涉及美國《反海外腐敗法》的案子。
認罪協議
我對法國人克里斯蒂安•薩普斯奇安的案子特別感興趣。他曾是阿爾卡特在拉美地區的副總裁助理。他的案子始於2008年,他的遭遇與我十分相似。在那個案子裏,為了獲取哥斯達黎加的一個合同,他們和法國電信公司在當地的子公司哥斯達黎加電力學院聘請了中間人。
1998年以前,阿爾卡特和阿爾斯通都屬於同一個工業集團。我是從阿爾卡特電纜子公司被調到阿爾斯通的。為此,1990—1992年,我在阿爾及利亞做了16個月的境外國家服務志願者。一直到1998年兩家公司分道揚鑣之前,它們選擇中間人的內部流程幾乎都是一樣的。與阿爾斯通一樣,阿爾卡特支付給中間人的費用都是分期支付的。唯一的不同之處在於,在佛羅里達被逮捕的薩普斯奇安監守自盜,收了30萬美元的回扣。這與我的案子有天壤之別。
但是,我在詳細研究他的刑事案卷的時候,發現他被判處的刑罰比我輕得多:他在承認自己賺了不義之財的情況下,卻只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而我卻可能面臨125年的監禁。我問過斯坦這個問題,“博學”的他給我的解釋是,雖然法律在聯邦一級的實施標準是一樣的,但是在康涅狄格州和佛羅里達州,也就是我和薩普斯奇安分別被起訴的地方,法律實施標準可能存在着細微的差別。他繼續説道:“必須參照的《美國聯邦量刑指南》正是為了糾正這種差異而制定的。”
顯然,他拒絕承認那個案例對我有什麼特殊的參照意義,因為他不打算與美國司法部進行一次真正的角力。面對律師的這種冷漠,我只能去尋求懷亞特看守所的內部資源,求助於最有經驗的傑克——“法國販毒網”的老江湖。
經歷近半個世紀的司法糾紛,以及36年的牢獄生活,我的這位獄友自認為比大多數律師更靠譜,其實他的感覺並非完全錯誤。因為這麼多年來,他所有的申訴狀都是自己寫的,要求他的律師過目之後直接交給法官。
“對那些法官和檢察官,一定要把他們擠到牆角,”他囑咐我,“只要你們簽訂了刑期確定的協議(有約束力的認罪協議),他們就對你無可奈何。你和檢察官在商定刑期的基礎上達成一份協議,你簽字後,沒有人能再給你加刑,就連法官也不行。我希望這就是你的律師和檢察官談判的內容!”
“我什麼都不知道。他們告訴我檢察官提出了6個月的刑期,所以我想應該就是6個月的刑期吧。”
“你不能光想,你必須確定。特別是不要籤沒有寫明刑期的空頭協議,因為之後檢察官可以讓你在量刑的時候吃虧。這些檢察官可以隨便更改刑期……你明白嗎?這就叫給自己挖坑……”
我不會直接告訴他,但我承認,他的想法可能是正確的。我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就是砧板上的魚肉。我的兩個律師在律所執業前都擔任過助理檢察官,他們應該瞭解這種骯髒的手段。為什麼他們沒有和我説清楚認罪協議還有不同的類型呢?如果不是諮詢了傑克,我是無法知道這些的。
第二天,我又打電話給斯坦,問他認罪協議的細節:
“不,不是刑期確定的認罪協議。在康涅狄格州,我們不用這種認罪協議,但我承認,這種協議在很多州都是適用的,特別是在馬薩諸塞州和紐約州。告訴你這些情況的人,他的案子一定是由適用於這種認罪協議的地區管轄的。”
“很明顯,又是一個與我做對的康涅狄格州的特殊之處。那你希望我簽署哪一種認罪協議?”
“空白協議。”
“如果認罪協議上沒有寫明刑期,那我怎麼能確定我最終只會被判6個月?”
“在康涅狄格州,認罪協議的文本內容比較微妙。這裏的司法人員不喜歡受人擺佈。但是大家都相互信任。法官、律師、檢察官,我們都在一起工作幾十年了,沒有人會食言。如果諾維克和我説是6個月,那最後就一定是6個月。相信我,不用擔心。而且我們又有新的麻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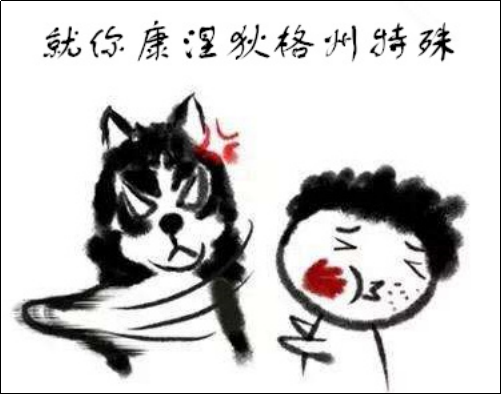
“是嗎?是什麼?”
“你必須承認10項指控中的兩項,而不是原先設想的一項。”
“什麼?但是,一個月前,你不是向我保證他們只會指控我一項罪名嗎?”
“我確實是這麼和諾維克談判的,但是最終做出決定的不是他,而是遠在華盛頓美國司法部的卡恩的上司。”
“但他們為什麼會改變主意呢?”
“他們比較瞭解你和阿爾卡特的薩普斯奇安的案子,大概薩普斯奇安承認了兩項指控。”
“但是薩普斯奇安拿了30萬美元的回扣。這與我的案子毫不相同。斯坦,我覺得無論美國司法部提出什麼要求,你都會説同意,而不是反對。快點去找那些沒有獲取個人利益的員工案例!做好你的工作!”
“我們會的,但恐怕這無濟於事。別忘了,皮耶魯齊,你必須要在彭波尼之前認罪。否則,我們就會完全失去協商的餘地……”
儘管美國司法部的提議非常過分與不合理,我卻只能在接受和拒絕中選擇,沒有爭辯的餘地。我再次面臨無解的兩難困境:是選擇“最糟糕的”,還是選擇有可能“沒那麼糟糕的”;賭注是下在“瘟疫”上,還是下在“霍亂”上。像往常一樣,我又在糾結“或者”“還是”“否則”“要麼”……我列出一堆公式,最後一項可用下面的方法解題:要麼我接受兩項認罪指控,最後可能被判處10年監禁(如果我相信斯坦的話,實際上將只有6個月);要麼我明確拒絕,決定走訴訟程序,但可能被判處15 ~ 19年有期徒刑。
我相信,檢察官會用這個新的下三爛招數同時對付我和阿爾斯通。這對公司高層來説也是一個信號:“看看我們的手段!如果你們不乖乖和我們合作,你們就會像他這麼倒黴!”在這個事件中,我顯然只是一個工具、一個人質、一個因為他人利益而被綁架的囚徒。但在那個時候,我很難看清陰謀的全貌。
無論是真還是假,斯坦和莉茲都透露出一種沮喪。儘管如此,他們仍然極力慫恿我接受協議。於是,瀕臨絕望的我同意承認兩項指控。我真的別無選擇。但在簽訂認罪協議之前,我要求他們把文本發給我。
我在文本里發現,這都是典型美國式的認罪協議條款:我必須承諾,絕不公開改口説自己無罪,我也無權上訴。在撰寫判決書的時候,我也沒有機會提到塔拉罕的事情!我的辯護詞裏只能用個人背景(家庭、教育、宗教……)作為論據。因此,我無法説出我認為的事實真相,也不能闡明我在阿爾斯通公司中的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與其他同案人員相比較,法官如何來評估我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呢?斯坦假惺惺地回答我:“法官最終會拿到檢察官的事實版本。”更奇怪的是,協議中也沒有根據《美國聯邦量刑指南》寫明各項指控並計算對應的量刑幅度。這和我研究過的所有認罪協議剛好相反。當我對此表現出驚訝時,斯坦辯駁説:“這又是康涅狄格州的一種習慣做法,你要麼接受,要麼拒絕!”
最終,我同意了。我還能怎麼做呢?我於2013年7月29日被傳喚前往紐黑文法院,去簽署認罪協議。
聽證會由同一個法官主持,她在3個月前,也就是4月19日,拒絕了我的保釋申請。我已經在看守所被關100天了,這對我來説好像有一個世紀之久。
“弗雷德裏克•皮耶魯齊,”評審團主席馬格里斯説道,“在接受你的認罪協議之前,我想請你宣誓。書記員,請你帶領被告宣誓。”
書記員只是簡單地讓我站起來,舉起右手,聽證會就開始了。
“皮耶魯齊先生,既然你發誓會説真話,那麼如果你做偽證或虛假陳述,你將會被追究法律責任,明白了嗎?”
“明白,法官大人。”
“請説出你的全名、年齡,然後告訴我們你的學歷。”
“弗雷德裏克•邁克爾•皮耶魯齊,45歲,在法國獲得工程學學士學位,還持有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你懂英語嗎?”
“懂。”
“你和你的律師溝通是否有什麼困難?”
“法官大人,我被關在懷亞特看守所,嗯……那裏的情況有點兒複雜……”
沒等我的話説完,我的律師便站起來説道:
“法官大人,皮耶魯齊先生確實受到通話限制,所以我們有時交談不便,但是他和我以及我的同事莉茲就案情進展見過3次面,而且我們現在能夠毫無障礙地和他交談。”
好吧,我明白我來這裏是為了重述我的辯護詞,之前已經跟着斯坦從頭到尾唸了一遍。現在不是抱怨的時候,更不是批評美國司法系統的時候。
“皮耶魯齊先生,”馬格里斯不動聲色地接着斯坦的話説,“你是否在接受藥物治療?”
“是的。我在服用鎮靜劑,這是為了緩解入獄的壓力,也是為了解決失眠問題。”
“這些藥物是否會影響你理解本次聽證會中的辯論內容?”
“不會,法官大人。”
“在過去的48小時內,你有沒有吸食過毒品或攝入酒精?”
“沒有,法官大人。”
“你的律師是否告知過你可能被判的最高刑期,你是否和他討論過這個問題?”
“是的,法官大人。”
“所以你完全理解你將要簽訂的協議?”
“是的,法官大人。”
“你有受到威脅嗎?”
我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有人身威脅嗎?顯然沒有。儘管我被關在一座戒備森嚴的看守所裏,沒法接觸案卷材料,這算威脅嗎?但如果我提到這一點,那我的認罪就是無效的。所以我的回答是否定的。美國的司法正義也得以繼續大行其道。
“皮耶魯齊先生,”馬格里斯一個音節一個音節地強調,“為了確保你能理解所做決定的後果,請你用幾句話向我們總結一下你幹了什麼事情,以及你犯有哪些罪行。”
我們終於説到這裏了。現在我應該給他們表演我和斯坦一起準備的套話。我開始了承認自己罪行的長篇大論:
“法官大人,1999—2006年,我是阿爾斯通集團全球鍋爐銷售部副總裁。當時,我的工作地點是康涅狄格州温莎鎮。2002—2009年,阿爾斯通電力分公司和阿爾斯通其他分公司的員工、我們的合作伙伴日本丸紅株式會社的員工,以及公司的外聘中間人,共同密謀向外國官員行賄,目的是獲得印度尼西亞塔拉罕發電廠項目。我和我的同謀將這些賄賂款偽裝成佣金。我們之間用郵件交流,討論這筆交易的細節。最後,我們成功地拿下了塔拉罕項目的合同。”
“謝謝你,諾維克檢察官對此聲明滿意嗎?”
“非常滿意,法官大人。”諾維克的表演也無懈可擊。
“皮耶魯齊先生,我總結如下:你承認了兩項指控。第一項可判處5年有期徒刑,至多可並處10萬美元罰款。第二項可判處5年有期徒刑,至多可並處25萬美元罰款。根據美國的移民法律,你的認罪協議同樣有法律效力。你知道嗎?”
“是的,法官大人。”
“現在請仔細聽我説,皮耶魯齊先生。你馬上會接受一位緩刑監督官的訊問。他將負責撰寫一份量刑報告。這份報告之後會提交給法庭。然後法庭會根據這份報告給你判處適當的刑罰。你明白了嗎,先生?”
“是的,法官大人。”
“這份報告必須在10月10日之前提交。檢察官必須在10月17日之前對該報告給出答覆意見。法庭將在2013年10月25日開庭,決定你的刑罰。當然,你必須出席本次聽證會。”
“是的,法官大人。”
“好,那麼,聽證會到此結束。祝大家度過愉快的下午,特別是祝大家假期愉快。”
法官大人不是在開玩笑,她説這話的時候一本正經。這幾個日期的描述或多或少與檢察官向斯坦提及的6個月監禁一致,所以這給了我一絲安慰。自由指日可待:10月25日!
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從2013年7月29日開始休假。康涅狄格州的悶熱環境讓人喘不過氣來。把我帶回懷亞特看守所的裝甲囚車變成了一個大火爐。在我身邊,一名年輕的囚犯將臉埋在手心裏。法院剛剛宣讀了他的判決:因販毒被判入獄96個月。雖然我感到越來越熱,但我還是盡力安慰他:“如果你表現良好,你就可以減去15%的刑期,這樣你就可以在35歲的時候出獄。你的人生路還很長,你還有時間組建一個家庭、生孩子、找工作……”我對他説的這段話,其實也是對我自己説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但是在這個悶熱的車廂內,我的話聽起來很無力。在看守所裏被關了這麼長時間後,一名35歲的黑人男子能夠在美國重新開始生活的概率有多大?這個國家應該為他提供什麼?那我呢,這個國家又為我準備了什麼?滾燙的車廂讓人感覺如同身處地獄。我都快熱暈了。
【掃描下方二維碼,六折購買《美國陷阱》。】

【本文為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