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榮、湯禎瀅:從“參議院綜合症”透視美國政黨極化的成因
【文/金燦榮 湯禎瀅】
2018年10月6日,佈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在一片爭議聲中驚險通過了美國參議院的投票表決,成功出任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投票結果顯示,共和黨參議員中除一人棄權、一人缺席外全部投贊成票,而民主黨參議員中除一人外全部投反對票,可謂完全以黨派劃分立場。
這類政黨極化現象在美國日益顯著,政府預算、醫療改革和移民政策等事務常因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分歧而久拖不決由此引發了人們對美國政治制度弊病的思考。有學者認為三權分立體系和議會風格的政黨搭配已經開始呈現根本性“錯配”症狀。也有學者從理論層面反思了美國的民主體制,如弗朗西斯·福山就提出,美國的民主政治(democracy)已經變成了否決政治(vetocracy),由於制衡機制的存在,政治體制的某一個部分能相對輕易地阻撓其他部分,整個體制其實完全受制於否決權。

卡瓦諾在一片爭議中被任命為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圖片來源:網絡)
曾高度自信的美國民主體制未來如何,似乎也只能寄希望於體制的自我糾錯能力。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後,美國政治制度弊病更加公開化,自我墮落式政治行為讓各界大跌眼鏡。那麼,美國民主體制究竟是如何從“別人家的孩子”變成“熊孩子”的呢?根源在哪?它是否有自我拯救的可能?
通過研究,筆者發現美國參議院內部的政黨極化可謂美國政黨極化現象的縮影,美國學者將參議院暴露出來的問題稱為“參議院綜合症”(Senate Syndrome),表現為阻撓與限制模式(pattern of obstruction and restriction),含義是少數派利用審議程序阻撓法案通過,而多數派利用審議程序限制少數派阻礙的力量。
本文通過觀察美國現代“參議院綜合症”的成因,透視了美國政黨極化的根本原因,首先從政治制度和政治過程兩個層面考察了“參議院綜合症”產生的動因,進而對“參議院綜合症”背後政黨極化的兩種表現形式進行了分析,最後基於歷史、制度與政治實踐分析了當代美國政黨極化的成因。由此,本文認為美國體制要自我拯救可謂困難重重,通過制度改革緩解政黨極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參議院綜合症”產生的雙重動因
美國政治學會的施茨奈德將美國政治史比喻為政黨和憲法的不幸婚姻史,是在不可抗之力和不可易之物結合下的神奇變種。
作為立法機構,美國參議院是政治體制內的特例,其特殊性表現在:與眾議院分享立法權力;參議員在規則範圍內擁有極大的自由和權力;多數派需與少數派合作以保證參議院運轉。然而,這種特殊設計使美國政府成為一個脆弱且好內鬥的政治系統。
在新的政治和社會發展階段,現代的美國參議院漸露疲態,最後發展成當下嚴重的立法審議功能障礙,立法效率之低下使現代參議院成為許多重要法案的“墳墓”,而其人事任命功能也成為黨爭和泄憤的工具。
有學者將這種始於21世紀初的現象稱為“參議院綜合症”,在這種模式下,參議院全體辯論與其説是討論和商議的平台,更不如説是多數派和少數派“狹路相逢”對抗決鬥的場所。通過竭澤而漁般地利用參議院的程序,少數派對多數派“圍追堵截”,多數派對少數派“嚴防死守”。
其中,少數派的阻撓形式包括:否決對法案和提名進行投票的一致同意協議(unanimous consent agreements),使法案遲遲不能進入全體辯論環節;頑固抵抗多數派領導人限制辯論和修正案數量的請求;利用“議事阻礙”(filibuster)拖延和阻止投票;指責多數派政黨對立法機制運轉障礙的放任不作為。
多數派的對抗則表現出條件反射式的特徵:頻繁訴諸“結束辯論”(cloture)申請;採取“填樹”戰術(filling the amendment tree)限制少數派提交修正案的機會,終結提交修正案環節;降低會議頻率,避免少數派攪局;利用預算過程迴避“結束辯論”難題;指責少數派的阻撓主義。
其中,由於“議事阻礙”的顯著阻撓效果引發爭議,該規則在奧巴馬時期進行了改革。按參議院早期規定,啓動“結束辯論”程序需要徵得60名參議員的同意。然而,參議院的多數派人數往往達不到60人,因此難以啓動程序。
為此,奧巴馬時期,美國參議院對議事規則進行了改革,針對總統提名的候選人的辯論時間予以壓縮,而涉及總統提名的司法和行政官員候選人的表決,只需要簡單多數同意就可以啓動“結束辯論”程序,從制度上緩解了“議事阻礙”阻撓議事的現象。
早期的參議院遵循的是互惠和禮讓原則,採取了“激勵和約束”的設置(set of 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在歷史上,參議院經歷了多次改革,為了實現合理議事,議事規則開始變得複雜,早期參議院的優良作風也逐漸不復存在。

美國參議院(圖片來源:網絡)
與早期參議院相比,現代參議院擁有了美國政治中的新特徵,這些特徵包括政黨的興起、政黨對於參議員參選重要性的變化、數十年規則制定以及參議員之間非正式慣例的出現等等,參議院議事僵局也正是來源於此,但追根溯源,參議院少數派和多數派的競爭合作模式演化成近乎對抗性的“阻撓與限制”模式,是兩百多年以來政黨聯盟在憲法範圍內圍繞立法程序和政策偏好競爭的結果,而這種結果反過來又影響着政黨聯盟競爭的過程,“參議院綜合症”的惡化過程就是政黨極化發展的過程。概括起來,可從政治制度和政治過程兩層因素分析。
(一)政治制度因素
首先,制憲者們希望參議院的運行比眾議院更加冷靜、系統和智慧,因此在制度設計之初,他們給予了參議院更多的期望和自由。
例如,當選參議員的年齡要求為年滿30歲(比眾議員大),且其所持美國公民身份不少於九年;參議員的任期為六年;各州擁有兩名參議員名額等。這些基本要求保證了參議員見聞廣博和成熟穩重的特質、參議院的穩定性,以及各州的平等性。
而對參議院的演化影響最為深遠的因素在於參議院可自行制定程序規則,這賦予了參議員在全體辯論環節和提交修正案環節極大的自由權力:
其一,參議員可以無限制地進行辯論,除非獲得在場60位參議員的同意啓動“結束辯論”;
其二,參議員可以無限制地針對任何法案提交任何無關的修正案。
這兩項權力讓少數派如虎添翼,在阻撓法案的過程中處於“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地位。其次,如上文所述的“參議院綜合症”,其產生根源正是美國政治體制設計,即“少數人權利與多數決定原則”(Minority Rights,Majority Rule)下的少數派和多數派競爭合作的立法模式,這種設計反映的是美國政治體系的競爭型價值觀:既保護多數派順暢行事的權力,也保護少數派防止多數派獨斷專行的權力,但這種制度設計在美國參眾兩院產生的實際結果卻相反。
在1789年參眾兩院開始運轉之初,制憲者無意偏袒任何一方,當時兩院多數派和少數派的角色和權重相同。時至今日,國會兩院的多數派和少數派權重格局卻截然相反:在多數派統治的眾議院,少數派對國家政策並沒有實質性影響力;而多數派領導的參議院,少數派利用“議事阻礙”等議事程序能實現對多數派議程安排的有力阻撓,從某種程度上看,少數派才是參議院的實際操縱者,這種情況在奧巴馬執政時期尤為凸顯。
美國歷史上共有168次總統人事任命被“阻撓”,其中奧巴馬時期的人事任命被阻撓82次,而之前43位總統的人事任命總共才被阻撓86次。奧巴馬連任後,提名了35名聯邦法官以填補法院系統的法官空缺,卻因為參議院內少數派(共和黨人)的阻撓,遲遲未能進入投票表決階段。其中,凱特琳·哈里根(KathleenKerrigan)在被提名近兩年半後,依舊在等待對其提名進行直接表決的機會。根據統計,奧巴馬總統提名的地區法院法官和上訴法院法官中,等候任命超過百天的比例分別是42%和78%,該數據在布什執政時期只有8%和15%。
簡而言之,憲法中關於參議院內部程序規則的缺失與參議員行使權力的自由相互作用,最後發展到參議員將極端程序進行極端利用。這種制度性因素影響之所以難解,究其原因除了地位崇高的憲法難以改變之外,更具體的原因在於,其一,改變“議事阻礙”規則需要至少67名參議員的同意。然而,任何類似的爭議性議題通常都難以獲取2/3的投票,在政黨日益極化的情況下更是難以實現;其二,多數派和少數派的概念需要放置於具體的時期內和具體的議題上,參議員們深知自己在一定情況下會成為少數派,屆時“議事阻礙”等阻撓性程序將是他們維護自己和政黨利益的強大武器,因此,縱使怨聲頗高,參議員們也無誠意改變規則。
(二)政治過程因素
20世紀50年代之前,參議院屬於安分守己的內斂型機構,與媒體絕緣,影響力主要集中於委員會的資深領導者。參議員們遵循着互惠制度(system of reciprocity)和排資論輩制度(seniority system),面對手中握有的權力“克己復禮”。由於當時的參議員在進入各委員會之前已經是某領域的專家,因此關於法案的討論通常在委員會內部即可塵埃落定,無須召集全體辯論。
這種情況在20世紀中期以後發生了改變,原因有二:
一是個人主義的發展。20世紀60年代,在國內社會運動和國際局勢的刺激下,利益集團數目猛增且種類繁多,為了爭取利益和話語權,利益集團需在參議院內部培植自己的代言人;同時隨着電視的普及,媒體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專業性和資歷不再是參議員獲取影響力的唯一途徑。為了藉助媒體資源達成選舉和政策等目標,參議員在參議院全體辯論和提交修正案環節變得日益活躍。參議員們的注意力開始集中在處理與利益集團、政策團體和媒體的關係上,參議院逐漸成為向外型機構,直至20世紀70年代中期,個人主義參議院最終成型。

電視的普及改變了美國的政治生態(圖片來源:網絡)
二是黨派極化的興起。20世紀80年代末,政策和利益訴求的個人主義化導致黨派重組,進而使參議院開始出現黨派和意識形態極化趨勢,參議員們依據自身黨派和意識形態站隊,共和黨和民主黨內部同質程度日益加深。1989年,紐特·金裏奇成為國會保守派共和黨領袖,正式拉開了由眾議院蔓延至參議院的黨派極化帷幕。日益壯大且意識形態不一的兩黨影響着參議員的提名,而參議員在參議院內外的黨派性言行又推動了大眾兩極化,温和派候選人難以在選舉中脱穎而出,這反過來又惡化了兩黨的競爭,進一步加劇了政黨極化現象。
“參議院綜合症”背後的政黨極化:兩種表現形式
靜態的制度性因素是導致參議院議事僵局的基礎性因素,而參議員為了自身利益和黨派利益,需要結成同盟,由此自然會出現意識形態極化和黨派鬥爭。政黨極化正是意識形態極化和黨派鬥爭加劇的結果,是兩黨謀求各自利益的需要,所以通過分析政黨極化研究參議院議事僵局更具現實意義。其中,政黨極化有兩種表現形式,即意識形態和政黨競爭。
(一)意識形態極化
在參議院內部,政黨的意識形態極化體現在具體國內議題上,如社會福利、種族問題和文化問題等,表現為共和黨人愈是趨向保守,兩黨的意識形態愈發相去甚遠。這種差異始於20世紀60年代,共和黨在種族問題上日漸保守,80年代和90年代共和黨開始在文化問題上呈現保守趨勢,最後政黨極化呈現的是兩派對壘的意識形態分歧,即以共和黨為首的保守派和以民主黨為代表的自由派。
政黨的意識形態後天差異是政黨和意識形態經過長期自我優化組合、各取所需的結果。意識形態和政黨形成的完美組合會產生互為強化的效果,其路徑有三種:其一,一致的意識形態能改變政治積極分子對政黨施壓的方式;其二,一致的意識形態有助於政治家選擇正確的政黨;其三,清晰的政黨差異有助於將意識形態傳輸給大眾。
換言之,意識形態極化既有助於強化共和黨和民主黨對自身的領導,又有助於兩黨吸收相同利益訴求的政治家、爭取更廣泛的民意基礎以贏得選舉。
實際上,政黨是利益的結盟,意識形態將政黨的利益訴求變為顯性可識別的特徵,即政黨的意義是表明誰和誰是盟友,而意識形態的意義是表明政黨要維護哪個羣體。選民根據政黨的意識形態判斷政黨所代表的利益羣體,通過黨派選擇的過程,使具有相同意識形態的政治家進入國會;同時,當選的議員們會將鮮明的意識形態貫徹到底以期獲得連任。
這種雙向互動使得温和派的參選人難以被選民識別而無法進入參議院,從而逐步強化了參議院內意識形態極化的過程。因此,縱使打破參議院的立法僵局需要温和派的存在,但事實是温和派已經成為“瀕危物種”,美國人高喊結束這種極化現象,但在現有的投票體制下卻根本沒有可能,這就如好萊塢的電影,大家都認為需要減少暴力和色情畫面,這兩者卻正是好萊塢電影賣座的原因。
(二)政黨競爭加劇
參議院的議事主題廣泛並非所有的事務都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差別,例如,與國內議題相比,涉及國家安全和外交議題的意識形態分歧則較弱。然而,議題性質的差異依舊不足以緩和參議院內政黨極化的趨勢和程度,這是由於參議院內部還存在“制度權力的絕對競爭”,這造就了多數派的“不安全感”和少數派的“盼頭”。
國家政治機構內部的制度權力競爭是現代美國政治的顯著特徵之一,參議院則是政黨權力競爭的核心陣地。很長一段時期內,民主黨被理所當然地視為參議院多數派,因為在1932年至1980年期間,除了第80屆國會和第83屆國會,民主黨一直牢牢佔據着參議院多數派的位置。由於多數派政黨地位穩固,少數派政黨只能安分蟄伏,參議員們在立法過程中也無須格外固守其政黨立場,更多的是根據議題本身就事論事,這種穩定局面削弱了政黨間的競爭意識,淡化了政黨競爭的氛圍,進而減少了政黨極化的可能性。
然而,共和黨在1980年選舉中的超預期表現,開啓了參議院多數派權力“流轉”的時代。1980年至2018年參議院的多數派控制權七次轉手,其中共和黨掌權了十屆國會,民主黨則掌權了九屆國會。作為競爭性政黨體系重要特徵的“不安全感”會促使政黨全力以赴壯大政黨力量。
因此,不管是為了自身的職業生涯還是出於對黨的忠誠,在分庭抗禮的不確定局面下,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通常將各自的黨內分歧擱置一邊,調動和團結一切資源保護政黨的席位、搶佔參議院多數派控制權,因此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在參議院的行為方式逐漸趨向涇渭分明的黨派路線。由於權力的歸屬不確定,多數派充分利用現有的控制權擴大與少數派的差異,達到鞏固權力的目的。而少數派不再願意妥協,成為多數派的“盼頭”讓他們希望等到重掌權力時,讓自己青睞的法案或人事任命通過。
例如,2016年2月,為了佔據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席位,共和黨一直擱置奧巴馬提名的温和派大法官梅里克·加蘭德的任命直至總統選舉結束。共和黨聲稱要將該人事任命留給下任總統決定,其實是希望特朗普當選後提名任命保守派大法官。
總而言之,因為參議院本身最初的制度設計過於寬鬆,使參議院在規則趨穩且政治環境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進行規則改革變得十分困難。更重要的是,在參議院的制度特徵和政治生態環境的影響下,政黨極化在參議院內部肆意發展而未能得到遏制,最終將枱面下的政見分歧演變成了枱面上你爭我奪的政治博弈。
也就是説,憲法賦予參議院較為自由的規則選擇權,其實就是賦予了參議院產生“綜合症”的基因,這種基因以政黨極化的形式在參議院生根發芽直到最後形成“參議院綜合症”的“惡果”,“參議院綜合症”實質上就是政黨極化的結果。
當代美國政黨極化的成因:基於制度與實踐的分析
將政黨極化置於美國曆史的大背景下看,它只是美國社會的一種常態,國會內的政黨極化始終是美國政治史的主題之一。
美國斯坦福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戴維·布雷迪通過比較歷史上政黨中位數差異後認為,目前的政黨極化只是歷史的再次重現而已,如政黨中位數差異在1895年達到高峯後驟降,在20世紀50年代前後降至最低。
參議院制度是美國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集中體現了其政治體制的優勢和問題,是透視美國政治制度特點和政治實踐過程的重要着眼點。上文從政治制度和政治過程層面,論證了參議院內部出現議事僵局的原因,揭示了議事僵局背後的政黨極化。依此邏輯,下文將從靜態的政治制度和動態的政治過程角度分析當代美國政黨極化的成因。
首先,美國政黨隨着憲制政府的建立而產生,政黨的發展受到憲法制度的制約,因此美國的政黨極化實際上植根於憲法制度。而在以社會契約精神平地建國的美國,政黨極化現象的起伏其實是圍繞如何解讀社會契約的鬥爭;
其次,美國兩黨為了使自己的政治學説在政府政策中體現出來、用選舉成員擔任公職的方式來謀求政治權力,但在政治活動的實踐過程中,個人主義催生的黨派主義使政治精英醉心於追求個人影響力和政黨利益,普通大眾沉迷於政治精英制造的輿論,其結果就是精英極化和大眾意識形態兩極化的出現,反過來又進一步強化了政黨極化現象。
(一)政黨極化的制度根源——憲法和社會契約
1.源於憲法的極化“基因”。
美國的政黨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政黨制度被稱為美國的“第二憲法”。憲法對政黨制度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一人行政負責制促成了兩黨制的持續且不利於小黨的生存;
二是“贏者通吃”的選舉制促成大黨興旺小黨凋敝的現象;
三是聯邦制將美國政府劃分為聯邦和州兩級,造成了美國兩黨制的多中心狀態;
四是行政立法分權製造成總統和國會多數黨分屬兩黨的現象,降低了政府內政黨的凝聚力且增加了議事僵局,促進了美國政黨無責任制的狀況。
美國學者丹·伍德和蘇林·喬丹認為,制憲者們設計憲法的初衷就是維持極化體系。制憲者們害怕和憎恨民主,無意於建立一個可以解決黨派鬥爭的體系,於是他們制定了一套旨在預防民眾治理的機構,將權貴階級的利益制度化的同時,提高改變制度的難度,保證政治衝突的永久性存在,這也就使美國政治具有先天的極化“基因”。這種設計的效果不負眾望地貫穿於美國曆史,美利堅合眾國初期時圍繞聯邦主義和19世紀50年代圍繞奴隸制問題的戰爭就是黨派衝突的結果。

美國南北戰爭(圖片來源:網絡)
建國時期,聯邦黨為權貴階級爭取利益,而反聯邦黨/民主共和黨則尋求消除權貴階級優勢和自身階級優勢;
進步時期,“頑固保守派”共和黨試圖為權貴階級保持優勢,而民粹主義民主黨則試圖消除這些優勢以更廣泛地擴大政府的利益;
20世紀80年代以後,民主黨試圖維持在新政/偉大社會中平民階級擁有的優勢,而共和黨試圖消除這些優勢,並且採取更嚴格的政府福利分配。源於憲法的極化“基因”使美國政治順理成章地出現兩極分化現象,政治僵局也日益成為常態,參議院則是這種設計的典型縮影。
制憲者們有意建立一個能夠保護少數人利益的體系,卻無意於建立一個解決衝突的體系。“少數人權力和多數決定原則”與參議院自行制定規則的權力相結合,既保證了少數派為自身利益進行鬥爭的權利,又保證了多數派維護自身利益的權力。當多數派和少數派的力量旗鼓相當之時,政治僵局則應運而生。
2.基於社會契約的階級鬥爭。
貫穿美國曆史的政黨極化實際上是圍繞“誰受益和誰買單”的經濟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源於對美國社會契約的兩種解讀,即制憲者社會契約和新政社會契約。尤其在20世紀,美國極化現象的軌跡與民眾最低收入的演化軌跡一致。
作為美國政治常態的政黨極化在歷史上有三個高峯期:建國時期、進步時代和20世紀80年代至今。在建國時期,雖然沒有政黨,但是基於階級差異的兩極分化已經存在。權貴階級與平民階級形成對抗,最終按照權貴階級的意願建立了美國政府,例如由於普選的州政府不易掌控,因此富裕階級通過強化聯邦權力,弱化州的權力,尤其是有關經濟事務的權力來限制平民階層的制度挑戰力量,這種設計的結果就是在聯邦政府內實施阻撓比採取行動更有效。
早期憲法中,制憲者社會契約將權貴階級置於具有絕對經濟優勢的地位,其中包括低税、貨幣穩定、低息借款和聯邦法規的自主權等,此時的權貴階級仍然掌握着國會和法院的主導權,因此1789年至1932年,美國政治極化的結果仍然是維持制憲者制定的社會契約。
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促使人們反思權貴階級手中擁有的優勢是否合理,關於美國的社會契約產生了新的解讀。根據新政社會契約,向富人收更高的税、降低關税、降低信用工具的價值、提高監管、增加政府幹預等手段使平民階級獲益。20世紀60年代,偉大社會計劃強化了平民階級的利益,削弱了權貴階級的優勢。
1933年至20世紀70年代末,共和黨處於絕對主導地位,致力於挑戰新政社會契約,試圖恢復制憲者社會契約以獲取權貴階級優勢。因此,20世紀80年代至今,美國的政治鬥爭引發的政黨極化的實質是兩大階級圍繞新政社會契約的鬥爭。參議院多數派和少數派代表了各自不同的選民羣體和階級利益,圍繞着不同法案和政策發生的鬥爭僵局,正是因為既得利益者拒絕改變對社會契約的解讀,而對立階級努力改變當下社會契約解讀的對抗過程。
(二)政黨極化的政治過程——精英和大眾
孕育政黨極化的制度條件是選舉制度和兩黨制度,而造成政黨極化的直接行為主體則是精英和大眾。
首先,以選舉勝利為導向的政黨精英通過選擇偏離中間路線的極化政綱,驅動政黨極化過程。美國歷史上高度極化時期的顯著特徵之一就是政黨領袖為了黨派目的而鬥爭。在建國時代,麥迪遜和傑斐遜與漢密爾頓抗爭引發了聯邦主義運動;在進步時代,威廉·詹寧斯·布萊恩和伍德羅·威爾遜等政黨領袖煽動民主黨的民粹主義熱情;20世紀80年代以後,保羅·韋裏希,羅納德·里根和紐特·金裏奇等政黨領袖狡猾地恢復了權貴階級的優勢。
政黨極化是各政黨獲取優勢的戰略手段,也是戰略結果。政黨極化的原始動力在於增強黨派影響力,這依賴於美國以州和國會選區為地理空間單位的選舉制度。這意味着,以選舉勝利為導向的政黨精英們需要同時在多個不同區域競爭,為此他們必須選擇不同於中間投票人理想政策的政綱才能脱穎而出。
中間選民定理認為所有選民的選擇偏好都可以在座標平面上找到對應的一點,這樣的政策偏好圖呈現在座標平面上是一個正態分佈的鐘形曲線,所有的選民都只會將他手中的選票投給所提政綱與自己的政策偏好最接近的候選人,因此形成的是單峯偏好而非雙峯偏好。
然而,該定理卻與實際選舉情況不符。在單區和多區環境中,參選政黨的行為風格取決於平衡競爭目標的需要,兩大政黨必須確保與對方爭取選民投票的同時,阻擋其他潛在政黨的崛起,即實現迎合選民和進入威懾的雙重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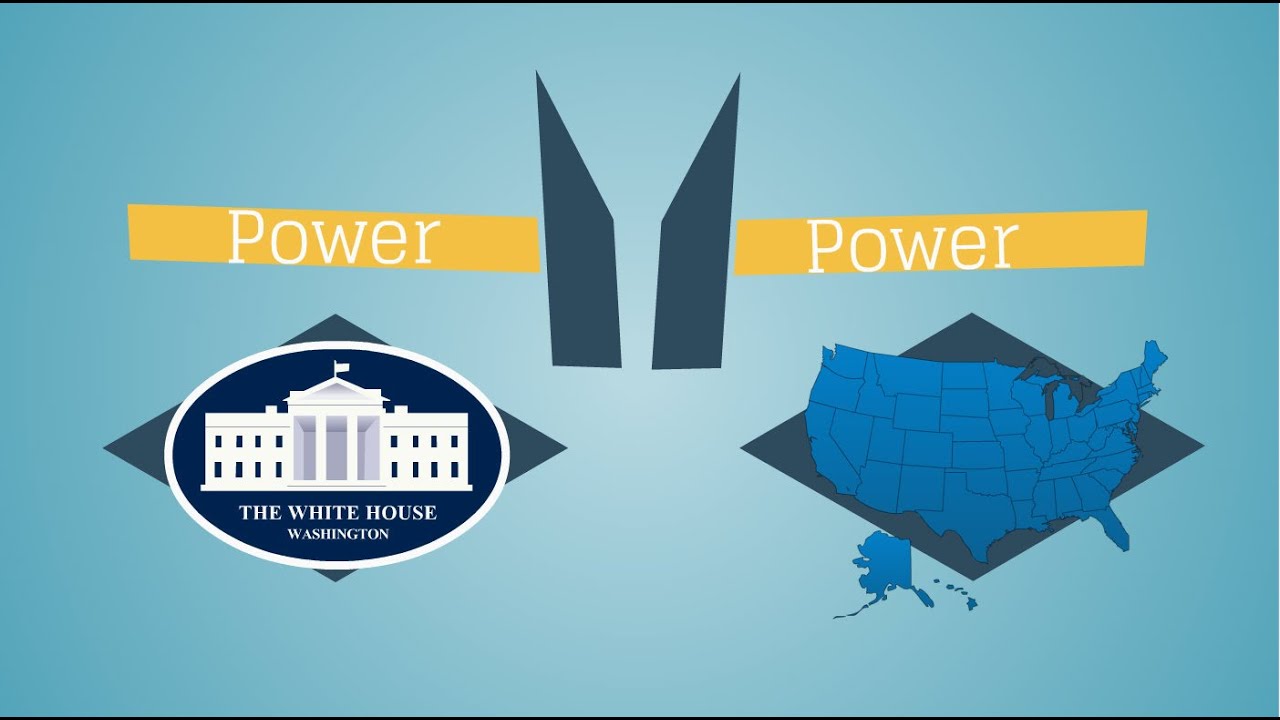
“聯邦主義”示意圖(圖片來源:網絡)
斯坦福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史蒂文·卡蘭德認為如果兩大黨僅在單個地區競選,那麼兩大黨可以通過爭取中間選民以贏得選舉,而且無需擔心其他政黨會趁機崛起。然而兩大黨的競爭範圍不僅侷限於一城一池,而是全國範圍不同區域。在多個區域競爭的情況下,為了維持兩大黨主導競選的平衡局面且保證其中一黨能贏得選舉,雙方都需要對稱地偏離中間路線,選擇非中間政策立場。簡而言之,共和黨和民主黨不僅要竭盡全力贏得全國性選舉,還要穩定兩黨主導競選的局面,防止新的競爭力量出現。為此,共和黨和民主黨只能分別提出有別於對方的分歧性政綱,極化現象則應運而生。
其次,精英通過“自上而下”的影響,為大眾提供極化的意識形態和選擇,這種政治環境與現代媒體相配合使大眾的選擇“非此即彼”,進一步強化了政黨極化現象。通過強化意識形態色彩以突出政黨特色,利用媒體報道以引導公共輿論的討論方向,政黨精英促使民意兩極化,為政黨極化創造了大眾基礎。
大眾中的温和派別無選擇,只能通過對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領袖和政策主張等方面的比較,為手中持有的選票勉強找到“歸宿”。例如,在2018年的調查中,44%的中立者雖然選擇傾向於共和黨,但因為對共和黨領袖感到失望而拒絕加入共和黨;58%的中立者傾向於共和黨,不是因為認為共和黨的政策好,而是因為民主黨的政策更糟糕(見下頁表)。這種“矮子裏拔高個”特徵在希拉里和特朗普競選過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實際上,精英極化不是簡單地創造了一個極化的政治環境而已,而是深刻地塑造了大眾的推理過程和政策態度,因為極化的政治環境從根本上影響了大眾做決定的方式,增強了政黨所持意見的影響力,降低了實質信息的影響力。為了強化大眾參與黨派驅動性推理,精英極化採取更加清晰的政策信號和更加突出的政黨身份特徵,而進行黨派驅動推理的民眾則會主動尋找支持其政黨政策的信息,反駁挑戰其政黨地位的信息。
在這個過程中,現代的媒體則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發表極端化言論,雖然讓其反對者深惡痛絕,但卻牢牢地吸引了其支持者。除此之外,媒體報道將政黨的分歧塑造成政黨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而非戰略動機的分歧。雖然媒體的報道為大眾提供了公平審視兩黨的平台,但由於大眾緊密聚集於單一新聞來源,對報道的選擇性閲讀使大眾的意識形態傾向難以被説服,政黨極化因此在大眾中得到了持續性的動力,例如,47%的受訪者引用福克斯新聞作為其政府和政治新聞的主要來源,遠遠超過調查中的任何其他羣體。
總之,政黨極化現象是美國政治歷史上的常態,這種常態源於美國至高無上的憲法,根植於貫穿於歷史的階級鬥爭。在個人主義和現代媒體的催化下,始於精英的極化現象擴散至大眾層面,反過來又增強了精英極化的羣眾基礎,政黨極化就是在如此的循環之下演化至今。需要説明的是,政治極化並不必然引發政黨極化,例如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美國國內的人權運動和國際上的越南戰爭,使美國人在許多議題上陷入極化,但沒有造成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明顯分歧。
結語
極化是美國政治系統內的常態,其程度的高低取決於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狀況,當極化到一定程度時,兩極中的某一極的勢力會必然衰弱,整體極化趨勢會自然而然地跌入低谷。而政黨極化是一種自上而下、精英驅使的過程,普通民眾作為回應精英極化的一方對極化的趨勢走向影響較小。
如美國政治學家莫里斯·菲奧瑞納認為,真正極化了的是政治精英與少數政黨活動家,有黨派歸屬的美國人現在更有可能附屬於他們認為“正確的”政黨。而總統作為精英的代表,既是極化的受害者,也是極化的始作俑者,甚至經常是政治極化的焦點,特朗普就是典型代表。
政黨極化是美國歷史上階級鬥爭的結果,是在不同歷史階段程度不同的一種政治常態。從建國時期至今,美國兩大政黨與各自階級一直站成一隊。
一個政黨一貫追求經濟精英的利益,認為有益於商業階級的就是有益於國家的。該政黨的名稱隨着時間而改變(聯邦黨人,輝格黨人,共和黨人),但動機一直保持不變。另一個政治黨(民主黨-共和黨,民主黨人)拒絕了這一理念,認為對於有益於廣大公民的才是有益於國家和商業的,政府有積極的義務保護羣眾免受來自財富主導體系的邪惡侵害。
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種理念鴻溝使民主黨和共和黨人分道揚鑣。因此,政黨極化本身並不是新生事物,當前美國政黨極化之所以引人側目的原因在於政黨對政治“遊戲規則”的認知差異,也就是關於民主概念的認知差異。個人對遊戲規則的違反會得到政治體系中大量政治積極分子以公開歡呼或默默支持的方式表達的廣泛支持,這些違規行為甚至已經形成黨派政治立場。
一些學者認為兩個陣營之間的深刻敵對情緒是“情感上的兩極分化”,導致國會政治中粗魯和教條主義不斷增加選民中黨派陣營之間高度不信任。在這種情況下,反對的觀點在政治辯論中不被視為不同的一面,而是一種道德錯誤的選擇。這種對抗局面必然導致國會等政治機構出現僵局,解局的辦法是“有為”和“無為”兩種,前者指制度改革,然而數年來美國國內關於制度改革爭論並無後文;後者指“守株待兔”地等待兩黨中的某一方勢力衰落,當共和黨或民主黨徹底分出勝負之後,政黨極化引發的僵局亦或可得以解決。
對於中國而言,隨着中美兩國政治、經貿等層面的交往程度加深,如何理解美國國內政治問題深刻影響了處理中美關係時的方式和效果。
就美國政黨極化問題來看,由於美國政黨發展的基礎是其代表的階級利益,這決定了各政黨的對華政策都需要以鞏固其階級基礎為前提,實質上反映的是美國國內的經濟發展狀況。當前美國國內經濟不平等加劇,保守主義勢力抬頭,近期的中美貿易摩擦正是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精英階層的新一輪黨派博弈手段,試圖通過解決中美貿易逆差等問題提振美國國內經濟,避免大眾因不滿現狀而對美國現有的社會契約進行挑戰。因此,中國在處理當前的中美關係時要將美國國內政治特徵考慮在內,正確評估美國國內的發展狀況和政黨極化趨勢,積極應對美國政黨極化為中美關係帶來的衝擊。(註釋略)
本文原載於公眾號“國關國政外交學人”,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