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艾利森:中美關係——“競爭夥伴”理論
【文/ 格雷厄姆·艾利森】
不可否認,在當下,大國關係的戰略基礎已經崩潰。一直以來,美國的總統們一直試圖將迅速發展的中國納入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來,但現在,美國得出的結論是,“戰略伙伴"即"戰略對手” 。幾十年來,中國一直保持着低調韜晦,但現在變得愈加奮發有為。
在這一點上,大國關係陷入了典型的修昔底德式的競爭旋渦中。中國是一個飛速發展的崛起國。而美國則是強大的守成國。隨着“make China great again”的堅定,它不可避免地觸碰了美國各個維度和各個階層的敏感神經——美國人很堂而皇之地將自己的國際主導性等同於國際合法性。
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當崛起國與守成國相遇時,警鐘已然響起。在過去的500年時間裏,修昔底德列舉了16次類似的競爭案例。其中有十二次最終以戰爭而告終。中美終究會註定一戰還是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正如亨利·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樣,修昔底德的陷阱提供了最好的歷史鏡頭,可以透過新聞傳媒和訊息聒噪來透視大國關係的潛在動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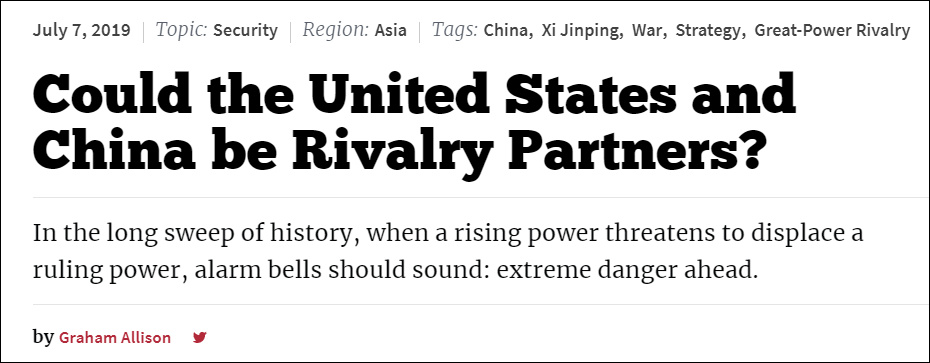
“中美可能成為競爭夥伴嗎”,截圖來自“國家利益”
自從我的手稿送到出版商那裏以來的三年時間裏,我一直在尋找方法來給這個問題一個積極正面的答案——實際上,是為了逃離修昔底德陷阱的答案。迄今為止,我已經評估了九種潛在的“逃脱途徑”。當然,每一種都各有利弊。在這一點上,沒有任何一個可行的選擇,是足夠令人信服的。
我現在正與中美雙方的有關學者一起以最積極的姿態來探索這一問題,**結合中國古代的“競爭夥伴”理論和約翰·肯尼迪總統在古巴導彈危機後形成的洞察力——即呼籲美蘇在“國際安全多元化”中同求共存。**當前能否將這兩種理念結合起來,今天雙方將面臨何種挑戰?他們能在“世界安全多元化”中,有效管理競爭夥伴關係嗎?美國的核心國家利益是“捍衞美國作為一個自由國家的利益,及其基本制度和價值觀的恆定”。但是,在今天這個威權主義崛起的時代,這個目標能否實現?
在冷戰初期,美國當時尊稱為“智者”的領導人(喬治·凱南、詹姆斯·弗雷斯特)持否定態度。但是,在經歷了古巴導彈危機後,肯尼迪總統卻改變了想法。在那場危機中,他認為,發生一場核戰爭的可能性為三分之一。 他最重要的對外政策演講(遇刺前五星期),標誌着美國冷戰戰略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儘管他從未動搖過前輩和自己的意識和信念。
未來的事實是,美蘇將不得不想方設法限制它們的競爭,甚至雙邊妥協: 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截然相反、和不同的政治制度中求同存異——冷戰的首要任務將是推動"國際安全多元化" 。如同伍德羅 · 威爾遜(Woodrow Wilson)長期以來使用修辭柔術一樣。
是什麼導致肯尼迪總統如此戲劇性地改變原有的主意?——是真實存在的核威懾經歷——美蘇面對面的對抗最終或以世界末日而告終。他對自己能在古巴核導彈危機後倖存下來表示感激,並希望自己的繼任者不再以身試險。羅納德·里根後來也把政治演藝內在化,聲稱“永遠不打那種誰也打不贏的核戰爭”。
從實操層面上來説,當時這意味着翻開了冷戰的新篇章。殘酷的競爭被謹慎、溝通、明示或暗示的約束甚至妥協行為所緩和了。肯尼迪政府發起了一系列倡議,在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設立了一條熱線專線,“以避免雙方在危機時期隨時可能發生的行動誤判和行為誤讀”,並最終達成了《核不擴散條約》。
雙方還進一步核實並豐富了肯尼迪所説的"危險現狀規則",其中包括: 不使用核武器;美蘇戰鬥人員不相互發射子彈或炸彈;確保對方的勢力範圍內不發生意外。在這些參數範圍限定下,兩個對手將繼續在其他方面展開激烈競爭,包括社會價值觀和政治體制。肯尼迪的洞察力能為中美戰略家們在今天思考如何逃脱修昔底德陷阱提供線索嗎?一千年前中國出現的“競爭夥伴關係”概念能否得以傳承和發展?
競爭夥伴聽起來像是自相矛盾的詞彙,但這是宋遼關係的史實。在澶淵之盟後,宋和遼同意在某些領域展開激烈競爭,同時在另一些領域展開熱烈合作。 這是一個獨特的朝貢關係版本。**維****持這種競爭夥伴關係需要管理反覆出現的危機,並不斷適應新的時空條件。然而,兩個競爭對手之間的和平時代持續了近120年。**而且,此舉創造了一箇中國早期的繁榮市場,刺激了中國的經濟增長,支持了藝術和理學的發展,中國歷史學家稱之為“黃金時代”。今天的問題是,中美之間是否能找到一種適應於21世紀的——能讓競爭和合作同時共存的創舉。

在一個結構型良好的市場經濟體系中,實體經濟間的競爭刺激了物美價廉商品的問世。正如亞當·斯密告訴我們的那樣,根據比較優勢原理和貿易的專業化整合,產生了一個比單邊經營更大的餡餅。因此,國內或國際市場的競爭推動了創新發明和各國經濟的增長。與此同時,除非嵌入到條約和強制執行的遊戲規則中,它。也為掠奪行為、壟斷勒索提供了機會。
此外,由於GDP是國家權力的基礎,美國人理所當然地擔心,即使展開公平的經濟競爭也很難取勝。由於對方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多,如果對方的生產力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那麼其國內生產總值將與美國相當。而生產率卻遠不止於此,這不僅是一個難以忽視的算術級數。
在軍事領域,競爭大多是零和遊戲。軍事關係的核心事實是,兩國都擁有可靠的第二次核打擊武器庫。這使得任何一方對其對手的攻擊都將是相互確保摧毀的。毋庸置疑,更大的GDP可以支持更大的國防預算,這將使兩個國家行為體能夠持續研發和部署新式武器,從網絡武器、高超音速飛機到海陸空無人機,以及為每支軍事力量提供耳目的衞星。先進的武器可以威脅對方的指揮和控制系統。隨着中國軍事力量的增長,改變了台海和南海等戰區邊界的戰略平衡,美國維持現狀承諾的可信度也在逐年下降。雙方技術領域的高級算法、5G、人工智能和基因組研究,成為GDP的關鍵驅動力。上述這些既為軍事力量的進步提供資金,也為軍事力量的進步提供動力。
**一方面,雙方面臨的大部分挑戰都在本國境內,比如努力尋找治理自身社會問題的方法。在美國,華盛頓特區已經成為了資本功能失調的縮略詞,挑戰不亞於重塑美國民主的功能性。****另一方面,密切合作和夥伴關係將不僅僅產生互利互惠。如果沒有中美的認真合作,任何一個國家行為體都無法確保其生存利益的確保和價值的實現。**這些合作包括但不限於:避免戰爭,特別是核戰爭; 防止恐怖主義擴散; 保護生物圈; 遏制流行病; 以及管理金融危機以避免大蕭條(及其政治後果)等等。在修昔底德陷阱式的競爭中,引發戰爭的最常見因素是外部事件——即第三方挑釁,甚至是像薩拉熱窩那樣的意外事件。因此,共同預防和管理符合兩國的重大利益。
鑑於地球上的每個公民都生活在同一個生物圈中,中美提出有效的環境保護方案迫在眉睫。《巴黎氣候協定》邁出了一小步,並開始採取行動應對氣候挑戰。特朗普總統退出協議並否認氣候問題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而埃博拉或豬流感等病原體得傳播將是無國界的。因此,正如JFK所言,“我們都呼吸着同樣的空氣”,中美的共治對保護全球公民的健康是十分必要的。
最後,金融危機。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後,引發了一場全球經濟的大衰退,並引發了第二次大蕭條。歷史證明,只有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共同努力,才能使局面得到控制。2008年,他們做到了。正如美國財政部時任部長漢克·保爾森(漢克·保爾森在那次事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所説的那樣,中國的協調合作與美國的行動同等重要,亦或許更為重要。
在一個有利於不同國際政治體系之間和平競爭的年代裏,競爭夥伴理論能否成為一個全新的戰略概念起點,以應對當前中美關係的險態?競爭,實際上是激烈的競爭,將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殘酷的事實是,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自殺的同時殺死另一方。那麼熱烈的合作式競爭在戰略上將是必要的。建立一個競爭與合作相結合的國際大戰略,需要雙方戰略想象力的飛躍,這將遠遠超越當前的傳統智慧,就像凱南在1946年脱離華盛頓共識四年後提出的冷戰戰略一樣。對美蘇關係和宋遼關係的反思可以為這一未竟的事業提供重要參考。
本文原載於微信號“國關國政外交學人”,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英文原文刊於“國家利益”2019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