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雨子:《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國式神話的“重構”與“返魅”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聆雨子】
7月的蟬鳴過去大半,始終沉寂的暑期檔,就像遲來的酷熱一樣,終於被一部國產動畫強行點亮。
點映期先聲奪人之後,《哪吒之魔童降世》在持續升温的口碑積累中,強勢登陸院線,意料之中地又收割了一波如潮好評。
這當然是個有點意外的局面,畢竟在相當廣泛的羣眾認知裏,“國漫”遭遇的慣性懷疑,幾乎不亞於“中國足球”。
因此,每一次爆款,都是一次偏見和輕視中的自我正名,也是一次尋路和求強中的方向鎖定。因其難得,才更需珍惜,也更需思考品評。
觀影歸來,我雖還不想輕易地使用“神作”或“驚豔”這樣的大詞,但必須要説,它讓我看到的,是“成熟”。

《哪吒之魔童歸來》中的哪吒形象
母題的成熟:世界觀和封神宇宙
始終困擾着中國動畫的問題在於:我們究竟如何面對那些,屬於本民族的古老故事。
“天天唸叨學美國日本,偏偏連自家老祖宗的東西都拍不出、拍不好”;
“都21世紀了,數來數去,能拿出手的形象還是隻有一隻孫猴子,真不害臊”。
兩個質問都尖鋭,前者指責的是沒有繼承的創新,後者批判的是沒有創新的繼承,雖然角度和措辭彼此對立,卻一樣餘音繚繞。
我們無從否認,中國動畫史上最富於史詩感的作品,都有華夏血液深處的迴響:《大鬧天宮》、《哪吒鬧海》、《天書奇談》、《金猴降妖》。
就像我們無從否認,這些年國產動畫僅有的幾個高光時刻,中國神話依然屢戰屢勝地宣示在場:無論《大聖歸來》,還是《白蛇:緣起》。
但我們只能承認,觀念在演進、美學在裂變、技術在革命、娛樂訴求在更迭,沒有人會滿足把三打白骨精看上一輩子,強如六小齡童老師,還不是囿於過度迷信往昔的成功,身陷網友羣嘲。
就像我們只能承認,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和所謂“中國學派”的奇蹟,畢竟屬於計劃經濟環境下的“史前榮耀”,被我們津津樂道的很多“動畫經典”,其實叫“美術片”更加合適。
繼承和創新,都是具有永恆正確性的東西,又都是不可拋開彼此獨自存在的東西,要想不被罵,你只能讓自己做到:在繼承中實現創新,在創新中完成繼承。

《大鬧天宮》片段
回到這次的《哪吒之魔童降世》。
一方面,它當然很“創新”,甚至可以説,很“顛覆”。
王霸四海貪得無厭的龍族成了困居水底的煉獄守護者,仙風道骨鬚髮飄飄的太乙真人成了一口四川普通話的大胖子,迂腐古板的李靖成了有擔當的慈父,面目模糊的殷夫人成了英姿颯爽的女俠,向父尋仇成了黑能量入腦後的舉止失控,割肉剔骨成了正能量覺醒後的以身擋災。
當初那個為非作歹要吃童男童女的敖丙太子,成了主人公一體兩面的鏡像、“內心另一個我”的外化、圈粉無數的白衣秀士小鮮肉、惺惺相惜的“唯一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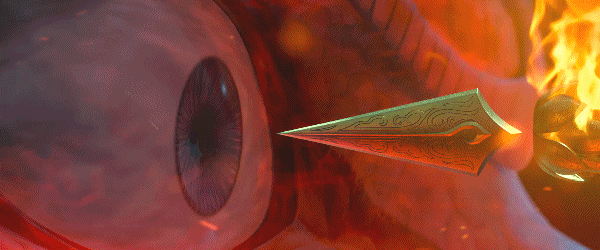
敖丙與哪吒
父子之間、母子之間、敵友之間、師徒之間,無數組關係被重置了。
乾坤圈原來是一種類似緊箍咒的禁錮裝置,風火輪竟然能和一頭豬實現無縫互變。
至於哪吒,熊貓眼、齊劉海、牙齒錯落、凶神惡煞、暴躁乖戾、愚頑魯莽,怎麼看也不像四十年前拔劍自刎賺盡觀眾眼淚的俊朗少年。

這些屬於“顛覆”的東西,是一目瞭然的。
可另一些東西,卻很容易被忽略,那就是,它依然保留和遵循着很多來自《封神演義》的元設定:
靈珠子的身世與宿命、啓示錄般的殺劫、人對妖和神的恐懼、神對妖和人的規訓。
出生即被視為不祥、闖禍為家族帶來災殃、鬥夜叉、鬥敖丙、水淹陳塘關、以命報父母恩、蓮花中重生一道精魂,這些耳熟能詳的故事脈絡,看似改頭換面、包上某種陌生的質地,但其實,依然一個個按照邏輯線、有條不紊地發生。
這種對神話“元設定”的遵循所帶來的最大加成,就在於“世界觀”的宏闊。
一個故事的人物關係網和情節線,被放置在怎樣的世界架構當中,怎樣的地理、水文、種羣當中,遵循着什麼樣的身份規則和技能點進階規則,有着怎樣的價值體系、行為方式、社會屬性、職業特徵等,內含哪些歷史元素和宗教元素。這就是動畫的“世界觀”。
相比於漫威、指環王、冰與火之歌,相比於海賊王、火影忍者、鋼之鍊金術師,“世界觀”一直是國產動畫最顯得單薄、最顯得低幼的東西。
從《夢迴金沙城》到《魁拔》到《秦時明月》到《大魚海棠》,“世界觀”也一直是國產動畫着力於為自己補課的東西。
為什麼我們一次次求助於《西遊記》,正是因為它能提供一個“四大部洲、東土西天、三界五行、諸山列國”組成的完整“世界觀”佈局。《封神演義》也是一樣。
所以這次,我們看到了符咒、封印、結界、石化,看到了神族、龍族、人族、妖族的分野與對立,看到了水系魔法和火系魔法相生相剋的碰撞共舞,看到了法寶的層出不窮——“哪吒標配四件套”自不必説,還添上了乾坤社稷圖、指點江山筆以及萬龍甲。
也就是説,我們終於看到了一個遼闊的玄幻的東方大陸,一個屬於我們的諸神盛典。
此刻我願意相信,如果我們真的能在銀幕上覆活屬於華夏神譜的宇宙,那《大聖歸來》和《哪吒之魔童降世》,就相當於我們的《鋼鐵俠》與《美國隊長》,《西遊記》和《封神演義》,就相當於我們的《復仇者聯盟》與《X戰警》。
人物的成熟:“得神而忘形”
最體現本片“繼承與創新”之辯證的,還在主人公哪吒的塑造上。
儘管當初預告片一出,就已經有人痛心疾首,説這個“史上最醜”的邪典怪嬰,把他們內心的英雄,褻瀆得過於面目全非。
殊不知,中國神話裏最有人氣的形象,大多是仙氣、妖氣和人間煙火氣的結合體:哪吒也好,孫悟空也好,二郎神也好,白素貞也好,還有濟公、呂洞賓、鍾馗……他們都在扶危濟困、救苦救難,卻從不示現以一般神佛的不苟言笑、不怒自威,相反,他們非常情緒化,敢愛敢恨敢闖禍,和秩序、或者説“天道”之間,保持着某種若即若離的緊張關係。
哪吒和孫悟空還更特殊一些,因為後者多了一份“猴子氣”,前者則多了一份“孩子氣”。潑猴子、熊孩子——鬧騰、惡作劇、搞破壞,從來都是這倆的關鍵詞。
於是他們都有一個充滿冒犯感的童年和少年,一個鬧的是東海、一個鬧的是天宮。
這種“熊孩子和潑猴子”人設,自帶可觀的戲劇價值,尤其對動畫而言,“鬧”就意味着嘻哈鬼馬,也意味着叛逆和不羈,意味着“熱血中二魂”。
更何況,如果能實現從“鬧”到“不鬧”的跨越,那文本內部,就天然擁有了人物成長性。
這就是為什麼,2015年和2019年,不鬧天的大聖,不鬧海的哪吒,能各自帶出了一個屬於自己的暑期爆款。

《大聖歸來》截圖
其實,哪吒的形象本就經歷過漫長的歷史變遷,但一以貫之的是,他始終都是叛逆者和抗爭者。
只不過之前,他抗爭的是“神權”,是一組外在的形象,是龍王、天庭和父親,這一次,他抗爭的是“神示”,是一組內在的判定,是宿命,是世人為你貼上的標籤。
“我命由我不由天”——“魔”與“童”的碰撞張力,靈珠和魔丸的何去何從,馴服惡念,用人性為觸媒尋回神性,打破那“一座大山”式的“人心中的成見”,看見責任,看見愛。
敍述雖然略顯雞湯,但歷程其實無限艱難。
這同樣是一場屬於哪吒的“鬧海”。是他的搏鬥、他的修行、他的參悟、他的成人禮。
這個哪吒和我們熟悉的哪吒,走過的其實是一樣的道路。
天地負責造物,但不負責“造悟”。
集天地之靈氣精華而生的英雄,都必須贏得與心魔的交戰,才能完成自我。
這是中國神話裏最深層的哲學命題,是古典的東方式的浪漫、東方式的倔強。
所以,你可以説電影做了觸目驚心的置換,把所有性格細節和行為細節都向着更吻合現代審美的方向變化了。
哪吒的搖滾中二風、太乙真人的諧星肥宅風、申公豹的口吃渣爛風、敖丙的優質偶像風乃至於兩位主角的“國民CP”風,固然解構了神話法相莊嚴的一面,融會貫通了神話裏最與人性相通的一面。
但“解構”並不一定要以“惡搞”為前提,以“失序”為代價。
因為解構之後,還可以重構。因為重構,所以在“祛媚”之後,得以“返魅”。
因為格調沒有變、氣韻沒有變、精神稟賦沒有變、內在的質地沒有變。
這就是為什麼這樣一個全新的文本,依然要以哪吒作為男一號,而不去另起爐灶、隨便編寫一個什麼超能力少年自我覺知的經歷。
因為我們永遠需要來自本民族精神原型的符號人物,我們變的是“形”,留下的卻是“神”。
“忘形而得神”之後,大家依然可以高歌一曲:是他是他就是他,我們的朋友小哪吒。

至於其它優點,都是大家可以看到、反覆在講的了:
凌厲而鬼魅、卻不失英雄風采、且自帶辨識度和記憶點的造型設計。
超過1400個特效鏡頭組成的高燃動作場面。
羣戰時的虛擬調度。30秒以上的一鏡到底。
雖然也有瑕疵:部分笑點還是略有生硬和刻意的隔靴搔癢感。總在太乙真人的褲襠和放屁上做文章也未免跌份。
但一切足以再一次證明:技術,早就不是國產動畫的絕對短板。我們一直缺的,只是故事的研磨、情緒的注入,只是怎樣以“好看性”,來實現“動人性”。
不敢説《哪吒之魔童降世》就是答案,但至少,我們又一次地看到了力量和希望之所在。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