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善波:説《萬曆十五年》被高估,其實真瞭解黃仁宇“大歷史”觀的人不多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邵善波】
黃仁宇寫的《萬曆十五年》,先前因電視劇《人民的名義》而大熱,近日在觀察者網被反覆提及,再次引起關注。但這本書雖然火了三十多年,而瞭解及真正掌握黃仁宇的“大歷史”觀的人,看來卻並不多。

《萬曆十五年》在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被多次提及
對黃仁宇老師的論述,因我本人與黃老師有些淵源,所以算有點發言權。
1992年初,我曾邀請黃老師到香港參加一個關於“一國兩制”的研討會。這緣起於在《萬曆十五年》的一個版本中,他附文詳細地談到“一國兩制”在全球歷史中的四個案例,包括英國、荷蘭、美國南北戰爭前、中國魏朝。他的有關説法與中國官方對“一國兩制”是個“獨創”的説法很不一樣。
後來因為“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港強推政改方案,研討會開不成,我就陪黃老師去廣州參觀黃埔軍校的舊址。黃老師是黃埔校友,但不是黃埔廣州老校的學生。他去到黃埔軍校原址時還是非常激動。
在幾天的旅程中,老師不斷提點我,要看大局,觀長遠,不要糾纏在眼前的小事。這既可能是因為他對我不斷談香港迴歸問題、中英之間的磨擦及矛盾(畢竟那是我當時每天面對的工作)有點不耐煩,但有關觀點也確是黃老師研究歷史及看事情的基本立場和態度。

黃仁宇(資料圖)
《萬曆十五年》的書寫,是透過從社會細微點滴的觀察,洞察社會及制度的整體運作,進而歸納出“大歷史”的視野,引申出一些大規律。這研究方法不為當時的學術界接受,是可以理解的。雖然學術界本應兼容開放,歡迎不同的角度及嘗試,但現實中往往並非總是如此。
黃老師在學術界失意,《萬曆十五年》這本原本沒人願意出版的書,卻反而在他被去職後得以出版。原版最初為英文,1976年出中文版後,意外地在台灣及大陸紅火,受關注及討論達三十多年,實乃學術及出版界內的一個異數。黃老師九泉之下,應可一伸他幾十年不被認可的怨氣。
從《萬曆十五年》到大歷史,黃老師從“小”看“大”,採歸納法,大膽推斷。其學術方法不為美國當時歷史學界所接受。應指出,就算到今天,也仍不為很多大中華區的歷史學者接受,這是個事實。這與他的書長時間受讀者的歡迎,形成奇怪的反差。
黃仁宇從軍後才轉入學術研究,以其在抗日戰爭及國共內戰中的軍旅生涯體驗和成長過程,作為他探索國家歷史的基礎及動力,學術底子薄弱是自然的事。他的理論欠經典理論的支撐,缺乏嚴謹的論證,個別具體事例上也出現差錯,都是事實。有的偏差多少與他對國家的熱情和個人性格的執着有關。但他提出的一些看法,在當今中國的百年大變、大轉型中,有很適時及精闢的觀察與提點,也是不能否定的。
黃老師的論述,給了我們這一代人,在面對國家的大轉變時,如何理解這個轉變過程的一種大局觀和大視野,使我們能從一個宏觀的“大歷史”角度,看待眼前發生的事及其將來的發展,而非拘泥和執着於狹小的歷史事件本身。這不是一般學者能做到的。這或可解釋為什麼他雖然不獲美國及國內學術界的接受,但在一般的讀者羣中仍長期受到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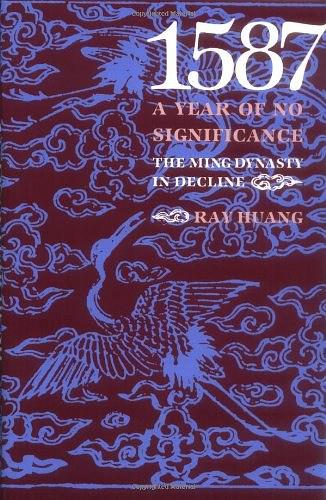
《萬曆十五年》,耶魯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
黃老師分析中國歷史,先從“大國”、“一統”的歷史事實開始,他將形成這一基本事實的原因歸結為“防外患”與“治水”這兩個因素。這兩個因素使得中國要有整體統籌的應對,因此而讓“大中國”成為必然。這可能不是黃老師獨有的結論,論證中國“大一統”傳統形成的研究非常多,這兩個因素也不是唯一的,但這不重要。黃老師的關鍵論述,是在中國如何治理大幅員、多人口的國家的層次上。
偌大的國家,交通及通訊不便,一箇中央指令要下達全國,到達邊遠地區就要幾個月,以當時的科技水平,如何治理,不能以我們今日的觀念及標準去理解。管治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必然要依賴一個龐大的官僚隊伍。國家的治理,首先是對官僚隊伍的治理。
在當時的條件及要求下,以儒家的道德體系來管控官員,是有其內在道理的一個選擇。管治主要依靠道德,而不是嚴格、詳盡的法規,成了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核心元素,一個特色。中國能以此持續存在二千多年,在世界文明史中,也是獨有的。但也因為這樣,形成了中國政治生態“泛道德”的傾向,造成了不少非理性的傳統後果。黃老師對上世紀末一些學生的激情表現,就非常不以為然。主要是他認為簡單的道德評判流於表面和片面,集體的“義憤”行動,並不能解決國家發展中出現的問題。
以道德管控官員及社會,是無辦法中的辦法,法制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只能是輔助性質,而且也難以過份規範化,這自然也引申出很多問題,如官員的虛偽、形式主義、陽奉陰違等等。故此,經過一段時間,加上其他因素,如農地未能適應人口增長的壓力等,必然出現僵化及崩潰,只能依靠改朝換代加以調整。但改朝換代後只能在一段時期內使社會關係得到一定程度的調整,卻不能徹底改變形成治理方式的一整套客觀因素,治理方法基本上無變化,二、三百年來一次輪迴,二千年來如是,直到新中國的成立。這是黃老師的大歷史觀的前半部。
黃老師的“潛水艇三文治”(submarine sandwich)比喻,主要是指出,中國政治的上層,即中央政權,與地方百姓的下層,兩者中間缺乏有效的聯繫,朝廷的官員只派到縣,中央給予的資源極少。再往下是靠民間的鄉紳父老。兩者之間,即朝廷(中央政府)與基層百姓之間,長期只能通過一大批以道德和等級制度管控的官僚,依照一些粗略、原則性的指示及規範,去進行治理。
國民政府推翻清朝後,承接了清朝的中央角色,建立了一個上層的現代中央體制,但缺乏在地的基礎,施政手法離不開兩千年來的傳統形式,原來的陋習自然也除不掉。共產黨的工作則從基層羣眾做起,取得政權後,一方面承接了國民黨政府的中央體制,另一方面又延續了自己原有的基層政權組織基礎。

1970年代政治宣傳畫
黃老師認為共產黨的政權組織形式,是中國兩千多年來,第一次將上下兩層有機地連接起來,形成了落實“數字化管理”即現代化管理的基本條件及可能性,淡化了單依賴道德及人情、人際關係的管治模式。這是兩千年來中國治理歷史中的一個根本大變。基於這一觀點,黃老師對中國的前途非常樂觀。他雖然出身國民黨,難得的是這個觀點超越黨派成見。
有人認為黃老師提出的“數字化管理”在現實當中完全行不通。這是對“數字化管理”的誤解。此用詞超前,雖與今日的“大數據”並不一樣,但我們現時的大數據使用,其實就是“數字化管理”的極高級版。黃老師的“數字化管理”,其實就是指現代化管理,是去道德化、去人際關係的管理制度,即靠制度,不依靠道德及人情。沒有這個條件,市場經濟和現代社會治理,無法實現。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有機會到上海考察,具體瞭解到非數字化管理的實際情況。當時有幸與一老幹部談起上海破舊的基建,她的回答令我很感動。她表示國家窮困,上海從來都相對較好,故作為老大哥,上海有的財政盈餘,大部分都上繳中央,故無多少資源改善本地的基礎設施。她講述時的態度不是埋怨,而是驕傲,能以老大的身份貢獻國家,她覺得是光榮,是上海的責任。後來我才知道,上海長期是中央財政的主要來源。這種安排,完全就像一個大家庭的成員供養父母,誰有能力,誰地位高,誰就多出一分力。這是依據人倫關係的做法,是“數字化管理”的相反版。

1980年代的上海
由這個現實聯想到黃老師的分析,才能充分理解朱鎔基總理推行分税制的重大歷史意義。分税制第一次在中國劃分了地方及中央的税收種類,理順了、明確了、穩定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將過去長期按不同情況,通過遊説、施壓、政策交換等等的協商程序,去處理雙方的財政問題,變成一個按既定規矩,有章可循的穩定分權分利制度,徹底解決了兩千多年來中央與地方關係這個中國管治體制內的老大難問題,從此很難再出現地方權力坐大、挑戰中央的情況。這可視為中國現代治理上一個“數字化管理”的實例。
另一個可供支持黃老師觀點的,是耶魯大學的人類學教授、港人蕭鳳霞的一個觀察。蕭教授專門研究嶺南的人文生態,她認為嶺南以往能有獨立的發展及風格,就是因為“山高皇帝遠”,傳統的管治在地方留有很大的空間及彈性。但自從新中國成立,共產黨執政後,北京一聲令下,如要廣種糧,則南方無論是山區還是平地,都會種糧。這一刀切的號令,自然造成不少損失。
但這例子對我的啓發是,可從反面來證明黃老師的一個推論及觀察,即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二千多年來,首次可將中央政權的政令,及時、有效地伸延到全國的幅員。“三文治”的頂層與底層,首次能有效地通過現代治理的技術及模式,有機連接起來。
當然,這種有機連接本身並不能保證中央政令的正確,隨之而來的風險是,如果中央的決策錯誤,造成的損失也是全局性的,其殺傷力會比在以前的制度下有更大的負面後果。但這不能成為反對治理現代化、系統化的理由,而需要中央的決策更科學化、更仔細、更周詳。這正是今天中國政府面對的一個挑戰。
聽説黃老師在台灣的一次演講,令台下一些國民黨官員的後代感動到痛哭。他們認為第一次有人能講出他們父輩當時面對的難處。因為黃老師坦承,國民黨官員貪污腐敗是一個廣泛的現象,也是導致政權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但當年官員的操守與他們面對的時代大環境有一定的關係,不能簡單地以道德的標準評判。
如當時國民政府為軍方提供的資源遠遠不足,甚至不提供任何資源,部隊所需由領隊自行就地解決,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然難免出現強搶、沒收民資的情況,也造成貪污的土壤,國民黨軍隊的惡名與此有很大關係。黃老師本人也曾奉命要帶一隊兵到某地點,當時他也面臨不跟着部下講粗口、食狗肉,就根本無人聽你命令的現實。那時,做將軍的如沒有大房子及排場,也似乎沒有威信,沒有人會聽你的指揮。
黃老師初期看到國民黨軍隊的腐敗情況非常憤怒,但後來在“大歷史”的視野下,逐漸能將這些現象放在當時的時代大環境下去理解。也正是依據他自身的經歷和理論,黃老師不斷提醒我,不能簡單地以道德標準判斷眼前的事。我認為他不是簡單地為貪腐找藉口,而是強調要從大視野去看問題。這對當前的反貪腐運動,應有些啓發的意義。
另外黃老師在香港時的一個故事,也算是國家百年大變中新舊觀念衝突的小例子。他在港時,特地在灣仔的一間餐廳拜會了他以前的上司何世禮將軍(何東爵士的後人),他告訴我是為了化解他數十年的一個心結。

何世禮將軍(資料圖)
原來抗戰期間,何將軍曾下令他的部下捐血,以救助一些來華援助而受傷的美國軍人。黃當時以身體受諸父母為由,竟然抗命不從。作為一個下層軍官,在隊伍中造成很壞的影響。他後來深感自己當時的無知,懺悔不已,故不忘利用到港的機會,向老上司致歉。何將軍表示早已忘記此事,一笑置之。老觀念與新科學,難免在當代中國大變局中,激發出不少矛盾。但歷史向前走的大趨勢,是舊觀念所無法阻擋的。
黃仁宇老師的大歷史觀,紅火了三十年,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的論述不一定很嚴謹,細節不一定準確,更可能不符合學術界的一些要求、風格和潮流,但他的理論、觀點和視野,在中國當前的大變局下,有一定的借鑑意義。大歷史觀要求我們要看遠、看大,觀具體事物時要考慮背景、當時的大環境,不要過度以道德眼光去評判眼前的事。
大陸和香港的電視劇、舞台劇,有些是利用《萬曆十五年》一書的風行,來推銷自己的“私貨”,劇中的觀點,多與黃老師的理論無多大關係,有的甚至與他的觀點相反。但如因此能引大家去讀讀原著,也未嘗不是好事。
黃老師肯定今天共產黨的大政,不是因為個人的喜好或什麼主義和意識形態,而是因為大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中國到了今天,跳出了過去二千年的治理模式,進入了現代社會治理的行列,其大治、復興是必然的。黃老師生前對中國的未來非常樂觀,非常有信心。他離世後的中國故事,證明他是對的。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