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雨欣:唐代財經官僚的崛起,註定了天寶年間會出林九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劉雨欣】
在這個“爽劇橫行”的年代裏,《長安十二時辰》很會反彈琵琶。刷完全劇,我被好些情節噎得夠嗆!全劇處處描摹着大唐的社會矛盾,給人一種“這樣的長安真心不值得救”的印象,可主角們就是執着地奔走在查案的第一線;從第一集開始,上至皇太子下至販夫走卒都知道右相林九郎是個什麼貨色,彷彿全大唐都恨死了這位奸相,但聖人就是喜歡他,喜歡他,喜歡他……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不過話説回來,有這樣的對比也好,如此我們才能更好地感受到盛世危機的敍事帶來的歷史張力。看劇之餘也不由思考:為什麼天寶三載的大唐會落到這般不值得救的地步?為什麼奸佞能夠身居高位?
這些問題讓我想起了台灣歷史學者盧建榮寫過的一本書——《聚斂的迷思——唐代財經技術官僚雛形的出現與文化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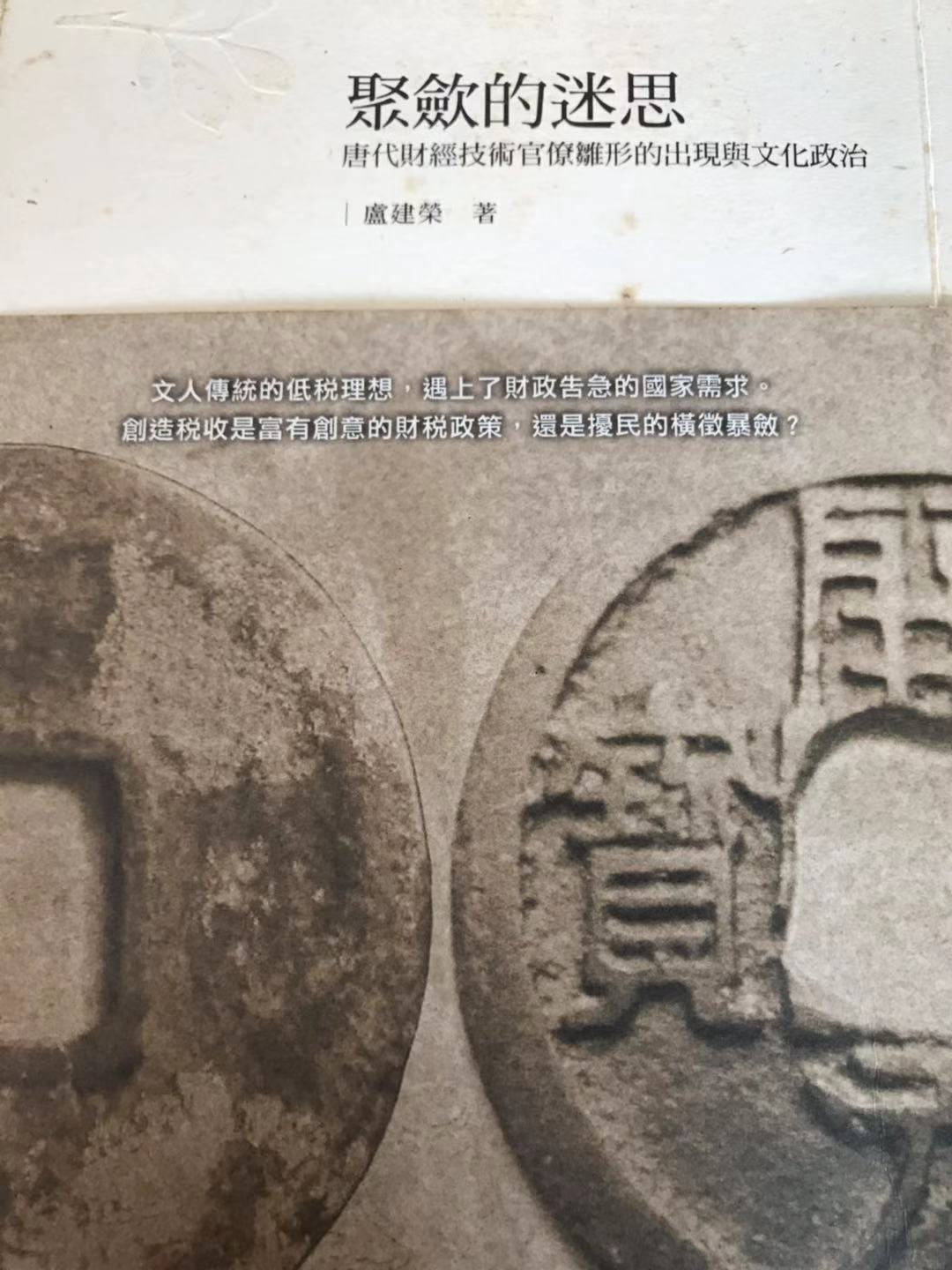
盧建榮《聚斂的迷思》書影
上層建築出的問題還得從經濟基礎的脈絡中找。若將此書合着《長安十二時辰》的劇情來思考問題,或許能對那段歷史形成更深刻的理解。
不過需要強調一點,對這本書以上層精英官僚為核心的歷史觀,以及不時透出的“台獨”式的傲慢表達,我們自該立場鮮明地予以批判。而出於對學術“知己知彼”的考慮,書中一些細節敍述很值得玩味,在對《長安十二時辰》的敍事形成補充之餘,還能展現中古官僚政治的一些面相,供我們思考。
唐代財經官的工具理性
單純從歷史敍事的角度來看,這位研究者寫這本書有兩個目的:一是,介紹唐代主管財經的户部官員們、理財家們在面臨天災人禍導致的財政危機時如何力挽狂瀾;二是,考察財經官僚的政治生命,描摹財經官在被同僚們以“橫徵暴斂”之名咬住時,是如何自處的,以及在這一過程中,皇帝的態度是怎麼樣的。
而以古鑑今是許多歷史學者寫書的大目標,這位盧先生也是如此。通過書寫這些內容,作者的最終目的在於借唐史、唐人的歷史經驗分析台灣的政治、經濟問題。
在這本書裏,有兩位主角,一位是杜佑,一位是劉晏。在作者看來,他們是活躍在“八世紀後二十年的大理財家”,“他們身處的是一個極度困難的時代”,而且他們面臨的困難與當時台灣面對的問題很相似。所以,作者邊寫他們的故事,還會不時吐槽一下:
他們提出的理財方案或可行或不可行,也跟台灣極度相似,但台灣卻沒有他們的魄力敢於執行。天災一旦發生,政府就立即啓動急難救助金髮放,現在先進國家莫不如此。只是台灣政府比起先進國家在發放上極其繁瑣,讓災民感到尊嚴受損。像這次的莫拉克風災,政府雖派人到災民家照相存證,卻處理得漫不經心。台灣年年受災卻始終沒有一個機構全盤統籌,大多是靠臨時任務編組……對比之下,距今一千二、三百年前的唐朝倒是有個全國救災總署。
當時主持救災總署工作的劉晏認為如遇災害,貧户必然無法生存,因此也必然會向政府索求援助,根本無需政府浪費時間和人力實地查勘。且救災的重點是平抑物價,政府應該把力氣放在打擊囤積居奇上。
除了災害之外,戰爭對於國家財政也會形成巨大壓力。當唐王朝面臨河北叛亂戰事曠日持久之際,財政卻瀕臨破產。彼時,擔任“財政部長”的杜佑就主張徵富人税以應對危機。可是,此舉為杜佑引來了彈劾,杜氏因此下台。而他的繼任者無法解決問題,權力中樞也就不得不向河北低頭。
劉晏對於救災行動的統籌調度、杜佑徵富人税的想法延續到今天可視為進步國家施政的重要指標,“只有政府施政做到了上述這些大指標,才能符合最大社會公益”,如此也才能讓台灣發展得更“先進”、更“現代化”。(詳參《聚斂的迷思》自序5-8頁)
在作者具體的敍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唐王朝在經濟方面面臨的壓力:
對於國家而言,最理想的經濟狀態是百姓富足故而不逃税,國家富足而不必重斂於民。可惜正如杜佑在《通典》中所説,盛唐時期國用充盈、國家財政良性發展的形勢在天寶年間戛然而止,國家很實際地面對着“出納之職,支計屢空”的窘境。在此背景下,一些言利之臣順勢而行。既然支計屢空,便剽掠民間!由此帶來的結果是“每歲所入,數增百萬”,國庫看似是比從前更充盈了,可老百姓壓力山大。(同書,第32-33頁)
在國家急需用錢的狀態下,如若課重税,則百姓不堪其擾。但税若收少了,朝廷用度又難以滿足。這個燒腦的問題叫古今多少户部官抓耳撓腮!《長安十二時辰》裏寫了一個户部小吏徐賓給出的解決方案是改革税法,讓富人更多地承擔社會責任。

這和杜佑所想在大方向上看起來是一致的。杜佑認為應該以“輕重術”為國生財,對於百姓仍應實行輕徭薄賦的政策。他的思想承襲《管子》,只是當時的客觀形勢使之所想難以在全國範圍內付諸實踐。
黃仁宇先生在分析中國古代政治時指出,中國古代的官僚有一個特點,即非常注重刑法,而在交通、通訊、金融、信息蒐集等能力上存在明顯短板。(詳參《黃仁宇的大歷史觀》,第20-21頁。)實際上,
從《通典》的記述可以看出,唐代出現過舉茂才必得通曉《管子》的情況。(杜佑《通典》卷十七《選舉五•雜議論下》),而盧建榮筆下的財經官們的羣像也能對黃仁宇的觀點形成局部的挑戰與駁斥。
奸相為什麼是皇帝的心頭肉?
細想想,右相林九郎也是好慘一男的,從第一集開始被罵到全劇終。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偏偏被聖人奉為肚中蛔蟲、心頭肉……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劇中的右相即為歷史上的李林甫。如果光把他的崛起視為皇帝昏聵的結果,恐怕是把複雜問題簡單化了。如他這種權相能夠把控御史台,屹立朝堂多年,實際上有客觀的政治、經濟背景支持。純屬是時勢造奸雄!
依照《聚斂的迷思》分析,公元721年是我們理解玄宗朝財經官員崛起進程的一個重要時間點。在這一年,契丹、突厥、吐蕃等少數民族對唐王朝的邊防形成了持續的壓力。即位才九年的李隆基決定採取積極的國防策略,以邊軍主動出擊禦敵。這種軍事策略展現了皇帝的雄心,但也需要完備的財政體系支撐,如何增加朝廷收入以紓解邊防用度壓力便成為這一時期的重點政策。這樣的現實需求使得張説、劉幽求、郭元振等熟知軍政要務的幹練之才站在了朝堂的關鍵位置上。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唐玄宗熱愛文學,因而在取士時對進士科很是偏愛。而當朝廷面臨軍事作戰需要時,熟稔理財之道和通曉軍務的吏幹之才才是玄宗的心頭所好。張説、裴光庭、郭元振、李適之、牛仙客、王晙等人都是因其在這些方面的特長而得到拔擢的。(同書,第104頁。)
文學名家張九齡就曾和牛仙客在玄宗面前有過一場朝堂對決。時值用兵之際,玄宗想以牛仙客為相,但張九齡當即以牛仙客出身胥吏、缺乏儒學學養為由嚴詞反對。玄宗無奈……此時,李林甫跳出來指責張九齡不知變通,認為只要有智識便可為相。李林甫還順着玄宗的心意繼續説道,天子掌用人之權,更不必受文學之士的轄制。在李林甫的激勵下,玄宗這才順利將牛仙客推上了相位。
在張九齡等文壇巨擘眼中,文學之士才具備宰輔之質,所謂的吏幹之才充其量只是在特定崗位上比較堪用。而如劉晏這類財經官僚日後能夠身居高位,某種程度上確實倒還要感謝李林甫在此時給玄宗吹的耳旁風。是時,士人只可因文學拜相,此時,士人可由財經拜相。從社會流動的角度來看,有識之士們又多了一條上升階梯。公元734年,李林甫崛起,靠的也是由户部尚書兼任宰相的路徑。
充實財政不外乎開源、節流兩種方法。一些思維敏鋭的財政官員便建議由國家壟斷鹽業經營等方式來充實國用。玄宗本人曾有意於推行此道,然而山呼海嘯的反對之聲最終讓這項鹽業專營的計劃泡湯了。
似乎,財經官們的生財之道總會為那些有着輕徭薄賦理念的同僚所阻礙。可是別忘了,財經官們手裏有兩張王牌——財政開源的迫切需求,以及與之相應的皇帝的支持。隨着主張財政變革的官僚們掌握了户部尚書、户部侍郎這些關鍵性職位後,他們的話語權、決策權就得到了極大的提升。李林甫上任之後,以“資課”法擴充朝廷税收。對於“資課”究竟是什麼,學界有着不同的解釋,但可以達成共識的一點是“資課”確係一種斂財的新税法。玄宗對這種新法也是支持的。
財(斂)政(財)改革在形成氣候之後,會帶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尤有甚者,財經技術官僚們“帶着監察官的頭銜出使各地,並督導地方官執行財政政策,這就意味着在改革雷厲風行的時刻,監察機構無形中變成財經技術官僚推動改革的附庸機構”。(同書,第134-135頁。)以至於度支司機構的會計職能也基本取代了“皇家賬房”太府機構的權責。(同書,第354頁。)所以,王朝越需要錢,財經官的權勢就越膨脹。財經官壟斷的資源越多,皇帝也就更需要他。一定程度上,構成了惡性循環。
朝廷漸漸淪為“户部派”的天下,那些傳統的、文質彬彬的士大夫們妥妥地被排擠、打壓。《長安十二時辰》裏有許多片段都能佐證這一點,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這個何孚與右相對峙的場景: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除了排除異己,財經官們為了夯實自己的權勢,也懂得平衡各方利益,該做小伏低時自也會適度放下手中的權力。譬如允許節度使可以自行籌錢,不讓既得利益集團覺得自己利益受損。(同書,第374頁。)
説到這兒,大家可能會想到另一個問題:嚴苛的税法從理論上講也會傷害官僚貴族的利益。那這些財經官們豈不如商鞅一般,會折損於自己所立的法?然而卻沒有跡象能證明這一點。在《聚斂的迷思》中,作者特地描摹了一段劉晏與門生的對話來説明這一問題。
門生問道:“老師,您覺得朝中官員有否因為户部興革而造成金錢、資產的損失?”
劉晏答曰:“國朝開國以來以迄玄宗治下,大門大户的官員經營普遍欠佳。照理説,玄宗朝户部興革之事於他們沒產生什麼切膚之痛才對。事實上,就我所知從開元九年到天寶十五載,像盧懷慎、杜暹、李元紘、張嘉貞、王丘,以及潘好禮等人,都沒有田產。我相信,這絕非少數例外,而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老師是説,改革來、改革去,對大户官員們來説,沒有什麼好損失的嗎?”
“可以這麼説。你當還記得我們談過的有關關內屯田與否的論辯,多數官員如關切他們薪資的漲調問題,就可推知,他們普遍偏窮。”
“這些官員中最富的當推盧從願。他不過有田一百頃,便被皇帝視為‘多田翁’。”
“那是宇文融向玄宗皇帝報告其事,皇帝才説出口的。可知一位官員擁有過多資產不是好事,否則宇文融不會使用一位官員的資產情況去打擊他。”
門生咋舌,劉晏遂解釋道:“玄宗朝幾位宰相,像姚崇、張九齡、張嘉貞等人在《誡子書》中紛紛告誡子弟勿置田產,理由是目擊許多達官貴人死後子孫爭產和怠惰之事,在這裏也可以看出户部興革並未限制官員購買田產。”
……
“這樣説來,除了職田有幾年見奪於朝廷,使官員薪資變少之外,官員的資產並未因户部興革而變少。”
“反過來,户部興革帶來更多貪污的機會,這對官員不僅無損,而且還意外發了橫財呢。”
(同書,第136-138頁。)
這段對話並非是歷史上真實發生的,但作者卻將許多史料囊括其中。可以説這個腦洞開得還是比較契合歷史實際的。
為什麼財經官總是難以善終?
討人嫌的奸相李林甫、元載最終未得善終。而上文提及的劉晏也在身死之後揹負爭議與罵名。唐代財經官們的人生貌似大多都以悲劇收場。
“元載的人生是個失敗人生,這注定了他的傳記文本是不會有好話的。在《舊唐書•元載傳》文本中許多不載的部分,經上述仔細推敲,史官還真漏載許多重大事情呢。公元七七七年陰曆三月,元載以專橫被殺。他的親吏和所培植的財經接班梯次如楊炎等人,不是死,就是外貶。後來楊炎班師回朝,第一個要對付的人就是劉晏,以其是元載案的主審故也。劉晏死於七八〇年。在楊炎,是為故主復仇,在千百年後的今天讀者看來,這是在摧折帝國棟樑呢。不論如何,元載、劉晏的去世以及第五琦晚年處身外郡不得歸朝,而且在七七〇年先過世,這意味着一個財經美好時代的結束,未來是財經官遭逢腥風血雨的嚴峻年代。”(同書,第72頁。)
今天,我們該如何理解他們的宿命呢?這也是《聚斂的迷思》想要探討的問題。在作者看來,他們難得善終,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成為了皇帝的“棄子”,最後被士大夫們用“橫徵暴斂”、“欺君罔上”的嘴炮打下去了。
作者對於他們還是抱有“理解之同情”,認為他們的存在是時代的需要。正因有他們思考國家財政的充實之道,唐王朝才能在玄宗朝及之後繼續續命。肅宗、代宗兩朝正處於內戰和戰後修復階段,朝廷更需要擅長理財的官員解決錢糧問題。在這種形勢比人強的狀態下,主持戰時財務事務的元載、第五琦、劉晏之流,必然存在,也必須存在。(同書,第374頁。)
關於第五琦還有個故事值得一説——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公元755年,安祿山起兵叛唐,李唐王朝的權力中心內部急劇動盪。太子李亨終於逃脱了父親李隆基的掌控,宣佈即位為帝,尊父親為太上皇。
事已至此,李隆基只得同意兒子的安排,並派房琯等重臣攜傳國玉璽前去輔佐肅宗李亨。李亨當即便任命房琯為宰相。戰時經濟本就蕭條,肅宗朝只能通過徵收商税、酒税等方式勉強應付軍隊及朝廷的基本開支。監察御史、江淮租調使第五琦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肅宗重用,負責為朝廷理財。
具體怎麼做呢?第五琦想出的一個辦法是鑄新貨幣“乾元重寶”,使得一個新錢值十個舊錢,以此通過通貨膨脹的方式將民間的錢聚集到國家手中。對於第五琦的這些作為,房琯意見很大,便在李亨面前告了他的狀並建議撤換此人。在房琯看來,如此斂財純屬禍國殃民。肅宗對此並非不知,只是礙於錢糧之需非如此不可。他對房琯説了一句這樣的話:“天下形勢危急,六軍所需需要有人籌措。你可以討厭第五琦,但你想得出別的生財之道嗎?”房琯無言以對。可見聚斂之臣最堅強的後盾還是皇帝。而當這一後盾消失,自然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在結論部分,作者還説到:
“‘聚斂’的這頂帽子一旦安給對手之後,士大夫集團就坐等收割政治效益了。士大夫集團的批評很少發生在對手財經措施的失策上,他們多的是對對手的人格進行謀殺。唯一的政策辯論焦點落在底下一條紅線上:不可對農民重複課徵。但財經技術官僚動的腦筋是欲將商税納入擴充税基的計劃之中,其實是一種不蹈上述紅線的有效思路,卻又為士大夫集團所封殺。……我們好不容易碰到杜佑要多徵富商税,還有劉晏在救荒政策上,明訂貧下農户不經申請就可領災難救濟金的規定。這兩個辦法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台灣仍停滯在商議階段,卻是達到賦税公平的上佳政策。可是在八世紀的唐朝,杜、劉兩人是要受到士大夫集團的圍剿的。”
(同書,第375-376頁。)
這説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仍有可商榷之處。每項改革都有積極的一面,但如果過度放大這積極面,似乎就顯得對財經改革的苛政部分太過寬容。畢竟,站在普通百姓的立場看,這一羣體的崛起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唐代官僚政治、國家經濟畸形的表現。這種畸形最後也實實在在地由百姓買了單。即便説在財政改革中,官員們注意到了保護小農階層,但作者在行文也頻頻提及農民依然受着征斂的重壓。
次之,每一個歷史人物的所作所為都會在歷史長河的盪滌中被檢視。這一羣體中出了幾個極端的例子,如李林甫、元載,生前煊赫,死後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已然説明了很多問題。
複次,幹練的本事與賢能的秉性其實並非不可調和的矛盾,優秀的人才可以兼具二者。譬如玄宗早期用過的賢相姚崇、宋璟、張九齡都是如此。再如公元722年,時在相位的張説也面臨着籌措國防費用的任務。他主要想的辦法是削減邊境二十萬屯軍,使之務農。如此,雖未開源,但也節約了軍費開支。
而劉晏與元載雖都屬作者所説的“財經技術官僚”,但兩者在施政秉性上還是截然不同的,因而在審視兩者命運時,也應從不同的角度來詮釋,並不能劃一地用“財經官僚慘遭文官集團的圍剿”這一精英政治的視角來做總結吧。
就此而言,在解答“財經官為什麼難以善終”這一問題時,還是得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其中既有貪贓枉法、自作自受的情況,也有朝堂政治風向的誤傷、政敵的構陷。
先賢有訓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在歷史上,輕徭薄賦一貫是衡量某一時期政治是否清明的一個標準。不過,理想與現實總有差距。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是否仍應當堅守此道?讀者們大概自有想法,而這或許正是玄宗朝這段歷史最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個維度。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