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亮:“工業黨”意識,一種被忽視的人文精神
【文/餘亮,本文首發於《東方學刊》第4期,部分內容有刪節。】
在今天人們的一般印象中,“工業”這個詞很難與“人文”聯繫在一起。前者和沉重、強力、機械、污染等印象關聯,後者則指向詩意、優雅、情感、文化底藴等等,二者相去甚遠。然而流行於中國互聯網上的“工業黨”一詞卻裹挾着“情懷黨”一詞一起出現,在與後者的對比中定義自己,從而以文化問題的面貌呈現。
“工業黨”這個詞在社會主義歷史中曾經出現過,比如1920年代蘇聯政府以“工業黨”指稱一些工程師專家羣體,以破壞工業化名義逮捕他們(1)。1960年代蘇聯赫魯曉夫時期成立工業部門聯合黨委,以“工業黨”來指涉他們(2)。二者都是被動的命名。今天的“工業黨”概念則是自我賦名,身份意識強烈。與蘇聯沒有直接關聯,但與波瀾壯闊的近現代歷史的隱秘聯繫不絕如縷。馬丁·威納(Martin Wiener)在《英國文化與工業精神的衰落(1850-1980)》一書中沒有使用“工業黨”一詞,卻明確書寫了富有工業精神的英國資產階級如何被鄉紳貴族文化所俘獲和壓制,因此此書被中國敏鋭的論者視作“紳士馴服工業黨”的故事(3)。

當西方世界持續陷入去工業化困境,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歷史命題仍然在曲折中前行,並不斷叩問當代人的精神世界,“工業黨”是其中的一個迴響。若問工業黨羣體是如何產生的,原因很多,筆者觀察到的一個直接原因是:一部分富有家國情懷的理工知識人對近十年來由人文知識分子掌控的輿論領域之不滿。他們認為對方在事關國家社會發展的重大事項上缺乏科技常識,從而產生親自表達的願望。主要通過互聯網邁進原本隔膜的宣傳領域,憑藉專業知識,採取通俗的表達方式,開展“撥亂反正”的輿論和知識行動。
2011年甬温線動車事故是“工業黨”話語突入主流輿論領域的一次重大契機。當時,動車事故引發輿論界對高鐵建設山呼海嘯般的批判。主流“意見領袖”們在各類媒體上猛烈批判高鐵“大躍進”,批判國有企業體制,呼喊“等一等你的靈魂”(4),而初創的觀察者網逆流而上,不僅製作大量正面高鐵新聞,還邀請寒竹、江南、梅新育、馬平(任衝昊筆名)等一批具備戰略思維的作者從技術、戰略等角度討論並支持高鐵發展,內容細化到諸如專用客運軌道與客貨共用軌道的區別,公路安全指數與鐵路安全指數的差距,高鐵對區域經濟發展的重大改變等等,縱橫捭闔,深入淺出,為扭轉輿論做出貢獻,開創了別樣的話語陣地。
幾乎同一時間,被稱作“工業黨”作品的《大目標》(5)一書出版,“工業黨”概念廣泛浮現於互聯網輿論場。此後,在諸多事關科技、工業的重大話題上,包括中美貿易戰引發的輿論衝擊中,工業黨都發揮了支撐主流輿論的作用。
工業黨直面當今愈演愈烈的國際競爭,從“做成事”而不是“慰情懷”的角度思考問題。其言論的與眾不同吸引了大批讀者。土木工程專業出身的馬前卒(任衝昊筆名)成為問答網站“知乎”點贊前三的大V;化學物理專業出身的袁嵐峯以其雄辯且富於數據的文章為中國科技發展鼓呼,經過觀察者網編輯發表獲得廣泛影響(6);專注宏觀政策研究的賈晉京以其工業分析能力成就中國智庫界一派特色;計算機專業出身的陳經在十多年前對當下中國經濟的諸多成功預測被重新關注(7);製造業工程師出身的寧南山在個人微信公眾號中縱論中西產業,不斷斬獲“10萬+”閲讀量;陳平、路風、文一等強調工業創新的非主流經濟學家以其雄辯在網絡平台引發熱烈關注;一羣“工業黨”網民集體創作的穿越小説《臨高啓明》持續描述重建現代工業體系的過程,在網絡小説領域取得一定影響力;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科幻小説家劉慈欣也被看作具有“工業黨”思想……
究竟什麼是“工業黨”?開拓性著作《歷史轉折中的宏大敍事:“工業黨”網絡思潮的政治分析》一文給出的描述性定義是:
“總體上信奉工業化至上的理念及與之配套的政治經濟文化主張,以工業化和技術升級的線索重新組織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敍事,具有明確的民族主義意識,並形成了規模龐大的網絡粉絲社羣和亞文化。廣義的‘工業黨’還可以指代歷史上帶有‘技術專家治國’和工業主義色彩的思潮,也可以指代各國支持和實踐工業化的技術工程人員、政黨和政治力量。”(8)
這個定義從民族誌研究角度出發,描述表面上的思想光譜特徵,但是以“工業化”定義“工業黨”,有循環定義的缺陷,同時強化了“工業黨”給人的理工刻板印象。本文認為,認識“工業黨”的關鍵在於理解“工業黨”意識是什麼。“工業黨”意識深深植根於現代人複雜糾葛的精神矛盾之中,是世界觀,是方法論,也是精神症候,如同幽靈,遊弋於形形色色的“工業黨”論述之中,等待提煉。思考“工業黨”意識,有益於反思今天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政治問題。
一、工業文化的主體性自覺
中國不缺工業化問題討論,但“工業黨”這個概念具備強烈的“主體性”氣息,事關“做什麼樣的新人”這個重大文化政治問題。我們很容易觀察到,幾乎任何學科討論都會涉及相關的人格討論,如西方經濟學強調所謂“經濟理性人”,法學強調“法律人”,更不用説“文學是人學”成為文學專業的流行觀念。它們通過塑造主體人格來張揚各自的旗幟。理工學科原有“科學人”的概念,然而有關工業的討論往往和人格無關。在諸多工業化相關研究裏,工業只是一串串數字和報告,沒有生氣和人格精神。
在2017年1月工信部和財政部發布的《關於推進工業文化發展的指導意見》中,出現了幾個事關人格的説法:“弘揚工匠精神”“培育企業家精神”和“加強產業工人的職業精神培育”。
“企業家精神”興起於市場經濟時代,但其描述對象限於企業上層,關注點偏向財富和管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強調無產階級當家做主,塑造了工人主人翁意識,偏向底層,但在改革開放後相對弱化。在今天被傳媒輿論更多提起的是工匠精神,偏向於中產階級期待(例如2016年關於日本馬桶蓋的輿論,體現出中國中產階級對精緻消費品的需求,並將這種需求的滿足寄託於工匠精神(9))。需要注意的是,官方文件進一步提出了“大國工匠”概念,其大國意識與中產的工匠需求拉開了距離。
“工業黨”介於企業家和工人(工匠)之間。現實中的“工業黨”分子多屬社會中間階層(10),相比“中產”,用“基層骨幹”描述他們的層級更合適。“工業黨”意識作為新時代“基層骨幹”的奮進意識,一邊填補企業家精神的不足,一邊婉轉回應着工人當家做主遇挫的歷史。它固然從工業文化裏汲取養料,但是超越工業文化層面,滲透到歷史與現實的方方面面,涉及人生觀、世界觀和認識論、方法論。
作為被“工業黨”定義的對立面,很少有人會自稱“情懷黨”,但有很多自我指涉的近義詞廣泛流通,比如“小清新”“小而美”“小確幸”(微小而確定的幸福)等等,甚至可以包括整個1980年代流行的“詩人”概念。**“工業黨/情懷黨”這對看似戲謔的網絡亞文化概念背後,藴含人類對自身與世界關係的描述歷史,隱隱展現兩條相輔相成的人文脈絡。**我們很容易在各個領域觀察到近似的對立範疇,如政治領域的“現實主義/理想主義”,文學領域的“敍事傳統/抒情傳統”,甚至可以上溯到中國秦漢時期開始的儒法鬥爭。
當代“工業黨”和“情懷黨”的矛盾可以通過一個戲劇性的新聞來體現:一位上海白領厭倦了都市索然無味的生活,要去尋找桃花源隱居,“什麼現代設施都不要,只要有水有電有網線”(11)。類似新聞很多,然而水電網背後就是整個工業體系,很難被徹底掩蓋,卻被剔除出情懷的象徵體系。“工業黨”意識作為中產意識的一面,要和另一面——小資意識爭奪話語權,並把自身上升為一種情懷(例如馬平撰文稱“工業是天底下最浪漫的事”(12)),讓被遮蔽的價值體現出來,把被顛倒的再顛倒回去。
馬克思提供了一個建築學的比喻來描述生產方式與意識形態的關係,也就是耳熟能詳的“上層建築 / 經濟基礎”比喻。上層建築反映經濟基礎,但往往是意識形態式的虛假反映,用以維護和掩蓋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工業黨”思維方法的最重要特質在於,它具有一種拆解上層與地基之間隔斷的能力,從上層透視技術基礎,把融於實踐而並不彰顯的技術知識和經驗內化為思維“修養”,成為主體性的一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當代“工業黨”的主體性正是在他們眼中的對手“情懷黨”的蹙逼下產生的。
二、現代情懷的擴張
雖然“情懷黨”被“工業黨”作為貶義詞,但“情懷”並非像物理學概念“以太”一樣可以被驗證為虛假事物然後一筆勾銷,而是構成“現代”的基本成分。把“情懷”這個詞講清楚並報以理解非常重要。部分“工業黨”人士認為,醉心於懷舊、鄉愁的“情懷”文化來自農業生產方式(王小東、馬前卒、嚴鵬),有其道理,卻忽視了這是現代資本主義複雜運作的結果,內在於現代生活,遠非“農業社會情懷”可以歸納。
現代性一般被認為發端自西方,現代情懷亦如此。**“情懷”這個中文詞彙沒有合適的英文對應詞彙,同時包含了feeling和ideal的意味,是情感、理想、執念和一種自我審美態度的交織,泛指一種想象層面的自我主張和提升,一種超越現實維度的“心靈”取向。**最重要的意涵在於對某一對象包含着一份不捨的責任,如家國情懷、階級情懷等表述所體現的那樣。情懷是構造“新人”的重要元素,其所指經歷了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再到後冷戰時代的變遷。限於篇幅,梳理這個變遷將由另文完成,本文僅簡要言之如下——
工業化被看作現代性的基本特徵之一(13),無法離開現代思想文化和情感的土壤。在西方世界,啓蒙主義時代產生了對於客觀知識和個人情感的推崇態度和新的認識方法。啓蒙把人而不是神放在世界的中心,在認識論上反對從先驗真理出發進行演繹的神學思維邏輯, 倡導還原手段,從基本現象、事實着手,在這個基礎上歸納和提煉“真理”(14),這也為科學研究和工業生產準備了方法。
個人既然要擺脱宗教和封建秩序,就需要以“自我”為憑藉站立於世。這引發兩個方向的“自我” 建設,一個是韋伯、吉登斯等所謂的“理性化”,強調計算、精確、效率等等,一個是查爾斯·泰勒所謂的發掘深度內在的自我觀念,憑藉獨白、反思等形式來創造內心世界。**深度的個人內心——換一個詞——現代情懷,由此產生。**從盧梭的《懺悔錄》到亞米契斯的《情感教育》,從德國浪漫主義到“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15),文化領域的革命性作品無不可理解成一種情懷身份的建構。理性化與情感化,恰對應着工業意識與情懷。
霍布斯鮑姆認為近代西方世界發生了政治與經濟的雙元革命。那麼在個人領域,也發生了知識和情感的雙元精神革命。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權力)”,是“啓蒙”的典型觀念。同樣,情感也是力量。二者互相生成,構造現代人精神主體,讓他們帶着知識和情懷去開拓世界。在一些研究者筆下,這種構造被直接稱作“工業啓蒙”(16),例如韋伯從新教倫理角度想象了一種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個人工作精神,是為討論工業啓蒙的典型。
然而構建新情懷不止是資產階級新人的任務。資本主義和工業化擴張帶來劇烈的社會變革、剝削壓迫、殖民衝突等問題。受到衝擊的不同勢力和階層,從舊貴族到工人平民都發起反抗,文化與情感排斥最為直接。舊勢力需要披上新的晚禮服,受害者等待新的救世啓示,由此誕生出保守主義、社會主義、後現代主義等多種面向的反制思想,並形成各自的“情懷模式”,彼此複雜糾纏。
馬泰·卡林內斯庫在《現代性的五副面孔》裏劃分了兩種現代性,一種是資產階級現代性, 與理性、科學、效率、精確、功利關聯,另一種是美學現代性,以浪漫派為代表,以批判資產階級現代性為宗旨,與主觀、綿延的自我、頹廢、反叛、無政府主義、為藝術而藝術等觀念密不可分(17)。第一種現代性來源於韋伯所謂的“工具理性”,當中顯然包含了工業需要的人格品質;第二種現代性直指當代小布爾喬亞情懷。二者看似你死我活,卻互相激發。馬丁·威納同樣指出,這是“中產階級兩副面孔間的文化競爭”(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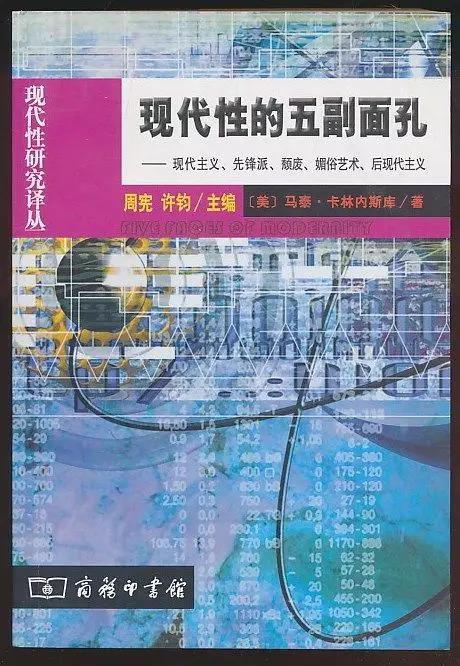
西方現代性隨着殖民擴張一波一波向外擴散、衝擊。工業與情懷之張力,在西方世界內部有其限度,在後發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中國則獲得了新的維度。在中國,我們可以把從秉承格物致知理念的洋務運動到改造國民性的新文化運動,再到社會主義建設和新人改造都看作是呼應雙元革命的不同環節。
社會主義實踐遭遇的挫折及其自我改革(例如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新的情感後果。套用列寧的觀點,“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現代市場經濟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着小資情懷。**支撐現代社會的工業基礎,在現代文化世界裏則普遍被看作壓抑性的存在。**當代中國“工業黨”意識經歷過社會主義實踐的浸染,依然具有革命意識特徵,超越了一般以個人利益為核心的市場理性,因此有被保守的日常生活和消費主義文化排擠出去的危險。**在應然層面,具備工業思維本應是現代人的基本素養要求,但在實然層面,工業思維則總是遭到現代情懷的拒斥,在多數人身上處於非自覺狀態。**需要認識到,“工業黨”意識正是在全球去工業化趨勢和西方主流自由主義話語衰敗的背景下興起的。
三、“工業黨”意識對主流人文精神的挑戰
思考當代中國“工業黨”意識,不能忽視中國獨特的思想文化和社會基礎:
第一,回溯歷史,不難發現即便在重視道德教化勝於格物致知的儒家內部,也有經世主義對道德主義的鬥爭。**當代“工業黨”對實踐性的強調,內涵於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方法路線之中。**羣眾路線,實踐理性,過去以階級政治名義出現,包含着避免知識分子脱離工農羣眾和生產實踐的訴求。“上山下鄉”和“學農學工學兵”固然在操作上出現巨大錯誤,但是在今天,知識分子與一線結合仍然有堅實的必要性。“工業黨”話語以潛在的方式接續了社會主義知識改造的訴求。
第二,中國有全世界數量最多的工程師。根據教育部發布的第一份《中國工程教育質量報告》,截至2013年,我國普通高校工科畢業生數達到2876668人,本科工科在校生數達到4953334人,總規模已位居世界第一(19)。 在英國,與鄉紳理想辯論的人多屬學者或者統治階層內部人士,而中國的“工業黨”活躍分子往往來自社會基層和中層。
另外,隨着中國崛起,中美關係出現對抗,維護中國自身道路獨立性的呼聲漸高,“工業黨”思潮逐漸從現代化理論思潮當中獨立出來。同時,因為產品和技術思維隨着中國製造的崛起和互聯網創業熱潮而廣為傳播,“工業黨”意識就具有更廣泛的發展基礎,與主流情懷的衝突也不斷產生。以下重點從這種衝突中,梳理出“工業黨”意識對主流人文意識的幾大挑戰,同時藉此認識其自身的若干特徵。
1.挑戰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區隔意識
“工業黨”受到來自傳統右翼(自由主義)和左翼兩邊的批評。右翼認為“工業黨”意識是國家主義的變種,只重視集體、組織,忽視個人。這只是源於自由主義者恐懼意識的習慣性誤解。值得關注的是來自左翼的批評:“工業黨”只講生產力,不講生產關係。在《讀書》雜誌舉辦的一次研討會上,吳子楓認為:“唯科學技術論、唯生產力決定論——這是工業黨的觀點。”(20)在另一次文學研討會上,周展安認為:“所謂‘工業黨’的社會實踐,強調富國強兵,做實業,這是一個從北宋啓動到明清時候發展的實學思潮的當代表現,到了晚清因為民族國家的崛起表現為金鐵主義,表現有很多,這個東西我覺得是比較值得警惕的。”(21)
這裏的關鍵問題不在於“工業黨”是不是不講生產關係,而在於批判者在認識論上對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機械切割,以及由此產生的萬能式批評。語詞的截然分離,讓人忘記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兩個詞本是作為生產方式的兩面,在現實中互相結合,絲絲入扣。****技術與組織、產權等密不可分。
這個割裂更是社會主義歷史上政治與技術的緊張關係的一個迴響。回溯新中國1949年到1979年的政治經濟實踐,一個重要特點在於警惕技術的中立化,強調生產和科學技術發展的社會主義性質。工業化和階級政治辯證地交織在一起,才有了諸如工人當家做主,“兩參一改三結合”“鞍鋼憲法”等積極嘗試。然而社會主義實踐困難重重,“文革”是對困難的激進反應,最終以“政治掛帥還是經濟掛帥”這種極端衝突方式呈現,反而割裂了技術與政治的有機關係。
技術在社會主義文化政治裏扮演了一個曖昧的角色。十七年文學對技術的角色有積極探索。例如在經典小説《創業史》中,技術員在鄉村改造過程中扮演了國家意志的角色(22)。在小説《百鍊成鋼》中,技術探索成為工人自力更生的主人翁精神的體現。到了“文革”時期,主流文學往往把技術人員設置為反動的“白專道路”代表。縱觀改革開放前的文化場域,技術可以是正面的國家意志或主人翁精神,可以是反面的白專道路,但技術不是技術本身。
技術的“去政治化”是錯誤的,但筆者認為,對技術的“去技術化”理解同樣是一種誤區。我們需要理解,技術是人類對政治、經濟、治理實踐中的智慧手段和權力運作的凝練,相比當代左翼關注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問題,“政治的去技術化”同樣是嚴重問題。在“文革” 後期,以鄧小平“治理整頓”為代表的專業主義道路最終勝出“抓革命促生產”道路,其中的經驗教訓尚未得到左翼的真正汲取。
今天,割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技術與政治的認識論,進一步呈現為圍繞發展主義展開的批判。
21世紀初,香港曾發生左翼文化研究學者和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的辯論。言必稱哈耶克的香港新自由主義者暴露了自己的意識形態教條。左翼則以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許寶強為代表。他出版了《資本主義不是什麼》一書,從第三世界尋找另類發展經驗,比如稱讚印度一些地方低GDP發展的幸福經驗(23)。
當代左翼常被指責為只破不立,只能批判而不能給出方案,《資本主義不是什麼》想要打破這個困境,嘗試提出新方案,然而這個“方案”並不能回應印度的現實。低GDP發展背後是印度的政治經濟社會落後、人均壽命低下。一位左翼學者曾寫下游記稱讚印度的和諧,“不只牛,猴子、狗、各種鳥……動物們都自由自在地在城市裏生活着,看上去倒是與人類和諧共處,相安無事”,並批評莫迪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正在改變這一切(24)。“工業黨”代表人物毛克疾則用數據顯示印度的狂犬病致死率世界第一,動物和諧只是表象(25)。印度人追求發展的訴求日益強烈。在互聯網上,印度的 GDP 增速被熱議。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前院長馬凱碩預測中國和印度將成為新的超級大國(26)。中國高新企業紛紛去印度開拓市場。中興前印度高管汪濤從產業和市場開拓者的角度細述印度方方面面,獲得大量點擊(27)。左翼批判理論迴避了GDP以及國際競爭這個堅硬內核,從而使其敍述感召力遠不如“工業黨”話語。
學者潘毅在改革開放時代的工人研究方面獨樹一幟,曾親自走進工廠流水線打工,積極參與實踐,提出了“宿舍勞動體制”概念。然而這種實踐體驗被學院“生產關係”視野包裹, 聚焦於壓迫性體制和工人的困苦,從中尋找反抗空隙,較少關注產業特點和工業目標達成。問題是,當代學院左翼在遇到工人問題時總是做出千篇一律的言説模式:“一邊是國家權力,一邊是全球資本,工人和左翼處在二者夾擊中。”不能討論諸如大國芯片競爭, 富士康與全球半導體產業變遷的關係及這個過程中工人階級的命運和機遇。“工業黨”的討論則會細化到諸如國產芯片在多少納米工藝上遇到難題,芯片工藝對人的素質要求是什麼等等(28)。 張慧瑜批評今天的“工業黨”敍事裏看不見工人(29),這是個切中要害的批評,但反過來,左翼的工人敍事裏也看不到工業。
批判“發展主義”已經成為文化研究學科的一個基本訴求,“對於改善人的生活狀況而言,除現代化和工業化之外,有沒有另類的發展(或不發展)的可能?”(30)這個訴求在實際運作中再次被小資情懷徵用,變成不要污染,不要衝突,甚至不要一切發展,只要一種輕鬆幸福生活的態度。今天在西方,建基於左翼自由主義的“政治正確”觀念因為脱離現實而遭到廣泛詬病, 正如“ 白左”一詞的遭遇所呈現的(31)。我們需要認識到,部分學院左翼同樣過於追求完美的思想和説法,以至於很難認同任何現存事物的合理性,從而形成了另一種僵化的政治正確。
批判理論具有精密思辨的優勢,但也需要有“工業黨”式肯定性論述來充實心臟。工業化如何與社會主義結合,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論題,如果缺少對生產力和技術知識的理解,不理解如何做成事情,只陷入抽象的生產關係批判,就難以有效討論。從地下的水電管線到天上的飛船火箭,基層“工業黨”往往從事過一線生產、研發工作,至少在生產力上更瞭解事實,擁有學院人士缺乏的實踐體解。
實踐理性本是從馬克思主義到鄧小平理論所強調的要害。只有對實踐以及實踐知識的感知才能將被語詞分開的事物重新結合起來,從而夯實對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政治與技術的理解。這是“工業黨”對已經規制化的社會科學的一個挑戰。
2.挑戰文理工區隔與通識教育侷限
“工業黨”與“情懷黨”的區隔可以在現代學科領域劃分中找到映射。當代人文與理工學科高度分化,這被認為是知識爆炸以及學科自覺意識發展帶來的後果,但其中也包含了隱蔽的文化政治鬥爭因素。如前所述,英國工業革命之後興起的英國文學,實質是貴族階級為了和資產階級暴發户爭奪影響力而發明的工具。一種試圖凌駕於事務科學之上的人文學科由此呼之欲出。早有學者如英國人阿什比注意到“‘學者—紳士’與‘實幹家’之間的文化衝突”(33),“一些文人學者堅持認為科學家和工程師需要‘文化的同化’與‘人性化’。他們推進旨在挑戰和解構科學與技術的意識形態:後現代主義、文化相對主義、(愛丁堡學派)強綱領、科學知識社會學、社會建構主義,等等。”(34)
當代“工業黨”顯著地跨越了文理工知識分子疆界,頻繁闖進公共問題討論,以實際行動反對人文學科對實務學科的凌駕。由此帶給人文學術和教育機制的一個挑戰就是:要求理工人士“人文化”的同時,是否更應該要求人文人士“理工化”?換言之,“理工”知識是否應該被納入“大人文”範疇?
中國的教育改革已經呼喊和實踐了很多年。無論是官方倡導的“素質教育”,還是部分學者提倡的“通識教育”,宗旨都在於克服工具理性,改變人文教育建制僵化,避免單純專業教育,培養健全人格,追求全面發展。
1999年發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文件中, 對“全面發展”的表述非常突出。全面發展的一個含義是文理兼備。流行的通識教育已經踐行學生選課時文理互通,看似是一種進步,但是在“工業黨”思維觀照下,一些誤區也呈現出來。
第一個誤區是注意到“文理”兼備 ,卻沒有意識到“理工”兼備和“文理工”平衡。
技術(工科)與科學(理科)不同,是一種不斷進化的技藝。複雜性科學專家和技術思想家布萊恩·阿瑟認為,技術和科學有交叉,但很多時候平行發展,遵循不同的邏輯。技術具有生物進化的特性——多種實踐摸索並行,大部分失敗,成功者也無法一勞永逸,必須持續適應新情況,不斷積累,直到下一次進化,週而復始(35)。歐陽瑩之在《工程學:無盡的前沿》一書中這樣區分工科與理科——與實驗室科學家不同,工程師要面對現實約束去解決問題,具有極強的實踐性和切身性。瓦特等改變世界的工程師均非科班出身,而是在勞動實踐中創造出了成果。

工業、技術知識因為其強烈的實踐性而區別於人文學科知識,尤其是一些已經意識形態化的學科,可以從文字到文字,從概念到概念。諸如文科的“理性人”“自我”“自由”之類概念表現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形態(雖然常常是虛浮的),便於流通。美國政府展開對中國“千人計劃” 中的理工科學者的約束(36),嚴格防範技術知識的流通。但是對人文學術領域的國際交流很少控制,任人拿去各種西方概念、理論而毫不擔心。這可以看作是兩種知識性質差別的一個註腳。
缺少實踐磨練的全面發展只是一個美好幻想。而今天的通識教育往往是讓理工科學生學一點人文知識,讓文科的學生學一點科學知識,忽視了工科的知識和方法。更加根本的問題是,當今人文學科普遍地被一種不自覺的區隔所束縛——一些知識被認為是理工知識,不進入人文視野。
我們應該毫不猶豫地把工程學知識看作人文知識,把技術文化看作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正如西方人文主義時代的大師把工程學看作人文能力的一部分,代表者如達·芬奇。“工程技術作為一種創造性和科學性的活動,它通過改造自然以服務於大眾的需求和願望,具有自然和人為的雙重維度。”(37)與自然科學的純然主客二元劃分不同,工程學需要為人服務,總是把人的主體性放在考慮之中,工程學也就天然帶有人文屬性。
工科實踐裏包含了細微的人文情感結構。例如芯片開發製造行業對人的素質要求極高。試摘錄網上一段談芯片產業的話:
“最重要的是一次投片的費用最少也要數十萬元,先進工藝高達一千萬到幾千萬。如此高的試錯和時間成本對一次成功率的要求極高,不得不把流程拖長,反覆驗證,需要多個工種密切配合,團隊中一個人出錯,3個月後回來的芯片可能就是一塊兒石頭。修改一輪,又3個月出去了。與試錯成本高並存的是排錯難度大……一顆手指甲蓋大小的芯片,裏面有上億個晶體管,而最終能在電路板上測量到的信號線卻只有十幾根到幾百根。如何根據這少得可憐的信息,推理出哪個晶體管設計錯誤,難度不言而喻。試錯週期長需要邏輯嚴謹細緻的工作態度,排錯難度大需要一套科學的實驗方法。而這兩方面恰恰是國內教育的軟肋。過分重視知識的記憶,而忽略邏輯和方法。”(38)
這樣的芯片知識並非純客體知識,而是體現出了對人的要求。我們需要反思,工程師人格難道不應該被重視人格培育的通識教育、文化研究教育納入視野?技術進化永遠處於“搖搖欲墜”狀態,也正因此需要不斷努力,以免一步落後步步落後,這樣的觀念難道不應該被納入世界觀和認識論教育?人文專業擅長討論人的主體性,往往落腳於日常生活,為什麼不能納入工業生產的維度?文科博士每到春節年關醉心於抒發鄉愁,為什麼不能討論高鐵等現代交通對人文的影響?今天越來越多的人質疑,素質教育難道就是琴棋書畫和情商教育,而科技素養只是一個理工科教育問題?我們需要維護一個現代常識:科技素養才是最重要的現代“人文”素質。
**技術知識及其實踐知識被排除出人文專業教育,只從屬於理工學科,是一個巨大的結構性錯誤。**人文不是指一套固定的知識和邏輯,而是一個讓不同認識論和方法論博弈的場域。必須要建立一種人文與技術合一的通識教育,倡導對實踐知識和技能的尊重以及對人文的廣闊理解。正如《工程學:無盡的前沿》以其科普姿態展示出的,文科人士理解基本的理工科知識方法並沒有門檻,關鍵在於是否願意。想要把對技術的理解轉化為技術文化來傳播流通, 需要難度較大的中介工作,這應該是人文學者與理工學者共同擔當的任務。

第二個誤區是流行的通識教育理念對“功利”的片面排斥。
李曼麗、汪永銓《關於“通識教育”概念內涵的討論》是通識教育研究領域的一篇代表性文獻, 在知網上被大量引用(截至2019年3月被引用493次),李曼麗的代表著作《通識教育——一種大學教育觀》被引用623次(根據百度學術查詢)。其中關於通識教育的定義被廣為引用——“簡言之:就性質而言,通識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組成部分,是所有大學生都應接受的非專業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識教育旨在培養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的、有社會責任感的、全面發展的社會的人和國家的公民;就其內容而言,通識教育是一種廣泛的、非專業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識、技能和態度的教育。”(39)在此,“非功利”被看作通識教育的屬性,引用者往往做進一步的割裂,用功利/非功利、做事/做人等對立範疇來描述專業教育和通識教育的區別。流行語“培養自由而無用的靈魂”可謂這種時尚的典型。
功利不是一個壞詞,對功利的追求才導致生產力的發展。需要區別的是隻為個人的功利還是社會的功利,正如馬克思強調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應該統一。一概排斥功利的心態是一種虛偽意識。
對非功利的偏執幻想可能是東亞“勤勞革命”的一個副作用。人們用“地獄模式”來形容東亞人生活工作的刻苦。對非功利的嚮往,可能正是為了平衡辛苦工作而產生的意識形態,以便依靠幻想來疏解身心壓力。然而這在意識形態上造成了扭曲,使得人們不能正確體驗生產與勞動。長期來看,會如同英國鄉紳文化那樣破壞經濟社會發展的文化基礎。在當下,其對教育改革的有害影響已經出現,比如傳統理工強省上海、浙江高考考生棄考物理現象嚴重(40)。1980年代,民間流行的學科信念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今天氾濫民間的是各種濫竽充數的國學班、語文班。今天的素質教育觀念往往把一種觀賞價值當作培養目標,熱衷於提倡琴棋書畫吹拉彈唱, 甚至有教育主管者亦熱衷於一味提倡音樂書法教育和減負,從娃娃就開始割裂做人和做事的關係。
歐陽瑩之指出,工程師在西方長期被所謂人文“貴族”歧視。她駁斥文化“貴族”加諸工程師頭上的“功利”“粗暴”“不近人情”等標籤,更是對後現代主義解構文化提出批評,對重文輕理傾向表達了警惕(41)。一個社會的價值觀傾向有其生產關係基礎。今日出現的重文輕理趨勢背後,是製造業與金融業的生產關係博弈。在西方國家,金融業與製造業失去協調關係,精英熱衷於通過金融霸權和伎倆從全世界賺快錢。這種趨勢在中國也有苗頭,製造業已然被很多人視作低端。人們推崇創新,卻經常把創新看作可以脱離製造業基礎而存在。事關製造的知識被看作灰暗的知識,不符合人文學科的“優雅”品位。這種意識反過來導致資源錯配,加重文理區隔,製造業被排擠。
綜合以上兩大誤區可以看到,對功利的一概排斥,與對理工教育有意無意的削弱之間存在某種聯繫,似乎人文素質教育是非功利化的、高雅的,理工教育則是功利化的、世俗的。功利與否不應該是判斷人文精神的標準,這不止是教育問題,而是涉及到根本的現代人生活觀問題——
3.挑戰有情與有用的倫理觀區隔
一位文學教授在其頗有影響的文學史代表作中區分了“有情”與“事功”。“事功”不難理解,而“有情”在其筆下指一種與政治史詩敍事相對,忠於個人內心的抒情傳統,是一種被政治事功壓抑的現代性。“歷史喧譁之後,一切灰飛煙滅,但或有一二‘有情’聲音能夠縈繞不去,成為一個時代最後的啓示?”(42)作者固然暴露出歷史虛無主義,但“有情”與“有用”的關係確實始終纏繞着現代人。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感情作為人類的特徵之一,當然是無需置疑的存在。需要被批判反思的,是雷蒙·威廉斯意義上的“情感結構”。“有情” 已然成為當代中國人文精神的核心要求。這其中既有古代天人合一、感時傷物傳統的原因,也有現代政治的原因,例如改革開放前人們對高壓政治不滿,從而歡迎以人道主義面目出現的“有情”。但今天的“有情”主要源於一種與資本主義日常生活方式聯繫的幸福至上主義。對綠色、環保、動保、和平、福利、自我、心靈、快樂教育、休閒生活等等的流行訴求都歸屬於此。一度刷屏的央視記者街頭採訪問題“你幸福嗎?”可以被看作一種道德律令般的要求。
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追求有用,卻在意識形態裏避免有用。事功幾乎被等同於利益和投機。但恰恰是不滅的事功讓“有情”有了物質基礎。只是人們往往忘記腳下的基礎,漂浮於情懷的樓閣中。
“工業黨”要把被顛倒的世界顛倒回來。任衝昊(馬平)在《工業化時代何謂江南小鎮?以蘇州為例》一文中提供了一個“顛倒”範例。所謂杏花春雨江南,在一般人文觀念中往往和古典、詩意關聯。然而建築系出身的作者通過歷史對照和數據説明,蘇州的江南美景正是新中國基建帶來的結果。過去的蘇州沒有下水管網工程,沒有像樣的市政管理,雜亂無章,臭水遍地, 一個現代人若真的置身其中會難以忍受(43)。所以除了氣候、地形等自然稟賦,工業基建才是江南“有情”的來源,只是深埋地下,被上層建築所掩蓋。
流行讀物中關於西藏雪域高原的幻想是另一個典型。曾經在西藏工作過的學者強舸問道: “當你感慨磕長頭的虔誠靈魂時,可曾想過他們身下的公路是誰修的?”他指出頻繁的藏傳佛教朝聖行為實際是改革開放後發明出的事物,因為過去貧瘠的道路和物質條件根本無法支撐這種朝聖行動,是新中國艱苦卓絕的修路運動帶來了這個現象(44)。現代化支撐了情懷,但這個情懷又反噬現代化自身。
對“工業黨”的指責不乏“無情”之辭,比如“如果説小清新是過分強調人的價值,那麼工業黨無疑是在過分忽視了人的價值”。甚至升級到手腳和靈魂的區別——“工業黨是一個國家的軀幹和雙手,但是別忘了,情懷黨是一個國家的靈魂和大腦。如果説工業黨是幹活的,情懷黨就是想事情的。”(45)
這樣的評價,錯誤不只在於認為“工業黨”意識不關乎個人幸福,也不只在於強行區分勞力者與勞心者這種腐朽意識,而在於意識不到“工業黨”思維背後有一種危機意識。它提醒人們,不要在對幸福的浪漫憧憬中忘記生死存亡的危機仍然可能來臨。幸福值得追求,但不能忘記艱辛的意義,不能忘記“承擔責任”是一種需要通過實踐磨練而非高談闊論來習得的能力。這種危機意識甚至與馬克思主義的未來意識也產生了差距,後者嚮往一個終將出現的幸福烏托邦,所有人可以“上午打獵,下午釣魚,晚飯後從事批判”。
科幻小説《三體》難得創造了可以表達“工業黨”情懷的文學隱喻。“不知什麼時候開始,人類有了一種幻覺,以為生存成了唾手可得的東西。”(46)只有在這個幻覺的基礎上,人們才能把主要想象力都用在對日常幸福的斤斤計較上,而忘記了生存基礎並非一勞永逸永遠存在, 人類會永遠面對挑戰。
陳頎在評論《三體》的文章中認為:“末人們傲慢地自以為‘我們已發現幸福’,殊不知維持他們的普世道德感和愛心的是徹頭徹尾的自私,以及對人類生存的真正責任的逃避。”(47)末人,便是把日常幸福當作人生核心和終極目標的人。
當代人的幸福主義是一種與“歷史終結論”匹配的觀念,隱藏着一種默認,即可以建立不再有根本衝突和根本挑戰的生活狀態。即便有戰爭(局部)、災禍也都只是事故而已。所以他們只思考“永久避開衝突”的終極方案,不再思考“永久準備應對沖突”的方案。前者幻想一個幸福共同體,後者才意味着“命運共同體”。
兩種觀念的區別,對應着兩種事關經濟和政治本質的不同理解。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存在一種均衡的經濟制度,可以讓生產和繁榮永久自動地運作下去。這種觀念自然會要求一個程序正義型政府,或者説自由市場經濟的守夜人政府。而“白左”要求的是在分配領域執行福利手段來維持“小確幸”生活,由此自然要求一個政治正確型政府,或者説福利國家。部分左翼雖然強調政治經濟學,強調常態化的鬥爭,但其烏托邦理想中隱藏着希望永久消除痛苦的訴求,忽視生存哲學和發展哲學不可割裂。“工業黨”為生存而發展,更接近“落後就要捱打”的近現代史警鐘。
工業黨傾向的政治經濟學家強調顛覆式創新的重要性,因而重視演化經濟學與文化對經濟的影響。陳平從混沌物理學中汲取方法,強調經濟複雜性勝於經濟穩定性(48),面對大變局, 呼籲能打仗的“將才”來領導經濟變革和貿易博弈。孫滌在反思西方主流經濟學時提出,工於算計的理性人並不能帶來創新,帶來創新的是企業家非理性的“動物精神”(49)。“工業黨”意識就包含着一種生死拼搏的動物精神,鮮明區別於日常幸福主義中的“寵物意識”。從馬克斯·韋伯到馬丁·威納,貫穿着一個經濟學的理念,即文化,包括價值觀和意志力對經濟發展具有關鍵影響。馬克思主義強調的主觀能動性也暗合着這個理念。
大眾傳播領域的“工業黨”更是用一種極端的提問方式,表達出他們心目中的政治經濟問題本質——通信專業的學者方承志在其網絡長文《技術大停滯》(50)中,用關於復活節島的悲劇故事來説明,侷限於小島的社會制度、文化再發達,只要無法衝出小島,最終只能毀滅。袁嵐峯在接受“觀視頻工作室”採訪時被問到對2049年的期望,回答是“希望中國能引領世界科學發展,尤其是引領人類移民太空”(51)。劉慈欣則説:“不管地球達到了怎樣的繁榮,那些沒有太空航行的未來都是暗淡的。”(52)不存在終極的幸福,只有無盡的突破任務。“工業黨”的情懷就在於:面對永恆的生存危機挑戰,敢於不斷鬥爭下去的偉大氣魄。
這些樸素話語隱含了一種挑戰流行政治學的政府觀念。究竟什麼是好的政府?流行的説法有“民有、民治、民享”“法治”“最大責任政府,最小權力政府”等等。“工業黨”主張的是一個目的論的有為政府,其目標超越地球層面。這是一個國際主義或全球化主義也沒有的太空維度,看似科幻,卻以“降維打擊”的形式給耽於地表的人帶來啓示,是一種“高維度的現實主義”。
把視線從太空轉向地球環境,兩種觀念的分野導致了兩種看待緊迫問題的思路。例如在環保問題上,一種是市民階層的反工業化態度,表現在對化工項目的無差別抗議活動。這種態度往往也以產業升級的面目出現,表現為各地匆忙上馬各種華而不實的文化產業園區,以取代傳統產業園區。另一種是“工業黨”的思路,主張用進一步工業化和科技發展來克服工業化帶來的問題。
“工業黨”的現實主義態度往往被反對者批評為缺少理想。但我們不妨做一個類比。丘吉爾認為“民主是最不壞的制度”,這就是一種現實主義。張維為認為“最不壞”的評價標準不應該專屬“西方民主”,還可以用在很多領域,中國發展模式就是當今世界最不壞的發展模式(53)。同樣,“工業黨”發展觀不追求矯飾的美麗,可以稱作“最不壞的發展道路”。鄧小平時代的改革路線常常被歸結為一句話——“摸着石頭過河”,這句話的意義在“工業黨” 意識裏獲得了映照,如同工程學的一般方法:確定目標,圍繞目標尋找現實手段,而不拘泥於任何一種左或者右的教條。
文化多元主義是今天中產階級“有情”的一大內涵。《歷史轉折中的宏大敍事:“工業黨”網絡思潮的政治分析》一文提醒“工業黨”不要忽視多元主義合理性。這也是對“工業黨” 的一個常見批評,但也許弄錯了方向。流行於西方的文化多元主義包含合理訴求,在今天已然變成幸福主義生態圈裏的一支。恰恰是“工業黨”思維能夠提醒多元主義忽視了什麼關鍵問題從而導致失敗。“工業黨”思維擁有主線,多元主義忽視主線。
舊工業時代伴生等級森嚴的科層制,因而“工業黨”會被誤認為偏好一種等級結構而忽視多元。然而科技和經濟模式的發展已經革新了層級觀念。新經濟結構是一種網狀多元結構,但又有層級,相關論述很多,這裏不做贅述(54)。新經濟條件下的“工業黨”思維已經超越科層等級思維,成為一種有層級和因勢利導的多元思維,是對自然進化論中的多元競爭觀念的提升——在多元競爭的基礎上,必須把握趨勢找到合適的更高層級,而不是任其各自自生自滅。
“情懷黨”的多元則是一種並置,一種互不相干的消極多元,正如歐美世界如今成為種族大拼盤,各個族裔各行其是卻無法融合,衝突不斷,其結果也是一種“單元”——絕對的妥協和“愛”,消滅了人類的決斷能力,導致生死攸關時刻的失敗。這是自由主義多元文化的內在矛盾。
當中國處於內外交困的1917年,青年毛澤東撰文希望中國人要“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這句話在和平繁榮時期同樣具有意義。若要文明長存,必須要有一點“野蠻”能力,否則就會耽於幸福,死於安樂。有情與有用的關係,庶幾類同於文明與野蠻的關係。
四、一個總結:何為“工業黨”意識
行文至此,我嘗試給“工業黨”意識做一個提煉式的總結,儘管這未必是當下“工業黨” 羣體的普遍意識:其核心是對於經濟基礎和政治社會治理當中的技術和實踐過程加以自覺認知,並提升為上層建築中的思想文化構造,凝練為永恆奮鬥的意識。
“工業黨”意識是貫穿人類歷史的務實意識在現代獲得的新形式。它面向永恆的生存挑戰,具有濃厚的憂患意識,在當代則表現為民族競爭意識和發展突破意識;它反對廉價的道德與情懷,在當代則表現為反對圍繞個人日常不斷自我循環氾濫的幸福主義意識;它立足實踐,在當代則表現為科技發展基礎上的歷史唯物主義實踐理性,重視把實踐“體驗”轉化為知識而避免旁觀式批判。在方法上,把科技思維和工程實踐知識內化為一種人文思維方式,把被遮蔽的“基礎設施”重新轉化為上層建築視野的一部分,讓文化政治重新植入生產和技術實踐的土壤中。
“工業黨”意識不止是現代史上工業與反工業力量博弈產生的意識形態後果,還是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敍事主義和抒情主義歷史張力的當代迴響。它以當代世界最具力度的“工業化”為宿主,不自覺地融合了專業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等諸多意識形態和思維方法。作為中國崛起背景下中間階層的奮進意識,不只涉及國族和生存意識,同時還是面對社會主義挫折經驗而產生的一種意識形態自我調整,從而具有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階段匹配的意識形態特徵。
正如汪暉對五四運動的評價——那是一場具有明顯政治動機的文化運動。在19世紀傳統的權力政治之外,開闢出了一個文化政治空間,暫時懸置國家政治、政黨政治、議會政治等權力政治範疇,讓家庭、性別、階級、語言、文學、勞動等社會問題浮出水面,重新確定了政治的地基,催生出新的政治(55)。“工業黨”思潮同樣以文化運動面目出現,卻反向擱置了左右對立、文化多元等政治議題,重新召回傳統的生存挑戰、科技競賽、地緣政治、文明衝突等議題,開拓出一個似舊彌新的文化政治空間。
“工業黨”無意識地革新了文化生產方式,但是對於文化政治尚缺乏自覺。在未來必須建立這個自覺,否則如果耽於技術知識本身而不能把自身上升為人文精神和話語權,並落實於實踐,也將陷入機械唯物主義的泥潭。
當代“工業黨”意識的誕生,就像科幻小説裏的機器人或者克隆人尋找自我的故事。懵懂的機器人漸漸從自為狀態向自覺狀態過渡,具有了自我意識和鮮活的主體性,在照亮世界的同時也需要照亮自我。“工業黨”當然也有自身的問題,它誕生於社會與思想的雙重危機意識,因此自身也是普遍性世界問題的一種症候,這將是另一個研究議題。本文僅粗淺拋出問題,以引發進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翻頁查看本文註釋)
本文註釋:
(1)〔俄〕列昂尼德·姆列欽:《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第77頁。
(2)聞一:《俄羅斯通史(1917-1991)》,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3年,第371頁。
(3)參見張明揚:《紳士如何馴服工業黨?》,載《財新週刊》,2015年第15期。
(4)童大煥:《中國你慢些走等一等你的靈魂》(2011年7月26日),騰訊評論,http://view.news.qq.com/a/20110726/000049.htm。作者為媒體人,這段言論在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
(5)任衝昊、王巍、周小路、白熊:《大目標——我們與這個世界的政治協商》,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年。
(6)可參見袁嵐峯:《中國科技實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國》(2015年8月12日),觀察者網,https://www.guancha.cn/YuanLanFeng/2015_08_12_330260_1.shtml。此文不僅得到廣泛轉發,還引起多位院士注意。
(7)《中國的官辦經濟》,陳經在2006年間寫成併發在西西河網,被網友整理成了PDF文件。2016年由中國發展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中對中國經濟的十大預測全部應驗。
(8)盧南峯、吳靖:《歷史轉折中的宏大敍事:“工業黨”網絡思潮的政治分析》,載《東方學刊》,2018年秋季刊(總第1期),第52頁。
(9)可參見嚴鵬:《富強求索——工業文化與中國復興》,第九章第三節《喧囂與騷動:馬桶蓋的奇幻漂流》,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6年。
(10)根據“工業黨”小説代表作《臨高啓明》的讀者組織的問卷調查統計,《臨高啓明》讀者中,大學及以上學歷的佔92.13%。目前生活於一線城市的佔43.7%,二三線城市的佔43.02%。讀者中正在上學的比例佔36.6%,已經參加工作的人數排名前三的行業分別是: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佔10.57%),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佔7.26%),製造業(佔6.38%)。家庭年收入在10萬以下的佔33.35%,10萬-100萬的佔63.57%,100萬以上的佔3.08%。參見知乎網:“如何看待澳宋第一次人口普查(《臨高啓明》讀者情況調查)的調查結果?”(2017年11月30日)。轉引自李強:《“集體智慧”的多重變奏——由〈臨高啓明〉看網文生產機制與意識形態之關係》,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18年第2期。根據《臨高啓明》小説自身對於“工業黨”主人公們的描述,這是一羣各行各業身懷專業技能卻不甚得志的年輕人。
(11)《37 歲白領裸辭尋找隱居地 要求有水電能上網》(2013年3月11日),新聞晨報,http://news.youth.cn/sh/201303/ t20130311_2963169.htm。
(12)見馬平:《工業是天底下最浪漫的事》(2012年8月9日),觀察者網,https://www.guancha.cn/ma-ping/2012_08_09_90013.shtml。
(13)例如,吉登斯的《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一書即持此觀點。〔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趙旭東、方文、王銘銘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
(14)參見汪暉:《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啓蒙運動》,載《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上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3年。
(15)參見〔德〕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張旭東、魏文生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
(16)“工業啓蒙”概念由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提出,參見嚴鵬:《富強競賽——工業文化與國家競爭》,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7年,第9頁。
(17)〔美〕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顧愛彬、李瑞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48頁。
(18)〔美〕馬丁·威納:《英國文化與工業精神的衰落(1850-1980)》,王章輝、吳必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28頁。
(19)參見施雨岑、劉奕湛:《教育部發布首份〈中國工程教育質量報告〉》(2014年11月13日),中國中央政府門户網站,http://www.gov.cn/xinwen/2014-11/13/content_2778139.htm。
(20)見王洪喆等:《政治經濟學·信息不對稱·開放源代碼——人工智能與後人類時代(下)》,載《讀書》,2017年第10期。
(21)郭春林:《第一屆全國青年文藝論壇轉型年代、青年與中國故事第三單元:“文藝前沿與未來生長點”》,知網會議論文庫,http://cpfd.cnki.com.cn/Article/CPFDTOTAL-ZYMS201311001005.htm。
(22)參見李哲:《倫理世界的技術魅影——以〈創業史〉中的“農技員”形象為中心》,載《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
(23)許寶強:《資本主義不是什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十章第一節,“不需增長的發展——印度的卡華拿邦的發展經驗”,第253頁。
(24)小疼:《印度行:感覺就像來自星星的醉漢》(2005年1月18日),觀察者網,https://www.guancha.cn/ XiaoTeng/2015_01_18_306634.shtml。
(25)毛克疾:《在印度,做狗比較幸福》(2014年10月21日),觀察者網,https://www.guancha.cn/MaoKeJi/2014_10_21_278157.shtml。
(26)可參見馬凱碩:《2050年世界經濟可能中國第一印度第二》(2013年11月4日),央廣網,http://china.cnr.cn/ygxw/201311/t20131104_514026825.shtml。
(27)參見汪濤:《讓印度通告訴您中印對峙背後的驚天秘密》(2017年8月9日),微信“純科學”公眾號,https://mp.weixin.qq.com/s/vWI8b9RtfECTp5dBGvAi3g。單篇微信文章點擊10萬+,點贊數超過5萬。
(28) 可參見《一文讀懂:真實的中國芯片產業》(2018年5月15日),電子產品世界,http://www.eepw.com.cn/article/201805/379875.htm;lynn0085:《終於有人講透了芯片是什麼(設計—製造—封測)》(2018年4月19日),CDSN博客,https://blog.csdn.net/lynn0085/article/details/80005716。
(29)郭春林:《第一屆全國青年文藝論壇轉型年代、青年與中國故事第三單元:“文藝前沿與未來生長點”》,知網會議論文庫,http://cpfd.cnki.com.cn/Article/CPFDTOTAL-ZYMS201311001005.htm。
(30)參見雷啓立:《序言:堅持一種可能》,載許寶強著:《資本主義不是什麼》,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
(31)在線俚語詞典Urban Dictionary的解釋是:白左是個中國表達,這個詞特指一些天真的西方人,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卻只為了滿足自己的道德優越感而提倡和平與平等。白左只關注諸如移民、少數族裔、LGBT和環境等問題。他們非常迷戀政治正確,他們為了文化的多元性,甚至引進一些較為落後的伊斯蘭價值觀。福克斯新聞主持人卡爾森稱白左對真實世界的真實問題無知。參見唐豔飛:《哈哈,中國向西方逆向輸出了一次價值觀》(2017年5月20日),觀察者網,https://www.guancha.cn/culture/2017_05_20_409300.shtml。
(32)可參見新聞《遼寧省監獄局:罪犯利用噪音作掩護,撬開會見室門窗脱逃》(2018年10月18日)跟帖,觀察者網,https://www.guancha.cn/society/2018_10_08_474658.shtml。
(33)〔美〕歐陽瑩之:《工程學:無盡的前沿》,李嘯虎、吳新忠、閆宏秀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44頁。
(34)同上,第145頁。
(35)參見〔美〕布萊恩·阿瑟:《技術的本質》,曹東溟、王健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
(36)參見《中國千人計劃“竊取”美國機密?英媒:嫉妒中國成功》(2018年8月12日),上觀新聞,https://www.jfdaily. com/news/detail?id=99711。
(37)〔美〕歐陽瑩之:《工程學:無盡的前沿》,李嘯虎、吳新忠、閆宏秀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頁。
(38)此文在科技圈流傳很廣,參見 https://news.pedaily.cn/201603/20160316394539.shtml。
(39)李曼麗:《通識教育——一種大學教育觀》,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8頁。
(40)參見陸一:《大道至簡:高考改革不應使選擇高度複雜化》,載《財新》,2018年第3期。
(41)可參見〔美〕歐陽瑩之:《工程學:無盡的前沿》,李嘯虎、吳新忠、閆宏秀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四章,“處在社會中的工程師”。
(42)王德威:《“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載《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三十三期(2008年9月),第84頁。
(43)參見馬平:《工業化時代何謂江南小鎮?以蘇州為例》(2015年2月1日),觀察者網,https://www.guancha.cn/ MaPing/2015_02_01_308193.shtml。
(44)參見強舸:《當你感慨磕長頭的虔誠靈魂時,可曾想過他們身下的公路是誰修的?》(2017年7月11日),觀察者網,https://www.guancha.cn/QiangGe/2017_07_11_417542.shtml。
(45)在豆瓣網的“工業黨”詞條下可以看到這些評論:https://www.douban.com/note/514584133/。
(46)劉慈欣:《三體·死神永生》,重慶:重慶出版社,2016年,第170頁。
(47)陳頎:《文明衝突與文化自覺:〈三體〉的科幻與現實》,載強世功編:《政治與法律評論(第七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四節,“文明衝突的末人敍事”。
(48)參見陳平:《文明分岔、經濟混沌和演化經濟動力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49)參見孫滌:《還要維持“經濟理性人”迷信,哪怕洪水滔天?》(2013年11月19日),觀察者網,https://www.guancha.cn/SunDi/2013_11_19_186786.shtml。
(50)參見資水東流:《範氏春夢中的地球工業文明:低熵體的困境和下一級技術台階》(2015年6月8日),百度文庫,https:// wenku.baidu.com/view/67b9969e5f0e7cd185253637.html?mark_pay_doc=0&mark_rec_page=1&mark_rec_position=2&clear_ uda_param=1。
(51)觀視頻工作室:視頻《2049年,中國的成功,會給全人類一個發展的新方向》 ,陽光寬頻網,https://www.365yg.com/a64462 49574829933070#mid=1572156053646350。
(52)見2018年11月8日劉慈欣在被授予2018年克拉克想象力服務社會獎現場的演講詞:《不管地球達到了怎樣的繁榮,那些沒有太空航行的未來都是暗淡的》,搜狐科技,http://www.sohu.com/a/274919682_658762。
(53)參見張維為:《中國模式可能是最不壞的模式》(2009年9月23日),鳳凰資訊,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zhongguojingyan/200909/0923_8129_1361006.shtml。
(54)可參見〔美〕凱文·凱利:《失控》,東西文庫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三章第四節“嵌套層級的優點”,第66—67頁。
(55)參見汪暉:《什麼是“五四”文化運動的政治?——關於“五四”的問答》,載汪暉:《文化與政治的變奏一戰和中國的“思想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