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雷:再看美國的月亮,還那麼圓嗎?
【文/ 田雷】
“起明,我隱隱約約有種感覺,這兒的很多事情,跟我們過去想的不一樣。”——郭燕,《北京人在紐約》第一集
有些歲月,種下問題;有些歲月,收穫答案。——美國女作家佐拉·尼爾·赫斯頓(Zora Neale Hurston)
教室裏,一名老年教師在講課,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鏡,中山裝略顯鬆垮,口袋彆着一支鋼筆, 黑板上粉筆寫着六個大字:“今日美國講座”:
“美國的種族歧視永遠不會消除。如果一個白人看見三個黑人男子同時進入電梯,他會在電梯門關閉的前一瞬間,逃出電梯。在白人看來,黑人永遠是懶惰、無知、野蠻的種族,那麼美國的華人呢,總該是聰明勤快吧,但是他們説,華人破壞了當地居民的工作機會。另外……”
就在這時,坐在教室後排的一位男同學打斷了他,那個年輕人早已搖頭嘆氣老半天了,終於忍無可忍,拍桌子站了起來:
“老師,您去過美國嗎?您是從書本里看來的美國吧?”
坐在男同學A旁邊的,是一位留着長髮的男同學B,這時候站出來附和:“對啊,老師,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這挑戰突如其來,讓講台上的老師有些措手不及,他有些疑惑:“你們兩個是哪個系的?”
A同學顯然不想理睬這個問題,他開始了自己的演講:
“所謂的American Dream,就是在夢想面前人人機會均等。全世界只有美國能做到這一點。”
老師沒有讓學生繼續講下去,他以長者的姿態給出了自己的人生經驗:
“年輕人,你畢竟too young,too naive!”
A同學果然不吃這一套:“老師,我一定會去美國的!I find out for myself !”
説完收拾書本,走出教室。

《中國合夥人》劇照
一
這場景,似曾相識,彷彿在哪裏見到過?沒有錯,它來自2013年公映的一部電影《中國合夥人》。A同學,就是影片中的“孟曉駿”,後來,他如願以償,到美國去追尋他的美國夢。還記得吧,他拿到簽證,如人生贏家一樣昂首走出使館,高呼“USA,here I come”,門口排成長隊的等候者無不投去羨慕的目光,此處確實有掌聲。離開中國前,機場送別,電影用男主角“成冬青”的旁白交待了孟的心聲:“孟曉駿説,他從生下來就在等着這一天。”還記得孟在走進安檢前的最後一句話吧,是,“我不回來了。”
這部電影,英文名翻譯成American Dreams in China,銀幕上的角色,包括三位追夢人為之奮鬥的“新夢想”,都不難在現實中對號入座,所映射出的東西比歷史還要更真實。影片中有個讓全場鬨堂大笑的片段,一個學生模樣的小夥子,多次被拒籤後,喊出了“美國人民需要我”這樣的金句,被保安強行帶離出場。確實如此,回到改革開放之初,由十一屆三中全會所開啓的第一個十年,是一個人上人都在做着美國夢的年代,所謂“千萬裏我追尋着你”。只是在影片中,“孟曉駿”終於還是回來了,人前“載譽歸來”,背後卻隱藏着一段遍體鱗傷的美國往事,按照整部電影的基調,他,作為“新夢想”的三大合夥人之一,最終還是實現了自己的American Dream,只不過是in China而已。
這場發生在師生間的代際衝突,在整部電影中,屬於很容易被進度君跳過的段落;但就本文所要討論的題目而言,某些線索放在今天可謂細思極恐,既隱藏着歷史的進程,也在訴説個人的奮鬥。“孟曉駿”當然不是一個人,他代表着“八十年代新一輩”的一個類型,那個“我一定會去美國的”類型。在那代人中間,“孟曉駿”千千萬萬,學而優的他們年復一年尋夢美利堅,學術界既是最初的容身所,大概也是追夢抗阻力最小的領域。以這些歲月種下前因,也就有了我們今天所收穫的後果——這40年來,我們讀過的美國書,很可能大都來自“孟曉駿”們的手筆,寫作或者編譯。
一開始,是他們厭倦了,在他們眼中,老一輩的“今日美國講座”,不過是不分青紅皂白地批判一番;繼而,他們中的幸運兒,很多想必歷經艱辛而不悔,終於踏足美利堅的大地,他們所做的,就是用最寶貴的學術時光為我們展示並營造了一個“美國”,那個當年在我們眼中光怪陸離的“美國”,如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片頭,音樂響起,時代廣場燈火輝煌,漫天雪花飛舞,曼哈頓島摩天大樓林立,布魯克林大橋在晨曦中已經車水馬龍,總而言之,那個“在夢裏你是我的唯一”的美國(當年的北京又是什麼樣子,可以參見大約同期播出的《我愛我家》)。結果就是,他們那一代在美國的見聞錄,就成為我們這一輩所讀的美國書。能到美國去看一看的,畢竟只是少數人,一個時代的精英弄潮兒;而我們能做到的,就是從這些美國書中“走遍美國”。這一代的旅美作家,在此意義上,都有一個共同的筆名“孟曉駿”,我們曾經通過他們的書寫,不僅是閲讀美國,還以美國為方法去理解到底什麼是世界、未來和現代化。
但到了今天,“八十年代”已經俱往矣,我們已經步入了一個新時代。向前看,“貿易戰”不是一個要不要打的問題,它已經來臨。假設我們現在要站在大學講台上,來一場“今日美國講座”,要是我們還只能按照“孟曉駿”們的書來講“今日美國”,比如孟氏第一條,“所謂的American Dream,就是在夢想面前人人機會均等。全世界只有美國能做到這一點”,這句話,在1980年代可以説得光明磊落,但到了今天,我未必可以説出口,因為我知道美國不是這個樣子的——我自己就翻譯了一本副標題叫“危機中的美國夢”的書。四十年河東與河西,某種意義上,反而是那位看上去古板僵化的年長講者説對了,他笑到了最後。終有一天,“孟曉駿”們認識到了自己年輕時的天真——未必是錯誤。當年長者講,“美國的種族歧視永遠不會消除”,這話擱在美國學界,不是一個再正確不過的論斷嗎?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客串老師的,其實是北京大學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唐曉峯教授,唐教授本人就曾在1986年至1994年留學美國,取得博士學位,西方哪個國家他沒去過,作為隱藏最深的彩蛋,他的兩分鐘客串,以及那句台詞“年輕人,你畢竟too young,too naive”,可謂神來之筆。
如題所示,貿易戰之後,如何讀美國書,這是本文提出的一個問題,而在進入這個問題時,我選擇同“孟曉駿”一起思考。

《中國合夥人》劇照
二
影片中,“孟曉駿”之所以再也聽不下去了,是因為他已經不再相信了。講台上那位老教授戴着黑框眼鏡,孟自己也戴着一副“眼鏡”,無形但卻有色:美國是批不得的,或者説,任何批評,不過只是故意批判一番。請注意,孟在此時的認識論非常簡單:“老師,您去過美國嗎?您是從書本里看來的美國吧?”這就有意思了,耳聽為虛,眼見方為實,書本里的“百聞”不如親自去美國的“一見”。電影到這裏,“王陽”還站出來,給了孟一記有力的聲援,“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有趣的是,實踐論原本是為了解放思想的武器,現在反而成為打擊不同意見的工具。這時,孟和王兩人渾身上下充斥着年輕人的理直氣壯,完全忘記了他們也沒有去過美國。仔細追究,最能概括孟之認識論的,並不是“王陽”補刀的那句,而是另一句家喻户曉的話:“想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親口嘗一嘗。”
親口嘗一嘗梨子的滋味,某種意義上概括了過去40年國人認識美國的方法論。遠觀不行,從書本中讀“美國”如霧裏看花,不排除有些書甚至有些教育只是洗腦;只有親自漂洋過海,才能看得真切,求得真經,獲得啓蒙。這些年我們讀過的美國書,以署名林達的美國三部曲為代表。這些書的作者筆下的文字之所以深深吸引並打動整整一代讀者,某一歷史階段甚至塑造了文化精英對美國的認識和想象,首先是因為他們是旅美作家。瞧,他們就在美國生活或讀書,因為人在美國,也就獲得了為我們講述美國夢的資質。

《中國合夥人》劇照
記得本世紀初讀大學高年級時,林達的美國三部曲成為我的案頭書,從《歷史深處的憂慮》到《總統是靠不住的》和《我也有一個夢想》,我對每一本都手不釋卷,幾乎讀到廢寢忘食的地步。當年,林達的美國敍事對年輕學子影響深遠,大到可以指引研究方向的選擇——後來讀研究生時,我投身美國憲法而義無反顧,林達在三聯的三部曲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劑定心丸。那些年的讀者不是盲目的,閲讀本身就是個披沙揀金的過程,放在當時,林達的敍事確實有很多閃光點。但今天回頭看,真正讓林達走到時代之風口浪尖的,也是三部曲最大的賣點,奧秘在於林達系列的副標題“近距離看美國”。在這三本書中,作者為我們帶路美國,其鏡頭是移步換景的,但機位和焦距卻保持不變,所主打的就是一個字“近”,越近越好,直至講述者把自己同風景融為一體。
説起“近距離”取景,劉瑜也是深諳此道的寫作高手。她是政治學科班出身,但成功之道仍根自於同樣的手法。劉瑜一系列近距離看美國政治的報刊文結集出版時,整本書就叫做《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門道就在這“細節”中,真要看清楚“細節”,唯有“近距離”,在此意義上,林達和劉瑜都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就我個人的閲讀體驗而言,薛湧也是繞不過去的作者,他的美國寫作,大致流行於林達之後和劉瑜之前,在本世紀起首幾年,尤其圍繞着2004年小布什和克林頓的總統選戰。薛湧的寫作,尤其是他對“文化內戰”的討論,令人大開眼界,而他最後結集出版的書,同樣是在吆喝“美國政治筆記”或者“美國社會觀察筆記”。所謂“筆記”,自我定位就是一種發自現場的報道。
林達的“近距離”、薛湧的“觀察筆記”以及劉瑜的“細節”,這些講述美國的寫作,都貫徹了“孟曉駿”的方法論,他們終於奮鬥到美國,終於親口嚐到了梨子的滋味。而他們的寫作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一時間躋身國民閲讀的爆款行列,不僅取決於作品自身的品質,還要看時代的風口,在具體的歷史進程中,“近距離”的寫作手法同當年國內讀者的“審美”觀是相得益彰的。為什麼“近距離”的筆記體,或如林達的寫作手法所示範,那些來自大洋彼岸的信札,竟藴含着打動一個時代的力量?就在於讀者相信“近距離”。這裏存在着一個“審美”的定律:當年的讀者相信,觀察者同被觀察對象距離越近,則其下筆就越真實,因為聚焦後的顯微鏡頭,是容不得造假的。正因此,那些年佔據我們書架的都是“近距離”作品,渴望捕捉生活的細節,抗拒鳥瞰鏡頭下的簡史或跨時段視野的大歷史寫作。在《民主的細節》一書中,劉瑜就是這樣自我介紹的:“全書中以講故事的形式,把‘美國的民主’這樣一個概念性的東西拆解成點點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在此意義上,旅美作家把他們的比較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現在就讓“我們”來告訴你們梨子這種水果的滋味吧。
大眾讀物要做到風靡一時,當然不可能脱離其據以流傳的文化脈絡和社會土壤。流行作者要訴諸讀者的預期心理,與讀者共舞,刺激但不刺痛他們,不可能直接説不。那些來自大洋彼岸的筆記觀察,無論筆下的世界多麼光怪陸離,歸根到底都談不上觀念的顛覆,反而精準迎合了做美國夢的讀者羣體。準確地説,那一代“孟曉駿”們的美國寫作,通過點點滴滴的“細節”敍事,一方面瓦解了一個早已被放棄的“舊”的美國觀,另一方面則在構建一個當年風光無限的“新”的美國觀。早在“孟曉駿”站出來挑戰老教授時,新舊之間的交鋒就展開了它的首個回合。這個被樹立起來的“新美國”,其所代表的道路和模式被認為終結了歷史,一度是讓全世界精英團結起來的“政治正確”,它道成肉身,如同一尊無法批評的偶像,好像“孟曉駿”年輕時代對“美國夢”的暢想:“全世界只有美國能做到”。那時的他不僅是在想象,也是在信仰。
但信仰不再,又會如何?在電影中,“孟曉駿”確實嚐到了梨子的滋味,但完全沒有想到的是,它苦澀難嚥。“我已經變得不再是我”,影片裏“載譽歸來”就已經是打臉了——走之前,明明説好“我不回來了”。實踐的確在檢驗,但首先驗證的卻是長者對年輕人的批判,整整一代,無論是他們作為作者,還是我們作為讀者,都有那麼一些天真。我們遺忘了“近距離”的取景也隱藏着“鏡頭”,細節記錄也出自講故事的人,更何況,孟所想象的“人人機會均等”在美國也只是夢,吃梨子的人未必就“融入”了作為觀察對象的美國。也因此,就認識美國而言,“孟曉駿”的兩分法恰恰是錯誤的,去過美國的未必就能識得美國真面目,而書本也有可能是去偽存真之後的實事求是。“近距離”並不意味着講述者就是無立場的,可以價值無涉地講述這一切,反而是距離越近,權力越大,一旦鏡頭聚焦於“細節”,也就意味着更廣闊的背景和更深遠的歷史被遮蔽起來,“近距離看”的另一面就是“屏蔽”。但在這種“審美”文化的籠罩下,劉瑜“拆解成點點滴滴”的手法就是免檢作品,被推定為主觀真誠且客觀真實的觀察體寫作。但問題在於,這種講法最容易造成古訓説的一個認知錯誤:“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我們以“孟曉駿”為標本的分析到此為止,雖然可以對號入座,但絕不是要作誅心之論。以林達為代表的這一系列“近距離看美國”,它們的成功絕非浪得虛名,其中很多作品堪稱中文寫作的精品,影響力所至,更是打動了一代知識青年。但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定他們的作品擺脱了敍事的政治,或者找到了一個在政治上中立的支點。不僅他們做不到,任何人都找不到。歸根到底,沒有無立場的立場,或者説,無立場的立場本身就是一種立場。從文化政治的角度解讀這些美國敍事,就能看到,“孟曉駿”們在埋葬前一套認識論的同時,又培植出自己的一整套方法,兩者之間無縫對接。在這裏,並不是講述者私心自用,他們有多少洞見,也就有多少盲區,反之亦成立。準確地説,同樣是“近距離看美國”的方法,此前我們能望見的都是洞見,現在卻輪到盲區登場了,時代的進程要對前一歷史階段的“審美”方法做個清算。
在歷史的進程中,誰都不是無辜者,我們作為讀者更要自我反省。我們只看到了我們想要看到的“美國”,對於不想看到的,就視而不見,其中的任性遠非作者所能享有——某種意義上,“看見的”和“看不見的”也是不斷變動的,如同黑屋子裏的探照燈,我們能看到什麼,視乎操控者把燈光轉向何處,沒有陽光普照這回事。前不久,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書《看不見的美國》,收在其市場號召力巨大的系列“譯文紀實”中。書名原題是Hidden America,這題目就很值得玩味,“美國”就擺在那裏,是誰把這個龐然大物的某些器官給“隱藏”起來了?為什麼此前“看不見”呢?為什麼現在要“看見”呢?為什麼我們現在終於明白了還有“沒看見”的,甚至是不是還有那些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看見”的?簡言之,“看見”背後也隱藏着政治學。在此意義上,我們一定要警惕那些起名叫《看見……》的書,因為所有的“看見”嚴格説都是虛假廣告。如果不首先交待作者之鏡頭在光影之間是如何操作的,那麼“看見”就未必是“啓蒙”,也可能是遮蔽、掩蓋或議題操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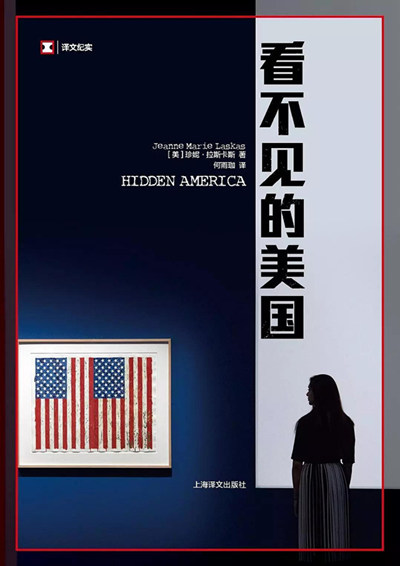
在呈現生活的複雜時,文藝工作者往往敏感又敏鋭,反而是學院派後知後覺。《北京人在紐約》的主題曲,就已經道出紐約客對紐約的愛恨交織:這裏既是天堂,也是地獄,但這並未妨礙北上廣的精英們當年“千萬裏我追尋着你”。第一集,在蝸居的地下室裏,郭燕對王起明説:“我隱隱約約有種感覺,這兒的很多事情,跟我們過去想的不一樣。”回到1990年代初,家住北京三環路內和平里的大提琴手,他們從前是怎樣想象紐約的,腳踏實地之後又發現有何不同?沒過多久,在“湘院樓”刷盤子時,王起明就被上了自由市場經濟學的第一課:“這裏是有錢就是爺,沒錢就他媽的是奴才”,但為什麼我們當年只看到了錢能使人自由,卻沒有領會貫穿其中的主奴辯證法呢?又是誰給我們披上了這個“無知之幕”,讓劇中人以及我們都相信,大幕揭開後,我們一定是先富起來的,是王起明在發達後所説的“爺”?“格陵蘭公司”開工的前夜,王起明關起門來。也許首先他需要説服自己,於是做了一番論證“剝削與被剝削之間的辯證關係”的就職演説。這個論證是這樣展開的:他創辦了這個公司,所以是“家長”,是“爺爺”;工人們是來打工的,所以“只能是孩子”;工人的“美德”就是“要本分,當孫子”,這樣才能“讓我成為一個像樣的爺爺”。這個爺爺和孫子的關係怎麼能維繫呢?道理很簡單,如王起明所言,“誰願意失業?沒人願意失業吧”。當年的“孟曉駿”正暢想着詩與遠方,他們不會懂這樣的“辯證法”,但對於活在當下的我們,這一切如“996”一樣都是生活中隨處可見的苟且。整部電視劇,明明講了一個妻離子散的倫常“悲劇”,主人公的命運如郭燕在酒醉後所言,“我變不成美國人,也早就忘了中國人是什麼滋味了”,但為什麼我們當年看到的都是花花世界的解放和自由呢?説到底,還是時候未到。
回到《中國合夥人》裏,老教授沒有同“孟曉駿”將辯論進行下去,也許他知道,你永遠無法説服一個願意相信的人。每一代“年輕人”都有自己看世界的角度和方法,取決於他們三觀形成時遇到何種激情燃燒的歲月。看《上甘嶺》長大的孩子,同青春期到電影院看《黃河絕戀》的,眼中的美國以及世界不太可能一樣。為什麼今天重看《北京人在紐約》,我們能發現很多隱藏劇情,從前滿眼的自由、平等和解放,現在卻洞悉出其間的壓迫、冷漠、扭曲和荒誕,劇中人以為他們掙脱了一個權力蔓延至末梢的規訓社會,最終卻發現,外面,其實是一個更大的監獄……變的不是劇本,也不是美國,而是我們自己,是人心,是生活教會了我們,讓我們不再如1990年代那樣對外面的世界無知無畏。
這麼説來,這屆的年輕人,如要認識一個更真實的美國,就要檢討這些年來文化精英所營造的美國觀,尤其要從旅美觀察筆記的敍事體中跳出來,意識到“近距離”視角反而容易造成井蛙效應。至於怎麼做,首先就是要做新時代的“孟曉駿”,要學會質疑,問一句“您是從書本里看來的美國吧”,更要理解任何書本以及敍事背後都有“看見”的政治學。在此意義上,貿易戰,“不願打、不怕打、必要時不得不打”,來得正是時候。自此後,若繼續固守“孟曉駿”的美國夢,以美國模式作為普遍的道路以及歷史之終結,只能越來越苦悶並顯得過於天真,只有解放思想者,才能輕裝前行。
又一次,我們到了《中國合夥人》所刻畫的那個代際交接的時刻,舊觀念已經搖搖欲墜,在新一輩的年輕人看來,它早已失去了前40年那無往不利的道德感召力,是時候辭舊迎新了。

《中國合夥人》劇照
三
我們這一輩“八零後”,學術人生都是讀“孟曉駿”的書長大的。
這些旅美先行者是怎麼講美國的,又是怎麼以美國為模式去規定一個理想社會,宣告歷史終結的,是跨世紀大學生當年的“啓蒙”核心文本。那些年,我們在這些書中“走遍美國”,漸漸遺忘了要做歌裏唱的社會主義接班人,滿心想着向美國學習。在“改革春風吹滿地”的歲月,檢驗改革是否成功,一個實踐中的標杆就是美國,而所謂改革,在某些人心中,就是要把美國的今天變成中國的明天。其中當然有反覆,整整20年前的1999年,北約轟炸我駐南聯盟大使館,讓我們這代年輕人眼見什麼是霸權和欺凌;但很快,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更深刻地改變了我們所處的歷史進程。在那個網吧互聯網的歲月,我們這一代的文化偶像在網絡空間高呼“今夜,我們都是美國人”,那聲音自是迴腸蕩氣,“河殤”的心態又一次還魂,要等到2008年北京奧運前後才退出歷史的舞台。
法學,作為一個在改革時代重建的學科,知識上的對外開放,既有必要,也是必需。其實,我們根本不用留學,在國內法學院讀書,同樣是喝洋墨水長大的,成長於歐風美雨的潤澤中,法學研究的議程以及學者的思考路徑,也早已得到了澆灌,栽下什麼花兒,就結出何種果實。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討論外國法的某某制度並追問其對中國的啓示,這種硬性碰瓷的寫作,是中國法學界最常見的套路。讀一讀這些年法學院的畢業論文,由此檢閲法學教育流水線的成品,所謂像法律人一樣去思考,大概第一條就是追問外國法對我們的啓示,以中國為病人,以西方做醫生,除此之外,我們什麼都不信。
讀美國書,學美國法,做美國人,法學界“洋務運動”鼎盛時,沒少見證三觀顛倒的怪狀——只有當我們開始學會把那些曾被顛倒的再顛倒回來時,當心境撥亂反正後,才能洞悉那些年間的荒誕。我國憲法第一條開宗明義,宣告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為什麼學界卻奉自由主義為正統,認真對待社會主義反而會被打入另冊,被視為學術上的大逆不道呢?現在我們不妨捫心自問,在社會主義國家談論社會主義的法治,這到底是逆了誰的道呢?記得我讀研究生時,因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紙解釋,一時間滿城皆談憲法司法化。但塵埃落定後,想一想那些高光時刻,當我們高談闊論美國的“馬伯裏訴麥迪遜”時,中國憲法的條款哪兒去了?關心中國問題的法律人,不能説沒有,但寥寥無幾。但硬要“司法化”,説到底這不是用打開美國憲法的説明書去啓動中國憲法嗎?所謂“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歸根到底,我們沉醉在自己編織的法學“美國夢”中,若是説有陷阱,這才是最難走出的“美國陷阱”。
何以至此,為什麼夢醒後卻發現身處陷阱,就本文的討論而言,我們還是要反思一下那些年讀過的書。學法的朋友一定還記得,法學書架上曾有一排排以封面顏色來區分學科門類的書,紅色的是法理,紫色的是憲法,黑色的是刑法……這一套色彩斑斕的書,思路也許借鑑了商務印書館的漢譯系列,就是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承擔的大型叢書“美國法律文庫”。迄今為止,這或許是中國法學界規模最大的漢譯工程,空前,很有可能也會絕後。它的編委會匯聚了當年中國法學界最優秀的學者,大致就在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出版了近百本的美國法學著作,其中不乏體量浩大的案例教科書。“美國法律文庫”之所以一時間多少英雄豪傑,並不只是學術自由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在調控,它是當年“中美元首法治計劃”由學界承擔的一個項目,操作模式是我們出力,美國人出錢(由美國駐華大使館新聞文化處資助),某種意義上象徵着當年中美之間結成的“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按照整套文庫的出版説明:“文庫”所選書目均以能夠體現美國法學教育的基本模式以及法學理論研究的最高水平為標準,計劃數目約上百種,既包括經典法學教科書,也包括經典法學專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信“文庫”的出版不僅有助於促進中美文化交流,亦將為建立和完善中國的法治體系提供重要的理論借鑑。
千萬不要誤會,完全沒有要批評以上説明及其理念的意思,我曾是這套文庫的忠實讀者,也有幸在其收尾之際承擔起了其中一本小書的翻譯。更何況,這段出自前輩手筆的話,讀來可謂是恰如其分,在此我們要做的,只是以它作為一個歷史進程中的文本,捕捉藴藏其中的一個時代的精神風貌。某種意義上,話説得越恰當貼切,越表明它是某個具體語境中的集體無意識:翻譯美國法學經典,是“為建立和完善中國的法治體系提供重要的理論借鑑”。以外來的高水平理論為借鑑,提高中國法治建設的知識水平,對於這個判斷,我們沒有必要在規範意義上分對錯;真要論,這句話也無可厚非,現在一如當年,“他山之石”的存在對我們認識並改造自己都有意義。
但意義不能籠而統之,要做具體的分析。時代早已是今非昔比,那麼我們的思維能否與時俱進?在這個問題上,我自問還有一兩分發言資格,並非基於我個人的專業研究——生活在現代學術體制內,學者往往只要在一個領域內埋頭種地就行,不用抬頭看天——而是基於我這兩年來無名卻有實的出版經驗。無名,指的是我當然沒有出版人資質,有實,是説要從茫茫英文書海中選書,判斷哪本書值得翻譯過來,學術價值多大,社會效益如何,市場潛力怎樣。同個人的專業研究相比,選書是一種相當不同的經驗:要“亂讀書”,大部分為了出版策劃而翻開的書,淺嘗輒止即可,同時要對讀者的口味以及社會的風向保持敏鋭的體察。説到底,這是對讀者而非同行負責的閲讀。選書經驗不斷累積,我也形成了一個更為確信的判斷:美國書不是不讀了,還要繼續讀,但讀什麼以及怎麼讀,都要做一次思維的反轉。
此前,我們讀美國的書,是為了從中拿起美國的理論,以之為武器去改造中國的現實。這種恨不得把中國變成美國的改革方案,現在看來正是走不得的改旗易幟之邪路,但當年在學界卻大有市場,一度通行無阻。那麼現在,讀美國的書,就是要用美國人的自我批評作為鏡鑑,來正一正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衣冠,同此前40年相比,可以説是反其道而行之。讀美國書,不是為了做美國夢,而是為了防止我們也患上美國病,為了在為時未晚時動手醫治我們可能已經患上的美國病,為了讓我們的明天不至於陷入美國今天的困局。在此意義上,“美國”,一旦為我們所重新看見,也構成了我們的一種方法論。也就是説,正因為美國在某些方面的“發達”,它已經把問題活生生甚至血淋淋地呈現出來,這樣的美國構成了一種可做人類學觀察的社會樣本,讓我們,也即一個社會主義的中國,可以知道要對什麼“説不”:不能怎麼改。有些制度不能改;有些改,非但不能讓機體更強健,反而是在革自己的命。
感謝美國高度發達且精緻細分的圖書市場,只要走馬觀花過一遍,就能看出某些此前為我們視而不見的議題近年卻能浮出水面,成為市場的賣點和社會的焦點。美國夢早已流失了它的本土資源,舉目可見的,是“不平等”及其衍生的種種問題。“這個世界還會好嗎”不再是盛世危言,未來已來,它甚至比想象中的還要更糟糕,這大致是美國朝野各方的共識。當然,作為現狀的“不平等”,包括它的前因和後果,應如何講述;它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還是社會倫理問題;以及何種平等才是應追求的,在美國本土可以見到五花八門的論述。姑且這麼説,美國這些年已經失去了此前的道路自信,如果説他們曾經最熱衷散佈“中國即將崩潰”的論調,那麼現在則將批判的槍口對準了自己。看看美國近期出版的新書,大面積都是唱衰美國的危機論,也是在這種行情下,我曾經開玩笑説,這年頭美國學者如果不出本書把美國批判一番,都不好意思説自己還有獨立精神自由思想。
2016年下半年,《我們的孩子》中文版還沒有問世時,曾有一位資深的出版人對我斷言,這本書在國內市場不太可能受歡迎,因為它在講美國的不美好,而美國又怎麼可能不好,國內讀者不答應。現在回想起來,那口氣就如同電影中的“孟曉駿”。這裏無所謂誰對誰錯,只能説明世道在變。而在新時代尤其是貿易戰到來後,美國不再是夢,而是成為一種讓我們反觀自己的方法。如果説當年國人眼中主要看到了美國那“天堂”的一面,那麼也許現在是時候讓我們揭示“地獄”美國的一面了。美國作為一種方法,可以展示出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個人主義社會的種種病理,由此成為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導師”。所謂不忘初心,不就是無論如何都不能讓自己變成當初討厭的那副樣子嗎!美國擺在那裏,意義就在於讓我們知不可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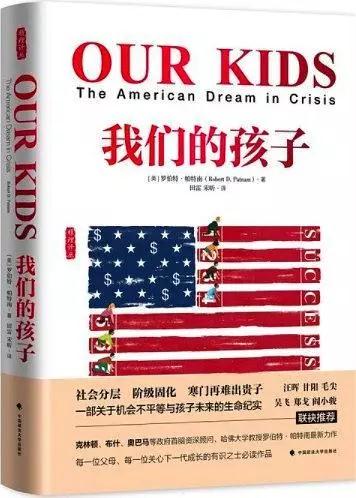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解,我還是要多交待兩句。我們將美國作為一種知不可為的方法,當然不能反過來就推定我們假設中國是盡善盡美的。這樣的誅心之論,我們不背鍋。中國當然有很多問題,但在繼續深化改革的道路上,知道什麼是萬萬不能做的,其意義甚至遠大於知道什麼是可以或應當做的,因為改革牽動千家萬户,有些改革是不可逆的,改了之後就改不回去了。也不能就此斷定我們認為美國就是一無是處。很多方面,美國仍有值得我們認真學習之處,哪怕只是為了師夷長技。更何況,中國上一階段的改革沒少經歷過以美國為師的模式,也因此在相關領域內患上了美國病。也許美國已經久病成醫了呢,現在則解鈴還須繫鈴人。但無論是知不可為,還是知可為,怎麼認識自己,怎麼認識世界,最終都是中國自己的事情,都要由我們自己來規定,所謂主體性,意義也就在這裏。
四
貿易戰之後,如何讀美國書,最後總結並延伸一下本文的討論。
第一,認識美國,尤其是看見那個此前不為我們所見的美國,在貿易戰到來時,在許多此前的美國研究被實踐表明百無一用之後,更顯迫切。因此,我們要繼續讀美國的書,在知識心態上不可閉關鎖國。
第二,讀美國的書,不能拿來主義,要有自己的主體意識。切不可認為寫在英文書裏的就是大寫的真理,不能盡信書。社會科學都有各自的本土語境,尤其要意識到美國社科學者的論述同樣有其政治性。比方説,若是你聽過薛兆豐先生的課後,非要從他畢業的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那裏尋找自由市場的論據,我不能説這就是錯誤,但確實存在着偏差,大致類似我們中了一個國家課題然後必須按照要求來完成,異曲同工而已。
第三,以美國為方法,此前我們是要知可為,那麼現在則變成了知不可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都要心態更放開,不虛美,但也不隱惡,實事求是地理解一個複雜的美國。近年來,國內出版人往往銷量當先,引進了一些在美國政治文化中屬於吵架的書,但須知美國也有“咪蒙”,甚至在出版界只多不少,這些書讀起來也許很過癮,讀一本一時爽,但讀得越多,最終就是各種嘈雜聲音混成一片。我建議,出版界接下來減少引進這些美國人關起門來自己吵架的書。在此給出一個略顯粗暴的簡單辦法,也許在美國亞馬遜網站上點評數在500以上的論政書,十之八九都是吵架的。與之相關,我也遺憾地看到,某些原本在美國語境中帶有社會批判維度的嚴肅作品,卻在我們出版界的妙手下,包裝成安撫心靈的雞湯書或激發焦慮的經管書。就此而言,出版人應當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要相信站着把錢掙了也不是不可能。
第四,不僅是讀美國的書,我們還要把美國當作一部書來讀。美國這部書不好讀,之前我們之所以引進了太多似是而非的知識,結果在真刀實槍面前不堪一擊,就在於我們不過是走馬觀花。西方國家是去了一些,但往往聽其言就信其行,坎布里奇逛過一圈歸國後就成為權威,到處可見“兄弟我在哈佛的時候”這種自命不凡的開場白;甚至就在剛才,我還在朋友圈裏看到某高校大張旗鼓,宣講所謂“海外引智”的項目。把美國當作一本書來讀,就是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在此意義上,未來的美國研究者都應當首先是“人類學家”。
第五,在目前國內的一流高校中,有着這樣一批學者,他們好比國際學術界設在國內的分舵,寫作英文文章,發表國際期刊,中國只是案例或素材。何不如此暢想,不遠的將來,我們也有了著名的中文學術刊物,就叫《美國季刊》(The America Quarterly)吧,這刊物影響因子高得很,因此在全球高校評價體系內權威極重,就是為了能在這份刊物上露個臉,美國不少學者不惜時間學習中文,把他們原本的美國研究首先貢獻給這個中文的刊物。據説因為用中文寫作極其困難,非經年累月之功力不可為,美國多家常青藤盟校設立海外發文項目,為本校學者的寫作進行中文潤色。為了掌握中國的美國學研究前沿,美國學者紛紛來華訪問,有時候拖家帶口,對他們來説,這是個機會,讓小孩子打小就能學中文。
這個中國夢,當然很遙遠,但如果你覺得它荒誕不經,那隻能説明,你在上一個由美國所規定的夢中沉睡得太久了,醒一醒!

本文原載於《東方學刊》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