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霞緋:解放前夕的第二條戰線,還有這些感人故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胡霞緋】
時近祖國70週年華誕,社會各界開始了各種以“我和我的祖國”為主題的讀書會、快閃慶祝活動。藉此機會,我又重讀了一遍金衝及先生在1948年前後的日記《第二條戰線——論解放戰爭時期的學生運動》,再一次被那段“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的歲月打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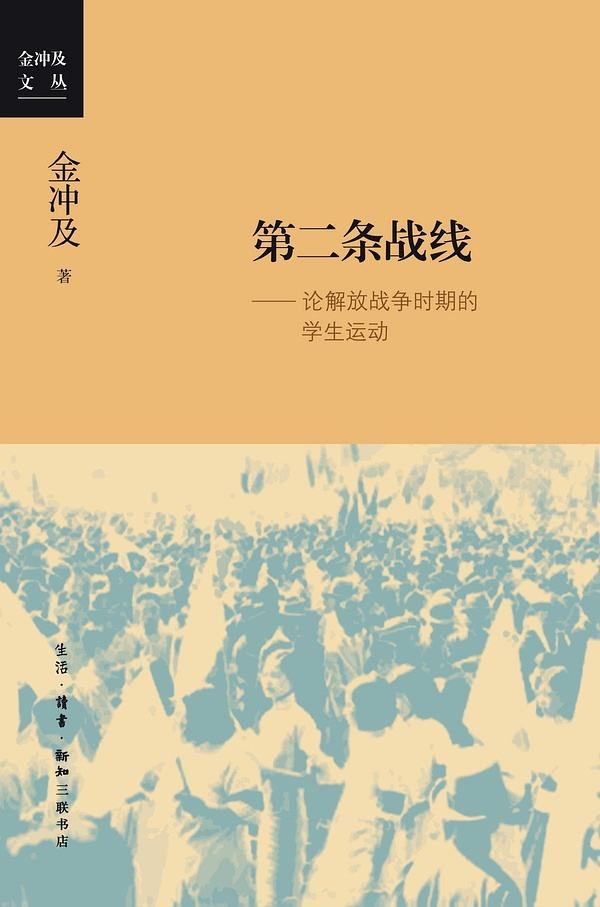
作為解放戰爭時期的“第二條戰線”,學生運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金衝及先生的這部日記,為我們近距離的審視解放戰爭中的學生運動,提供了很好的材料。本文即以此日記為中心,佐之以其他相關材料,刻畫1948年前後上海復旦大學學生運動的種種面向。
一、上海:學生運動開展的重要場域
解放前夜,民眾生活有多困難?有太多的史料,告訴了我們問題的答案——
1948年4月,生活在南京的葉聖陶藉由一點生活中的見聞發出瞭如此的感慨:“丁士秋來看二官。她在醫院為護士,據云病人頗有在院謀自殺者,為護士提心吊膽之事。自殺原因都為經濟。社會窮困至此,能不悲嘆。”同樣,一位在抗日戰爭時期加入中共的老黨員張渝民觀察到,從抗戰勝利初期開始,由於經濟凋敝,物價飛漲,上海各大中小學“分別向學生增收第二期的學費”,“金額較第一期增長達4倍以上,相當於淪陷時期的7倍”。
如此高昂的學費使得諸多家境清寒的學生家庭不堪重負。在這種情況下,1945年春節前後,基督教青年會、女青年會等組織聯合舉辦義賣活動以救助貧困學生。上海各校的中共地下黨員也利用這次機會,積極動員身邊的同學參加義賣活動,在義賣當天有上千名學生走上街頭。然而,國民黨政府認為此次上千名學生參與的義賣活動並不合法,“明令禁止,並抓走在街頭義賣助學章的70名學生。三青團造謠説,義賣助學章的錢是給新四軍當軍費的,威脅參加義賣活動的學生,致使那次助學運動遭受挫折”。從張先生的這些敍述,頗能感知到當時學生活動規模之大。這一方面揭示了青年學子的無奈、不滿,同時也體現出了中共地下黨員在高校中的滲透力與動員力。
到了1946年初,學費又再度上漲,據時人回憶其數額“較上學期第二期收費又猛漲數倍,大大超過一般職工的負擔能力,出現了一個龐大的清寒學生羣體,其中嚴重困難的學生,約佔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一”。這樣的情形着實觸目驚心。

著名作家、教育家葉聖陶(1894—1988)
在此背景之下,中共指示要把爭取和平民主運動同保衞羣眾切身利益的鬥爭緊密結合起來。兩相併重也成為了地下黨員工作的重點所在。當時的上海市學委決定吸取之前活動失敗的教訓,再度開展助學運動併成立助學機構。經過宣傳與醖釀,“兩萬多名學生走上街頭義賣助學章,結果大大超過5000萬元預定目標,達到8389萬元,共計幫助四千餘名學生解決了困難”。這次助學運動取得了成功,但國民政府卻依然以不合法的名義,希望學校可以開除某些參加助學活動的學生。
得知這一情況後,上海市學委立即組織後援會和家長聯合會向社會發出呼籲,期望爭取到輿論的支持。《大公報》、《文匯報》等當時滬上知名的刊物成為了學委書寫心聲的重要平台。基層學校學生的抗議、各種社會組織與官方的論辯也使得當時學生運動的政治鬥爭的色彩漸趨強烈。而面對聲勢日廣的學生運動,國民黨當局非但不正視、檢討,反而視其為洪水猛獸。在蔣介石眼裏,“最近發生之學生運動,實已越出國民道德與國家法律所許可之範圍,顯系‘共產黨’直接間接所指使。如長此放任,不但學風敗壞,法紀蕩然,勢必使作育青年之教育機關,成為毀法亂紀之策源地,國家何貴有如此之學校,亦何惜於如此恣肆暴戾之青年。”隨後,1947年5月18日,國民政府在臨時國務會議中頒佈了《“戡亂”時期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禁止十人以上的請願活動、罷工、罷課和示威遊行等活動。
金衝及等進步學生,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展開革命活動的。

老照片裏的“北平區反飢餓反內戰大遊行”
二、社會變化與人生追求的形塑
據金衝及先生回憶,自1947年5、6月間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達到高潮後,國民政府對復旦的學生運動進行了壓制。學生自治會被強行封閉,部分同學也被逮捕囚禁。學生運動一時間在高壓之下趨於沉寂。然而到了12月份情況卻發生了轉變:“12月下旬的嚴冬時刻,上海街頭每天都可以看到凍死的難民,慘不忍睹,同濟大學首先發起勸募寒衣運動。復旦地下黨抓住勸募寒衣和不久後的抗議九龍城事件這些合法運動,發動並團結校內大多數同學,衝破原來沉寂的空氣,打開一個活躍的新局面;在積極的知識分子中,又建立核心組織,舉辦各種讀書會和社團,提高大家的認識,形成行動中的骨幹力量和廣泛網絡,使運動能廣泛持久地開展下去。”
當時學生活動的開展與社會形勢有着密切的結合,而地下黨組織則對於學生運動發揮着重要的醖釀、催化與組織作用。透過日記的一些更細化的描述,我們則可以具體看到地下黨組織的運作模式,同時還可以觀察到以金衝及為代表的復旦青年學生如何在激變的時代中轉變觀念,砥礪自我,形成對共產主義的信仰——
在日記裏他説:“由南車站路沿車站東路往東到海潮路折回一帶調查。那裏的難民真太苦了,他們怎麼住?就在地上挖了一個洞,上面用兩根竹子撐起幾張席子,爬進去頭會碰到頂,裏面一無長物,睡在泥上,至多鋪些稻草,年輕的人出去討飯,女人把一件衣服都沒有的小孩擁在胸前。這種樣子,真難怪前幾天每天會凍死一兩百人啊。……他們起初不明白我們的來意,後來明白了,就立刻將我們圍起來。‘老闆,給我再寫一雙鞋子’、‘老闆,你看看我這個褲子’。有的絮絮地告訴我們,他們原來是皖北、豫東一帶的居民,因為旱災之後繼以黃泛不能過活而逃出來的。一雙雙哀求的眼睛,我看見了就打寒戰。可是我們募捐的東西太少了,又不敢放膽地寫領物券,只有硬着心腸一家一家地發過去。唉,我們的力量真是太微小了,真是‘安得寒衣千萬件,盡濟天下無告民’。”
此外,他還記錄到:“前幾天在南市,人沒有幾個,有分發、有調查,居然還算能井井有條,今天全體總動員的到浦東去總分發,聯絡站在青年會小學,裏裏外外擠滿了人。……宣傳隊到了,這倒有勁,一位女同學拿了擴聲筒教小學生:‘十萬塊大票發出來呀……’一面唱一面解釋,旁邊司徒漢們將鑼鼓傢伙敲起來,熱鬧非凡。另一面,難民排隊領衣時,農院的一位麻臉同學指着一幅很大的畫着十萬大票壓死着一個老百姓的漫畫,向他們演講:‘窮人富人生下來是一樣的人,為什麼現在他們有許多東西可以吃而你們沒有東西吃呢?就因為他們把你們的一份東西也吃了去了。’深入淺出,倒的確有道理。”
在書中,類似的記述還有很多。什麼樣的主義能夠深入人心,關鍵要看這個主義能否解決國家與民眾的關鍵訴求。
三、道路抉擇與心態表達
在金先生的日記裏,可以看到,在基層高校中,黨員與積極分子的作用是十分關鍵的。他們需注意密切同其他同學的聯繫,並逐步幫助其他同學提高思想覺悟,進而引導這些同學加入到中共的隊伍中來。早在皖南事變後,面對國民政府對於青年活動頻繁鎮壓的事實,中共中央南方局號召進步青年們“勤學、勤業、勤交友”,由此保存力量,靜待時機。
金衝及先生記述,他參加了兩次中國共產黨,是“黨的兩個不同系統幾乎同時”來發展他加入黨組織的。這一事例頗能體現當時地下黨組織在高校中的運作實態。
關於兩次入黨的緣起,金先生如是寫道:“我的兩次入黨都在1948年上半年,前後相隔大約一個月。第一次是四五月間,來發展我的是復旦大學史地系一年級的同班同學卓家緯,她是屬於南京市委上海聯絡站系統的。第二次是五六月間,來發展我的是我在復旦附中讀書時關係最密切的同學、當時在復旦大學土木工程系一年級學習的邱慎初,他是屬於上海市委系統的。”
原先史地系便有一個秘密的學生核心小組,不斷組織各種學生愛國運動。小組共七人,金衝及與卓家緯都在其中。另有幾人都是黨員,但分屬於黨的不同系統。1948年1月,金衝及因參加同濟大學“一•二九”事件被學校記過,而至四月時,卓家緯便來發展他入黨了。此後為了完成入黨的相關流程,金衝及寫下了一份自傳敍述了個人經歷與入黨原因交於卓家緯。“自傳交上去後不久,她告訴我:組織上已經批准了。某一天(具體日子已記不清了),會有人到你在江蘇路的家裏來,説他姓何,由他介紹而來,那就是來接關係的。”
而對於與這位何先生的會面,金衝及如是回憶:“到了那一天,果然有一位戴眼鏡的男同志來了,大約比我大六七歲,説是姓何,是卓家緯要他來找我的。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看來並不是復旦的同學……他先問問我的情況,然後説:以後他會定期到我家來的,現階段主要是幫助我學習。”此後,金衝及便與老何接上了關係。然而,就在不久之後,好友邱慎初便又找到金衝及説要發展他入黨。在聽説金衝及已經入黨後,邱慎初頗為吃驚。金衝及在日記中寫道:“他大吃一驚,問我是誰介紹的?我説是卓家緯。隔了幾天,他很緊張地來找我,説組織上查過了,黨內沒有這個人。……我一下子就慌了,急忙問他:那怎麼辦呢?他説不要緊,你再寫一份自傳交給我。這樣,我又寫了第二份自傳。”

復旦大學的老校門
到六月初,金衝及得到了組織正式批准他入黨的通知:“邱慎初告訴我:組織上已經批准我入黨了,會有人來同你接關係,暗號是送你一本書……到時候,有人按照暗號來宿舍裏找到我。這次來的人我認識,是新聞系二年級的同學江濃,台灣人,我前幾天剛見過。”而這些情況,老何並不知曉。“他仍過一段時間就到我家裏來一次。那時,學校里正放暑假,同學們大多分散回家。他來,主要是給我分析當時的政治形勢,幫助我學習黨的指示精神,並沒有安排什麼行動任務。這種關係保持了三個多月。我‘觀察’來‘觀察’去,始終沒有發現有什麼不正常的地方。有一次,我憋不住了,在學習中直截了當地問他:託派是怎麼一回事?他分析了一番,講得也很正確。這下,我就更糊塗了。”
至八九月間,形勢開始變得更為複雜。國民黨特種刑事法庭在上海、天津等學生活動活躍的城市開始了大範圍的逮捕行動。在復旦要逮捕的便有三十多人,金衝及也在其中。為了躲避通緝,他藏匿在外,直到上海解放才回到學校。之後,便遇到了曾經屬於南京市委上海聯絡站的復旦新聞系同學程極明。從他那裏得知了一些關於組織的情況:“他的組織關係是1949年初轉到上海市委系統的。他問我:大逮捕後你到哪裏去了?組織上(指南京市委上海聯絡站)本來準備送你到解放區去,可是找不到你了。我把前面所説的那些情況向他詳細地説了一遍。他告訴我那是南京市委系統的,‘老何’的名字叫賀崇寅,也是他的聯繫人,現在正擔任上海總工會的秘書處處長。並且還陪我去看了一次賀崇寅。以後,他又告訴我,卓家緯在建國後不久因病去世了。”
實際上,解放前在復旦大學至少有四五個黨的不同系統,規模最大的是上海市委領導的復旦黨總支。在解放的前夜,由於國統區形勢複雜、處境險惡,在周恩來主持下的南方局決定採取建立平行支部、實行單線聯繫等措施維繫黨組織。由此,在一個單位內便會有不止一個系統,相互之間不產生聯繫。這樣即使一個組織遭到破壞,另外的幾個系統也能得以保全。這種情況只由較高層的負責人掌握,普通黨員與基層組織的負責人是不知曉的。
以上便是筆者繹讀金先生日記的一些片段。諸位讀者如對此感興趣,不妨找原作來一讀。史料比起任何詮釋性的語句,更能凸顯那個年代裏,一位嚮往光明與進步的青年,是如何在黨組織的領導下進行鬥爭的。今天重温這段歷史,讓人覺得無比的感動,正是這些前輩們忘我的奉獻,才有今天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局面。
“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筆者堅信,前人的心路,一定能鼓舞更多年青一代,而忘記了歷史,或者是按照某一種別有用心的意識形態來曲解歷史,就是對無數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前輩最大的不尊重!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