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武:《醜陋的中國人》為何不配與魯迅相提並論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孫武】
9月25日是魯迅先生誕辰。作為新文化運動旗手,魯迅先生一直以“鬥士”的形象出現在國人面前,他對中國人劣根性的批判,向來不留情面,這一點也影響到了不少後來人。
比如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這本書以“批判國民劣根性”的名義,在海峽兩岸出版、暢銷多年,影響深遠,尤其是“點撥”了許多年輕人。
這樣一本書在境內一版再版,在一些網站上評分還不低,奇怪的是,對於書中嚴重的偏見,網上卻很難搜索到有人全面地指出和反駁。

我在上一篇文章裏,提出《萬曆十五年》批判中國社會“以道德代法律”是大而化之的偏頗之論。因為,健全的法律也需要落實到人心,普遍的道德也離不開制度的建設,這兩者不可能是對立和替代的關係。今天的許多事實,恰恰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重視道德教育的意義,因為人心的治理才是更值得研究的難題。
像香港目前的情況,如果對警察全部頂格處理,對暴徒全部底線處理,那樣的法條只是形式上的公正,根本治理不了人心。
相比之下,《醜陋的中國人》存在的問題就不僅是偏頗了。這一點,李敖早已指出:
“這種作者不敢實指有名有姓的醜陋的中國人,卻泛指所有的中國人都醜陋,用來替他的懦弱墊背……”
即便不指名道姓,要批判國民劣根性也並非不可以,但首要的條件是態度公允、舉證準確,不能有太多的偏見和私貨,比如:
“我雖然來美國只是短期旅行,但就我所看到的現象,覺得美國人比較友善,比較快樂,經常有笑容。我曾在中國朋友家裏看到他們的孩子,雖然很快樂,卻很少笑,是不是我們中國人面部肌肉構造不一樣?還是我們這個民族太陰沉? ”
又如:
“中國人往往不習慣於理智反省,而習慣於情緒的反省。例如夫妻吵架,丈夫對太太説:你對我不好。太太把菜往桌上一摜。説:‘我怎麼對你不好,我對你不好,還做菜給你吃?’這動作就是一種不友善的表示,這樣的反省,還不如不反省。 ”
這樣的例子,即便對存心要批判中國的人來説,是不是水平也太低了?
而作者似乎也並不是真想要批判,他也算敢於表明心跡:
“我們應該感謝鴉片戰爭,如果沒有鴉片戰爭,現在會是一種什麼情況?至少在座的各位,説不定頭上還留看一根辮子,女人還纏着小腳,大家還穿看長袍馬褂。陸上坐兩人小轎。水上乘小舢板。如果鴉片戰爭提早二百年前發生,也許中國改變得更早一些,再往前推到一千年前發生的話,整個歷史就會完全不一樣。”
這種心態,恐怕連“崇洋媚外”都算不上,是恨殖民者來得晚了啊。
柏楊大力批判的“纏足”,其實,這根本談不上“中國人的劣根性”,因為在宋代以前並沒有“纏足”的記錄,到了近現代也漸漸就廢止了,顯然這種陋習不能上升到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層面。
維多利亞時期的歐洲人,將患上肺結核視為女性美麗的標準。為了美白,她們敷含鴉片的面膜,用氨水洗臉,以有毒的硃砂當唇釉,甚至還用砷水沐浴。套用柏楊的話,我們或許也可以問:為什麼西方文化之中,會產生這種殘酷的東西?
為了迎合細腰的時尚,當時的女性長期佩戴不符人體結構的束腰,以呼吸不暢、嬌喘連連的病態為美,壓得五臟六腑都漂移了。套用柏楊的話,我們或許也可以問:為什麼西方文化之中,會產生這種殘酷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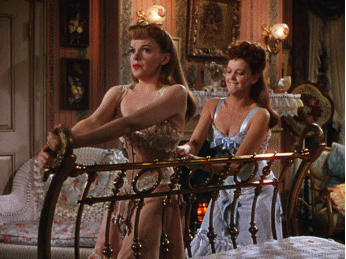
使得裹小腳漸漸消亡的,是高跟鞋在明末清初的傳入。一個社會的風尚、陋習,往往是會隨着社會的發展而改變的(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從民族劣根性或者文化基因的角度,就完全找錯了問題。
而柏楊最重要的一個論斷,則是所謂中國人的“醬缸文化”。
“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像長江大河,滔滔不絕的流下去。但因為時間久了,長江大河裏的許多污穢骯髒的東西,像死魚、死貓、死耗子,開始沉澱,使這個水不能流動,變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個醬缸,一個污泥坑,發酸發臭。”
柏楊明確講到了“任何一個民族”,但他卻又把“醬缸文化”貼作“醜陋的中國人”的標籤,實在是令人費解。
柏楊的“醬缸文化”之論,雖然邏輯就有缺陷,可因為據説有偉大的人物——魯迅曾經也作出過中國人有“染缸文化”的論斷,因此就沒有人敢駁斥了。但魯迅的批判有力與否,與柏楊的偏見是否成立,這真的有關係嗎?
對魯迅先生,我同樣滿懷敬意。魯迅最高的成就是小説,相比之下,雜文就等而下之了,即便認為應該把魯迅從神還原為人的夏志清,也在《中國現代小説史》中專闢一章來介紹魯迅,對魯迅的小説成就給予高度評價。
而一直流傳的那段“染缸文化”的話,則是出自魯迅給許廣平的書信。我們一定要考慮這段話的上下文背景和寫作場合。
在網上搜那段話,得到的結果基本都是片段,下面根據《魯迅全集》,我給出這封信的全文。
廣平兄:
這回要先講“兄”字的講義了。這是我自己制定,沿用下來的例子,就是:舊日或近來所識的朋友,舊同學而至今還在來往的,直接聽講的學生,寫信的時候我都稱“兄”;此外如原是前輩,或較為生疏,較需客氣的,就稱先生,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大人……之類。總之,我這“兄”字的意思,不過比直呼其名略勝一籌,並不如許叔重先生所説,真含有“老哥”的意義。但這些理由,只有我自己知道,則你一見而大驚力爭,蓋無足怪也。然而現已説明,則亦毫不為奇焉矣。
現在的所謂教育,世界上無論那一國,其實都不過是製造許多適應環境的機器的方法罷了。要適如其分,發展各各的個性,這時候還未到來,也料不定將來究竟可有這樣的時候。我疑心將來的黃金世界裏,也會有將叛徒處死刑,而大家尚以為是黃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們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書似的每本一律。要徹底地毀壞這種大勢的,就容易變成“個人的無政府主義者”,如《工人綏惠略夫》裏所描寫的綏惠略夫就是。這一類人物的運命,在現在——也許雖在將來——是要救羣眾,而反被羣眾所迫害,終至於成了單身,忿激之餘,一轉而仇視一切,無論對誰都開槍,自己也歸於毀滅。
社會上千奇百怪,無所不有;在學校裏,只有捧線裝書和希望得到文憑者,雖然根柢上不離“利害”二字,但是還要算好的。中國大約太老了,社會上事無大小,都惡劣不堪,像一隻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什麼新東西去,都變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來改革之外,也再沒有別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懷念“過去”,就是希望“將來”,而對於“現在”這一個題目,都繳了白卷,因為誰也開不出藥方。所有最好的藥方,即所謂“希望將來”的就是。
“將來”這回事,雖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樣,但有是一定會有的,就是一定會到來的,所慮者到了那時,就成了那時的“現在”。然而人們也不必這樣悲觀,只要“那時的現在”比“現在的現在”好一點,就很好了,這就是進步。
這些空想,也無法證明一定是空想,所以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種慰安,正如信徒的上帝。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所以很多着偏激的聲音。其實這或者是年齡和經歷的關係,也許未必一定的確的,因為我終於不能證實: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須是有不平而不悲觀,常抗戰而亦自衞,倘荊棘非踐不可,固然不得不踐,但若無須必踐,即不必隨便去踐,這就是我之所以主張“壕塹戰”的原因,其實也無非想多留下幾個戰士,以得更多的戰績。
子路先生確是勇士,但他因為“吾聞君子死冠不免”,於是“結纓而死”,我總覺得有點迂。掉了一頂帽子,又有何妨呢,卻看得這麼鄭重,實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當了。仲尼先生自己“厄於陳蔡”,卻並不餓死,真是滑得可觀。子路先生倘若不信他的胡説,披頭散髮的戰起來,也許不至於死的罷。但這種散發的戰法,也就是屬於我所謂“壕塹戰”的。
時候不早了,就此結束了。
魯迅。三月十八日。
魯迅這裏所謂“黑色的染缸”、“漆黑”,到底講得是什麼?在這封信裏,其實是有所闡述的。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因為我終於不能證實: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
根據夏濟安在《魯迅作品的黑暗面》中的研究,魯迅從小就喜歡一個豪俠肩住閘門的傳奇故事,他曾經寫道:
“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揹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黑色的染缸”這個意象,與其説更接近柏楊的“醬缸”,不如説更接近魯迅要用肩扛住的“黑暗的閘門”。
這種黑暗,到底有什麼內涵?夏濟安做了精彩的分析:
“黑暗閘門”的重壓大致有兩個來源:一是中國傳統文學與文化,二是他自身不安的內心。魯迅強烈地感到這兩股力量壓迫着他,穿透着他,卻又無可逃脱。他相信年輕一代可以不受這些重壓的煩擾,自在地成長生活。這觀點你或許並不同意,但無可否認,魯迅的確在絕望中發出希望的吶喊。他英雄的姿態暗含着失敗,而他選定的立場則更近乎悲劇。魯迅援引千斤閘壓死豪俠的典故,大概也是他自覺無力對抗黑暗,只能自我犧牲吧。正是這種領悟,讓他的作品裏總縈繞着一種哀情,也成為他天才的標誌。
倘若有一種事物,如同黑暗的閘門,神秘迫人,無可挽回,可將光明徹底斬斷,那一定是死亡。死亡對於任何一個人,甚至全人類,都是難以承受之重。不論是反動派,還是進步人士,都不得逃脱。要獲得幸福,唯有像斯賓諾莎一樣,不去考慮死亡的命題。然而,儘管魯迅身為中國現代主義的先驅,他卻明顯感到這駭人的重擔。
希望與理想被魯迅作品的陰鬱所沖淡。在散文詩和短篇小説中,他熟練地刻畫死亡的醜陋,故事裏的許多活人也都臉色蒼白、眼神冷漠、行動遲緩,與行屍走肉無異;葬禮、墓地、行刑、砍頭,和生病,更是魯迅反覆想像、創作的主題。死亡的黑影以各種形式在他的作品中蔓延,從《狂人日記》中死亡的隱約威脅,到《祝福》中祥林嫂的悄然消逝,再到真正的死亡的恐怖:如《藥》裏被砍頭的烈士和患癆病的小栓,《白光》中追求虛幻白光,最終溺水而死的老學究,還有《孤獨者》中面含冰冷微笑的死屍。不過,反觀《阿Q正傳》,當死亡降臨無知的村民,“大團圓”或許倒也有它可喜的一面。
除死亡以外,還有一樣是魯迅絕對憎惡的,那就是有着“腐朽的名教,僵死的語言”的舊中國。從他的演講和作品來看,死亡本身與以死亡為象徵的舊時代,他似乎更懼怕後者。這裏就有一個有趣的問題:舊中國和死亡,魯迅更憎惡哪個?作為五四運動的知識分子領袖,他應當更厭惡前者。但他也是一個病態的天才,想必死亡才是他更痛恨的東西;況且,憑他對革命的熱情,也只足夠應付他自己揹負着的死魂靈,更不必説整個舊中國了。
總結一下。
1. 魯迅的作品是黑暗的。他人生觀中許多黑暗的看法,在這樣一封書信中有所表露。比如,“我疑心將來的黃金世界裏,也會有將叛徒處死刑”。
2. 這封信的主題是非常深刻的,探討“過去和將來”,探討對黑暗的抵抗,探討的是“世界上無論那一國”都要遇到的根本性的問題,“實有”,存在論(本體論)意義上的。魯迅真正的敵人是虛無主義,是一切價值的“死亡”。魯迅反抗絕望,反抗的是這種生命深處的絕望。
如果你還不理解這種絕望,對這樣的句子你是否有所感受: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阮籍)
“生命就是在礁石叢生的大海上航行的一片孤舟,你小心翼翼地繞過了一個又一個的礁石,那麼最後朝向的就是死亡。”(叔本華)
(這兩個例子參見駱玉明的演講:《魯迅與魏晉》)
面對這種黑暗和絕望,魯迅是憑靠什麼力量和精神加以反抗的呢?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魯迅寫道: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嘗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後繼的戰鬥,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説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於全體,那簡直是誣衊。
3. 相比之下,批判舊中國社會,乃至要上升到民族性的問題,在信中根本不是主題,也不夠分量。
在魯迅公開發表的作品中,並沒有用“染缸”批判中國人劣根性的集中論述,魯迅是一個藝術上的天才,他不是一個憤青(至少相當程度上不是)。
無論如何,只要將魯迅的原文與柏楊的原文加以比較,都可以得到顯而易見的結論:《醜陋的中國人》根本不配和魯迅的文字相提並論。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