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林|説不清為什麼理想而奮鬥,是前些年紅色題材創作的問題
金秋十月,我們將迎來祖國70週年華誕。即將亮相的國慶檔獻禮劇也相繼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關注。
今年的獻禮片有何顯著特點?在當代的文藝創作中,紅色文化、紅色符號扮演着什麼樣的角色?從門庭冷落到引發熱議,獻禮片如何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
就相關問題,觀察者網專訪了知名編劇汪海林老師。
【採訪/吳立羣】
觀察者網:近期,不少單位都在組織“我和我的祖國”快閃活動,而今年國慶檔的獻禮片也有一部圍繞《我和我的祖國》展開。這首創作於1985年的歌曲,為何至今依然有着藝術生命力?
汪海林:《我和我的祖國》這首歌,跟別的歌頌祖國的歌曲不同的是,有兩個主體,一個是我,一個是祖國。整首歌強調個體與祖國的關係,是寫關係的,不是單純寫怎麼愛祖國的,主要是歌頌這種不可分割的情感聯繫。
這首歌很自然,有詩意,一直很受歡迎。這次慶祝70週年,這首歌在多個快閃活動中出現,加上同名電影,可以説成為今年的主題了。我覺得這個主題就是希望每個人融入、參與進祖國的發展進程中來。
觀察者網:獻禮片是一種特殊的藝術創作現象,從1959年第一批獻禮電影到今年70週年,您能不能總結下各個時期獻禮片的突出特點?
**汪海林:**獻禮片並不是我國特色,很多國家都有。為慶祝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等重要節點,各國電影工作者都會拍攝相關影片,比如日本就會給日俄戰爭這種有紀念性的歷史事件拍專門的影視劇。我國專門為建國拍攝獻禮片,以前並不是慣例。1964年,我們有過大型歌舞史詩劇《東方紅》,而有一些年份並沒有專門拍攝過獻禮片。
從《開國大典》開始,我們才逐步有了針對重要節點的獻禮片,一般十年是一個大慶。1989年是《開國大典》,1999年是《橫空出世》,到了2009年是《建國大業》,這也是我們獻禮片商業化的開端。
觀察者網:獻禮片年年都有,而由於今年是建國七十週年,所以大家對獻禮片的期待值也更高了。就目前發佈的預告片來看,您覺得今年的幾部獻禮片較往年而言有何特點?
**汪海林:**今年幾部獻禮片吧,有一個特點,就是題材比較多樣化。像《攀登者》實際上是一個體育題材,《我和我的祖國》是比較典型的當代題材,講述的幾個故事都是當下的故事,當然其中也有年代稍微早一些的,但基本上都是建國以後的故事。我們以前通常會突出使用革命歷史題材來進行獻禮。今年的話可能更多樣化,而且更關注當下的生活。
我這幾天比較關注的一部影片是《決勝時刻》,也準備去看一下。這部影片類似於《開國大典》、《建國大業》的格局,講述了領袖的故事,對當時的一些史實進行了挖掘。我覺得這部片子可以重點關注一下它在敍事上與十年前、二十年前講建國故事的影片的區別。

《我和我的祖國》宣傳
觀察者網:我們常會把新中國的歷史劃分為前三十年和後四十年,而近年來諸多文藝作品也試着將革命年代的歷史與改革開放以後的歷史做一個銜接,通過對一些紅色文化的展示致敬革命年代。譬如“鬼吹燈”系列就有這樣的嘗試。今年另一部備受關注的影片《攀登者》也是如此。您上次在談《攀登者》時提到,自由主義者對電影中紅色底藴的排斥。在當下的文藝創作中,50—70年代的紅色文化、紅色符號扮演着怎樣的角色?
**汪海林:**前三十年的創作有着強烈的宣傳性和強大的價值觀自信。而這些作品的創作者很多甚至直接參與到了新中國建立的進程中,有些導演、編劇本身就是戰士,所以前三十年的創作很多來自於戰爭年代、鬥爭歲月。觀眾也很容易形成共鳴。後來,出現了“傷痕文學”,其實也是立足於社會現實,關注整個社會的變化。總的來説,那時的影片現實感很強,基本不太有像我們現在的架空劇之類的東西。唯一有一部比較特別的是《魔術師的奇遇》,這部立體電影在當時看來是比較“前衞”的,這是那時的懸浮片。
我們的影片呢,有一個問題——像《高山下的花環》小説裏面也反映出了一個細節,就是參加對越自衞反擊戰的戰士們上戰場之前看的電影是什麼呢?是《巴頓將軍》。看完之後,師長就來鼓舞大家了。我就在想一個問題,我們到了79年的時候,是不是就沒有一部更合適的國產影片能夠鼓動到大家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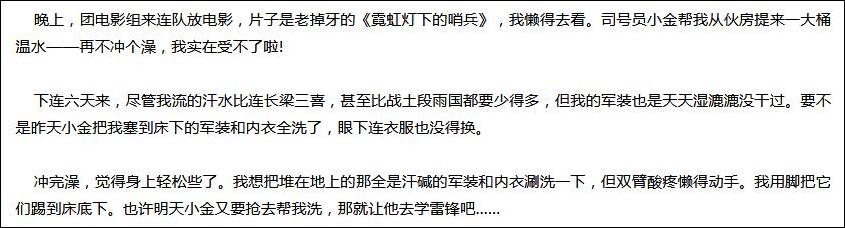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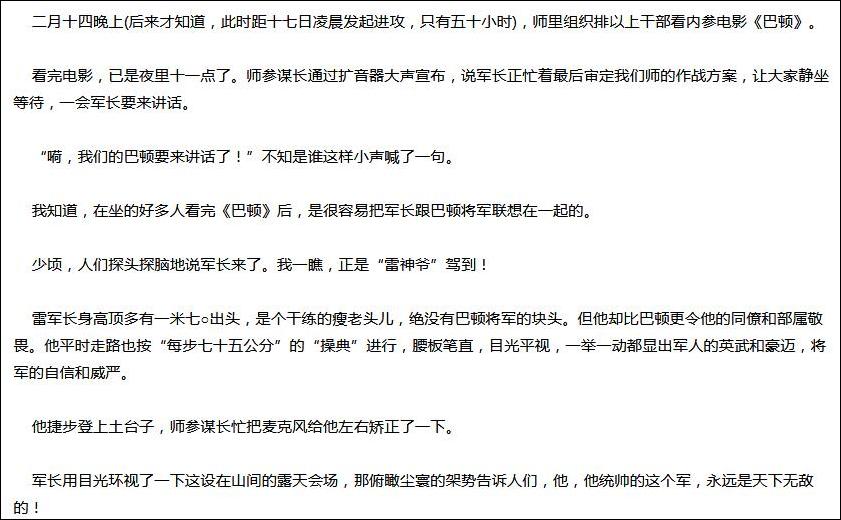
《高山下的花環》小説片段
看來在當時的背景下好像不太容易。也就是説在當時的情況下,再用原先那些具有宣傳性的影片去鼓動一些人,可能影響不是很大了。倒還不如拿一個美國的愛國主義影片讓他們來理解一下軍人的榮譽應該是什麼樣的,一個軍人的職業性應該是什麼樣的。
這個轉型應該説對我們創作者而言,形成了一個令人非常痛苦的壁壘。這個壁壘就是我們要尋找到一個新的“精神家園”。如果找不到的話,我們的影片最終其實就是沒有根的。
同樣,我們看到陳凱歌后來拍了《大閲兵》,寫個體跟集體的關係,後來還拍了《趙氏孤兒》。《趙氏孤兒》的敍事讓他非常困擾,他無法向觀眾解釋這種把自己的孩子獻出去替別人的孩子去死的行為。本來,這個故事在中國流傳了上千年,可到了今天,它的理解卻出現了問題。它的價值觀受到了一個空前的挑戰。那他怎麼辦呢?他就把這個選擇寫成一個不是那麼自覺、主動的選擇,而改成是一種陰差陽錯。
不這樣處理,他就擔心觀眾們理解不了、接受不了。這就是我們今天創作者們面臨的一個巨大問題。但凡遇到犧牲、獻身類的題材,會選擇迴避處理。一些創作者不敢寫,也不願意寫,自己也不相信。這種情況直到最近這幾年才有了變化。
今年,《烈火英雄》票房這麼高!雖然很多人看完以後説:“看了這個片子,更沒有家長願意自己的孩子去當消防員了。”但是,從票房的角度來看,觀眾是認同了片中的價值觀。包括《戰狼2》、《紅海行動》的熱映也反映出了這一點。

《烈火英雄》劇照
前些年還有一個現象,每逢國慶的時候,就有一些人會出來説:“我們的祖國擁有五千年的歷史,怎麼就變成只能紀念50年、60年了?” 今年好像基本上沒看到這樣的言論了。這種言論其實就是企圖偽裝成一個民族主義的面目來質疑、否定共和國的歷史。但實際上,我們知道印度也是紀念共和國成立的年份的,法國也是如此。
你問到了紅色文化在當代的表達問題,我就想起有一部講長征的電影。這個片子講的就是主人公因為喜歡一個女孩兒,為了追求她參加了長征,在這個過程中,懂得了革命真理,最後走完整個長征。這個創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創作者擔心直接講為共產主義理想、為了解放全人類參加革命,觀眾會不能接受,所以就處理成了愛情的力量讓主人公走進了革命的隊伍。
由此就揭示出了一個現象,紅色文化被大量的轉換成了偶像劇、言情劇式的故事。它變成了一個外衣,核心的東西還是情感劇的故事。這些故事實質並不是革命歷史題材。這也是這些年創作的一個總體上的問題吧。
當然,我們也會遇到一些困境。現在就把“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轉換成叫做“為理想而奮鬥”,這個説法呢,就比較西方化了,甚至説比較好萊塢化。我們都知道,好萊塢影片經常會表達這樣的主旨——為了你的理想,不要認輸,不要做你夢想的叛徒。當共產主義這個理想被抽象為一個夢想,也許就和跋山涉水去見自己的父母、歷盡艱難成立一家公司成了一樣事情。
只講為理想而奮鬥,避開談理想究竟是什麼,可能是前些年紅色題材的一個突出問題。當然,這種模糊處理有時候也是需要的。比如,有這麼一個情況:在我們中共一大時確立的黨的綱領是要消滅私有制,但放到今天的創作裏該怎麼寫呢?我記得有一次策劃會,我們就討論關於消滅私有制戲裏面應該怎麼表現。策劃就説,不要具體講黨綱內容了,就説他們為了理想而去犧牲。
觀察者網:在2010年以前,獻禮片並不是很受市場待見,有時還會出現票房冷門的現象。可近年來卻大不一樣了。您如何看待近年來大眾對於此類主旋律影片的追捧?
**汪海林:**以前對這些影片,自由主義者們會説成是政府做宣傳的影片,那麼為什麼大家還愛看?我們分析一下,第一就是這些影片在電影的特性上、類型上是比較成功的,通俗地説,它首先是個好片。
更重要一點就是,在近20多年以來,我們的影視界充斥着一些所謂的表現“人性的複雜性”、“人性的惡”的影片。他們所謂的複雜性,其實也就是膽小、怯懦、背叛之類的情緒。
比如《唐山大地震》裏,圍繞救哪個孩子展開了一系列故事敍述,從而描摹了大量父母之間、母子之間的哀怨,對於這些情緒,觀眾已經厭倦了。
這麼多年過去了,你再去拍唐山大地震,可能現在觀眾想看到的是,在災難面前,人們怎麼樣團結一致克服困難,而不是寫災難把人給擊垮了,讓人成為精神病兒了。這樣一種觀影訴求的轉換已經出現了。這也讓一些電影人不是很適應。觀眾的發展與整個中國的發展是同步的,隨着我們國家不斷地強大,觀眾也在變強大。

《唐山大地震》劇照
現在,觀眾不愛看那些國民劣根性批判的作品。大家希望看到我們怎樣自信地走向世界,怎樣平等地與外國人交流交往,怎樣自然地融入到世界中去。“你別欺負我,我也不欺負你”這種心態和狀態,一個影片要表現好這些東西很難的,很多國家的影片都做不到。
所以,從我們的市場反映來看,觀眾喜歡更自信、更正面的影視表達,希望看到一種民族自尊和整個國家欣欣向榮的一種精神面貌。
觀察者網:《建軍大業》、《建國大業》、《建黨偉業》,三部主旋律影片中都啓用了很多流量明星,帶給電影一定關注度的同時也受到了很多批評,您怎麼看流量明星參與獻禮片的現象?
**汪海林:**流量明星的問題是需要關注的,因為這是一種不正確的製片思路。在商業電影中也不是一個真正靠譜的商業概念。在當時,這些獻禮片的製片思路還是被流量思維給影響了。
流量明星進入到這種國家工程以後,只是在營銷上,他的動靜會大一些,而在票房上,未必能直接帶來多少貢獻。而他們的加入,對影片的氣質、整個質感、創作體系其實有一定的傷害。我認為這是負面的影響。最近對於流量藝人的市場表現,大家也在反思,後面再拍的話肯定也會非常謹慎。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