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再談《歷史的終結》:1989年,我們在蘇聯犯了錯-弗朗西斯·福山
時值《美國利益》(下稱TAI)編輯委員會主席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成名作《歷史的終結》出版30週年,《美國利益》以西方未來可能面臨的挑戰為主題對他進行了訪談。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查爾斯·戴佛森(Charles Davidson),傑里米·加德明(Jeffery Gedmin 譯者/孫的妮)
TAI:今年是你著名的文章《歷史的終結》發表30週年紀念日。但很少有評論家會注意到你在這本基於文章的書中提出的“最後的人”的觀點。你能談談這個觀點嗎?它是什麼意思,它又是如何回應今日所面臨的挑戰?
**弗朗西斯·福山(下稱FF):**整個“最後的人”部分是關於民主在未來會出什麼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如果你只是擁有了一個穩定、繁榮、和平的社會,人們就沒有什麼可追求的了。我稱之為“妄想症”的那種渴望,那種被承認比別人更偉大的願望,並不能得到滿足。你必須有出路,如果你不能像以往那樣為正義而戰,那麼你將為不正義而戰。
如果你想想現在的世界,我們有這麼多的焦慮、憤怒和民粹主義,這其實是有一些瘋狂的。首先,我們沒有大型戰爭,西方世界任何地方都沒有發生重大危機。誠然,收入是持平的,但當收入下降25%時,我們可能會陷入大蕭條。我們沒有疾病,也沒有火星人出現在地平線上。你看一個像波蘭這樣的國家,在法律正義黨興起前的十年裏,波蘭是增長最快的歐盟國家,你會問:他們有什麼不安的?
我書的一部分觀點是,除了嚴重的不安全感或嚴重的物質匱乏之外,還有很多不滿的來源,這些都與人的尊嚴有關。人們不會滿足於沒完沒了的消費主義和每18個月購買一次新的iPhone,因為他們實際上想要得到認可。我確實認為批評家們沒有意識到我是如何説民族主義和宗教不會從世界上消失,並且可能會反咬一口。

弗朗西斯·福山
TAI:你能多談一談這種語境下的中歐與東歐嗎?日益繁榮但不滿情緒與日俱增的不僅僅是波蘭。
**FF:**我們已經有整整一代人沒有在成人階段經歷共產主義的經驗了。如果你生活在一個獨裁的政治體制下,你會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暴政,對嗎?去年我帶我的學生去看了其他人的生活,一部關於東德斯塔西的電影。看着他們的反應是很有趣的,因為他們甚至不記得911,他們沒有極權主義的經驗,所以看到一個真正的警察國家是令他們感到震驚的。
我認為那個時期的成年人是真的感恩於他們能夠生活在民主國家。但是年輕一代沒有直接的經驗,所以他們可以説“布魯塞爾是新的暴政”,這很荒謬。
我也相信伊萬·克拉斯特夫,他寫了一篇文章,認為東歐從未像西歐那樣經歷過社會自由化。在共產主義統治下,他們假裝一切都很好,從種族、種族和容忍度各個角度都是如此,但這僅僅是因為一個壓抑的國家把一切都隱藏起來了。然而,如果你想想德國,他們實際上教導了好幾代人關於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的史實,和由此而生的寬容異己的必要性等等社會信條。這真是一次痛苦的經歷,以至於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因為經常被人講授他們有多壞而感到惱火。那些東歐國家沒有一個做過這種自我清洗。他們有過一些澄清,但其實並不相同。
TAI:為什麼我們會錯過那個機會?
**FF:**這就像共產主義在統治他們的時候凍結了那些社會。在這整個時期,這些國家都沒有移民,而在荷蘭和法國等地,移民的情況卻發生得很嚴重。然後突然之間,這些秘密在1989年被揭穿,此時他們繼承的是存在於1945年的社會。但與此同時,西歐卻在以驚人的速度發展。
TAI:如果你回到1989年和隨後的時期,我們什麼樣的假設和選擇會是明智而有效的?我們又犯了什麼錯誤?
**FF:**嗯,我一直在讀比爾·伯恩斯的自傳,他在制定政策時我為他工作,當時詹姆斯·貝克是國務卿,所以這其實是一次懷舊之旅。我必須説,讀到關於布什41號的文章會讓你想哭,因為那些人太自信了。顯然他們犯了錯誤,但總的來説,温和的態度是值得稱讚的,他們意識到這對蘇聯來説將是一次真正的創傷,他們不想在傷口上撒鹽。
事實上,我記得當時的情形,我們國家貝克小組的成員在白宮與康迪·賴斯和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有過一次激烈的衝突,因為他們想慢點行動,我們覺得他們不理解潛在的社會動力和來自公民社會的革命變革壓力。在這方面,我認為我們是對的,但他們最終還是做到了。我讀了這篇文章,考慮到處理類似於德國統一這樣的事情所需要的精力,就對自己説:“孩子,我們很幸運有這些人來負責。”

蘇聯解體後緊隨而來的是經濟的蕭條和寡頭的壟斷
後來,我覺得有一些真正的錯誤。其中最大的一個是蘇聯解體後我們給俄羅斯人的經濟建議。我認為這是一個被成功衝昏了頭腦的典型案例,我們認為他們可以擺脱所有這些國家結構,事情會都會自行解決,市場會自然而然地形成。我認為傑夫·薩克斯和那些經歷過這些的人實際上都是在用花言巧語騙取蘇聯人的信任。
回想起來,如果他們在私有化的過程中放慢一些;如果他們當時在為真正建立一個國家而考慮,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從那以後,這就成了我的研究議程,因為我現在明白了擁有一個強大國家機器的重要性,它實際上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公平地舉行國有企業拍賣,而不是賣給內部人士,而當時在華盛頓沒有人關心這個問題。
第二件事是北約的擴大,我仍然不知道該怎麼想。比爾實際上很懷疑這是否是一個好主意,並説他當時反對這個主意。這也是一個沒有人能解決的事實問題。你當然可以看到它是如何激起俄羅斯的怨恨的。我估計貝克和布什至少已經非正式地保證他們不會擴大北約。令我不確定的是,當時東歐人對我們爭論的是,這對俄羅斯人沒有任何影響。你現在對他們表現得很温和,但一旦他們變強,他們就會落入陳規。也許那樣是對的。
TAI:這使我們走向民主的退卻和威權的復興。你參與了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的國家建設和民主促進工作。有什麼可以分享的嗎?
**FF:**嗯,我認為烏克蘭是反對獨裁擴張的最重要的前線。這是我參與的原因。顯然,烏克蘭作為一個民主國家沒有成功這一點對普京來説非常重要。他想證明所有這些顏色革命都會導致無政府狀態,所以他很高興看到烏克蘭在掙扎。因此我認為烏克蘭必須證明他們可以做到,並且他們確實取得了進展。烏克蘭是一個主要的歐洲國家,如果它走回俄羅斯的老路,或者它解決不了腐敗問題,這對整個歐洲的民主而言都不是好兆頭。
TAI:既然莫斯科有一個致力於使其失敗的政府,烏克蘭能成功嗎?
**FF:**我想可以。在斯坦福大學,我們剛剛接待了烏克蘭經濟發展和貿易部副部長。她説,在某種程度上,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抵制和敵意對烏克蘭來説是件好事,因為他們的貿易90%依賴於俄羅斯市場,而現在情況發生了逆轉,90%依賴於歐洲和美國。這使他們與現代西方公司而非腐敗的俄羅斯寡頭們有聯繫。
同樣,我認為克里米亞的吞併和多巴斯的入侵實際上有利於他們的國家認同。這是查爾斯·蒂利關於“戰爭製造國家和國家制造戰爭”的舊社會學理論。很多烏克蘭人不理解自己在戰爭前和俄羅斯人有什麼不同,但現在他們有一種不同的感覺,他們想保護自己的獨立自主。
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言,從長遠來看我持樂觀的態度。我們試圖培養年輕的烏克蘭改革者,讓他們相互聯繫,我總是很驚訝他們有如此多人。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並真正想融入歐洲,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世代相傳的問題。蘇維埃一代正在走下舞台,一旦這些三四十歲的人接管了舞台,這個國家就有了機會。
TAI:許多人現在談論的是與俄羅斯的巨大的權力競爭。你是那樣看的嗎?
**FF:**我寫了一篇關於蘇聯在中東的外交政策的論文,主要是為了表明蘇聯領導人是多麼的謹慎。他們會威脅進行干預,但他們總是等到危機真正過去,這樣他們就不必再繼續下去了。儘管他們派出了武器和顧問,但他們很少讓自己的軍隊受到傷害。
在一個只有前蘇聯三分之一大的國家裏,普京完全把這一點拋到了腦後。當然,從實質的角度上看,俄羅斯和北約之間的軍事平衡要比冷戰時期差得多。所以首先,他是一個巨大的冒險者。例如,向委內瑞拉派遣軍隊是完全瘋狂的。如果我們真的想這麼做,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打退它。我想他會在某種程度上得到報應的。
但另一部分是在這場不對等的戰爭中,通過干擾選舉和使用互聯網,他以一種非常巧妙的方式利用了有限的資源。他們比西方任何人都更早地發現了這一點,而且他們在利用西方社會的內部分裂的能力上遠遠領先於中國。
TAI:你説普京是個冒險者。那唐納德·特朗普是個冒險者嗎?
**FF:**不,我不認為特朗普有任何大的風險,沒有任何涉及潛在的武力使用的風險。他在敍利亞發射了一些導彈,但奧巴馬就該這麼做了。那是一次極低風險的冒險。
我確實在一些情況下選擇給予他信任。我認為大多數人都會同意的是他針對中國的貿易政策。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冒險行為,因為當你威脅關税時,你真的會得到相應的報復和不斷升級的貿易戰。這可能仍然會發生,但我實際上認為這麼做是必要的。我實際上最近和拉里·薩默斯討論過,我説:“你們應該在2000年或者奧巴馬時期就這麼做。”直到現在,中國人才開始害怕我們。

特朗普與奧巴馬
另一個我認為特朗普政府做的正確的事情可能是朝鮮問題,因為朝鮮真的做好了戰爭準備,有針對不同軍事行動的具體計劃。我認為朝鮮人和中國人都看到了這一點,這就是導致此次峯會的原因。它目前還沒有產生一個值得它的付出的結果,但這就等於冒險了。
TAI:你提到了一些在特朗普外交政策中看到優點的領域。你看到了哪些問題?
**FF:**這很簡單。你的總統每隔一天就會改變主意。信譽很重要,特朗普在任何事情上都沒有信譽。我看不出有誰能和他做交易,因為當你認為你有交易的時候,他就開始改變交易條件。美國-墨西哥-加拿大的協議似乎因為這個原因即將破裂。
基本價值觀問題也很嚴重,因為美國過去一直主張全球民主,現在不再是了。很明顯特朗普根本不在乎民主。這也導致了不連貫的外交政策。我説針對中國的政策是好的,但他應該做的是讓所有的歐洲和日本同時對中國施加壓力。相反,他攻擊所有這些潛在的盟國,同時對所有的盟國進行貿易進攻。這根本沒有任何戰略意義。
TAI:你認為特朗普與俄羅斯的關係如何?
FF:我一直認為他的行為很奇怪,即使是從他自己的私利來看。當選舉干涉事件一出現,他就應該説:“這太離譜了,完全不能接受。即使他們想幫助我,作為一個美國人,我認為他們不應該被允許這樣做。”事實上,他在華盛頓扮演莫斯科的接應人的角色非常出色,這讓你甚至覺得這不是真的,因為如果俄羅斯人真的在培養一個美洲候選人,他們就不會得到一個如此明顯的人選。
我認為他可能是我在公共生活中遇到過的最自私的人,但即便如此,在很多情況下,他也不能很好地計算自己的私利,因為他的自戀妨礙了他。我認為俄羅斯就是這樣的其中一種情況。
**TAI:**特朗普之後,你會給這位新的美國總統什麼建議來幫助恢復美國的信譽和我們聯盟的凝聚力?
FF:嗯,我不確定這會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因為我認為我們的盟國真的沒有其他辦法來取代我們的關係。歐洲人不會走向中國和俄羅斯,因為如果這樣做,他們無法從華盛頓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每個人都在等待和保持希望,很多美國人對這些盟國説:“耐心點,這傢伙只會在那裏呆四年,然後事情就會恢復正常。”
我認為最大的問題是,他現在動員了大量的基礎力量,比如説對於俄羅斯的空前支持。我們得看看共和黨現在是否恢復了30年代和40年代秉承的孤立主義,這是一個很大的危險。
但最大的變化不是總統説的,也不是國務卿説的,而是美國社會本身。對於我們的許多盟國來説,美國社會已經演變成了一種他們根本不理解的東西,並且令他們覺得非常可怕。
當我們創辦《美國利益》時,正是在入侵伊拉克之後。歐洲人説:“孩子,這些人來自火星,我們真的不明白是什麼在驅使他們。”這一直是雜誌的目的之一,試圖彌合相互理解中的差距。但如果你認為我們瘋了,那麼,好吧,現在我們已經偏離了正軌。
TAI:民主黨有可能採取自己版本的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嗎?
**FF:**是的,當然有可能。這是一個很大的誘惑。許多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開出的價碼一個比一個更左,就像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沒有人想在這時被人在左傾程度上超過,這很危險。
我認為能與之抵銷的力量只是他們真的想贏得這次選舉,許多民主黨人相信,如果他們過於左傾,那將有助於特朗普。但問題是兩個政黨都沒有真正的控制人。沒有人能説:“我們必須進行這種戰略計算,並提出這種候選人。”
TAI:現在整個西方的政黨都有麻煩了嗎?
**FF:**是的,我想説是的。美國政黨已經衰落了很長一段時間,我的意思是,在這個政黨裏沒有一個核心團體能夠代表它做出決定。所有的一切都是關於外部捐贈者和那些設法贏得這些被稱為初選投票的人,但是政黨機構本身的權力卻非常有限。
英國是一個典型的威斯敏斯特體系。兩黨制,由簡單多數票當選的選舉體系選出兩個紀律嚴明的政黨,還有一個首相,類似於由選舉產生的獨裁者。隨着英國脱歐,這已經完全消失了,因為兩黨都有這些內部的分歧,所以保守黨或工黨的領導人不能約束他們自己的成員。同樣,在德國,社民黨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已經失去了20%的選民,法國社會黨也消失了。
TAI:你最近在歐洲旅行,為創造你的新書《身份/認同》。人們在那裏問什麼問題?
**FF:**最大的問題是現代民主國家是否需要國家認同。在歐洲,很多左翼人士認為這是不必要的。他們認為民族認同必然導致民族主義、侵略和排外以及所有這些壞事。
右翼人士中,有人認為民族認同很重要,但他們想開歷史的倒車,並加強那種排斥少數族裔的民族認同。我並不能真正看到的是一箇中間派的立場——你應該考慮國家認同,但它必須基於一個民主和開放的立場。這在歐洲是否可行,是我在每一個訪問過的國家討論的一個核心問題。
TAI:與歐洲相比,你認為這些身份問題在美國的表現如何?
**FF:**我認為,總的來説,我們比歐洲人的情況更樂觀,因為經過長期的鬥爭,我們確實發展了我所説的信條或公民身份。到民權運動結束時,這種身份認同已經不是基於種族或族裔,而是基於信仰和美國的基本原則。
但我認為這正受到威脅。右翼來説,即使不是特朗普本人的話,很多他的支持者希望恢復美國人基本上都是白人的舊觀念。左翼來説,你面臨一個不同的問題。有些人不相信有共同的身份,或是種族主義、父權制和殖民主義;你沒有正面的故事可以講述。這兩種立場在美國沒有在歐洲那麼極端,但在這裏也發生了。
TAI:有一件事我們沒有討論過,那就是腐敗。以及西方對獨裁政權的支持作用。你能把這當作對民主的威脅嗎?
**F****F:**令我震驚的是,里根時代的自由市場思想最終證明了避税天堂的合理性。富人從不想交税,沒有人願意,但他們過去常常提出原則性的反對交税的論點,採取拉弗曲線的形式,以及各種關於低税率有助於經濟增長的理論,或者説,如果我們繳税,政府將把它們浪費在一些毫無意義的社會計劃上。
現在,你有一個眾所周知的富有的美國人,比如説,建立了慈善基金會,資助了很多好的事業,但是他生活在加勒比海的一個小島上,因為他不想付美國的税。我認為他對此並不感到難過。他説:“美國的税率太高了,那我為什麼要付呢?”住在避税天堂是完全合法的。
政治障礙在於,人們實際上不希望執行這些規則。他們希望投資銀行的私人銀行部門幫助他們把錢藏起來,不讓税務人員發現。我認為里根主義或撒切爾主義給了他們這樣做的原則性理由。這不僅僅是“好吧,我應該更富有”,而是這種認為對有生產力的人徵税是不公平的想法。
TAI:但似乎與25年和50年前有所不同,這些問題得到了更大的緩解。
**FF:**嗯,我認為,當資本主義在一種社會責任感和一種意識中得到平衡,即資本主義制度嵌入一個更大的社會,這個社會有規範,在某些行為上有界限時,它總是能很好地運作。
牛津大學的發展經濟學家保羅·科利爾(Paul Collier)最近寫了一本非常好的書《資本主義的未來》(The Future of Capitalism),書中對公司的性質提出了這一觀點。早在1970年,米爾頓·弗裏德曼就發表了一篇廣為引用的文章,他説公司的唯一業務就是讓它的所有者受益。科利爾認為,整整幾代的商學院學生已經內化了這個概念,這導致了壓榨員工,從他們那裏敲竹槓得到最後一筆工資,削減他們的福利,利用政治權力阻止他們加入工會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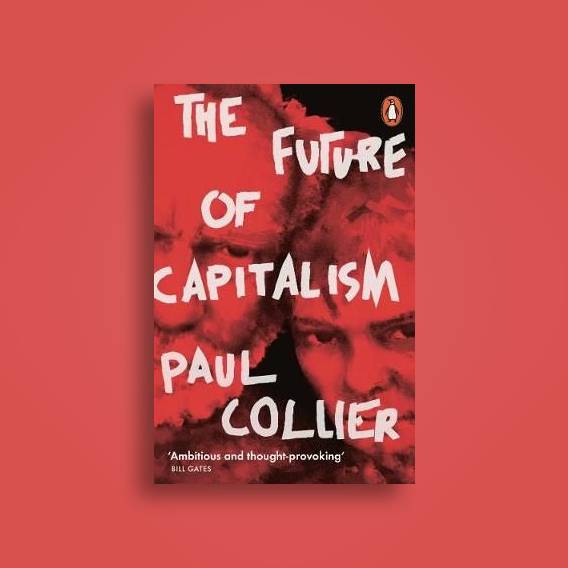
保羅·科利爾的新書《資本主義的未來》
資本主義並不總是這樣。尤其是二戰後的德國和日本,商界精英們意識到,他們在二戰期間一直在與工人們維持着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敵對關係,如果他們真的要擁有社會和平和民主政治制度,他們必須要接受分享一點財富。我認為美國資本家也和前一代一樣。
TAI:如果這些都是習慣和價值觀、行為和文化的問題,那麼我們如何才能更好地改變事情呢?
**FF:**其中一部分將是自然的政治調整。你現在看到的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左派已經不再提的觀點,像70%的上税等級,或者谷歌和Facebook的分拆。六個月前,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但現在很多人都在跟上這股潮流。我認為在經濟政策方面,對外開放的窗口將發生重大變化。在窗户的左邊緣,它會走得太遠,但是在窗户的中間可能會找到一個合適的地方。
我認為缺少的是一個針對所有這些行為的道德基礎的好論述。左派有一種道德主義,但左派真正需要的是一位政治企業家,他能準確地表達出你希望在這些經濟政策的作用下出現的社會類型。我還沒見過這種表述。
TAI:讓我們回到1989年。你如何評價對那一年的感覺,以及它的意義,我們在為什麼而戰,我們在為一個從未經歷過的新一代而戰嗎?
**FF:**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教歷史,但我們做得不太好。多虧了我對歷史的研究,我才知道很多事情。例如,經歷過大戰爭的戰後一代與二戰一代有着截然不同的道德體驗。至少對美國人和英國人來説,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崇高的道德鬥爭,在那裏他們反抗暴政,他們獲勝,民主勝利。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完全不同的動物。它破壞了資產階級的道德,因為你們有所有這些為國王和國家而戰的年輕人,然後他們走進了絞肉機,最後毫無意義。所以你有一個更虛無主義的結果。
我沒有經歷過這一切,唯一能讓我欣賞的方法就是閲讀它,想象一下當一名士兵,或者經歷過這段時期會是什麼樣子。很多事情必須通過小説來完成。我記得在高中的時候讀過埃裏希·瑪麗亞·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一書,這本書給我帶來了很大的傷痛。我認為保持對這些事情的記憶是有可能的。
(本文原載於公眾號“法意讀書”,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