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看西方學者的理論,總讓我懷疑:“他們説的是中國嗎?”
【文/ 葛兆光】
1
最近讀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著作《民族—國家與暴力》(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凡是讀到與中國有關的段落,總不免多看上幾眼,當然,這是因為自己關心的面向是中國思想文化的緣故,遇到西洋、東洋人的書中有討論中國事情的,總是格外留意。吉登斯在這本書中多次提到中國,想來是討論全球問題與普遍理論的西方學者視野中,已經有了“中國”的存在,儘管他們常常是帶着西方人的居高臨下,或者是把中國作為映射自身的“他者”( the other),不過西洋那些頂級理論中,中國不再是可有可無。不過,當我讀到下面一段文字的時候,卻大吃一驚,突然讓我起了一個疑問:“他們説的是中國嗎?”或者真的是本書譯校者王銘銘所説的,中國只是他們理論書寫時的一個“想象的異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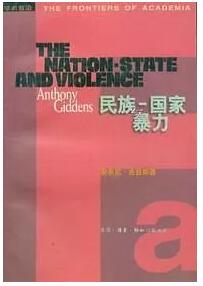
本書是吉登斯著作中最具有歷史社會學特色的一部作品。其理論思路源於《社會的構成》中有關社會轉型的論點,以全球社會變遷的歷程為敍述框架,力圖通過建構社會轉型的一般模式,闡明塑造現代社會的力量。作者本人則宣稱,本書的目的主要在於以系統的方式勾勒出世界史的粗線條。
這一段文字是這樣的:
唐時期的中國,相對來説就不存在來自外部攻擊的嚴重威脅,那時對老百姓的控制也是相當成功的。……社會秩序被依次劃分為五個等級,其中,軍隊同土匪、盜賊、乞丐均居於社會的低層,士紳集團居於上層,其他等級依次為農民、工匠和商人。通常並不會給予軍隊首領以政治職位,而且為了防止部隊及其指揮者之間的聯合,還對他們進行輪番調動。
據註釋,這裏的依據除了張仲禮的《中國紳士》(The Chinese Gentry)之外,有艾伯哈特的《中國史》(A History of China)、費正清的《中國的思想與制度》(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這兩位當然是權威,著作當然是名著,不過,如果翻譯沒有問題的話,吉登斯從這兩部著作中得到的結論卻是讓我覺得不怎麼對:首先,唐代並不是不存在外部的攻擊和威脅,突厥、吐蕃、回鶻、雲南輪番與唐王朝為敵,在唐王朝鼎盛的時期,尚且對四裔無可奈何,在安史大亂之後,外患更是令人憂心如焚,不要説相對處於弱勢時的代、德宗時期,就是漸漸強盛的憲宗時代,也免不了異族的種種騷擾和進攻。

其次,且不説唐代的軍人是否如此下賤還是值得考慮的,就是“士農工商”的等級差異,在唐代是否真的還像傳統時代一樣天經地義,這也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可是,這些出自中國學家之手卻又不是專門研究的中國學著作,並沒有對當時社會階層的異動有深入的考察。
再次,是誰説的唐代軍隊首領不能得到政治職位?難道唐代歷史上的藩鎮都是自封的麼?所謂軍隊的互相調動究竟是對當代中國政治的瞭解,還是對唐代歷史圖景的想象?而皇帝的軍事決策權究竟有多大,那個時候,各路藩鎮無視王朝的權威,競相比賽似地向中央挑戰,難道不就是因為他們擁兵自重麼?如果考慮到中晚唐的情況,大多數軍隊恰恰不能依從皇帝的旨意隨意調動,而大多數地方軍隊的首領,恰恰應當説都擁有很高的政治職位。
吉登斯不懂中文,雖然他來過中國。他對於中國的敍述,其實是借了另一些懂中文的西洋中國學家的敍述。在西方,很多由中國學家表述的關於“中國”的知識在支持着各種各樣關於“世界”的理論,只要這些理論家希望他們的論述是關於“世界”的,他們就只好鑿壁偷光式地向中國學家挪借關於中國的知識。可是,他們一不留神就出了紕漏,這應當怪誰呢?

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Baron Giddens,1938年1月18日-)英國社會學家。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對當代社會學領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以來最有名的社會科學學者。他與布萊爾提倡的“第三條路”(Third Way)政策也影響了英國甚至其他國家的政策。
2
其實,這一類情況很多。在我們的學術研究界,對於使用第二手資料的鄙夷一直是很厲害的,不過對於這些來自西洋的頂級理論家,有時候,口氣就似乎軟了下來,這些人心裏在想,誰叫他們是洋人呢?彷彿是外國人就可以網開一面。誰叫他們是討論全球普遍性理論的呢?似乎口氣很大的人就可以不拘小節。
近來對國人的批評風氣漸漸瀰漫,彼此針尖麥芒的,火氣也頗不小,不過,碰上洋人、洋著作就採取了雙重標準,彷彿洋人就可以擁有“治外法權”似的。仔細想想,信口雌黃的其實並不僅僅是國人。
就以被列入經典的為例,不必提曾經是爭論焦點的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韋伯的《儒教與道教》,僅僅在我的記憶中,比如有名的布留爾( L. Levy-Bruhl)《原始思維》,據説他關於原始人的思維的想法,是讀了沙畹譯的《史記》後才產生的,不過他的他的很多材料卻來自格羅特( J. J. M. Groot)的《中國宗教系統》(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六卷本,且不説他的西方視角與西方觀念,就是對於中國事情的判斷,他也不得不接受格羅特的説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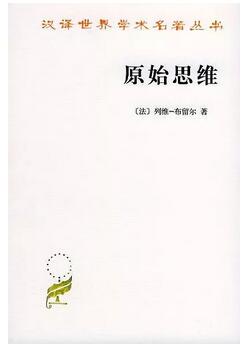
於是,對於“四”這個數字的論證中,他引述了格羅特關於中國的四方、四季、四色、四神,但是,偏偏這些中國例證可以説明的並不是四而是五,所謂的“聯想關係”的根本恰恰是“五行”,只取四而不取五,其實並不能理解中國古代人對於宇宙時空的“立場”。
同樣,他所相信並用來論證世界普遍性的原始祈雨風俗的一個支持例證,就是格羅特説的中國某些地區人們完全負擔寺院的開支,因為他們相信寺院能夠調節風雨,可是,這種説法即使有一些根據,卻也不是普遍性的。
根據何茲全、謝和耐(Jacques Gernet)等人對古代中國寺院經濟的研究,寺院在很早以前就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經濟支持系統,而在 20世紀之初也就是格羅特在中國調查的時候,寺院的主要功能中,祈雨大約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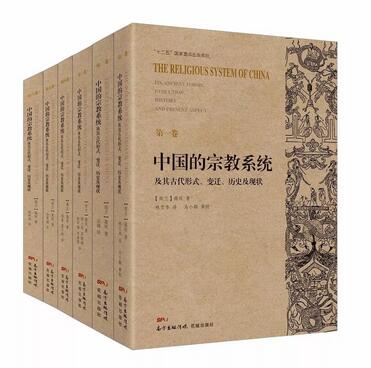
本書共6卷,作者以田野調查與經典文本(以中國古代典籍為主)相結合,運用人類學、社會學和中國學結合的觀念和方法展開敍述,從西方角度對中國本土宗教進行了相當全面的介紹,包括喪葬禮儀、古代死亡與靈魂的觀念、墳墓制度(帝王陵寢、義冢及各地民間墳塋)、喪葬方式、居喪習俗、風水、靈魂與祖先崇拜、投胎轉世觀念、鬼神觀念、驅鬼辟邪習俗及儀式、神職人員等等各個方面。作者高延(J.J.M.de Groot,1854-1921)荷蘭萊頓大學漢學教授。是荷蘭籍漢學家、進化論人類學家,歐洲最早研究中國宗教的學者,中國宗教田野研究方面的先驅者。被認為是西方到中國的第一個真正的民族學學者。本書是其漢學研究代表作之一。
説起來,格羅特的書雖然是以“中國”為名的,但是實際上他只是以他在廈門的調查為基本依據的,特別是他的著作雖然出版於1892年至 1910年,然而他不僅沒有注意到這個古老的空間世界的廣袤,也沒有注意到注意到更新的時間流逝的加速度。於是,聽信了他的話的布留爾才會下這樣一個判斷:“要讓中國棄絕她的那些物理學家、醫生和風水先生卻很難。”可是,正是在格羅特出版它的六卷本的時候,主流中國社會已經開始對自己的傳統以及“物理學家、醫生和風水先生”棄如敝屣。
甚至一些相當專門而且精彩的著作中,也有着因為無法判斷中國學家的研究,而使一些中國論述出現問題的地方,像我非常佩服的愛裏亞德(Mircea Eliade)的《世界宗教史》,根據他自己的文獻解題,我們知道關於中國宗教,他參考了相當多中國學家的著作,如格羅特、沙畹、葛蘭言、馬伯樂、康德謨、芮沃壽等,不過,我們知道,這些人的研究取向是很不同的。
比如格羅特是傳教士似的實地考察,多是目治之學,雖然鑿實,不免有區域性限制;而葛蘭言的研究則近乎杜爾凱姆、施特勞斯的社會學,不免有一些遷就結構分析的想象與虛構;而還有一些中國學家則不免受到從歐洲一直注意着的印度學那裏得到啓示,在追溯歷史的時候,好發一些奇怪的想象性意見。
因此,愛裏亞德在關於中國道教和道家的論述中,在尚無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就把道教以呼吸與保精為中心的性技術,説成是在印度瑜伽影響下形成的,可是,如果他知道後來在馬王堆出土的《合陰陽》、《十問》,知道早期中國自己也曾經有過發達的性知識和性技巧,他還會這樣説嗎?
3
不是在批評這些理論家的論述,更不是在否定中國學家的研究。**其實我一直很欽佩“異域的眼睛”,有時,即使是偏執中也有深刻,畢竟他們有不在此山中的優越處,所以我在一篇評論愛裏亞德《世界宗教史》的評論中用了一個文學性的題目,叫“隔簾望月也是洞見”。**不過,也讓人感到憂慮的是,為什麼西方人常常是“隔簾望月”,而西方關於全球普遍性理論的建構中,一説到中國,總有這麼一些作為“洞見”的“偏見”?
最近,有人在批評《劍橋世界近代史》中的“世界”二字,“世界”由於缺少了中國甚至東亞而名不副實,那麼,如果不缺少中國或東亞是否就名副其實地成了“世界”?其實也不盡然。
《東方學》中説的一個道理很對,就算是關於“世界”的敍述中包含了中國,但是,那“中國”也不是這“中國”,正如薩義德( Edward Said)所説的那樣,它可能只是在學院中被研究,在博物館中被展覽,在各種關於人類和宇宙的學術著作中被理論表述出來的一個想象的“中國”,而且關於這種“中國”的知識還是“或多或少建立在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識”基礎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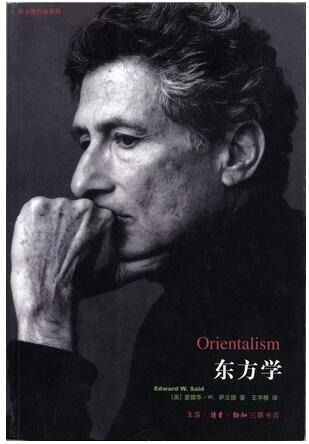
著者薩義德:“《東方學》這本書與當代歷史的動盪和喧騰是完全分不開的。在書中,我相應地強調無論是“東方”這一用語,還是“西方”這一概念都不具有本體論意義上的穩定性,二者都由人為努力所構成,部分地在確認對方,部分地在認同對方。”
而域外的中國學家們也確實常常是用西方人的視角,在好奇地審視,用西方價值觀念在選擇與評價,用不自覺的西方背景在理解中國的。這些建構世界普遍性理論與歷史的學者一旦借用他們的成就,就不自覺地接受了這種“想象的中國”,並把這個想象的中國加入他那個論述中的“世界”,或者在印證“中國”與“世界”(其實是西方)的一體性,或者在凸顯“中國”與“世界”的差異性。當然無論是一體還是差異,在這種或渾融或對立的描述中,他敍述了涵蓋東西方的整個“世界”。
不過常常遺憾地出現誤讀。因為域外的中國學家有深刻的洞見,也有不可理解的偏見,像《劍橋中國先秦史》,是集中了西方相當傑出的中國學家共同合作的成果,可是 David Shepherd Nivison所撰寫的第十一章《古典哲學著作》中把中國學者通常認為偽書的《子華子》與楊朱並列,作為敍述公元前 4世紀思想的資料,不免讓我感到詫異。
**另一本傑出中國學家謝和耐所撰,已經被譯成中文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在一連串的精彩論述之後,卻在“總結性描述”的第七章中説到“ 13世紀的中國人似乎比唐代的中國人在行為舉止上更自由隨意,而較少矜持拘謹”,這也讓我不可理解,因為我不知道究竟這裏所説的“中國人”是貴族、士大夫、城市市民,還是所有的中國人。**至少這種結論和我所看到的文獻記載相當不合,可是,倘若有一個正急於討論“全球文明一體化進程”的理論家看到這一結論,他會不會因此寫入什麼“全球個性解放普遍性進程”之類的理論中呢?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是法國著名漢學大師,法蘭西學院院士謝和耐的名作。細緻描述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的下層社會民眾生活。《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這個書名,雖只以寥寥幾個單詞,卻已把直至兩宋才臻於化境的中國日常生活藝術的舞台擺到了草原遊牧民族不斷進犯的黑暗佈景之下,從而在讀者心目中構成了一種巨大的懸念和反諷。
記得張隆溪曾經以福科(Michel Foucault)的《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的序文中所引的博爾赫斯的“小説家言”為例,指出博氏自稱出自《中國百科全書》的動物分類表,居然能夠成為福科用以表達對世界的深刻思考的象徵,並用它來“瓦解我們(西方)自古以來對於同與異的區別”,想象的虛構成了福科的利器。

張隆溪,1947年出生於四川成都,世界級華裔學術大師之一。北京大學碩士,美國哈佛大學博士,曾任教北大和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現任瑞典皇家人文、歷史及考古學院現在唯一健在華裔外籍院士、歐洲科學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及韋斯理大學傑出學人講座教授,北京大學燕京學堂特聘教授 。
不過,這種郢書燕説的幸運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碰上的,常常出現的倒是上面我們説到的那種情況,中國學家的“失之毫釐”導致了理論家們的“差之千里”,中國學家們偶然的一個疏忽,弄得沒有能力檢驗每一個證據的理論家們彷彿秦二世遇到趙高指鹿為馬,如果這個錯誤只是局部的證據倒也無妨,如果像福科那樣犯上一個幸運的錯誤倒也罷了,不過,如果這個錯誤不幸成了判斷“世界”的“普遍”的問題的基本依據,這個錯誤就彷彿南轅北轍了。
這並不是危言聳聽,因為在西方思想世界中對於現在這個世界的整體判斷中,“中國”常常是一個重要的“異數”,論全球政治格局也罷,論東西文化差異也罷,論現代後現代也罷,論意識形態衝突也罷,論民族國家與文明衝突也罷,哪一處也少不了想象的異邦“中國”,可是卻很難見到真正的實存“中國”。
於是,僅僅靠中國學家們提供的所謂“中國形象”,有時恐怕就是透過西方人的藍眼睛看到的,彷彿眼鏡上蒙了一層藍色透明紙看到的異域風情畫,所謂“中國事情”,有時恐怕就是透過西方人的邏輯與價值的篩子過濾的異邦奇事錄,這種場面我們已經經過《圖蘭朵》在太廟的演出看到過了,儘管有了一個天才的中國導演,儘管有了真正中國建築的背景,儘管有了五彩繽紛的中國服飾,可在很多中國人看來,那一場在中國中心演出的,畢竟是一場異域之夢幻劇。

4
在中國研究中,有一個可以從側面判斷其對中國學術的關心度的例證,這就是學術刊物所允許使用的其他刊物縮略號(簡稱),如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可以簡稱 JAOS,《支那學》(Shinagaku)可以簡稱 SG,被允許用縮略號,意味着它已經司空見慣,常常被引用則表明它在學界中人心目中的分量。可是在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開列出來的 46份這類雜誌中,日本佔了12份,而中國大陸的只有4種,即《考古》、《歷史研究》、《文史哲》和《文物》。
其中《歷史研究》的官方身份自然確立了它的權威性,《文史哲》被列入其中,也許是因為它的歷史,而《考古》與《文物》則是洋人無可奈何地需要我們提供的資料,從這份清單上也可以看出大陸學術界在西方中國研究中的角色,彷彿與經濟特區中所謂加工區的地位相似,出口的大約都是“初級毛坯”,至於進一步的“精緻論述”,大約洋人並不需要。
無疑,這是由“權力”與“話語”的關係決定的,在 20世紀學術世界中,民族與國家的地位常常與學術聲望和説話聲音大小密切相關。我曾經看到不少歐美中國學研究者竟然遠到日本去留學,我在日本著名的京都大學和東京大學都遇到過這些留學生,問到原因,當然主要的是因為有豐厚的獎學金。不過,把中國研究正宗算在日本的人也大大地有。一個研究中國禪宗的美國學者在日本訪問,在東京的一個小酒店的榻榻米上他説了一句讓我噎氣的話“中國禪還是日本人研究得深入”。還有一個研究中國的大鬍子歐洲人在京都見到我,我發現他的日本話要比中國話説得還好,他説“每年都到日本一次”,可是問到他是否到中國時,他也尷尬,“不多,去過一兩次吧”,可他的專業卻是中國思想史。於是,浮到我心頭的一句話,就是陳寅恪當年的詩句:“羣向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子羞欲死。”

日本奈良
毫無疑問,我們應當認真檢討自己,用英文法文德文同步出版的學術雜誌和學術論文很少,不像日本那樣,自己想了方法出了錢,巴巴地翻譯成洋文給他們看,還説這是“學術國際化”(當然“國際化”總是我們化過去,他們不化過來),也沒有用心地研究課題、方法與敍述語言有什麼樣的“通識”,總是懷着閉門造車出門合轍的心理,**甚至研究中國文史的學者中,至今還殘留着“天下中央”的感覺,覺得在中國文史這一畝三分地裏,似乎少了那個西洋農夫,也不會長不出莊稼來,反正自給自足。**至今我這個歷史悠久的行業中,還有很多人對外面精彩的世界一無所知,儘管在二三十年代中國對西洋人的中國研究已經很熟悉,儘管八九十年代中國學者要伸頭瞭解西洋研究已經比較容易,可是確實是很多人仍在“畫地為牢”,反正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
我沒有這麼強烈的民族主義,也不想與洋人,無論是西洋人還是東洋人去爭奪中國的解釋權,解釋總是解釋,一個“中國”作為文本,怎麼解釋也都不過分,誰叫現在據説已經是確定性瓦解的“後現代”了呢?何況他們的解釋有着他們特別的心情與背景。只是有些不服氣的是,為什麼那些號稱討論世界普遍性真理的理論家們,在他們討論“世界”中的“中國”時,總是沒有多少來自中國的學術和思想資源?在那裏彷彿“中國”是一個缺席者,空出來的那個座位總是有異邦人在李代桃僵地對理論家們進行“中國的敍述”,而中國學者卻總是心有不甘卻滿臉無奈地看着這隻缺席的座位。
也許,一個原因是在學術界已經被西方話語籠罩的情況下,表述的語言也只能是西方的,衡量的標準也只能是西方的,不用西語便不成“世界”的學術,或者説想進入世界學術語境就要用西語書寫,用中文寫作的人總是拿不了諾貝爾獎,害得國人跌足了好久,後來聽説實在不能用西語,用容易譯為西語的中文也湊合,於是,要拿獎,就只能讓作家先考 GRE。學術研究也差不多,自己失落了評判權力,就只好藉助 SCI什麼的當一把尺子,不用英文法文德文寫作的文史學界,就只好看着西方那些未必高明的中國學家越俎代庖。
我想問的是,有沒有人想過這樣一個道理,如果要研究世界普遍真理,為什麼理論家們不好好先學習漢語?或者説,為什麼一個涵蓋了中國、亞洲和西方的頂級世界理論,中國人不可以發明?
【本文原標題為《缺席的中國》,原載於《開放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