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辰:美歐的零負利率及釋放流動性對中國的挑戰和機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孟凡辰】
2019年11月1到18日,我回國走訪了北京、上海、廣州、海口和山西大同,和眾多國內有關省市領導,一流智庫朋友,高科技企業CEO以及基金投資合作伙伴等,進行了廣泛深入探討交流。這次回國,除了落實幾個全球獨特和領先的德國創新產品和服務,與中國合作伙伴的對接外,還分享了自己關於全球最主要宏觀經濟趨勢的思考和判斷。
一、西方發達國家零負利率和增加流動性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2015年歐洲央行啓動了第一輪債券購買計劃,到2018年被暫停時已購買歐洲各國國債2.6萬億歐元,換言之,這一舉措總共擴表向市場釋放了2.6萬億歐元流動性。歐洲央行在將利率保持為零的同時,在2019年9月12日宣佈重啓政府債券的回購。
10月10日,德國10年期債券利率,降為負0.53%;該日截止,歐洲央行已擴表至4.65萬億歐元。同時歐洲央行宣佈,鑑於計劃每月200億歐元債券回購,將很快面臨購買每國債券不得超過33%的上限,所以提議將有關上限最晚在2021年提高至40%。根據德國經濟週刊報道,歐洲央行每擴表1萬億歐元,可以幫助歐元區各國經濟實現0.2%-0.8%的增長。
在德國企業存款被銀行普遍收取負利率之際,美聯儲11月數據也顯示了連續3次降息,也開始重啓5400億美元的印鈔擴表計劃。或許是擔心其它國家會對美國印鈔轉移危機不滿,美聯儲迄今仍然否認這是新一輪的量化寬鬆。

當地時間2019年11月4日,德國黑森州法蘭克福,歐洲央行( ECB )新任行長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Christine Lagarde )進入歐洲央行辦公區,這是她就任來第一個工作日。(@東方IC)
眾所周知,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聯儲曾3次啓動QE(量化寬鬆),總擴表約2萬億美金,幫助美國度過危機,但是同時卻向全世界輸出了通脹,透支了發展中國家的需求和增長。美國和西方所有發達國家,在財政嚴重透支和選民税負已無法提升的前提下,只剩下對儲蓄直接收負利率和間接貶值這一手段,這一點大部分選民都無法理解。美國向自己的實體經濟盡最大可能輸入流動性,以降低融資成本。
2015年迄今,歐洲央行如此增加流動性,理論上通貨膨脹不可避免,但實際情況如何呢?以德國為例,如果2015年消費價格指數是100的話,2018年消費價格指數僅為103.8,三年只增加了3.8%。考慮到德國和中國經濟增長的互補性,我們接下來就以德國經濟兩德合併後的各類價格指數變化,説明其零負利率和流動性的增加,及其高端出口導向的全球化發展模式和對消費者價格指數的影響。
1991年到2018年,能源價格的增長是德國經濟能被有效化解的最大的負面因素之一,電力價格增加了117%,各類(進口)油氣價格上漲為119%,其它上漲價格品類,藥品116%,住房租金87%,裝飾品/手錶71%,麪包/穀物56%,牛奶/蛋製品47%,旅遊出行48%,啤酒47%,電話通訊43%,書籍42%,汽車36%,傢俱照明31%,鞋類30%。
消費價格指數下跌的有兩類,它們是電視機/收音機-75%,家電-12%。考慮到德國這段時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將近翻番,即增加了約100%,所以賺到收入超量增長的是被美英法主要掌控的能源、電力以及醫藥供應;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得以依賴的市場領域,其價格指數上漲皆遠低於可支配收入增長。
換言之,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主要以出口發達國家為導向,在買單超額收入增長的能源電力和醫藥行業暴利的同時,直接承接了其它所有制造業通貨膨脹壓力的轉移,已經並將繼續為西方國家流動性的泛濫買單。
中國下一步的轉型發展,應該如何應對這一挑戰和機遇呢?
二、中國實體經濟的轉型發展需要額外獲取西方國家的流動性
中國作為全球最大西方國家硬通貨儲備的擁有者和依賴出口增長最快的實體經濟體,如何能止損西方硬通貨長期貶值輸入通脹,同時得益西方國家流動性的泛濫?
作為一個德國國民經濟博士學位獲得者,我曾經的研究領域是後凱恩斯主義的理論依據;我的博士論文,是依據新古典主義的瓦爾拉商品勞工和資本市場的理論模型,對本質短期的凱恩斯主義非均衡理論擴充引入資本市場投資活動,開展動態長期化研究。
在這一過程中,尤其是在當時所在大學國民經濟理論的教學過程中,我充分了解西方經濟理論研究,但對一個開放的經濟體,並沒有完成理論層面的完整模型分析研究,對開放經濟體之間的商品勞工和資本的互動,及其相關金融及宏觀經濟政策博弈應用的研究,西方經濟學並未能提供理論依據。
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的宏觀經濟發展模式,是每出口1美元產品就減少國內1美元的供給;如果這1美元用於進口西方先進的產品和技術(服務),中國經濟就有了質的進步;如果這1美元被央行發行8-10人民幣收做外匯儲備,那麼1美元出口就會帶來2美元的通貨膨脹。所以中國出口導向的宏觀經濟發展,在把海外相關工作崗位和收入賺到國內來的同時,必然帶來通貨膨脹的輸入,這也是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普通員工工資收入從每月36人民幣,上升至當下4-5千人民幣的成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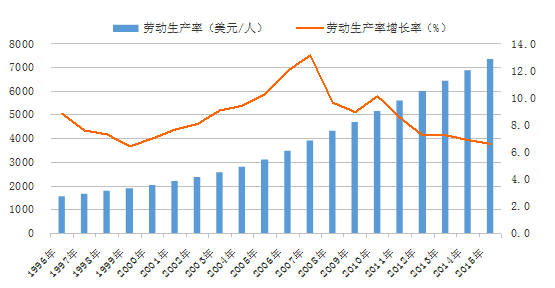
我國勞動生產率及增長率變動1996-2016(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當然另外一個收入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是中國實體經濟的勞動生產率達大幅提升,和向製造業價值鏈高端的拓展延伸。
美國當下對中國經濟進一步的轉型增長的遏制,主要是用關税打壓低端製造成本競爭力和利潤空間,強迫其向東南亞等更低勞動力成本國家轉移;同時對中國已佔據價值鏈高端的企業如華為,限制其在西方發達國家獲取高端市場的可能,並且限制其可持續研發和創新的硬通貨利潤和資金來源。
在中國實體經濟面臨發達國家硬通貨市場的時候,增長空間有限,如果要利用發達國家的研發創新能力及其成果的資金需求,就必然要求盡一切可能創新營造多種源泉渠道,將中國實體經濟更直接地對接到可以享用西方發達國家增加的流動性的渠道上。
在中國經濟整體負債已高達GDP約150%到200%的前提下,中國經濟相對於如美國的最大債務優勢,是外匯儲備依然足以覆蓋已有硬通貨外債;所以中國實體經濟面臨的融資挑戰,主要在依託人民幣國際化,即內債國際化。
不管各種人民幣債券在出售給發達國家投資機構和個人的時候是否需要抵押,只要是能獲取現有硬通貨外匯,能用人民幣償還未來支付,這類債務的本質就是內債國際化,多多益善,而且是對中國高達3萬億外匯儲備最有效的保值和對沖。
三、人民幣債券國際化的戰略需要和可行性
從地緣政治角度判斷,人民幣內債國際化可以營造很大的戰略優勢,西方國家尤其華爾街和金融資本,必然救助如同希臘等對西方金融體系擁有系統生存影響力的國家;對比中國宏觀經濟的現有出口導向定位,消滅潛在競爭對手尤其是過剩產能,是中國崛起及其發展模式的一種選擇。所以將人民幣內債英鎊化,歐元化甚至美元化,是對中國現行出口驅動發展模式的升級,更是中國內需驅動增長的外匯資金來源保障要求。
中國2019年進博會,被德國媒體和政治決策者普遍視為是宣傳需要,原因是中國過去數年出於保外匯儲備需要,進口降幅始終被管控在出口降幅之內,中國並沒有真正增加進口的外匯資金來源。如果沒有法國總統馬克龍的親臨中國2019年進博會,德國原本只計劃派一個經濟部的國務秘書參加,而不是教研部長來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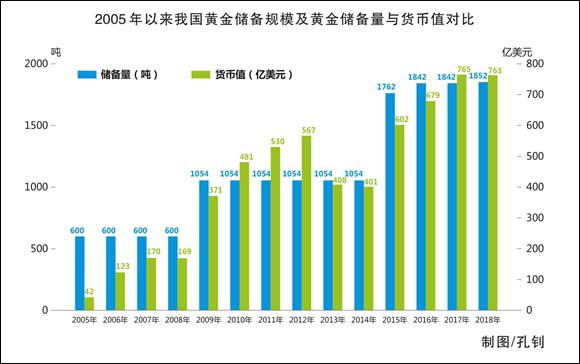
中國經濟的轉型發展內需需要的外匯,以及一帶一路的投資增量需求,很難進一步通過出口型實體經濟來獲取,本質需要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來保障,人民幣債券走出國門無疑會是最好的開源。當然我們接下來需要回答的核心問題是,這一戰略舉措有可行的外部市場環境嗎?
其實早在2017年3月7號,花旗銀行就已宣佈將中國國債收入其3個固定收益指數。
2018年3月23號布隆伯格作為北美三大國債指數擁有者(加花旗銀行和JP摩根)宣佈,將人民幣國債納入布隆伯格-巴克萊指數,即將人民幣國債比例從0增加到5%。
但是一年運作下來,相關國債基金的人民幣國債投資比例,僅為1-2%,遠未到5%的比例,根據金融時報報道,至少有5億美金投資缺口。
據我判斷,原因有二,首先是人民幣債券的產品和資訊供給不足,其次是對人民幣匯率風險的評估和顧慮;當然如果人民幣國債國際化,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核心組成部分,如果中國政治和金融決策者沒有如同出口創匯般共識,就不可能得到全力以赴的推進,且得到財政部和人民銀行的必要協同。
2019年9月4號JP摩根宣佈,將逐步把中國國債逐步納入其發展中國家指數(GBI-EM),最高可達10%;高盛隨即估算,這將意味着30億美金將流入中國國債市場。

9月份,摩根大通稱中國債券將被納入基準指數
用各類人民幣債券換取英鎊歐元甚至美元,本質如同發達國家央行將人民幣作為儲備與人民銀行置換人民幣一樣,無非是人民幣是按匯率置換而債券是依據匯率上浮1.03到1.04(考慮現行國債利率)。國際金融市場之所以看好人民幣債券,原因主要是發達國家債券利率普遍在2%以內(如美國10年期國債)甚至負利率(如德國國債),人民幣國債依然提供3-4%的收益;其次人民幣國債市場已經是數萬億的規模,這對無論是華爾街還是倫敦金融資本,都是全球最有吸引力的一個增量市場,和需要開墾的處女地。
這次在國內和有關領導,中國最頂級智囊及金融界領導談及大灣區機遇和營造時,對比美國硅谷,我判斷中國創新型中小企業如果能有渠道無縫隙對接國外債券融資市場,避免如阿里等股權融資的單一渠道高額代價(即股東軟銀賺錢無數),那麼中國金融市場就會實現真正服務實體經濟轉型需求。
畢竟美國的政府和企業債券的市場運營,已經國際化且非常透完,完全可以借鑑,而且中國金融業已到了完全能學習借鑑的發展階段了。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