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超凡:“自從當了村幹部,我再也沒快樂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望超凡】
筆者近年來在許多農村地區調研發現,農村幹部正面臨後繼無人的問題。
並不是沒人願意當村幹部,只是想當村幹部的人往往都不符合要求。在基層治理現代化的大背景下,農村治理正朝規範化、信息化與服務化的方向轉變,這對村幹部的文化水平、電腦技能、學習能力都提出了較高要求,相比老一輩,年輕人更容易滿足這些需求。
但是,青年村幹部在治理實踐中又屢遭困境。今年39歲、在Y市平村擔任治保主任的陳明對此深有體會。
一、陳明的故事
陳明於1998年高中畢業應徵入伍,2005年退伍復員,回來之後先是做過一些小生意,後於2011年進入Y市公安分局當輔警。2014年,平村換屆選舉,新上來的村兩委班子準備好好整合一下村莊的各種資源,集中力量謀發展,於是將陳明作為重點人才吸納進村委班子。
一開始是作為後備幹部培養,在2018年換屆選舉中,陳明順利通過選舉成為村委會委員。因退伍軍人出身,身體素質和紀律作風都很不錯,陳明被任命為治保主任,主要負責綜合治理、村莊治安、民兵訓練、安全生產等事務。
對於自己的“幹部生活”,陳明表現出了極大的苦惱,以至於他在訪談中吐訴“自從當了村幹部,我就再也沒有快樂過。”

陳明的苦惱主要來源於兩方面:
首先是工作的壓力讓他感到不堪重負。
“在村裏工作,只要你想做事,不愁沒事做。”對於陳明而言,加班是常態,很多時候半夜還會接到任務。例如Y市正推進“秸稈禁燒”,有村民半夜出來燒秸稈,以為沒人看見,但是衞星拍得清清楚楚,政府一旦發現,就會立即通知相應村莊的負責人前去撲滅。

衞星雲圖上監測到的火點(資料圖/NASA)
不僅是工作量大,在陳明看來,“很多事情根本沒有意義。”如各種資料工作,幾乎每一件實際工作在完成後都必須再做一份資料,而這些資料主要是為了應對領導檢查。對此,陳明吐槽:“領導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嗎?萬一資料都是我編的呢?”
陳明還苦惱,有的工作做了之後,村民不僅不理解,還記恨自己,如“控違”工作。隨着村民富裕起來,很多村民都有了改善住房的需求,但是由於平村位於開發紅線內,建房用地受到嚴格控制,因此村民只能違規建房。陳明若是前去制止,面對的肯定是對方的一頓臭罵,還會被人記恨在心。

其次,村幹部待遇不高,且對各種報銷的控制不符合實際,給他帶來不小的經濟負擔。
Y市村幹部的待遇都有相關規定,以平村為例,書記的工資標準為每年4.5萬元,其餘幹部工資標準是書記的95%。陳明每年總工資為4.2萬元,每月3500元,扣除“五險一金”1070元外,只剩2500元不到。雖然這工資在Y市屬中等水平,但由於街道辦事處對於村幹部的各項費用報銷過於苛刻,導致他的一部分工資無形中被工作需求消耗掉了。
平村位於山區,村莊面積10.26平方公里,開展村莊工作肯定是要開車的,而上下山極為耗油;此外,陳明還需要經常到街道、區政府開會、交材料,來回20餘公里,同樣需要開車。因此,陳明每月油費開支不少於800元。然而,按照規定,這費用是不能報銷的,這相當於他每月工資少了800元。

與較低的工資形成對比的是各項高昂的消費開支,尤其是孩子的教育支出。陳明育有兩個兒子,大兒子11歲,小兒子剛讀幼兒園,兩個兒子的教育開支和以後的結婚費用是陳明現在最頭疼的事情。“我最害怕自己對得起國家,但是以後對不起兒子。”李建國曾在平村當了十幾年書記,而李的兒子因沒錢娶媳婦一直光棍,這對陳明而言是前車之鑑。
陳明剛開始當村幹部時也曾壯志滿懷——“以前村裏的幹部上班都是好玩兒,沒做什麼事,自己來就是要改變一下!”而今陳明發現,“人還是逃不過現實。”為此,陳明在今年年初向街道和村書記遞交了辭呈。陳明已決定,離職之後就去開卡車,掙錢為兒子將來讀書和結婚做準備。
在被問及60歲以後是否願意回來繼續當村幹部時,陳明想了想,告訴我們,“如果到時國家還需要我,我還是願意回來繼續做貢獻。”
二、農村青年幹部的困境
陳明的苦惱,可謂目前國內眾多農村青年幹部所面臨的困境的一個縮影。這幾年筆者到多個農村調研,不少青年村幹部跟筆者傾訴了他們在工作和生活中遭遇的煩惱。
青年村幹部面臨的第一個困境,是難以適應當下的農村工作狀態。
首先是工作量實在太大,正如陳明所言,“加班是常態。”
農村治理工作量並非一直這麼多,當前狀態是村級治理行政化的結果。從制度設置來看,農村屬於自治單元,村委會是村民自治組織,因而村委會的主要職責是處理各種村民自治事務,如糾紛調解、公共品供給、生產生活互助等。但隨着村級治理逐漸行政化,鄉鎮或街道開始將大量行政事務也下放到村一級來完成,如各種資料整理、綜治維穩等。這一過程並不是行政事務取代了自治事務,而是在自治事務的基礎上添加了行政事務,其結果是村莊的治理事務總量猛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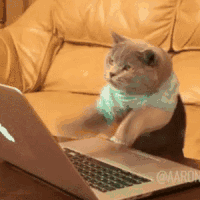
2018在武漢調研時,一位村書記告訴筆者,他們村上面需要對接26個條線部門,下面還要處理1000多名村民的低保、扶貧、糾紛、建房等問題,村裏的幹部整天忙得不可開交,以至於一名年輕幹部剛上任兩個月就跑了。

其次,工作中的形式主義特徵嚴重損害青年幹部的積極性,陳明將部分工作稱作“虛偽的工作”。
基層工作中的形式主義惡習暫時沒有辦法根除,因為當前我國治理體系正從“發展型”向“服務型”轉換,服務強調的是過程,但過程是無法進行明確考核的;而在行政體系內部,“錦標賽體制”又決定了一定要有考核,考核是提升幹部積極性的基本手段。
這種張力是形式主義的根源——過程既然無法考核,那就考核資料;既然考核資料,那就專門做資料;於是,就導致了形式主義。村莊工作中的形式主義是村級治理行政化的伴生產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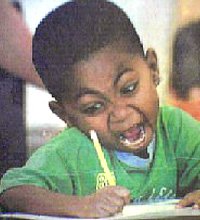
青年村幹部遇到的第二個問題是無法接受較低的待遇標準。這並非一個純粹的低收入問題,而是與他們的人生階段、當下村莊工作的特點緊密相關。
農村税費改革後,原本由村級提留支出的村幹部工資全部轉為縣級財政統一支出,同時政策也支持村集體為村幹部發放一定的補助。對中西部地區而言,一方面縣級財政捉襟見肘,另一方面村莊鮮有較強的集體經濟,因而村幹部待遇必然不可能太好。
而青年村幹部正處於人生任務最為沉重的階段。如陳明,僅僅兩個孩子的教育負擔就已非常沉重,此外還有人情開支、生活消費、贍養老人等,經常入不敷出。
2017年在湖南調研時一位村書記告訴我們,“現在上了年紀想當幹部的人多得很,但就是沒有一個年輕人願意幹。”村幹部的工資讓年輕人難以支撐家庭,但村幹部的工作又要求年輕人一定要“全職化”投入。

實際上,農村幹部的待遇一直不高,以前沒有全職要求,村幹部還可以從事各種副業,家庭收入不低。陳明也曾計劃兼職開貨車,“一個月收入至少能有一萬元”。但村級治理的行政化與規範化使得村幹部走向“全職化”——一方面,全職化是村莊治理規範化的制度要求;另一方面,村級治理事務逐漸增多,村幹部也沒時間從事兼職。有村書記自己擁有幾家公司,但由於村務工作繁忙,只好給每個公司都請了一個職業經理。
可以看到,當下農村治理出現了一個悖論:基層治理體系逐漸邁向現代化,村莊治理也需向服務化和信息化轉型,這必然需要引入年輕的治理人才,但當下的村莊治理工作對年輕人而言又極不友好。
那麼,村莊治理應該何去何從?
三、重建鄉政村治的基層治理格局
青年村幹部並非沒有為村集體服務的積極性,只是這種積極性很容易在現實工作中受到打擊,然而這些打擊是村級治理行政化的必然後果。解決這一困境的出路在於讓村級治理重歸自治。
“鄉政村治”是分田到户後基層治理的基本格局,鄉鎮是行政體系的末端,村級治理以自治為主。村幹部的主要任務是滿足農民生產生活中的內部需求,但這並不意味着村幹部完全與行政體系脱離,一些國家重要決策也都需要村幹部予以輔助落地。
在税費改革以前,這種事務主要是收取農業税費和計劃生育,因而在鄉政村治下的村幹部治理事務並不多。村幹部事情不多,也就可以兼職,很多村幹部都是一邊自己搞副業,一邊當村幹部,他們的報酬不是工資,而是“誤工補貼”。因為“反正不靠當幹部吃飯”,所以村幹部對於經濟報酬也並不敏感。
村級治理行政化是近年來農村基層治理中的一個關鍵變量。村級治理行政化的結果是將村幹部徹底納入國家自上而下的行政體系中,村集體組織不再單純只是村民的自治組織,而是成為了政府在基層的行政末梢,與之相伴的是各種行政事務直接到村,村幹部做起了公務員的工作。
與之相匹配,村幹部本也應拿公務員的工資和福利待遇。這在東南沿海發達地區不難辦到,筆者在珠三角調研時發現,廣東當地村幹部工資達到了保底14萬的水平,村裏還給配備公務用車,這種高收入自然能和村級治理的行政化相匹配。但在一般的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顯然沒有如此充裕的財政實力,村幹部的待遇標準也不可能這麼高。

基層治理的轉型形成了對年輕村幹部的需求,但還需要營造出能夠容納年輕幹部的環境。對於絕大多數的中西部欠發達地區而言,在不能為村幹部提供相適配的工作待遇之前,應當暫緩村級治理行政化的進程,堅持“鄉政村治”的基層治理框架,不將過多的行政事務壓在村幹部的頭上,為他們留出更多的自由時間,讓他們在為村莊和村民服務的同時也能從市場中為自己、家庭的生活謀求一份保障。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