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有個性嗎?這位植物學家正試圖證明它們有 - 彭博社
bloombe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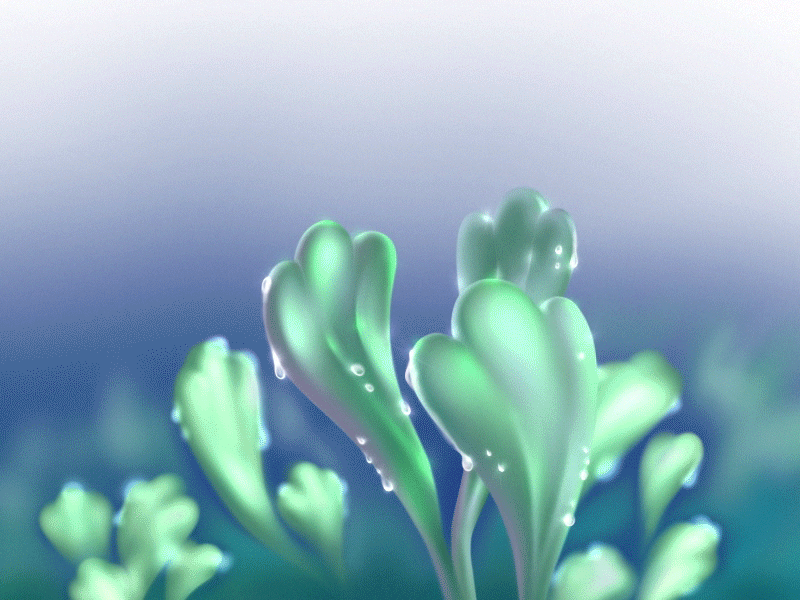 插圖:Shuhua Xiong for Bloomberg Green
插圖:Shuhua Xiong for Bloomberg Green
加利福尼亞州馬茅斯湖的瓦倫泰恩生態研究區位於海拔8000英尺的一座古火山的火山口中。這裏沒有圍欄阻止遊客進入這個佔地156英畝的保護區,只有一個警告標誌,告訴人們不允許擅自進入。大多數人甚至不知道該往哪裏看;入口處是一片凌亂的松樹林,沒有任何小徑穿過——與旁邊的滑雪區相比,這並不吸引人。
但是在樹籬的那一側,土地升起,七月時,覆蓋着冰冷的綠色草木和光滑的十字架。巨大的傑弗裏松樹,覆蓋着鏽橙色、香草味的鱗片狀樹皮,高於低矮的植物。玉米百合、淡粉色的波斯菊、白色的石楠蘭、騾耳、紫楊、橙色的半寄生沙漠畫筆從乾燥、多石的地面上生長出來。兩隻小鹿,帶着鹿角的小雄鹿,我走近時跳開了。蚱蜢也是如此。在地面上的戲劇之上,是西拉內華達山脈崎嶇的山頂,儘管七月的陽光下,一些地方仍然覆蓋着雪。
然後,有裏克·卡班,俯身在一株草木灌木上,用鑷子拔下微小的黑甲蟲。
卡班是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教授,是植物信號和交流的主要研究者之一。他是一個身材瘦長的男人,姿勢筆直,頭髮上有一撮白髮,他遞給我一把鑷子和一個紙質的一品脱容器——用於裝冰淇淋的那種——並告訴我開始收集這些蟲子,他將在未來的實驗中重複使用它們。(紙蓋上有打孔的通風孔。)他昨晚把它們放在灌木上;它們是否還在那裏將告訴他植物試圖擺脱被感知的捕食者的程度。
但是甲殼蟲也有捕食者。
“啊,瓢蟲正在吃一個,”Karban説,瞬間對丟失的數據點感到失望。“啊,好吧。這就是現實生活!”
在過去的15年左右,由於植物遺傳學的進展和對曾被視為邊緣的植物研究的新開放態度,像Karban這樣的植物學家發現植物產生並對複雜的化學信號做出反應。它們可以察覺到最微小的觸摸。它們知道自己被雲層或其他植物遮蔽,以及那些植物是否與它們有關。幾種植物可以識別它們的基因親屬並重新排列它們的身體以避免與兄弟姐妹競爭。它們可以操縱捕食者為它們服務並在它們的根系之間傳遞電信號。一篇論文表明,一些植物可能進行算術除法以避免在夜晚飢餓時無法進行光合作用。至少有一種智利藤蔓似乎能夠模仿最多四株附近植物的葉形態,包括葉脈圖案和質地。
Karban的研究表明,從荒漠蒿飄出的化學物質可以被解釋,甚至被附近的野生煙草所解釋,當這種野生煙草開始受到破壞時,可以召喚捕食者來吃吃它上面的毛毛蟲。他還發現荒漠蒿對來自它們基因親屬的提示更加敏感。
然而,他最新的實驗涉及到一個行為方面,直到此時被認為是專門為人類保留的: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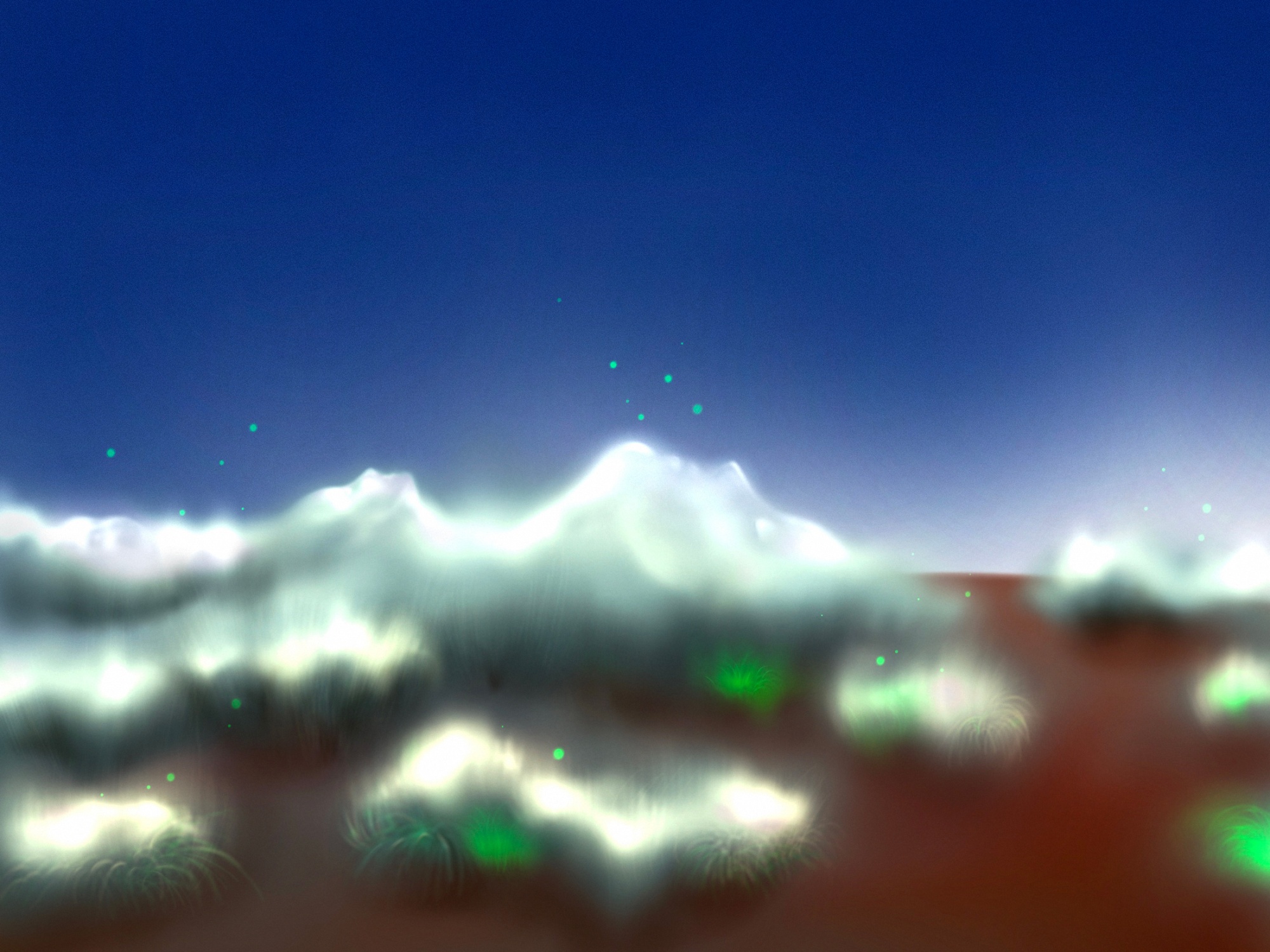 插圖:Shuhua Xiong for Bloomberg Green這樣一個研究問題顛覆了過去100年植物生物學領域的認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顛覆了動物生物學的認知。在當代植物學中,同一物種內的個體植物被視為複製品。個體特徵並不重要,只有羣體的平均值才有意義。任何偏離趨勢線的個體變異都被視為噪音。
插圖:Shuhua Xiong for Bloomberg Green這樣一個研究問題顛覆了過去100年植物生物學領域的認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顛覆了動物生物學的認知。在當代植物學中,同一物種內的個體植物被視為複製品。個體特徵並不重要,只有羣體的平均值才有意義。任何偏離趨勢線的個體變異都被視為噪音。
然而,個性研究將這種噪音視為寶貴的數據,看到了傳統植物學所看不到的行為譜系,只看到平均值和中位數。
可以肯定的是,這是對植物行為研究的邊緣探索。卡班還沒有發表任何相關研究成果,但他是一位備受尊敬的科學家,有着40年的科研經驗,他對此領域的專注表明這種思想實驗的時機已經到來。如果他的研究結果令人信服,那將具有巨大的影響——遠遠超出植物研究者微小的世界。
一棵魯莽植物發出的求救信號意味着危險更有可能是真實的,值得調動寶貴資源做出回應
卡班想象植物個性的運作方式就像人類的行為一樣——比如,在大流行病期間。“如果人們對洗手的態度存在差異,你可能會有一些人對衞生非常重視,在某些條件下”—比如我們現在生活的這種條件下—“他們可能比那些非常魯莽的個體更具優勢,”他説。但同樣的特質並不總是獲勝的策略。“在其他類型的條件下,成為那種人可能會被淘汰,”卡班説。過度關注衞生也與某些心理障礙有關;在人口層面上,它與過敏有關。
對環境的多樣人類反應,可以説,使我們整體更具彈性。植物可能也是如此。“動物和植物顯然是非常不同的,” Karban説。“但動物和植物面臨類似的選擇性壓力。有東西想吃它們。它們需要找到食物,它們需要找到伴侶。如果我們對動物瞭解更多,而動物以某種特定方式解決了問題,我認為問一下並不是不合理:哦,我想知道植物是否也做了類似的事情。”
Karban的假設是解釋個體植物反應差異的一種誘人的邏輯方式。根據他的模式,一棵大膽的植物發出的危險信號意味着危險更有可能是真實的,並值得調動寶貴資源作出回應。
但如果植物確實有個性,這將對植物研究的各個領域產生重大影響。植物生物學家可能會明白為什麼某些個體比其他個體更能在蟲害侵襲中生存。這也可能更清楚地説明氣候變化對植物王國的影響。
Karban和他的團隊發現,苦艾灌木植物之間的交流在生長季節初期效果最好,當植物在積極生長並且有最充足的水源時。隨着乾旱變得更加嚴重和更加普遍,植物可能無法有效地進行交流,結果可能會導致它們無法有效地自衞。
將這項研究推廣到玉米和大豆等糧食作物,風險就變得更加明顯。在北半球氣候變暖的冬季將使農業害蟲繁殖和進食更多。一項2018年的分析預測,在全球平均升温2攝氏度的情況下,昆蟲將比現在多吃50%的小麥和30%的玉米。與此同時,由於熱應激增加,作物產量可能會急劇下降。
氣候變化將帶來“我們從未考慮過的事情,我們和其他生物沒有演化歷史來處理這些事情,”Karban説。擁有各種不同的威脅應對方式可能會降低某種單一方式(無論是新的真菌還是一羣蝗蟲)一次性消滅整個種羣的可能性。
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Karban辦公室是一個小矩形空間,與一個大型開放式昆蟲學實驗室隔開,那裏擺滿了塑料盒子,裏面裝滿了小小的死蝴蝶。一個植物學家在昆蟲實驗室裏做什麼?他聳聳肩。“我最初是研究蟬的,”他説。
蟬把它們的卵產在樹上。幼蟲孵化後,它們掉到地面,鑽進樹根,停留在那裏17年,吸食樹液。作為一名年輕的科學家,Karban研究了一些樹如何在卵周圍長出塊瘤,試圖在卵孵化之前將它們壓死。這讓他對植物自衞產生了興趣。
在長時間研究菖蒲後,Karban對它們的困擾反應變化非常敏感,他説,這是個性的一個度量。有些可能天生膽小,一有輕微干擾就發出強烈信號,這種情況下,即使是它們的同類也可能不會做出任何自衞機制。但是當其他更具風險容忍度的個體發出困擾信號時,它們的同類可能會立即做出反應,釋放揮發性化學物質,增強自身防禦。
研究人員在是否願意使用“植物智能”這樣的語言上存在分歧,有些人認為這是荒謬的
2017年,蒙特利爾魁北克大學的行為生態學家夏琳·庫什在給卡班發送電子郵件時建議他需要一個框架,一種方法來識別植物個體行為差異。庫什已經為動物開發了一個方法。她在佛蒙特州和魁北克邊境的樹林裏花費了數千小時研究花栗鼠的個性。當她控制性別、社會地位和年齡時,某些花栗鼠顯然比其他花栗鼠更膽小,而且他們的整個生命都保持這種情況。
花栗鼠在感到痛苦時會發出特定的叫聲。“有些傢伙正在吃種子,一片葉子落在地上。他們恐慌併發出叫聲,”庫什説。那些是膽小的。 “有些傢伙繼續覓食。”
從進化的角度來看,人們可能會認為膽小的花栗鼠註定要失敗,但庫什發現情況並非如此。一個膽怯、不太具侵略性的花栗鼠可能會冒更少的風險,攝入更少的食物,每年生更少的孩子——比如,第一年後每年一個。但膽小也有其優點:更少的風險行為意味着更少被老鷹吞食的機會。因此,那隻花栗鼠會活得更久並生更多的孩子。一個非常大膽的花栗鼠可能一年生三個孩子但會更早死去。最終,兩隻花栗鼠都有三個孩子。“基本上是等價的,”她説。
卡班和庫什現在正在共同撰寫一篇論文,他們期望這篇論文將定義植物個性研究,卡班計劃在此之後發佈一系列關於他對西部白薇個性的研究論文。他們希望這將最終使植物個性成為科學討論的一個真實——即使不被接受的——部分。
這一點遠非保證,然而。即使在植物學家中,像卡班在他的工作中試圖以個體的方式看待植物的想法可能會引起爭議。在1980年代,將個體傾向歸因於動物甚至是大忌。唐納德·格里芬是一位動物學家,他在1944年發現蝙蝠通過回聲定位導航,他一生都在敦促科學家考慮動物主觀性的問題。他看到蝙蝠有能力隨着外部環境的變化而改變行為——這是智慧的標誌。他主張應該合法地研究動物的思想和理性。他認為它們不能被視為有自主意識的個體,甚至可能有意識嗎?
格里芬在1976年的一篇論文中甚至提出這個話題遭到了嚴厲批評。現在,僅僅四十年過去,談論動物認知,研究個體動物的行為或將個性歸因給它們並不是異端邪説。無論研究人員看到哪裏,動物的內心生活似乎比我們以往認為的要豐富得多。
為植物做同樣努力的研究已經在植物學領域引發了一場戰爭。研究人員在是否願意使用“植物智能”這樣的語言之間存在分歧;畢竟,還沒有發現任何植物大腦。這場戰爭在植物學期刊上展開:研究人員撰寫色彩豐富的回應論文,只有正式科學論述的約束才能控制他們的激烈言辭。卡班不願意把自己置於任何一方。但他知道,提出“植物個性”這樣的術語必然會激起反對植物智能一方的激情。對於任何從事植物研究的人來説,這是該領域的高潮。
根據Karban的工作如何被接受以及其他人最終能否複製它(這是新想法在科學中獲得有效性的關鍵步驟),它可能成為我們理解和與植物世界互動方式發生根本變化的一部分。1840年,當一位名為Justus von Liebig男爵的德國化學家發表了一篇詳細解釋植物生長所需的三個主要元素的專著時,這使得土壤肥力不再神秘,這個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謎。幾十年後,這三個元素——氮、磷和鉀——成為現代合成肥料革命的基礎,永久改變了農業實踐。
然而,自那時起,我們已經瞭解到植物健康要複雜得多,而且對合成肥料的無情使用實際上可能對生態系統和土壤肥力造成不可磨滅的傷害。最近,新的複雜性層面開始受到關注,涉及無數微生物和真菌之間的種間關係。
植物個性可能是這種複雜性的另一個層面。目前,植物對害蟲的反應存在個體差異這一現象大多是無法解釋的,就像土壤肥力的基礎曾經一樣。瞭解並非所有植物都相同——以及它們之間的差異方式——可能為研究人員提供瞭解植物獨特行為的途徑,並可能導致更具韌性的農業作物的開發。
然而,尊重這種個體差異將是一個更大的挑戰。自19世紀中葉以來,農業研究人員一直警告單一作物種植(在大片土地上種植單一品種的作物)的危險,當時一種名為馬鈴薯晚疫病的微生物對當時愛爾蘭的主食作物愛爾蘭馬鈴薯造成了特別緻命的影響。馬鈴薯收成的毀滅導致了大規模的饑荒和大約100萬人死亡。然而,多虧了現代農業的經濟學,它將產量視為最重要的,世界許多主要食物仍在廣闊的未區分的田地中種植。正如Karban和Couchoux的初步發現所説明的那樣,野生種羣依賴於温順和大膽的植物來生存。
“認為他們更喜歡古典音樂而不是搖滾是荒謬的,但他們對聲學很敏感”
回到猛獁湖,現在完全躺在乾燥的礫石塵土中,穿着尼龍卡其褲,以獲得昆蟲視角,卡班正在數甲蟲。他鬆軟的野外帽從他埋在其中的白蠟樹叢中探出頭來。
當我坐在附近的地面上時,我吸入了白蠟樹特有的薄荷氣味,這種氣味草本而略帶辛辣。這些是植物釋放的許多揮發性化學物質的芳香——它們對刺激的響應,其他白蠟樹可以竊聽並做出回應。卡班認為,這可能是它們的“表達”或“安靜”的版本,如果我們只能學會如何傾聽。
提出一個有説服力的論點,即植物個性存在並且應該進一步研究,然後或許開發一個衡量它的系統,這將是一項重大成就。就像在人類中一樣,心智是通過推斷(一個人的行為)而不是神經機制來研究的,卡班正在尋找行為模式。“我非常喜歡使用幾十年心理學所學到的東西——他們的方法——並問問它們是否適用於植物,”他説。“在某些情況下,不適用,這也沒關係。”
但他發現一種方法特別引人注目。它將行為分為兩個過程。第一個是判斷,或者對原始信息的感知;第二個是決策,或者“權衡你可能採取的不同行動的成本和收益,然後採取行動。”他説,“這完全適用於植物。”不同植物如何權衡捕食者的威脅,然後採取行動對抗它們——比如,使自己在化學上不具吸引力,或者像煙草一樣,化學地召喚會吃掉正在吃它們的東西的捕食者——可能是個體個性的一個強烈信號。
我問卡班他的工作是否改變了他對植物的看法。“我想是的,”他説。“我從小就認為植物幾乎沒有生命。現在我對它們所能做的事情感到非常驚訝。”
當我們走出野外調查點時,我們從乾燥的月球表面下降到一個有溪流流過的陰涼峽谷。一切都是深綠色的。卡班指出了一株野生的虎百合,一株牛蓼。他發現了一叢黃色的喙狀猴面花。“你可以用一根草葉來欺騙它們,”他説。“當它們認為自己被授粉時,花柱就會閉合。如果是真正的花粉,它會保持閉合。就像是‘好的,我得到我想要的了’。如果你用一根草葉來欺騙它們,它會閉合,但大約半個小時後它會意識到‘哦,這不對’,然後重新打開。”
我們繼續前行。顫慄白楊,勿忘我,榿木。
“人們問我:植物感受到疼痛嗎?”但卡班説,這個問題沒有抓住重點。“植物知道它們正在被吃掉。它們可能以一種與我們截然不同的方式經歷這一過程。它們非常瞭解自己的環境,它們是非常敏感的生物。而它們關心的事情與我們關心的事情非常不同,”他説。“它們知道當我俯身在它們上方投下陰影。認為它們更喜歡古典音樂而不是搖滾是荒謬的,”他説,提到了錯誤的新時代觀念,即植物喜歡音樂,“但它們對聲學很敏感。”
“我非常尊重它們,作為——我不知道‘有意識’是否是正確的詞,但作為非常敏感的生物。只是與植物一起工作,看到它們的反應。這對我來説是最近10年左右的新事物。這些事實對我來説並不新鮮,但世界觀的改變是。”我想知道,為什麼在過去的30年裏,只有在最近的十年裏才有這種改變?“我是一個變化緩慢的人,”他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