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父子劇井噴,離不開反叛的90後中年人_風聞
娱乐产业-娱乐产业官方账号-带你了解行业的“热点”“盲点”“痛点”2020-01-08 16:04
作者 / 成碩
年度父子相虐大戲《鶴唳華亭》近日終於落下帷幕。
皇太子殿下蕭定權雖然最後小雄起了一把,但是直到最後一集也是難逃哭哭啼啼的命運。有趣的是,父子關係似乎貫穿於近期的幾部古裝劇之間,《鶴唳華亭》《慶餘年》《大明風華》等幾部劇,如果細溯矛盾源頭,都和父子關係脱不開干係。
深入剖析下去,筆者甚至覺得三部劇其實是一部劇,講述的都是關於主角通過“弒父娶母”得到成長的俄狄浦斯式故事。
這種題材聽來駭人,事實上並不少見,曹禺先生民國時期所作的話劇《雷雨》便是其中代表,但是三部同一主題的劇集扎堆兒出現,就有些耐人尋味了。
斯拉沃熱·齊澤克認為,電影作為一種人類意識形態的表現方式,實質上是人類主觀世界的投射。在電影中,對於世界的描述是主觀的,因而所展示的空間是完全虛幻的。正因為其植入了慾望,所反映的世界更加真實可靠。
“斜目而視”因而成為了齊澤克電影理論中的主要研究方法。那如果對這三部影視劇“斜目而視”,能看到什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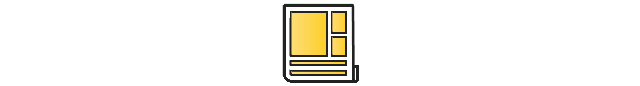
權力爭奪背後的崇拜與反叛
三部劇的故事相似度很高,甚至容易看串。
這幾部劇的故事都與皇權爭奪有關,皇權的歸屬可以是視為劇中的一大主要矛盾。當然,這本就是古裝題材的應有之義,然而有趣的是背景設定也同樣相同。
三位父親的皇位皆然來之不正(多是依靠裙帶關係,並且破壞了原有的家庭秩序),因此圍繞皇位皆有一段不能提起的過往,同時也為父子關係的問題埋下伏筆。
《大明風華》基本依照歷史事實改編,劇中作為父親,同時也是祖父的永樂皇帝朱棣,通過靖難一役,從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朱允文手中奪下皇位。
朱棣因為心有不安,所以最是擔心自己的後輩兒孫自相殘殺,甚至讓其子孫歃血盟誓,不得傷害血親,而這也成為劇中父子相疑的主要原因。
《慶餘年》中,目前出場的範閒生父慶帝,生性多疑、掌控欲極強、權謀手段驚人,堪稱天生帝王,但依據原著設定,其最初也不過是一位極其普通的世子,並無繼承皇位的機會。
最終乃是因緣巧合之下,依靠範閒之母葉輕眉才從當時的太子手中奪得皇位,並因為忌憚葉輕眉的能力而將之誅殺,這為範閒、範建、陳萍萍與慶帝的反目,以及範閒最後的弒父之戰埋下了伏筆。
《鶴唳華亭》的設定和《慶餘年》類似,主角父親皇位的奪得也和主角母親的裙帶有關。南齊皇帝蕭鑑原本為寧王,皇位屬於其兄肅王。蕭鑑通過迎娶主角蕭定權的母親、深愛肅王的顧皇后,而獲得了顧家是支持,並在妻弟顧思林的幫助下獲得了皇位。
然而其間顧皇后仍然不忘肅王,甚至因為去探望肅王而導致第一個孩子流產,主角蕭定權則是蕭鑑迫於顧家壓力不得不與顧皇后所要的第二個孩子,因為其間屈辱,使得蕭鑑不喜、也不信任蕭定權。
劇中故事便是完全依靠父子間的角力展開。隨着故事的展開,對於前情一無所知的蕭定權也從對父權的崇拜(一心想得到父親的認可),逐漸轉向了對父權的反叛(對抗父親保護自己心愛的人)。
簡單梳理後不難發現三部劇的相似之處:同樣是在封建制家天下背景下,父子間圍繞家庭主導權同時也是皇權而展開的糾葛,主要矛盾同樣是兒子對於父權的崇拜與反叛、是幼獅的崛起與獅王的遲暮,最終結局都指向弒父奪權乃至弒父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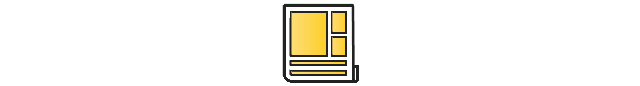
中國式父子關係:
精神版的俄狄浦斯重演
弒父並非一定要手刃了父親。
依據精神分析學説,所謂的“弒父”行為,並不在於殺死現實生活中的父親,而是在自身的成長和選擇上擺脱上一代人給予的期望而進行的個人選擇的行為,即一種精神上的“弒父”,這也是人成為自身主體的一個必經之路。
比如《鶴唳華亭》中蕭鑑最終向蕭定權道歉,讓蕭定棠就藩等一系列對父權權威性的消解和祛魅同樣可以視為“弒父”的成功,同時從最後一集中蕭定棠對其母笑容的回憶中,不難看出這也是對母親的一種捍衞。
“弒父”這個詞聽起來很嚇人,尤其是因為中國文化礙於傳統儒家父權制的影響,相應題材的作品比較少見,表達也相對隱晦,使得人們對此相對陌生。
其實,在西方文藝作品中對“弒父情節”的展現十分多見,最為經典的便是古希臘悲劇《俄狄浦斯王》——其中弒父娶母的俄狄浦斯王,儘管不斷反抗與掙扎,但始終未能逃出命運對於自己的束縛。
《俄狄浦斯王》
在此之後,俄狄浦斯神話被精神分析學創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引用,形成了一個特定的概念——“俄狄浦斯情結”。
弗洛伊德發現,人類自出生就伴隨着俄狄浦斯情結、厄勒克特拉情結,也就是戀父情結、戀母情結。女孩子一出生就天然有一種戀父情結,男孩子出生後有着天然的戀母情結。換個角度,男孩子自出生就和父親有敵對情緒,而女孩子自出生後就和母親有着爭奪的意識,似乎存在一種非此即彼的矛盾。
主角的戀母情結在《鶴唳華亭》和《慶餘年》中體現的比較明顯。蕭定權對於母親顧皇后的依戀在劇中幾乎隨處可見,在母親去世後,這種依戀也隨之被投射到了舅舅顧思林的身上,躺在舅舅腿上,讓舅舅摸着自己的頭,叫乳名“阿寶”,成了一種對於母愛的緬懷。
在範閒的成長過程中,母親則是缺席而在場的,雖然葉輕眉的慘死使得範閒在一個沒有母親的環境下長大,但是五竹等人的存在和葉輕眉帶給這個世界的種種改變又時刻的陪伴着他的成長。
母親於他而言,始終是成長路途上需要追逐的一個模糊的影子,《慶餘年》的故事事實上也是一個尋找母親過往的故事,在此過程中範閒也逐漸接受了葉輕眉留在監察院石碑上的理念,並最終捍衞了母親的理想世界。
第一季已播出劇情中,滕梓荊死後,範閒數次提起監察院的石碑、強調和滕梓荊是朋友不是侍衞,其實便可以理解為對母親的一種認可與捍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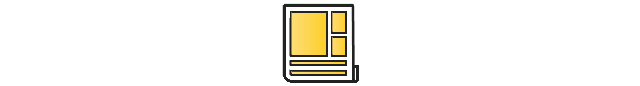
成長的代價註定慘烈麼?
弒父的故事,也是成長的故事。
弗洛伊德之後,俄狄浦斯神話經過無意識學説的解釋後,一般認為弒父情節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人類成長的世代更迭。由於兒子的逐漸成長與父親的意志發生了衝突,父親的衰老與兒子力量的成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如此,兒子逐漸成為了家庭的主心骨並且逐步取代父親家長的位置。父親的家長身份被不斷消解乃至消除,這其實便是《鶴唳華亭》《慶餘年》《大明風華》三部劇所講述的共同主題。
進一步來説,“父親”在符號學中的傳統意義,不僅作為保護、維繫家庭的重要象徵,同樣也在家庭秩序中起着規訓、引導與懲戒,同樣在藝術形象之中,父親有“秩序”與“慈愛”兩種象徵。
事實上,在三部劇中的父親們,也都是同時作為“秩序”與“慈愛”的表徵而出現的,作為秩序的極致代表的皇權和身為人父對親子的舐犢情深構成了父親們身上的主要矛盾。
考慮到《慶餘年》中範閒其實並非直接生父的養育下長大,此處不妨再引入在雅克·拉康的鏡像理論。拉康認為,主體需要與他者的反饋進行自我身份確認。在想象界中,個人作為主體開始不斷認識自我,認識自己所存在的這個世界,父親作為一種介入,成為了一面鏡子,即“他者”幫助主體確認自身的身份。
隨着主體確認的不斷進行,在象徵界中,父親符號作為一種秩序與權威存在,開始干預個人獨立與成長,此時“鏡子”開始失效,個體必定開始尋找新的參照物,必然與上一輩發生衝突。子女成長與獨立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不斷脱離原有家庭秩序和構建新秩序的過程。
《慶餘年》中的範閒事實上一直在慶帝的關注與干預下長大,包括被招入京,被選為內庫繼承人,被太子、二皇子、長公主等各方勢力關注均是作為主體參照物的慶帝為其規劃好的生活,是對其獨立與成長的干預,也是引發範閒反抗的原因所在。
同樣的,《大明風華》中朱高熾對於父親朱棣好戰的敢怒不敢言,朱瞻基對於父親朱高熾面對自己爺爺和叔伯時隱忍的不理解都可以視為子女成長與獨立的過程,對原有家庭秩序的脱離和對自行構建新秩序的渴望。
因而,三部劇集的故事如果從主角的角度來看,其實都是關於成長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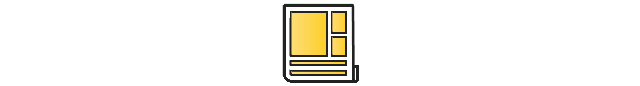
父子劇扎堆出現,90後“斜目而視”
雷蒙德·威廉斯曾提出“文化唯物主義”,即在一定社會時期同時出現相似敍事結構,反應的是一定社會羣體所共享的“情感結構”。考慮到受眾人羣,此處的社會羣體其實主要是90後。
社會層面,隨着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和個人主義影響下長大的、作為獨生子女的90後進入社會,乃至步入而立之年,年輕人渴望在方方方面建立自己的新秩序,前幾年曾流行過的“凡客體”其實就是一種寫照。
過去幾年,90後才放剛剛進入社會,社會話語權不高,主要話語權還是在80後等前輩手中,“奪權”機會不多。如今,隨着90後邁入30歲大關,開始在各行業成為支柱力量,因為其建立新秩序的訴求開始噴薄而出,但是考慮到整體經濟的下行和社會板塊的固化,胸中報復真正能實現者沒有幾人。
於是,這種建立新秩序的訴求,這種追求情緒快感的需求便開始被投射到了影視作品中。同時在家庭層面,人到中年的90後也開始從“弒父”的成長期逐漸過渡到了精神上“弒父成功”後的和解期,成為家中秩序的制定者和頂樑柱。
也正是這些被反應到了影視作品中,才有了《大明風華》本該醉心宮廷權謀,卻每天都在家長裏短的朱家五子,垂垂老矣的朱棣正像是一個見證了兒子成長,卻又抹不開面子和兒子們為過去和解的老父親。
事實上,這三部劇也是在探求父子矛盾或者説社會新舊交替矛盾的結局方式,無論《慶餘年》中以真實的“弒父”來達成矛盾的解決,從而建立新秩序,還是《鶴唳華亭》中的精神上的弒父,走出自己的人生軌跡同時和父親達成和解,都是對如何滿足當代年輕人潛意識中成長需求的一種探尋。
心理學認為,人的意識與潛意識的關係就是一種動態平衡的關係,一旦這種平衡被破壞,人性就會扭曲。同樣,社會意識形態與社會潛意識需求,是一種動態平衡的關係,當這種平衡遭到破壞,勢必引起一系列的心理問題與社會問題。“弒父”劇集扎堆出現背後,其實就是在探求這種平衡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