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釗為陳獨秀的辯護詞:執其兩端而用其中_風聞
guan_15573814801324-2020-01-13 14:39
立法史
編者按
章士釗是誰?毛主席的大恩人!當毛主席還是一介青年“毛潤之”時,章士釗就慷慨資助兩萬銀元――這番情誼,毛主席終生不忘――建國後,雖然政治鬥爭風起雲湧,無數人落入網羅,但章士釗卻始終安然無恙,不能不説是這番情誼在起作用。
陳獨秀是誰?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任總書記!這是黨史中繞不過去的始祖、源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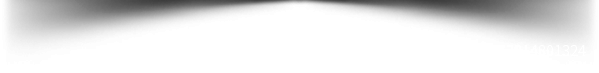
小編所要介紹的這篇章士釗為陳獨秀的辯護詞,雖然寫在八十多年前,但頗具時代意義。其中的許多觀點振聾發聵,今天依然震動人心。而且,有這兩個根紅苗正的“好人”坐鎮,辯詞彷彿上了保險,少去了很多質疑指責,所以屢屢被人提起。
章士釗在這篇辯詞中説主要了兩個問題:(一)對公言論不可入罪;(二)政府不是國家。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大革命失敗。國共兩黨正式決裂。在下一步中國革命向何處去的問題上,作為黨的總書記的陳獨秀與蘇聯的共產國際發生了嚴重分歧。
當時蘇聯共產黨也發生了分裂,分成了斯大林派和托洛斯基派。斯大林在政治鬥爭中勝利,把托洛斯基趕到了君士坦丁堡。所以,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示是根據斯大林的主張作出的。但陳獨秀是同情托洛斯基的。所以,難免不同意共產國際的指示。最終,陳獨秀被撤銷了總書記的職務,並被開除出黨。
陳獨秀並沒有因此停止革命活動。他自己組建了新黨:中共反對派。一邊宣傳托洛斯基的主張,一邊反對國民黨。但處境大不如前,受到了兩面夾擊:中共和共產國際認為他是叛徒,國民黨也打擊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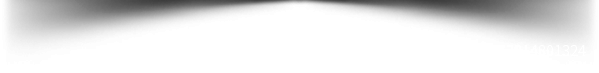
即使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陳獨秀和他的黨依然頑強地生存。1932年10月,正當他們的黨中央在上海的租借開會時,國民黨逮捕了他們。包括陳獨秀在內,有十餘人被捕,而且是全部領導人。“中共反對派”幾乎被一網打盡。
陳獨秀被捕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巨大反映。蔡元培、胡適等人展開營救陳獨秀的行動。已經是著名律師的章士釗義務為陳獨秀辯護。這篇辯詞理論功底紮實、文采斐然,轟動一時。中外報紙競相登載。章士釗在辯詞中説:
言論者何?近世文明國家,莫不爭言論自由。
而所謂自由,大都指公的方面而言。以雲私也,甲之自由。當以不侵乙之自由為限。一涉毀謗,即負罪責。獨至於公而不然.一黨在朝執政,凡所施設,一任天下之公開評薦。而國會、而新聞紙、而集會、而著書、而私居聚議,無論批評之酷達於何度,只需動因為公,界域得以“政治”二字標之,俱享有充分發表之權。
其在私法,個人所有,幾同神聖,一有侵奪,典章隨之。以言政權,適反乎是,甲黨柄政,不得視所柄為私有,乙黨倡言攻之,並有方法,取得國人共同信用,一轉移間,政權即為已黨所衣。“奪取政權”云云,”奪取”二字、絲毫不含法律意味。設有甲黨首領以奪權之罪控乙,於理天下當無此類法院足辯斯獄。”
章士釗將言論分成公、私兩個領域:
私人言論領域,以不侵別人的自由為限。一旦構成誹謗,即應當負法律責任;
但在公共領域不同,一個政黨當朝執政,所有行為都要任人評説,無論批評達到多麼嚴酷的地步,也都應當享有充分的自由。
想起今天有些官員,動輒以自己的名譽權、隱私權受到侵犯為由拒絕監督和披露,章士釗的辯詞多麼有針對性呀!
進入到公共的政治生活領域,個人的權利就要被削減,否則不要來當官。這種批評、指責、謾罵、質疑、造謠,不僅不能夠禁止,而且要用新聞、出版等法律加以保護。因為這是公共的言論領域,與對私人的領域不同。
章士釗的另一個觀點,今天也大有意義:政府不是國家。“國家與主持國家之機關(即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範疇,因而攻擊機關或人物之言論,遽斷為危及國家,於邏輯無取,即於法理不當。”因此,反對政府不是反對國家。政府可以變來變去,國家還是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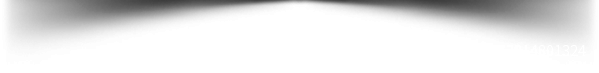
所以,章士釗認為陳獨秀無罪――陳反對的是國民黨政府,又不是中華民國。
章士釗在辯詞裏説:你到倫敦或者紐約的街頭,隨便拉住一個人問他,如果你説反對政府就是反對國家,他一定會認為你是“瘋子”!
在辯詞中,章士釗還緊緊攀附住孫中山和國民黨自身。反覆引用孫中山認為“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觀點和國民黨自己就暴力奪權的歷史抨擊檢察官的起訴。
一審法院最終判處了陳獨秀十三年有期徒刑,較之於死刑和無期徒刑的法律規定,辯方已經是很大的勝利了。
但為什麼如此有力的一篇辯護詞卻不能夠讓陳獨秀無罪呢?有人會説,這還用問嗎?當然是法院受到國民黨的指示,枉法判陳獨秀有罪了。幾乎所有人都會想當然地這樣認為。但這是真的嗎?難道從法律上講,陳獨秀真的無罪嗎?讓我們再深入一下,看一下陳獨秀的判決書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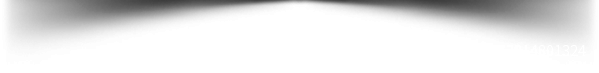
陳獨秀被控違反的是國民政府1931年頒佈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
第二條
以危害民國為目的,而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一)煽惑他人擾亂治安,或與叛徒勾結者。
(二)以文字、圖畫或演説為叛國之宣傳者。
第六條
以危害民國為目的而組織團體或集會,或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者,處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章士釗主張“對公言論”不能入罪,但第二條明確規定“宣傳”是可以定罪的。辯詞所説的是法理,抨擊的是立法。國民黨的議會為什麼會頒佈這樣的法律?應當譴責!但這不是司法的事情。法院不管這些,判決必須依據生效的實體法。既然有了法律,就要執行。所以,判決陳獨秀構成宣傳罪是沒有問題的。
針對“政府不是國家,反對國民黨政府不是反對民國”的辯護意見,判決書是這樣回答的:
查中華民國為民主國家,其主權寄於全民,故凡屬中華民國國民,無男女、種族、宗教、階級之區別,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見約法第六條),而在蘇維埃國家,則主權僅寄於工農階級,除此特殊階級以外之人,皆無參政權,是兩種制度,顯然為兩種國體。
該被告等所組織之中共反對派,既以打倒三民主義,實行共產主義為第一要旨,以顛覆(覆)國民黨國民政府而組織蘇維埃,由無產階級專政為最終目標,是不獨圖謀變更全民主治之中華民國國體,並將中華民國之建設從根本上推翻,其危害民國及叛國毫無疑義。
法院的觀點很清楚:推翻國民政府,建立蘇維埃政府,這可不是變更政府,這是變更國家。章士釗辯詞中所舉的國外政府的例子與此完全不同。國外政府變來變去很正常,政府今天下台,明天上台,所以推翻政府不是罪。但陳獨秀所説的變更政府,已經是另外一番天地了,哪裏還可能變回來?説他“叛國”是一點錯也沒有的。
章士釗的辯詞,都是法律的基本原則,卻偏偏不適用於本案。他只講了原則,沒有講例外。只講了法理,沒有講實體法。所以,雖然辯詞很精彩,但與法院的判決比較起來,還是後者更加持平――陳獨秀應該是有罪的。
當然了,這也沒什麼。不違反國民黨的法,又怎能叫共產黨人?陳獨秀在法庭上就絲毫不掩飾自己違法,他以此為榮。
那麼,章士釗的辯詞錯了嗎?他沒錯。律師的職責就在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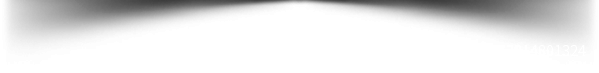
《中庸》裏有一句話:“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就是掌握了事物的兩個極端(過與不及),然後採用適中的態度應用於百姓,就是像堯舜一樣的君主了。其所講的,是儒家一向提倡的中庸之道。
但小編認為用這句話來説明法官與律師各自的作用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律師就是那些找“兩端”的人:原告律師(包括檢察官)去找有利於自己的那一端;被告律師去找有利於自己的另一端,一起提供給法官。法官則是那個“用其中”的人:根據律師提供的兩端居中裁判,作出像堯舜一樣的判決。
法官不是神仙。簡單的案件尚不明顯,遇到複雜的案件,法官就像在看不見岸的汪洋大海中游泳,放眼望去都是一模一樣的海水。這時非常需要參照物來給自己定位。律師的觀點就是提供給法官的參照物。讓法官能夠在這汪洋大海中找到方向,確定位置。
有些法官不讓律師説話,覺得他們的觀點極端、偏激,殊不知這是他們的職責。他們(律師)提供給法官“兩端”,能讓法官能夠全面、通盤地考慮問題,作出正確的裁判。如果法官不去聽應有的“兩端”,只聽“一端”斷案,公正就少了一層保障;如果法官得到的兩端是錯誤的,那麼他的居中裁判就幾乎不可能是正確的。
比如,找到0和10這兩個端點,很容易確定中點是5。但如果錯誤地以為兩個端點是0和6,那麼就會判定中點為3,從而犯下錯誤。所以,知道案件法律適用的兩端對法官正確裁判案件是至關重要的。而這正是律師的職責。
章士釗作為陳獨秀一方的律師,他的辯詞找盡了陳獨秀無罪一端的理由,將對陳獨秀有利的理由都説盡了,讓法官真正能夠“執其一端”居中裁決,這是一篇盡職盡責的辯護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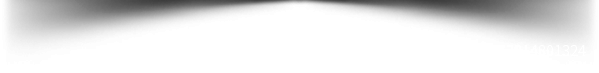
當然,辯詞雖然要有利於己方的當事人,也不能太偏頗,也要“有度”。因為律師的職責雖然是“找一端”,但也是為了正確適用法律,不是為了強詞奪理。如果極度偏激,甚至已經超出了法律範圍發表意見。那就起不到幫助法官的作用了。通俗的講,這篇辯詞就沒有用處了。律師也是失職。
像章士釗的這篇辯詞,雖是一面之辭,但始終在法律的範圍內發表意見,讓法官看到了無罪的這一端能找到的所有理由,真正起到了辯護律師的作用。幾十年後,它又因為自身閃耀着法律理論的智慧之光和時代背景,再次煥發出了生命力。
(立法網新媒體中心 周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