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家庭的“分”與“合”_風聞
严肃的人口学八卦-严肃的人口学八卦官方账号-以人口学的视角看世界、看社会2020-01-22 21:27
又到一年春運時,花式的搶票軟件,崩潰的12306,疫情也擋不住回家的渴望,再穿插着夫妻雙方回哪邊過節的糾結,都指向了中國人心中的同一個信仰——“大家庭的團聚”。雖然對家的眷戀從來就根植在每一箇中國人的內心深處,但是這種一年一度的狂歡式的遷徙以及“去你家還是回我家”式的靈魂拷問卻是近幾十年才新進的產物。從人口學的角度來看,這些現象產生的背後有兩個根本性原因:人口的大規模流動和家庭居住模式的改變。人口的遷移流動很容易理解,也講得很多,那麼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中國家庭居住模式的變遷,即中國家庭的“分”與“合”。

傳統的家庭居住模式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國傳統的家居模式應該有下面一些特點:對大家庭共同居住的偏好,**從夫居(所謂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兒子特別是長子承擔起照料年邁父母的責任。這些印象應該説大多數都是對的。在小農經濟時代,只有兒子才有財產繼承權,並且承擔着禮儀、祭祀等宗族事務。女兒嫁人,就不算是自家人了,大年三十也完全不用糾結去哪家過年,自有規定好的初二回孃家。那麼唯一的問題就是,在古代父母是否都會傾向於跟所有的兒子居住在一起,形成大的聯合家庭呢(注:父母與包括一對以上的已婚子女同住)?事實上從各種史料來看,自秦漢以來雖然聯合大家庭長期佔有一席之地,但這種家庭形式從來不是社會的主流**,其佔比也一直保持在10%以下。

商鞅變法啓動了古代家庭的“分離”
在家庭制度興起和完善的初期直至商周時代,家族成員共居共產的確是最普遍的中國家庭組織形式,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中國家庭產生了“分”的力量?制度的干預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商鞅變法一直被認為對秦國的經濟和軍事有極大的增強作用,但是它在推動家庭變革上的作用被長期忽略了。商鞅變法其中有這麼一條:“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史記》,卷68《商君列傳》),在實際上強制實行了分家析户的政策,採用經濟手段來強迫已婚兄弟自立門户,使得聯合大家庭的居住形式在中國社會迅速瓦解。之後的秦漢朝也都大致延續了鼓勵兄弟分家的政策,一方面是出於經濟税收和人口管理上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控制大家族的形成以消除政治上的威脅。
自唐朝起,制度又發生了一定的逆轉,官方開始倡導子孫合籍共居,並在法律上規定“祖父母在,父母在,不得別居異財”(《中國家庭史·隋唐五代時期》)。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國家庭又有了“合”的趨勢。唐代家庭的規模都要明顯大於秦漢時期,形成了所謂“漢型”和“唐型”家庭的分化。
然而即便在官方鼓勵大家庭的唐代,聯合家庭也仍然不是社會主流的家庭形式,這背後的原因就要歸結於經濟因素了。如費老所説,中國小農社會的農田經營形式是和大家庭制度不相適應的(費孝通,1982)。過多的人口分薄了田地等財產,家庭的經濟狀況就會陷入緊張狀態,兄弟在資源分配上的矛盾以及婆媳關係的緊張就會很容易引起分家。那些我們在電視劇中所常見的大家庭共同居住的情形,只會發生在上層貴族、士族大家之中。只有這些家族才有足夠的資源,將子孫聚攏在一起共同居住。
那麼在中國古代最主流的家庭居住模式是哪一種呢?從父輩的角度來看,當其他子女都分家出去之後,他們與長子、兒媳及其子女所形成的直系家庭(三代)承擔起了重要的養老功能。歷史文獻中所頻繁提及的“五口之家”,就是典型的三代直系家庭。然而直系家庭的重要性並不意味着它一定是最主流的家庭形式。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夫妻兩人或者和其未成年子女所組成的核心家庭,才是佔比最大的家庭結構類型。這就需要從人口要素的視角來理解。從生育上講,當一個家庭有n個兒子時,分家之後就會形成1個主幹家庭和n-1個核心家庭。在古代普遍子女較多的情況下,核心家庭的數量自然就超過了直系家庭。從死亡上講,由於古人的壽命都比較短,當雙親去世後直系家庭就自然瓦解了。那麼個體一生中處於直系家庭的時間就相對有限了。
《慶餘年》滕梓荊一家:中下層階級的典型居住安排

現代化力量下中國家庭的“分離”
如果説2000多年前的商鞅變法推動了中國家庭”分“的第一步,那麼近100年來的現代化進程則再一次賦予了中國家庭”分“的力量。中國這100年以來的歷史是極其複雜的,推動家庭變革的力量也是多元化的,但是其中最根本的動力來自於技術革新和生產方式轉變所引發的家庭功能和關係的變遷。當子代不再依附於父代經營和繼承土地,獨立自主的小家庭成為他們更加嚮往的生活方式。當社會保障體系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老人的養老問題,父代對子代的依賴也在同步削弱。當就業方式和地點變得靈活多樣,家庭不僅結構在變化,空間距離也不斷拉大。在這些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的直系家庭似乎也開始瓦解,向着更為簡單的核心家庭演化。
基於西方社會的家庭現代化理論似乎能夠很好預測這些年來中國家庭居住模式的變化。在一段時間內,學者們也相信中國家庭最終會像西方國家一樣,徹底實現核心化。



孩子成年後就離開父母單獨居住,父母晚年也會獨自養老,一直是西方比較主流的居住方式。
1
早在《小紅帽》的童話故事裏就已經描述,生病的外婆單獨住在森林的那頭。
2
小豬佩奇一家跟爺爺奶奶分開居住但又互相照料,是現代西方核心家庭的典範。

中國家庭近年來的“逆核心化”
那麼近些年來,中國家庭是否正在朝着核心化持續邁進呢?我與合作者即將發表在Demography期刊上的論文發現,事實並非如此(Li et.al., 2020)。利用1982年-2015年的普查和小普查數據,我們發現,在這期間中國核心家庭的比例持續下降,雖然這種下降很大程度是由單人家庭比例的上升所引起的,但是直系家庭的佔比保持了相當的穩定,甚至在近10年內還有明顯的上升趨勢(圖1)。截止到2015年,核心家庭的佔比下降到60%,單人家庭比例上升到12%,而直系家庭的比例達到了25%。
圖1:中國家庭結構類型變遷
(數據來源:Li et.al., 2020)
晚婚和不婚主義的興起是單人家庭急劇增加的重要原因
(圖片來源:電影《剩者為王》)
我們繼續在地級市層面分析中國家庭結構類型的變遷。根據一個地區家庭的平均規模大小,單人、核心和直系家庭各自所佔的比例,以及地方家庭類型的多樣性,我們將300多個地級市劃分為5種類型:大直系型(家庭規模偏大,直系家庭比例高)、大核心型(家庭規模偏大,核心家庭比例高)、小核心型(家庭規模小,核心家庭比例高)、直系混合型(直系家庭比例高,家庭類型多樣化程度高)以及小而多樣型(家庭規模小,各種家庭類型並存)。圖2展示了地區類型隨着年份的變化。可以清晰地發現,地區類型從1982年的以大直系和大核心為主,轉變成2010年以後直系混合與小而多樣型分庭抗爭的局面。核心家庭只在90年代出現了短暫的主導時刻。
圖1和圖2的結果説明,中國家庭並沒有完全遵循家庭現代化理論的預測,直系家庭一直佔據着相當穩定的地位,但是直系家庭的分佈在地區間存在顯著的差異。也就是説,有些地區有着明顯更多的直系家庭,而另一些地區則更傾向於更小的家庭類型。
圖2:地區家庭結構類型隨年份變化趨勢
(數據來源:Li et.al., 2020)

直系家庭的分佈
那麼又是什麼樣的因素來決定直系家庭的分佈呢?如果我們同樣從制度和經濟的角度來審視就會發現,那些經濟發展越好,城市化率越高,流動人口越多的地區,就越可能呈現出多樣化的小家庭類型。除此以外,文化因素也在深刻影響着直系家庭在我國的分佈。就整體而言,南方比北方地區擁有顯著更多的直系家庭。這是因為北方長期受遊牧民族影響,宗族文化的根基較為薄弱,並且在建國初期更早進行了工業化從而動搖了直系家庭的經濟基礎。
如果進一步以方言和民族區劃來代表我國內部的不同文化區域,我們可以發現:客家話、粵語、閩語、中原官話、蘭銀官話和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有着更高的直系家庭佔比。圖3中的藍色區域對應於直系家庭傳統更為深厚的地區,而紅色區域代表家庭類型更現代化的地區。
圖3:中國地區家庭類型分佈

直系家庭的存續力量
那麼似乎還有一個關鍵的問題並沒有完全回答,那就是為什麼直系家庭有這麼強大的存續力量,甚至在近十年還有不斷上升的趨勢?我和合作者在另一篇論文中試圖給出一個答案(李婷 等,2020)。我們考察了不同出生隊列人羣生活在直系家庭的概率,在控制了年齡和時期效應之後發現老年人生活在直系家庭的比重不斷降低,而兒童生活在直系家庭的可能性卻在不斷上升。換言之,直系家庭傳統的養老功能似乎在弱化,而撫幼功能卻在不斷增強****。
該怎麼理解這個看似矛盾的結果呢?可以從社會功能對家庭功能替代的視角來看。在過去的十幾年間,雖然仍然不盡如人意,但是老年人的養老保障已經得到很大增強。很多老人在經濟上已經能夠獨立,並且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來補充照料資源。
而在另一方面,我國0-6歲的幼兒托育、教育體系卻出現了相當程度的萎縮。在城市,公立的托育、幼兒教育資源嚴重不足;在農村,子代的外出流動使得父代需要承擔起更多照顧留守兒童的責任。因此,家庭更加需要老人來分擔照料孫子女的負擔。然而這種照料可能是一種臨時的家庭居住安排,父代採用兩家交替或者間歇式的方式來參與照料,也非常有可能在孫子女進入學齡階段後迴歸到自己的核心小家庭。
留守兒童和祖父母形成的隔代直系家庭,當範閒長大回到“父親”身邊後,奶奶又回到單人家庭模式
(圖片來源:《慶餘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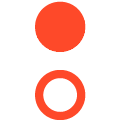
在過去的幾千年間,中國家庭不斷經歷着“分”與“合”的過程,雖然“分”的力量一直在起主導作用,但是家庭團結的動力和韌性似乎從未走遠。在需要的時候,家庭會改變居住模式以適應社會與家庭成員的需求。
大概無論家庭以什麼樣的形式呈現,每一箇中國人心中還是會懷揣着一份對大家庭親人們的眷戀;無論走多遠,我們還是會在每一個春運時分去“奮不顧身”地“堵塞”12306的網路。

參考文獻
[1]Li, T., Fan, W., and Song, J.(2020), “The household transition in China:1982-2015”, Demography. In press.
[2]李婷、宋健、成天異(2020),“中國三代直系家庭變遷:年齡、時期、隊列視角的觀察”。印刷出版中。
[3]費孝通(1982),“論中國家庭結構的變動”。1982年3月在日本國際文化會館的學術講演。
本期作者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副教授李婷
本期編輯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研究生温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