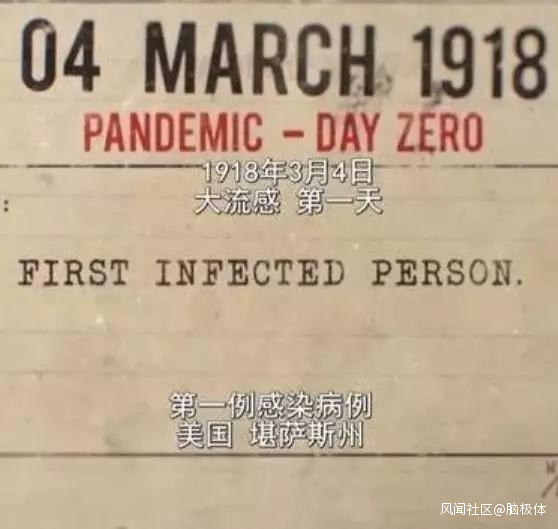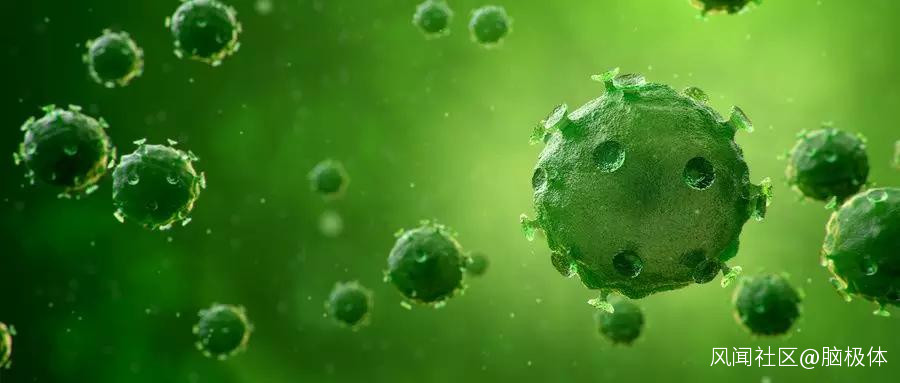尋找“零號病人”,為什麼是瘟疫史上的一件大事_風聞
脑极体-脑极体官方账号-从技术协同到产业革命,从智能密钥到已知尽头2020-02-22 10:04
如果現在最開始吃蝙蝠的人站在你面前,你想對他做什麼?
我想大部分網友都會和我一樣,打得它知道花兒為什麼這樣紅!
那如果是新冠病毒的“零號病人”,站在你面前呢?
最近大家想必沒少被相關新(謠)聞(言)刷屏,而輿論對其總是充滿了“罪魁禍首”的想象。但到底誰是此次疫情的“零號病人”,始終沒有真正定論。
零號病人真的是行走的“災難元兇”嗎?不。
其實在整個人類瘟疫史上,“零號病人”都是至關重要的。打……是不可能打的,最好是帶好口罩撥打120,讓醫療機構接走,這樣我們也許還能趕上春暖花開出門呢。
“零號病人”之於疫病,究竟意味着什麼?
首先必須釐清一點,“零號病人”這個稱呼,絕絕對對不是科學界的叫法。
它的出現,源於1984年,美國疾控中心在尋找將艾滋病從非洲傳入北美的感染源時,媒體的誤報。
一個叫做蘭迪·席爾茨(Randy Shilts)的新聞記者,在其出版的書籍《世紀的哭泣》裏,錯誤地將法裔加拿大航班乘務員蓋特恩·杜加斯看做是被標記的“0號病人”,隨後各大報紙也將其作為頭條,《紐約郵報》打出頭版頭條標題:這個男人把艾滋帶給了我們!《時代》週刊則刊登了專題報道:“零號病人令人目瞪口呆的故事”……
最後證明,蓋特恩·杜加斯並不是“零號病人”。即使他是,也不應該成為被大眾指責的“病毒元兇”。
“零號病人”,就此成了給人“武漢病毒”一樣帶有歧視色彩的稱呼,後者已經在WHO的堅持、中國人民的抗議中被消解,但“零號病人”卻還在被沿用和熱議。如何重新認識它,成了今天我們需要耐心學習的對象。
零號病人,指的是第一個得傳染病或開始散播病毒的患者。而在流行病學中,它被稱為“初始案例”或“標識病例”。
從名字中不難看出,“零號病人”的存在,一是確定了傳染疫病的爆發時間,二是能夠將傳染源鎖定和標識出來。
這就有了三個意義:
首先,對零號病人的接觸史、發病史、行為路徑進行排查,能夠快速找到潛在的中間宿主,以及判斷出主要的傳播方式和傳播途徑,從而採取更為有效的防控措施,來降低傳染力度。
比如我們已知蝙蝠身上攜帶的冠狀病毒和這次新冠疫情有着95%的同源性,但中間宿主究竟是誰?目前還眾説紛紜,“零號病人”的出現則能大大推進研究進程。
其次,零號病人雖然是第一個病毒攜帶者,但存在兩種情況:1.並未感染,“一號病人”另有其人,那麼瞭解他免疫機制,就對疾病防治有着很大的幫助;2.自己感染,那麼他的血清就極大可能存在幫助其他患者抵禦疾病的抗體,也會為後續的疫苗及藥物研發提供助益。
另外,初始病例的發現、調查、分析、處理能力,也是一個國家傳染病防控能力的體現,經歷了從非典到如今十幾年的發展,中國的傳染病防控體系已經達到國際一流的水平,能不能發揮更好的作用呢?
這也是為什麼,醫學專家可不像大眾一樣對零號病人“恨之入骨”,反而希望能夠儘早水落石出。因為找到他,就相當於找到了一把能從源頭剪斷流行病的利器。
點兵點將:零號病人尋找起來到底有多難?
雖然如此重要,但在人類的漫長抗擊流行病的歷史中,被找到的“零號病人”其實並沒有幾個,有的還存在許多非議,比如前面提到的美國艾滋病“零號病人”。
一方面,零號病人與“一號病人”的時間線並不一定等同,這就讓追溯過程猶如大海撈針。
無論是目前新冠病毒記錄在冊的最早患者——一名70多歲的武漢腦梗塞患者,還是被傳得沸沸揚揚的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畢業生黃燕玲,都不是此次疫情的“零號病人”。
前者患病在家,但家人並沒有出現發燒或呼吸系統症狀,而黃燕玲在畢業後則未曾回過武漢,也未曾被新冠病毒感染,都不符合相關特徵。
另外,追蹤“零號病人”的證據鏈很難一錘定音,總會被反覆推翻與再調整。
比如在非典期間,科學家們開始認定的“零號病人”是廣東省河源市的廚師黃某,他在2002年12月15日就出現了病症。但伴隨着確認過程的推進,最後又明確SARS的首例病例在2002年的11月16日已經出現。黃某則為此背了許久的“黑鍋”,形容自己活得像個逃犯。
有資料顯示,公元846年在入侵法國的諾曼人中間,突然爆發了天花流行。諾曼人的首領為阻止其繼續擴散,直接下令將所有病人和看護們統統殺掉了,這種“斬草除根”式的防疫手法,自然也就沒有給後人留下什麼有價值的循證證據。
再比如1918西班牙大流感,則通過對“零號病人”的追溯,不僅幫西班牙洗清了“冤屈”——事實證明,該疫情是一名叫吉特切爾的美軍士兵,在美國堪薩斯州所引發的,同時也通過對其傳染途徑的追溯,對美國的醫學防疫體系影響深遠。而追溯的依據,就是各國部隊軍醫記錄下來的病歷。
不過,近年來“大流感”又發生了反轉,有學者從一名英國軍醫1918年在《柳葉刀》上發表的文章,發現英國士兵在法國軍營罹患呼吸困難疾病的情況,這會不會幫吉特切爾翻身呢?
只能説“零號病人”的追蹤真的時不時就會變成“百年基業”。
那如果證據鏈保存完好,能不能快點找出這位“零號”呢?
恐怕也有點理想化。
其實,早在新冠疫情發生初期,就有專家提出,應儘快組織各單位到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做系統採樣和檢測。
但這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排查哪些攤位和病毒有關,這些攤位的進貨來源、出貨方,消化餐館的消費者等等,往往需要疾控、工商、動物保護、科研機構等協同發力,某一方掉鏈子都有可能導致錯過找到病毒源頭的最佳時機。
而且,此處還有一個特殊情況,SARS、埃博拉、艾滋病這些動物源頭的疾病,還可能追溯到病毒從動物進入人體的那一刻。但如果傳染病毒是人造投放的話,則意味着“零號病人”就不再是孤單的一個人,而是同時間的一羣人,更加難以追蹤。
這並不是在危言聳聽,比如1995年,伊拉克就曾承認,在美國政府的秘密援助下,曾經生產了8500公升的濃縮炭疽病毒。要知道,僅2.25千克就能夠襲擊一個大城市。而在2001年10月,美國便爆發了一系列炭疽桿菌吸入的恐怖襲擊。
人們很難找到第一個被該病毒傳染的是誰,最後只找到了第一位受害者,一個63歲的編輯羅伯特史蒂文斯在10月5日死亡。
縱觀人類瘟疫史上的種種做法,就知道“零號病人”的探索固然意義非凡,也受到了政治、經濟、文化、技術等多重因素影響,讓他們變成了隱匿在人羣中的“無名氏”,目前被人類找到源頭的傳染病屈指可數。
除了流行病學追蹤,人類還有哪些秘密武器?
目前來看,追蹤“零號病人”的工作,主要依賴於流行病學的軌跡追蹤,即通過對每一個早期病人進行問詢,來層層扒開這顆洋葱。
這也意味着工作量大、頭緒繁多、數據源頭複雜。同時還可能存在漏報、瞞報、誤報等情況。
有沒有什麼辦法來加速進展呢?
現代生物學與計算科學的進展,就有望加快這一進程。
比如通過基因測序,科學家們可以提取患者身上的病毒,快速瞭解病毒的傳播原理和可能的致病性。
2011年英國一家醫院突發多例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就是通過對細菌進行基因測序而快速追蹤到了最初的病源攜帶者,並將其隔離治療,從而控制了險情。2014年埃博拉病毒的“零號病人”,也是通過病毒比對,最終確定是一名幾內亞2歲男童。
這次新冠病毒也是通過基因測序來檢驗病毒的RNA,從而協助溯源病毒、監控變異趨勢。
提到基因測序,就必須提到人工智能在戰役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新型冠狀病毒是基因組序列最長的病毒之一,對其進行高通量的全基因組檢測,才能幫助臨牀做出判斷,而在總病患數多、檢測壓力大的背景下,利用AI算力及模型,就成為此次科技防疫的重點。包括BAT在內的AI企業都貢獻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比如阿里巴巴達摩院對算法增加了分佈式設計,提升比對效率;百度開放了線性時間算法LinearFold,以及世界上現有最快的RNA結構預測網站,將病毒RNA分析從55分鐘縮短至27秒等等,都在從病毒手中為人類爭搶時間。
當然,基因測序能否幫助我們找到新冠病毒的“零號病人”還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我們的當務之急,應該是兩件事:
1.延緩尋找整體疫情的“零號”,而是在地域限制條件下尋找“有限的零號”,比如武漢零號、新加坡零號等等,以便快速明確目標和方向,而不是在茫茫人羣中大海撈針。
2.加速對病毒自身的研究進程。目前病毒的習性已經被基本瞭解,傳播方式(飛沫傳播、氣溶膠傳播,糞口傳播等)也基本明確,在尋找零號病人的同時,着重對已有數據的分析挖掘可能會更快地幫助我們結束疫情。
總而言之,社會尋找“零號病人”,針對的是病毒而非人,目的是為了拯救我們自己,而不是找一個讓大眾釋放情緒的“罪魁禍首”。
與其責罵可能的“零號病人”,不如捫心自問,我們對那些動輒添油加醋、煽動惡意的報道,是否保持了警惕。
尋找、判斷、肯定、否定,是對尋找“病毒”的必經過程,而製造這些“零號謠言”的人,恐怕是更應該被隔離的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