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廠關門後,院辦和在街頭“要飯”的務工老哥聊了聊_風聞
跳海大院-跳海大院官方账号-2020-02-24 13:22
微信公眾號 跳海大院/meerjump 碳酸狗

昨天晚上狼人殺的時候,院辦不小心把自己眼鏡腿掰斷了。恰好趕上家裏的貓膀胱炎復發,就去了五羊找獸醫朋友看病,順路在旁邊的銀川眼睛超市配個鏡。
在眼鏡店旁,院辦在街頭看到一個頭埋在胳膊肘裏的中年男人,舉着一塊:“疫災狂、無工做、有難者,請貴助一飯、面”的牌子,旁邊是一個空紙箱,裏面只有一袋白饅頭,裏面有一隻已經長出了黑色黴點。
起初我以為他是一個職業乞討者,但我發現他並沒有討錢用的破碗,地上也沒有微信、支付寶收款二維碼,在2020年騙子與時俱進的時代,這個中年男人有些格格不入,我揣測他可能真是一個被疫情所困的務工人員。
我認識了一個失業務工者
我蹲了來,試探性問他“兄弟,工廠不開工,你為啥不回家啊?”,結果他猛然抬起頭、語速極快,對我不斷重複:“不是回不回家的問題,是隻要工廠開工,我就能賺錢吃飯”,“都怪這工廠還不開工,我咋辦嘛”、“我沒啥問題,只要工廠能開工,我就立刻能工作吃飯”,埋怨到激動處,還會攥緊雙拳猛錘一下空氣,恨不得隔空把自己工廠老闆抓來錘一頓,完全沒有理會我剛問的問題。
我第一次見到這麼熱血的乞討者,我看他這麼激動,以為自己説錯話激怒了他。為了表示自己沒有惡意,我説“兄弟你別急,有話慢慢説,我先微信給你30,你吃飽肚子先。”,他被我突然打斷後愣了一下,説:
“我手機早沒電了,那個,你有現金嗎?”
我迅速摸了摸口袋,發現居然一分錢現金都沒有,舉着已經準備好對空氣不停掃碼的手機,空氣裏有一種錯位的尷尬。
“要不兄弟你等一會,我去旁邊給你買點吃的?”
買飯途中我擔心剛那哥們以為我會跑路,於是時不時就故意走出門讓他好看見我,結果剛彈出腦袋,我倆就四目相對上,他發現我在看他後立刻把繼續埋在膝蓋裏,假裝根本不care我有沒有在買飯,我心想“害,沒想到哥們比我還傲嬌”
之後趁他吃上飯情緒穩定一些,我問他你現在吃不起飯了,晚上睡哪啊?
“我們單身工人沒人租房,都住20元一晚的民房牀位”
他説“旅館唄,海珠區那邊的城中村裏,好多小老闆都把自己的民房、改成旅館,一間屋子可以住二三十個人,一天只要十五,平時我們上班都住那。”
我不太能想象究竟是多大的屋子一屋子能住下二三十個人,就朝門口大概20平米的眼鏡店比劃了一下,問他一層屋子大概比這大還是小?
他探頭看了看,告訴我差不多,“那些旅館裏啥都沒有,就是牀擠牀,全都是上下鋪,只留一個人通過的縫隙。”
這麼説來我心大概就明白了,那種旅館裏每個月根本不是按“房租”計費,而是按“牀位”計費,一般短住20一晚,長住15一晚,廣州的打工者和一些年輕窮遊者很多都好下榻那裏,訣竅是找房的時候,儘量要白天去,“有些人心很壞,你要是晚上再去找房,他就會漲價。”
“如果你是剛來廣州找工作的,一般都會住在廣州東站那,那裏人多好找工作,租房的人多,附近改裝的民房也很多,價格反而便宜,基本上20一晚。反倒是那些城中村裏30一晚的牀位多的很。”,“不過要是有錢的話,哈哈,一切都不是問題。”
我問老哥你現在身上還有多少錢,住這麼便宜的地方,起碼還踏踏實實工作了大半年,咋也不至於吃不起飯吧,存款去哪了?
結果他告訴我,此時此刻,自己身上只剩200元,“馬上連牀位都住不起了,還好老闆是好人,讓我們能先欠着復工後再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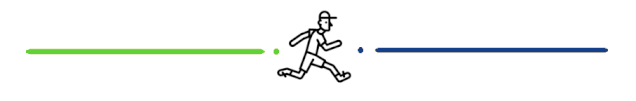
“其實我混的不差,月賺八千,是製衣廠的全能王”
我問是不是沒發工資,他大笑一聲説“害,工資肯定發了!不然還混啥!“,停下筷子,他掰着手指給我數,説自己是服裝廠裏的全能王,幹了好幾年,從裁布、車布、尾部包裝都會做,“走哪都有老闆搶着要我”,工資按件計費,一天能掙300多,一週就休一天,一個月到手能有8000出頭。
説完掃了我一眼,説“你們身上的衣服,甭管是名牌還是路邊攤,其實用的都是一個機器,無非是面料好一些,我們多砸幾道線而已”,頓了頓又説“哪怕是外面300的衣服,我們做出來,也不過是一件6元。”,説這話時他外面套着一件嶄新的白色厚衞衣、裏面穿着件袖口磨爛的紅色保暖內衣,説這都是自己加工出來的廠貨。
“但我還有老婆孩子在周口,年前想着很快就能復工,就留了一千,把所有的錢都寄回去了。孩子剛開始上小學,用錢的地方多。”,“所以我出來是來掙錢的,老婆為了我不工作照顧老人孩子,我上有老下有小,問家裏誰要錢?我沒掙到錢回去了,家裏又多一雙筷子,不是賠錢嗎?”
提到孩子的時候,他説話突然慢了下來,我看到他眼睛有些泛紅,吸了下鼻子。
説到這的時候,路邊剛好有一個從商場採購零食的女人經過,聽到這話時她停了一下,看了看老哥面前的紙殼,又看看我,停頓了一秒,直接把手裏一大包剛結完賬的麪包、八寶粥、礦泉水放下,消失在街頭人潮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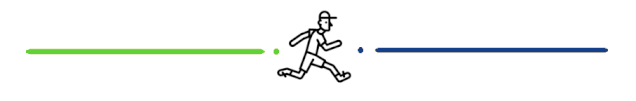
“連續吃了半個月方便麪,我實在受不了才來‘要飯’”
老哥反應過來後扯着嗓子喊了聲謝謝,但女人並沒有回頭,他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對我説“其實我也是第一次出來討飯,真的,挺丟人。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有一天出來混會要飯。”
扶了扶口罩,他又補充**“也還好我還有個口罩,能把臉擋住,不然讓人看到我長啥樣,多丟人啊。****”**,頓了頓,又補充道“但熟人不行,熟人就算戴着口罩,還是能認出我是誰,但我是真沒辦法了,吃不上飯,餓啊。”
他告訴我海珠區那的小旅館裏,不能做飯,所有的留守工人都在吃方便麪,頓頓吃,一天三頓,“那東西吃一頓兩頓可以,但我一個大男人,吃好幾天,就是沒勁,渾身都沒勁。”
可能是因為吃太久方便麪缺乏維生素的緣故,他的手上全是細小的裂口和死皮,整隻手都泛着白。
“我朋友比我先撐不住,實在是嘴巴起泡疼的受不了了,前幾天去上街要飯去了。回來的時候勸我們都放下面子,好歹出去還能吃口飯,我看他們去了,也想甭管別的,來試試運氣吧。”
怕我誤會,沒等我開口,他又像我們剛見面時那樣,開始不斷向我強調“我身體好的很,我真沒問題,也不是懶,能工作的話一切都好了,我不是找藉口。”
他説自己很怕被人當作乞丐,今天城管來找他,問他吃不上飯願不願意去收容所,“當時我就來氣了,我反問他,我能去,那其他工人能不能去,我們成百上千的人,難道是因為自己的問題吃不上飯嘛?工廠不開工,它收容所放得下那麼多人嘛?”
我們的對話引來了越來越多的人圍觀,開始不斷有人陸續往他的箱子裏捐助,只有一個人放了五元錢,其他人都放進了新鮮的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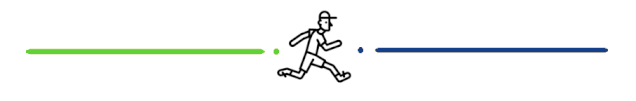
“我這個老男人和你們一樣,喜歡科幻電影,也喜歡TVB和香港老歌星”
過了一會,大概是吃飽了,老哥情緒也好了點,開始和我閒嘮平時的生活。我問他,你平時有沒有喜歡的明星,他愣了愣,説喜歡那些香港老歌星的。
我説你一河南老鐵,為啥喜歡的歌星都是香港的?他説自己從年輕的時候,就來廣州工作了。
“當時林子祥,喜歡你,張國榮,譚什麼麟、四大天王,張學友,這些都是第一代,大街小巷上都是他們的歌。還有那個誰,我忘了,反正是張學友的徒弟,頭髮炸的和雞窩一樣,不過那些都是第二代了。”
我並不知道張學友還有個徒弟,用百度搜了幾個人他掃了眼都説不對,來回看了幾次,他打斷説:
“找不到就算了,反正現在那些香港的明星好像都過氣了,我不懂,你説對不對?還有那些tvb電視劇,越來越沒意思了,我們現在早都不看了。”
我問他那現在他們過氣了,你還聽誰的歌?他説“現在誰還聽歌啊,我們都看電影。”
指了指自己,他説“你別看我現在就是個老男人,其實我最喜歡看那些科幻片,美國的那些,去年上映的每一部,我基本都在手機上看完了。什麼終結者、變形金剛啥的,不過特效都差不多,名字記不清。我覺得還是科幻片看着帶勁,挺厲害的。”
“我看你細皮嫩肉,是不是平時都坐辦公室,你們是不是賺錢多,還輕鬆。“
我急忙擺手説我兩賺的其實差不多,如實交代了自己前幾天買豬肉,結賬時對方告訴我68一斤我立刻擺手、一邊説打擾了一邊光速逃離現場的光輝事蹟,強調了一遍**“咱倆都一樣。****”**
他不信,質疑我“那你工作也得比我輕鬆,不管咋説,我是賣力氣,你是動腦子,我每天要從早上9點幹活到晚上11點呢。“,我尷尬的笑了笑,娓娓道來了我如何一週加班到兩三點、在雲南一邊吸氧一邊寫稿的社畜卑微事蹟。
講完後他對我投來同情的目光,建議我“年輕人還是少拼一點,那些老闆都有賺不完的錢,但我們只有一條命。
我哈哈一笑,説哥們兒你也得注意身體,最近要是還吃不起飯,你就來五山地鐵站找我,提前打個電話,好飯沒有,但是家常菜我肯定提前給你備好。
老哥又有些尷尬,和我説自己就算手機有電了,也沒話費,”那個卡不能用了,和手機沒啥關係。”
我沒當回事,口出狂言:沒事兒,你手機號告訴我,我給你交話費。你一個月話費大概多少?
“200”,我笑容突然凝固在了臉上,怎麼説,如果不是混熟了知道他是個好哥們,我差點以為自己遭受了敲詐。
“你平時也就看看電影,咋來的兩百話費?”,我説我都捨不得花200話費,他怕我誤會,“那都是以前了,現在哪還有錢。平時總歸是得多陪陪老婆,住的地方信號不好網不好,只能打電話,給老婆打完,還得給爸爸媽媽打,總歸得給家裏報個平安。”,“但現在肯定用不了那麼多了,不好意思給家裏再打電話。”
我有些心疼,但還是問了他電話號碼,説“沒事兒,我給你交就完事了”,可能是很少被人問及電話打緣故,他念叨了137後,就再也想不起後來的電話號碼。
“那你兄弟們的電話號呢,你總記得吧,給我留個聯繫方式唄。”
“我兄弟們的手機也停機了。”
“……”
四目相對,最後他掏出一個本子,裏面有本子保鮮袋甚至還有塊捲尺,他管那個袋子叫百寶箱。讓我把手機號和名字都寫上去,我寫完後問他能不能看懂,“我又不是文盲,這還能看不懂嗎,你太小瞧我了!”
指了指吃剩下的炒河粉、叉燒包和熱豆漿,他説“不過這兩天應該都不會找你了,不止夠吃好幾天了,回去還能給我兄弟們分一點。”
我囑咐他之後不管有沒有困難,都記得給我打個電話,“就當是朋友相識一場,你放心,你有些小麻煩啥的,都能來找我。”
活動了下蹲麻的腿,我正起身要走,被他突然叫停。他掏出自己寫着“疫災狂、無工做、有難者,請貴助一飯、面”的紙殼,翻了個面我才看到,原來背面還有另一個版本的文案:
“國有難,民更難,無工做,請貴助一面、飯”
“這是我朋友幫我想的文案,字是我自己寫的,寫的還不錯吧?他説這麼寫更有文化,你們這些文化人更喜歡看。你説,我到底是擺這面,還是擺我自己那面?”,但其實在問我之前,他一直用的都是自己寫的那面。
“當然是你自己寫的了,什麼文化不文化的,在疫情面前,我們都是一樣的普通人,真誠善良比啥文化都好使,你就用這面,最打動人了。”
他不信,重複問了我一遍“真的嗎”,我説真的。臨別時,我問他你叫啥名字,不方便的話,告訴我一個姓也行。
他説那有啥不方便的,告訴我自己叫莊國強(化名),笑了笑補充:
“在五百年前,我祖先可是個文化人,聖人,莊子,對吧?我沒記錯。”
“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