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春筍即將佔領菜市場_風聞
就知道吃-让吃喝变得更有意思。2020-03-13 09:20
動筆時,窗外正在下雨,雨水拍打的聲音讓周遭格外安靜。“荒林春雨足,新筍迸龍雛。”兩句詩令人心驚地脱口而出,找到當年語文課成績落下的病因了,不應景的詩句怎麼背得下來嘛。
幾番春雨的滋潤,毛茸茸的褐色小尖就露出來了,觀察地面的隆起和裂縫確認位置,再細心扒開周筍邊松厚的積土,挖出掩藏在土地下面,露出淡黃色的筍衣。
春雷響,萬物長。一聲春雷,便有了春日裏的第一波筍子,被稱為雷筍。食過春筍,才知春之味,春筍這東西,只要説起它,樣子和味道仿如隔世,正因不像一般家常菜那樣處處可得,才顯得珍貴。
十幾年前的我那時還未上小學,父母每日忙着工作沒空搭理我,這種躁動的不安分只有屁顛屁顛跟着爺爺奶奶到處野才不至於捅婁子。“野”,無非是在菜地裏打滾兒,山坡上撒歡兒,拿着竹伢子到處捅,順便觀察靠天收穫的植物。

尋筍是一件極其令人興奮的事情。雖住在普通小區樓房裏,但丘陵地區的山脈多,跟着走上三四個小時,便能行走於泥土之上,經常半路碰到上山提取山泉水的鄰居們。
在農村成長的老一輩人早就習慣靠山吃山,以農業為主的生產方式,對山野間的食材深諳其道。而大人們活兒不捨得讓我插手,更怕我幫倒忙,我只悄悄在一旁看着,也不多説話,除了上山採筍這件事,我有參與的份兒,提籃子的任務自然要承擔起來,拎起小鋤刀,頂着頭向坡上衝,春筍春筍你在哪。
踩着濕潤潤的泥土,越往山裏走,風越清,漫山遍野的竹子越茂密,借用蘇東坡的那句「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沒有肉吃不過人會瘦掉,但沒有竹子就會讓人變庸俗,人瘦還可變肥,人俗就難以醫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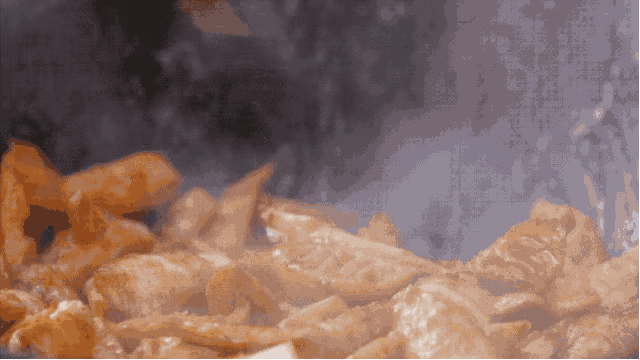
“筍子一定要多放油才好吃”。這句老話總讓我陷入油燜筍的故事裏,剛採到的嫩春筍對半切成小段,過水焯一遍去掉澀味,(筍的澀味是由於其中含有大量的草酸,春筍入冷水鍋,煮滾後轉中小火繼續煮五分鐘,全程保持開蓋,去除澀味。)
用熱油逼出焦香,再經醬油、生抽、老抽和糖提鮮,加水燜煮後,以大火收汁,明明無葷,但別有一番紅燒肉的風味。
一碗筍燒肉味道自然更加豐腴醇厚,一塊春筍燒肉塞進嘴裏,肉中夾着筍,緊緻而富有彈性。
來一碗片兒川,聽起來是流行的鹹辣重口,實際恰恰相反,只有一個鹹鮮,是杭州菜。用鮮筍片,新鮮雪菜和瘦肉製成的澆頭,片兒川之所以叫片兒川,是因為“汆(cuan)”與“川”(chuan)近音,本意是把澆頭的食材成“片兒狀”汆熟,時間長了“片兒汆”就叫成了“片兒川”。
我們最常吃的菜餚,是山筍的脆嫩和酸菜的酸香加上辣椒磨合成就的酸菜炒竹筍,是最愛的一道下飯菜,更是清湯麪、油拌麪最適合的澆頭。時不時也會包個酸菜鮮筍湯圓圖個新奇。
焯熟的筍絲加鹽醃漬拌入蒜泥、生抽、芝麻油和小米椒成為一道涼拌筍絲,饅頭作為主食,小米粥做“飲”食便於吞嚥,這三味在上午9點的餐桌上屢見不鮮。
相較於糯米燒賣,我最喜歡的還是這個冬春交替時節的筍丁鮮肉燒****賣。剛出鍋的燒賣,外皮晶瑩剔透,含苞待放,等不到熱氣全部散去,就忍不住埋頭咬上去,新鮮的肉糜本就肥而不膩,筍丁的“軟硬兼施”,才不枉費這一口。

鮮味從不等人。
有人説白灼筍是對春筍是否鮮嫩的極致考驗,大概只有剛破土的筍才可以這樣吃,小時候吃過的味道已經忘記了,可好巧不巧,近期宅家又把日本電影安排上了日程,竹筍這樣清幽的食材,和日本料理真的蠻搭的。
我説的是《武士的家計簿》,故事根據作為加賀藩會計的豬山直下留下的日記、信件、家用賬呈現了一個19世紀初一個貧困“珠算人”武士家族的日常生活,節奏平緩,故事瑣碎。
母親夾起一塊筍,説道“時鮮的竹筍呢”。咬下一口細細品嚼着。女兒道,“竹中家從鄉下帶來的,江户的大小姐也很喜歡”,脆韌的喀嚓聲,一慢再慢。
日本料理,就喜歡用山椒葉、裙帶菜之類的春季時令食材和筍一起煮食。
若竹煮,是將煮熟的竹筍切塊,加大石湯、醬油、味霖、砂糖、鹽、日本酒酒等煮制,加裙帶菜快速煮沸,最後再配以山椒葉。
土佐煮,會在竹筍的煮物中加入木魚花,在高知縣的土佐地區盛產鰹魚,所以土佐一詞指的就是木魚花。
一些竹筍在日式料理像竹筍飯,筍味噌湯都是以筍增鮮,日式拉麪中也經常會放入一些筍提味。

江南人對春天過敏,看見筍就“癢癢”,一定要趁機把春天的味道都吃進肚子才好。
醃篤鮮,夜打春雷第一聲,滿山新筍玉稜稜;買來配煮花豬肉,不問廚娘問老僧。
切鮮肉、切鹹肉、洗乾淨了下肉進剛燒開的滾水中,慢火燜煮,加筍。筍和肉在鍋裏慢慢翻滾,湯水由清澈慢慢變得粉白,表面浮着油花兒,鮮筍趁新鮮吃,脆嫩、鹹鮮,葷素連湯,豈不樂哉。
醃是鹹豬肉,鮮是鮮豬肉,篤是吳語方言,指的是燉的意思,用小火慢燉,把鹹肉和鮮肉溶於竹筍和清水。
我第一次吃醃篤鮮快被油悶死了,一鍋湯裏,只敢加筍吃,還要專門讓服務員拿了個小碗加清水往裏面涮涮。後去朋友家吃,本着盛情難卻的心思,滋味又截然不同,才知這樣一碗湯,必須是清湯,湯汁有內容,口感又清爽。
一般名菜都要來個名門正派之分,但到了家常飯桌上,誰還管得了一張嘴。上海的醃篤鮮,總愛加百葉結;蘇州人喜歡用雞肉代替豬肉。
醃篤鮮哪裏都有,在我看來並不分伯仲,因為主角永遠是筍,這種鋭利的小清新的感覺,才是可遇不可求的。
《紅樓夢》第五十八回,晴雯將一碗火腿鮮筍湯放在寶玉跟前,寶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説:”好燙!“襲人笑道:“菩薩,能幾日不見葷,饞的這樣起來。“一面説,一面忙端起輕輕用口吹。
區區一碗湯卻吃得”饞”,吃的“燙”,這原因自不必多細想。

曬筍乾是南方農家每年必做的功課。
清明前後的筍,尚未經過烈日的暴曬,鮮味被牢牢鎖住,剝去外皮,洗淨切片,整齊碼在竹匾上,一個陽光明媚的天氣,不到一週時間,筍中的水分蒸發,味道卻沒有被帶走。
真正的米飯殺手不見得是大魚大肉,這乾燥而單薄,褐黃的外表看不出任何美味的苗頭,冷水泡上半個小時,奇怪的知識增加了。
梅乾菜筍乾,豬肉末煸香,和梅乾菜、筍乾同炒,與米飯拌之送入口中。鮮筍紅燒肉好吃就算了,筍乾燜肉一樣不俗。
在筍乾面前,連肉都只是個配角,濃縮了筍的鮮味,又及其吸味,肉的油香和筍乾相得益彰。先吃光的總是筍,剩下肉塊不動筷子。
筍乾老鴨湯,記得那些年連康師傅都出了筍乾老鴨煲口味的方便麪。番茄筍乾豆腐煲,這種湯泡飯,是童年抹不去的顏色。

螺螄粉若沒有酸筍,現在應該不會出現售空的狀況,但也正是酸筍,臭的讓人臉色都不好了。
廣西地區地表水系發達,山高谷深,筍的產量大,這麼多筍碰上回南天,吃不完就變質,將筍醃製起來自然而然,同醃酸菜是一樣的道理。
開水燙乾淨酸壇在陽光下暴曬,筍切絲入壇,倒清水沒過筍後封壇,壇口用水封嚴實了,等半個月就可以拿出來了。這種不加鹽不加糖的醃製手法,是純天然的美味。
真正成為配菜,酸筍又經過熱油炒制,加辣椒,出鍋通風吹乾。這該死的“甜美”,真想念老友粉、螺螄粉、桂林米粉。
連大腸這種我不感冒的食物,炒一碗酸筍大腸就淪陷了。酸筍雞爪、酸筍蛤蜊、酸筍雞丁、酸筍小魚乾、酸筍牛肉...
一句廢話,成熟後的竹筍成了竹子。竹筒米飯,竹筒牛蛙,竹筒煲湯,哪一樣不是別有一番風味。

小時候食筍為了飽腹,摘筍為了有趣,現在滿山的春筍都沒人拔了。但還記得,嫩黃色的筍最佳,因為未完全長出土層或者剛破土而出的筍殼都是黃色,這時筍肉最鮮嫩。根部偏黃白色,中部到尖角呈現黃棕色,肉眼看富有光澤同樣很新鮮。可若是顏色呈現暗褐色,新鮮度就會差很多。剝去外皮,筍肉的顏色越白越脆嫩。
筍既可以與其他食材搭配,又能保持自己獨有的風味,怪不得這麼多文人墨客不吝溢美之詞讚揚它。
去遠方唸書,家人把筍乾放進行李箱,又拿出來,“哦,學校宿舍不能做飯吧”。工作後,新年落幕的一聲再見,家人讓我帶着筍乾離開,説“你帶着,怕你想吃”,又説“不想吃就不吃”,好像怕我嫌棄似的。
怎麼會呢。
今日互動
這麼多筍,你最愛哪一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