誕生於熱帶:現代醫學的源流_風聞
向来-微信公众号:向来之路2020-03-23 21:12
本文首發於微信公眾號:向來之路。
01
這次新冠戰疫,中醫在輿論中坐了過山車。
先是因“雙黃連”事件捱了一記悶棍(確實冤枉);後來官方認證加持了中西醫結合治療,再加上有一則視頻消息“自稱中醫黑的新冠患者被中醫治癒”(此事後續更好玩,在此不細述),中醫粉們彷彿揚眉吐氣、翻身做主人。
這些年,對中醫的各種褒揚、攻訐其實都習以為常了。但看着最近粉們揚眉吐氣、睥睨天下的口氣與脾性,心肝顫抖地比任何時候還要激烈。
作為一名從業多年,每年看診人數上萬的中年中醫。別的不敢説,對中醫的效用和侷限,心裏還是有把尺的。
從感情上,我能理解中醫粉們多年被“科學霸凌”否定到底的悶氣要藉機抒發;但從理智上,中醫在此次戰疫中依然是見招拆招——否則,萬眾焦急等待、望眼欲穿的不是疫苗,而是方子了。
“真理與謬誤只有一步之遙”,這句話對中醫支持者,也許比反擊中醫黑更重要。
02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要清晰認識自己,必須找到他者。
這個他者,是現代醫學。
有人會以“西醫”冠名之,如果以發源地的空間方位來説,倒也並不錯。
只是如果以“中西”二分的話,那樣會對“中醫”很不公平。
因為,現在的“西醫”,很大程度上是歐洲全球殖民的產物,東南西北的元素都融入其中,可以説是殖民地開拓到哪裏,哪裏就成為“西醫”的實驗室、診斷室、藥房以及藥廠。
這好比你是獨門一派,而它卻是麾下甚眾的武林聯盟,更何況還有以更精密、更細緻為目標的現代科技來助拳,如此稱霸江湖,再是自然不過了。
其實無論哪種醫學,都包括身體觀(如何認識身體)、疾病觀(怎樣定義疾病),以及治療方法這三個基本元素。
矇昧時代,在人的頭腦裏,天地未明、神人混沌。當人染疾,都以天怒人怨、鬼神作祟來解釋。要麼什麼也不做,接受懲罰;要麼就是跳大神。所以當人能把疾病從神鬼之説中分離開,然後想辦法認識它、處理應對它;這也就意味着醫學這門學科的誕生。
從這一點來看,東西方的醫學誕生的時間相距不遠,大概在公元五世紀至四世紀之間,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中國的扁鵲所代表的醫學範式,開啓了不同文明面對疾病的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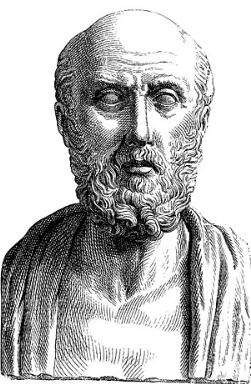
而西方醫學誕生之後,其前進的腳步卻實在令人沮喪。歷史學家約翰·巴里是這樣評價的:“在漫長的2500年裏,醫生給予病人的實際治療方法幾乎沒有任何進步。”
這並不意味着西方醫學沒有進步。文藝復興以後,比利時人維薩里和英國人哈維在人體構造與血液循環的發現,掀翻了古希臘古羅馬聖賢希波克拉底與蓋倫的權威。在身體觀方面,歐洲人極大領先於其他文明,只是這個領先並沒有明顯轉化為醫學實踐上的進步。
因為,醫學和其他科學如物理完全不同,它不能借助數理邏輯,純粹通過思辯和推理就獲得很大突破。醫學最終還是要以觀察、診斷與治療來解決病痛問題。觀察、診斷和治療的行為,在本質上受制於工具、資源,也受制於社會規則的。
工具、資源與社會這些外因的變化,往往是醫學進步的前提。在西方醫學發展的歷史中,從16世紀開始的全球殖民時代是具有關鍵性的外部因素變化。從此,西方的醫學面對的不再是蝸居一隅的歐洲人,而是多人種的病例、全球化的疾病再加上全球化的醫藥資源,催生了現代醫學的主要源流——熱帶醫學。
03
有趣的是,熱帶醫學的誕生,正是源於歐洲的醫學傳統“力所不逮”的地方。對殖民者來説,如何在充斥着炎熱、潮濕、暴力的陌生環境中生存下來,才是最重要的。任何醫學的權威、傳統都不及醫療效果來得實際——尤其殖民者們不是大學裏的教授、教會里的神父。
所以,熱帶醫學從誕生就帶有兩個鮮明的特色:以藥物治療為導向,改造殖民者的組織適應所生活的環境。前者產生了藥用植物學,後者產生了醫院制度。
早期的歐洲殖民者,其實就是海盜。在茫茫大海上討生活,這些“海上紳士們”(出自史蒂文森《金銀島》)面臨着患病乃至死亡的風險,並不低於被征服的殖民地原住民。因為最早沒有歐洲王室的支持,資金比較匱乏,再加上經常遭遇武力衝突,所以海盜一般配備的是外科醫生。

17世紀歐洲的醫生有內外科之分,人們認為外科醫生缺乏訓練,進行的只是純手工之事,而內科從事的是“知識型”的醫學。他們在大學接受自然史和熱病醫學理論的訓練,熟悉各種醫學文獻以及最新的藥物和治療方式。
而當利潤回報越來越豐厚時,“知識型”的內科醫生也投入到殖民的大潮中去,然而他們的醫學知識未能實現突破,在面對種類繁多的陌生動植物時,卻走上了博物學的路。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漢斯·斯隆(1660-1753年)與詹姆斯·佩蒂弗的合作。
斯隆是出生於愛爾蘭的內科醫生,他在牙買加娶了富裕的種植園主福克·羅斯的遺孀伊麗莎白·蘭利,繼承了她前夫種植園的部分收入。這筆錢使得他能夠在倫敦的布魯姆斯伯裏開業。他在1712年買下了切爾西莊園,然後成為草藥園的主人,後來還擔任皇家學會會長。

草藥園豐富的異域植物吸引了倫敦的藥劑師們,詹姆斯·佩蒂弗計劃講印度洋的植物與來自西印度羣島、幾內亞、東亞和印度其他地區的類似記載進行對比。他的目標是要彙整一部世界各地藥用植物學的完整著作。
他與漢斯·斯隆合作。斯隆一方面邀請佩蒂弗參加皇家學會的會議;另一方面,佩蒂弗則使用其全球網絡為皇家學會取得藥物和植物。拓展對全球各地替代藥物的需求,佩蒂弗於1699年在《皇家學會會刊》發表了一篇文章,鼓勵植物學家在英國殖民地蒐集藥用植物的替代品種。
通過在西方和東方的殖民地,對植物進行蒐集、記錄、使用等各項實踐,熱帶醫學萌芽了。從殖民藥用植物轉變為熱帶醫學涉及兩個過程。其一是將這些植物放入新的分類秩序,這導致現代本草學的出現;其二則是現代藥物和製劑的出現。
隨着歐洲的藥房在17、18世紀成為異國藥物的交換中心和知識中心,皇家內科醫生院及歐洲其他類似組織的醫生面臨失去醫學知識專家權威的可能。他們的因應方式是開始從事蒐集、研究、分類異國藥用植物和品項的龐大事業。由此產生了卡爾·林奈分類秩序。
與此同時,熱帶醫學更重要的助拳者出現了。18世紀末,歐洲出現了一種新的分類學方式和實驗室傳統。這是18世紀範圍更為廣大的科學變化的一部分,由法國的拉瓦錫開啓,以辨識物質的化學元素為基礎,拉瓦錫發展出一種新的化學分類法,以及一種對所有元素和化合物的全新瞭解。為了命名物質組成當中的化學元素,拉瓦錫進行了分類學實驗,同時針對植物和其他物質的實驗室實驗跟着發展,目的是追尋植物的“有效成分”。

這促成1800年代早期,主要的熱帶異國藥用植物的關鍵醫療成分的發現和命名,如來自鴉片的嗎啡、來自吐根的吐根鹼、來自馬錢子的馬錢子鹼、來自金雞納樹的奎寧、來自咖啡的咖啡因、來自煙草的尼古丁。
這些藥物,不僅解決了殖民者深受的熱帶病的困擾,而且西方醫學憑藉這些“神奇藥水”實現了霸權的地位。
04
而在殖民化的行動中,歐洲人高效的軍事組織不僅帶來了無往不利的戰鬥力,也創造了軍隊的衞生體制,這個衞生體制不僅是熱帶醫學的重要支柱,也是後來歐洲公共衞生的基礎。
隨着殖民地和歐洲各國的戰爭愈加頻繁,18世紀英法等國的海軍、陸軍中醫院開始興起:在醫院中講求紀律,執行更有效率的照護。醫學成為一種重要的管理程序,人的身體受到國家控制和規訓。
19世紀英國在東印度地區和西印度羣島的殖民軍隊出現了“死亡率革命”。這場革命主要由詹姆斯·麥格里戈和亨利·馬歇爾這些軍醫領導。主要政策是:灌輸簡單但嚴格的衞生做法、清潔和醫學紀律,以及在船上提供健康的飲食。強調軍營和醫院的設計、位置、通風、排水、清潔的飲用水等,以及對各種衞生條件都有紀律地加以注意。經過這次“革命”,英國在印度的士兵死亡率1869年降至2%以下。
後來,英國殖民者把醫院衞生措施擴展到殖民地的統治體制裏。1857年印度大起義後,英國政府廢止了東印度公司,1859年成立皇家委員會,調查英國陸軍的衞生條件。1860年代開始在孟加拉、馬德拉斯、旁遮普、孟買等地指派衞生委員會,監督“普通民眾”的健康狀態。1870年,加爾各答市主要街道都有自來水管提供用水,污水系統也建立了。1896,1897年孟買爆發鼠疫,是印度殖民公共衞生史的分水嶺,建立鼠疫研究室,強有力的地方衞生規定和措施。

隨着人員和物資在全球的流動,原來很多熱帶的“風土病”,也成為歐洲大陸的流行病,如此歐洲各國也開始逐漸確立自己的公共衞生體制。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因為當地人在政治社會地位的低下,英國殖民者在公共衞生政策上傾向於採取比本土更嚴格的隔離防疫措施,反而使得19世紀後期多次的流行病大爆發中,本土染病的嚴重情況不遜於殖民地。
到了20世紀,熱帶醫學憑藉其豐富的實踐和內涵,成為現代醫學最主要的傳統,一方面,它整合了歐洲人兩百年來的殖民主義在熱帶氣候下取得的各種醫學、環境和文化的經驗和洞見;另一方面,整合了新出現的病菌理論和寄生蟲學,將醫學注意力從疾病環境轉向寄生蟲和細菌。
05
梳理了熱帶醫學的發展,再回到開頭的話題。
其實無論哪一種醫學傳統,它的發展變化都是在醫學理論和醫學實踐之間的觀察、肯定、緊張、否定中螺旋上升、砥礪前行的,最終依歸還是在於治療效果。
我們對中醫的信心,確實根植於醫學理論和醫學實踐都具有悠久的歷史。但更重要的,是當代中國醫療體系中數十萬的中醫師,以及龐大的病例,為這個醫學提供生動活泛、源源不絕的實踐基礎。這裏沒有誇耀的意思,筆者每年看診的病人超過一萬人次,多的時候接近兩萬。
正如本文的內容講到的,正是因為實踐的空間覆蓋全球、實踐病例的樣本數也極大化,熱帶醫學才給西方醫學帶來了質的變化。相比之下,無論是歷史上僅限於東亞地區,還是如今僅限於中國的醫療體系,中醫在實踐的空間和數量上是遠不如現代醫學的。
對此,我們中醫醫師要有清醒的認識。而熱帶醫學援引植物學、細菌學為強力外援,進而成為西方醫學支柱的歷史,也該對中醫的進步有一定啓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