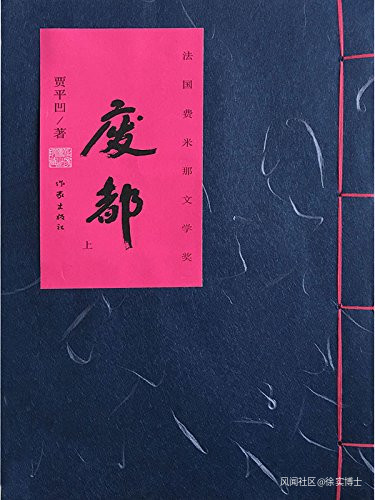“方方日記”昭示着“文化人”的墮落和沒落_風聞
徐实博士-资深生物制药专家-澄实生物 CEO2020-03-30 11:00
作於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方方日記”,在網上引起了很大爭議。《洛杉磯時報》等西方媒體拿這些文字做彈藥,一如既往地抹黑和嘲諷中國。國內為“方方日記”叫好的,絕大多數是上了年紀的所謂“文化人”。而中國年輕一代的態度截然相反,直斥方方的文字是垃圾——這是天大的好事,説明中國社會在迅速進化,年輕一代的眼界已將老朽的“文化人”遠遠拋在後面。
放在世界範圍來看,中國的抗疫工作已經是很高的水平。儘管早期湖北地方政府舉止失措、過過了制止疫情擴散的最佳時機,但是其後舉國上下的積極舉動在2個月內徹底扭轉了形勢,使中國從疫情的爆發地變成了世界範圍內離疫情最遠、最安全的地方。在黨的領導下,舉國上下本來做了許多積極的事情,可是方方日記中卻沒有一點積極的東西,從頭到尾都在咒罵中國的社會環境。有些“文化人”就是這樣,自己是個蛆,就以為世界是個大糞坑。當然,由80後、90後和00後構成的年輕一代,根本不吃他們這一套。
方方遭到輿論痛斥,倒是讓人想到了另外一茬事情:2018年之前,方方曾多年擔任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吃飯砸鍋的毒舌怨婦竟然都能當上一省作家協會主席,那麼作家協會到底是幹什麼的?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性?今天我們就來認真談談這個問題。
作家協會是地地道道的舶來品,中國作家協會有一個“外國爹”,那就是蘇聯作家協會。成立於1932年的蘇聯作家協會,是蘇聯宣傳戰線的重要力量,社會影響力不可小覷。近代歷史上,歐洲國家的作家若非像普希金、托爾斯泰那樣出身貴族,很多人連吃飯都成問題。例如,巴爾扎克和狄更斯這些出身平民的著名作家,都曾有不堪回首的窘迫歲月。在經濟窘迫的環境下,許多作家為了生存,不得不寫一些藝術價值不高、僅為迎合俗人胃口的三流作品。巴爾扎克亦未能免俗,以致他很不願意提及某些早期作品。更有甚者,還得通過被達官顯貴“包養”來解決生存問題——其實不止作家,肖邦、柴可夫斯基等著名藝術家照樣是被“包養”的。蘇聯作家協會的出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還是有些積極意義的:至少它為真正有文學愛好的作家提供了相對穩定的生活環境,使得作家能夠從事真正有深度的文學創作。
僅從產出來看,蘇聯作家協會展現出了極為強大的戰鬥力,使得蘇聯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足以佔據重要地位。側重描寫宏大歷史和社會變革的現實主義文學成為蘇聯文學的主流: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改編成的電影同樣成為經典。法捷耶夫的《毀滅》,阿列克謝.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都屬於思想深刻、藝術水平極高的名著。再到後來,蘇聯作協創作了大量反映偉大的衞國戰爭的優秀作品,其中,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瓦西里耶夫的《這裏的黎明靜悄悄》當屬上佳之作,電影《解放》的劇本則出自邦達列夫等著名作家的集體創作。
新中國成立以後,仿效蘇聯作家協會的架構,成立了中國作家協會。就連蘇聯作家協會負責人的正部級待遇,都一併搬了過來。然而與“外國爹”相比,中國作家協會的實際表現,用杜甫的兩句詩來形容比較恰當——“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改革開放之後,由於時任作協主席的巴金年老多病、無力視事,中國作協的管理日趨散漫,逐漸喪失了意識形態領域的建設能力。20世紀80年代,“傷痕文學”大行其道。鄧小平同志諷刺這種錯誤導向是“哭哭啼啼,沒有出息”。平心而論,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陳忠實的《白鹿原》,已算是中國當代文學中水平較高的作品。在此之後,中國作協創作出了哪些影響力巨大、反映時代風貌的文學作品呢?大家一時半會兒真想不出來。換句話説,中國作協的社會影響力現在是真的很弱,都快沒存在感了。要不是方方譁眾取寵,很多人甚至想不起來湖北竟然還有個作家協會。
為什麼中國作家協會的社會影響力持續下降?應該説,這是幾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第一個因素是,現代社會留給文學閲讀的時間已經很少了。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文學相對比較活躍的一段時間。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城市裏國營企事業單位的勞動強度普遍不高,許多大型國企的職工在工作之餘都有豐富多彩的文娛活動,工人俱樂部、文化宮總是很熱鬧。這意味着,許多平民百姓有相對充裕的時間用於閲讀。《平凡的世界》的印數足以説明這一點。而現在的中國城市中,工作節奏非常快。許多勞動者的實際勞動時間已經遠遠超出每天8小時,無論是碼農還是快遞小哥。因此,多數城市人口更傾向於用更輕巧便捷的方式接受信息,而很難將大塊的時間用於閲讀長篇文學作品。從微信平台的實際情況來看,5000字左右的文章已經趨近於多數人閲讀長度的上限。
第二個因素是,現代化的傳播方式已經對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構成強烈的競爭。一個10分鐘的視頻能夠傳遞的信息量,比一般人讀書一小時的收穫要豐富得多。年輕人平時都習慣通過B站、抖音、騰訊視頻等流媒體第一時間獲取新信息,看視頻又快又不累,還有必要去啃大塊頭著作嗎?網紅李子柒一個人的影響力,只怕比湖北省作家協會袞袞諸公的總和還高倆數量級。
第三個因素是,中國高等教育的普及,已經瓦解了傳統意義上的“文化人”存在的基礎。方方的自我定位就是“文化人”——具有超越大多數人的視野和文化素養,是文化作品生產的主力,能夠引領社會的價值觀。其實,上述自我定位不過是一廂情願的幻想罷了。許多“文化人”其實不愛學習、拒絕進步。賈平凹的小説《廢都》,以20世紀90年代初為社會背景,通過寫實的筆法諷刺“文化人”羣體的腐朽和墮落——“文化人”徒有假清高,喜歡炫耀優越感,對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卻並未起到實質性的作用。
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文化人”並不具備超越大多數人的視野和文化素養。恰恰相反,與211高校畢業生的平均水平相比,傳統“文化人”的視野和文化素養是非常差的。由於家庭經濟狀況迅速提升,許多90後早在20幾歲就去過許多國家,對於外部世界有着較為理性的認識。正因為如此,年輕一代對於“文化人”普遍感到不屑——爾等不學無術卻自命不凡,豈非自取其辱?
“文化人”也不是文化作品生產的主力。實話實説,國內流媒體平台海量的視頻早已將他們淹沒,“文化人”根本抓不住年輕一代。80後,90後,00後羣體,有幾個人有興趣讀完方方几十萬字的小説?時代變了,文字垃圾都沒地方推銷了。人比人得死——“局座”張召忠將軍的年紀和方方相仿,水平卻比她高了不知幾個數量級。局座召忠非常勤奮地在各種新媒體平台上分享思想,而且他本身也在不斷學習和進步,所以能夠保持與年輕一代的活躍對話。説到文化作品的生產效率和質量控制,局座召忠足以讓中國作家協會的絕大多數成員感到汗顏。
“文化人”更不可能引領社會的價值觀。毒舌怨婦被年輕一代唾棄,足以説明問題。一些思想僵化、缺乏起碼自信心的“老古董”,妄想讓年輕人接受他們的訓導、像他們一樣終生跪拜在西方價值觀面前,這真是天大的笑話。“方方日記”遭到羣嘲和痛斥,昭示着傳統“文化人”羣體的沒落和消亡。這其實是件好事,因為這恰恰意味着中國社會加速走向現代化,人民羣眾的思想境界迅速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