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什麼不愛用公筷?_風聞
福桃九分饱-福桃九分饱官方账号-同名微信公众号:futaojiufenbao。2020-04-13 13:20
疫情期間,分餐制再次被提出了。
週末去餐廳吃飯,每道菜上來,都備有公筷。吃飯的人一愣,一頓飯吃下來,桌上公筷無數,然而使用者寥寥。
昨天,國家衞健委提出,要把分餐制形成制度推廣,還提到了山東省提出的“分餐位上”、“分餐公勺”和“分餐自取”三種模式:
分盤上菜、公筷公勺或自助餐,選一個——聽起來還是公筷好適應一點。
可這不是我們第一次倡導分餐制,呼籲使用公筷了。
2003年“非典”時期,鍾南山院士就曾倡議大家實施分餐制,結果抗疫勝利後,大家又把這茬忘了。

© 《飲食男女》
如今又想起它來,活像又吃了一次歷史的大教訓。
為什麼分餐制在國內老是推行不起來呢?為什麼中國人不喜歡用公筷呢?
中國人明明是分餐制的老祖宗啊!
天下大勢,分分合合。
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港一港分餐到合餐的上下五千年。
有人就不愛聽分餐制:憑什麼?
一張大圓桌吃了幾千年,團團圍坐,熱鬧喜慶,是中國人的天性,比起這優良傳統,分餐太尷尬了,受不了。
可據飽弟瞭解,分餐制才是我們更早的傳統呀。
説起中國古代的宴席,最有名的是什麼?
很多人想到的,可能是那頓決定了中國歷史的鴻門宴。
然而,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一定不是在一張大圓桌跟前。
想一想,項莊剛喝點兒酒,繞着大圓桌舞劍轉圈圈,把自己晃吐了事小,一劍沒留神把項羽削了,那還了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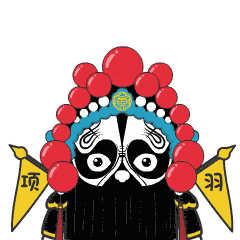
© 宿遷之聲
舞劍,作為一種傳統舞蹈,對錶演空間是有要求的:
像畫作中表現的,一人一案,主位在上,其他人分列左右,圍成一圈,中間留出一片空地,才方便舞蹈與觀看,也方便項莊在舞蹈動作中,一劍刺向“觀眾席”上的劉邦。
許多食器酒器、流傳畫作,包括今天以周秦兩漢為背景的影視作品,也保存了當時分餐制的痕跡。

▲《三國演義》,劉備入川的“高仿鴻門宴”,也是分餐制
中國人之所以形成分餐制,原因只有一個:過去吃不上飯啊。
在原始氏族社會,大家打獵採集回來,為了保證所有人都能吃上飯,就把得到的食物湊在一起,平均分配,優先男性勞動力,其次是婦孺。
後來根據這一習慣,新石器時代的人們發明了小食案。
然而,真正讓分餐制刻在中國人骨子裏的,是它發展成一種禮儀後,所體現的尊卑。
《周禮》記載“設席之法,先設者皆言筵,後加者為席。筵長席短,筵鋪陳於下,席在上,為人所坐藉”。“筵席”二字,自分餐制始。
同時,“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禮制伙食標準,以制度、道德的約束,讓分餐制超脱了基本的取食方式,化為封建社會等級的體現。
從此,席地而坐、據案而食,成了晚唐以前中國人在正式場合的主要就餐形式,也影響着平民的生活習慣。
分餐制這麼適合中國,為什麼又變成合餐制了呢?
我們先説學界看法。
有人認為,是器具和服飾帶來了圍桌吃飯的條件——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民族的胡牀桌凳傳入中原,人們在席地而坐之外,有了新的選擇,為合餐制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過去的席地而坐,是很難發展出合餐制的:
假如大家在地上坐一圈,頭挨頭肩並肩吃飯,已經是社恐火葬場了,中間再來一張大桌,擺滿酒菜……對手短的人類實在不太友好。
有了桌凳,力臂伸長,才可能圍在一起吃飯。
同時,當人們穿上“窄袖胡服”,也不用擔心寬袍大袖上桌夾菜,會垂到菜湯裏了。
也有人認為,是我們的烹調方式變了——
從唐到宋,我們的油料作物豐富了,鐵鍋也普及了,人們可吃到的菜式也多了。

▲炒菜的更大規模興盛,也在宋代
© 《風味人間》
一人一張小案擺那點兒東西,怎麼夠吃的!
於是唐代出現了**“會食制”**,還是分餐,不過是在一張大長桌,桌子越大了,能擺的菜就越多。
宋徽宗趙佶的《文會圖》裏,大家在一起飲酒賦詩,就是圍着一張大桌子。
不過,看桌子旁邊的小童在分盤盛食,説明大家還是分餐。
這些可能,多屬於今人基於典籍記載、考古發現的一些推論,事實未必全然相符。
然而,在合餐制開始定型的宋代,我們推導出了合餐制的“決勝點”。
酒樓的興盛,折射出了合餐制定鼎中原的一切原因。
城市裏出現酒樓,意味着有人需要它。
在商業開始發達的唐末北宋,這羣人,可能是來往的客商、出外的官差、會客宴飲的富户、飲酒取樂的豪門子弟。
▲《清明上河圖》裏,傘下這位賣竹帚的老哥,午飯可能就在身後的棚子解決了
客商屬於流動人口,官差出門也無處吃飯,他們需要一個能解決一餐的地方。
商賈要談生意、紈絝子弟要熱鬧,他們要找個地方一邊交際一邊吃喝。
這些人越來越多,甚至白天晚上都來——宋都汴梁取消了宵禁,晚上又來一波!小酒館實在裝不下他們,也裝不下分餐制了。
© 《清明上河圖》
那麼多人來吃飯,一片地肯定不夠用,那就加蓋,蓋一層,可用面積就翻一倍,能就餐的人就越多,於是就有了酒樓。
還不夠?那就取消一人一案,上大桌,讓一層樓裏儘量坐更多的人。
同時,店家心裏還有另一筆賬:合餐制,意味着更少的桌案和餐具,購買和維護成本都降了,翻枱率還上來了……性價比不要太高哦!
顧客與店家都歡迎,酒樓所代表的合餐制,自然也就在全國推廣了。
一般飯店飯攤,也以合餐桌椅為主,以更多的翻枱率保障利潤,好用價廉物美的飯食吸引平民消費者。
© 《清明上河圖》
**不過,又來了一個問題:**酒樓和商業設施越來越多,擠得城裏房子又不夠住了。
那……家裏也節約一下面積,就一張桌子吃飯吧!於是,合餐制也進入了尋常百姓家。
隨着中國城市化進程不斷加速,合餐制終於修煉成了中國餐飲方式的主流。
▲明代仇英的蘇州版《清明上河圖》,大家在酒樓吃得很開心呢
於是在以宋代為背景的電視劇《清平樂》裏,宋仁宗在宮中吃飯,很多時候還是分餐,可要微服出宮,也得接受茶館酒肆裏的大桌合餐了。
到明代,民間幾乎忘記了分餐制的存在。
東漢傳説“舉案齊眉”,説隱士梁鴻之妻孟光尊敬其夫,必跪而進食,將食案高舉到自己眉間。
可這幅明刻本書籍繡像,卻鬧了笑話:孟光直接把一張大方桌搬來了,讓“齊眉”成了一種有氧增肌運動。
其實,合餐制就像漢堡、盒飯、茶餐廳所代表的快餐文化一樣,屬於商業社會發展的產物。
既然它在屬於自己的時代,成了更實惠便捷的方式,老百姓忘了它,也屬正常。
不過,老百姓忘了,王公貴族們可不能忘。
宮廷朝堂是要講尊卑的,大家還是分餐,在進食這一動物行為的過程當中,互相留點面子,保持距離,舒服一點。
© 《延禧攻略》
清朝,乾隆帝的元旦乾清宮家宴,不僅皇帝、皇后、嬪妃的坐席要上下分開,皇帝還有專屬餐具:象牙筷子、金湯匙、黃瓷盤、金碟子……
這些,自然是分餐制才能實現的。
分餐制重回民間,要等到後世的清末民國。
但不是因為皇帝走了,而是洋人來了。
合餐制,因商業文化而立,其動搖,也是消費趨勢帶來的。
清末西風東漸,西餐揮舞刀叉殺來了。
舶來品所代表的高端與新奇,讓不少中國人接受了它的分餐制,甚至影響了吃中餐的方式。

© 《黃飛鴻之二:男兒當自強》
1932年《時事新報》的《青光副刊》上,提到了一種**“中菜西吃”**:
……將中國的菜,用西法的吃。更有進而以一特製的分格銅盤,中置一湯,四角分置各式的菜。可是這樣吃法太麻煩,並且失去舊式的一團和氣,飲酒猜拳的趣味。雖然,這是很合衞生。
當時上海報紙刊載,1930年粵菜館新新興記酒樓,“發明的粵菜一種,中山全餐,式訪歐美,人各一客,既經濟又衞生。”
顯然,“中菜西吃”的風行,其實順應了顧客兩大需求:
第一自然是趕時髦,第二則是衞生。
▲民國時期,飯店服務生在為客人分餐
曾領導撲滅東北鼠疫的學者伍連德,也提出了新的分餐制吃法:衞生餐枱。
法以厚圓木板一塊,其底面之中央鑲入一空圓鐵柱,尖端向上,將此板置於轉軸之上。則毫不費力,板可以隨意轉動。板上置大圓盤,羹餚陳列其中,每菜旁置公用箸匙一份,用以取菜至私用碗碟,而後入口。
這種圓桌轉盤+公筷公勺制,顯然是一種面對國情的折衷辦法,如今依然常見。
新中國成立後,“愛國衞生運動”在國內大舉開展,從餐館到地方政府,再到1958年後的公社食堂,公筷分餐,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推廣。
當時《人民日報》對安徽省推行公筷制的評價,有這麼一句話:“一件對人民健康極為有益的移風易俗的大事情。”
在疫病橫行的時代,公筷與分餐,儼然成了國運所繫。
從此,公共衞生狀況,與時髦消費觀念,成了推動中餐分餐制的雙手。
改革開放後,隨着洋快餐、自助餐進入中國,又一批中國人,開始將分餐視為一種日常。
▲1987年10月10日,北京第一家肯德基餐廳試營業
1988年,一碗毛蚶引發的上海甲肝大爆發,再次讓人們想起分餐制,以抵禦通過消化道傳染的甲肝病毒。
再之後,就是2003年“非典”帶來的新一輪分餐熱了。
今天,我們要想徹底、永久地恢復分餐制,自然是不可能的。
畢竟,從烹飪方法到飲食器皿,我們今天的飲食文化,全是按照合餐制來的。
爆炒熱炒,出鍋分盤,一番倒騰,鍋氣盡失,那還有什麼意思?想想大學食堂就知道了。

翹頭擺尾的松鼠鱖魚,萬一切段分開,造型豈不白費了?冬瓜盅要想分餐,總不能一人一個小冬瓜吧?
© Ins:dceating
濰坊朝天鍋要是分餐吃,沒了鍋,就成了大餅卷肉就鹹菜疙瘩了。
所以,合餐制在中餐的地位,確實太重要了。不過,它也不是牢不可破:
説到底,它不是什麼民族傳統,而是我們出於經濟實惠的創造。
疫情之下,我們的健康需求,既然高於經濟需求,也就不妨變通變通,採用一下更加衞生的分餐制。
説白了,如果大家還是希望能繼續合餐,那麼就從今天開始,做好分餐制。
如果擔心影響口味或氛圍,那就採取一下公筷公勺,也好呀。
畢竟,再不給自己創造一個安全下館子的條件,飽弟就要饞昏過去了……

參考文獻:
1.王仁湘,《從分餐到會食》,《中華文化畫報》2011年07期
2.劉容,《魏晉至隋唐我國用餐方式由分餐向合食轉變之緣由分析》,《前沿》2009年08期
3.林海聰,《分餐與共食——關於中國近代以來的漢族飲食風俗變革考論》,《民俗研究》2015年01期
4.唐豔香,《飯店與上海城市生活(1843-1949)》,復旦大學,2008.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