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9.4分歸來,我們人類啊,永遠是“胃腸的奴隸”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39411-2020-04-28 14:39
看過了“舌尖上的中國”,看穿了“風味人間”,對於美食紀錄片,我們還能抱有什麼期待呢?
《風味人間》第二季的歸來,還答案以驚喜。
不同於近幾年擅長以情感或場景作為主題的美食紀錄片,《風味人間》的第二季,食物終於再次成為了主角。
食物始終是平等的,差異終究來自於人。
對待同一種食物,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總有不同的態度。
這一季的《風味人間》共八集,每一集都找到了一個有趣的切口。而從切口看見的,是不同地域的人們作為“胃腸的奴隸”,對美食始終如一的熱愛。
第一集的切口,選擇了“甜”。
豆瓣網友評論,“一開始就比甜寵劇都甜”。
甜蜜,是一種讓不同的人都能會心一笑的體驗。然而,有人在意甜味背後的善良與温暖,有人在意甜曾經意味着的權力與能量,有人則喜愛苦盡甘來的那口“回甘”之意。
01.
後廚裏的武林故事
《風味人間》第一季,講了太多故事,一併帶給我們太多關於美食的震撼與喜悦。
想必你還記得《山海之間》裏乘風破浪的鏢旗魚小哥。他迎着風浪,單手持魚叉站在船頭,連續三天只為追逐一條旗魚。旗魚“來無張弛,去無相辭”,且受驚後便難覓蹤影,小哥只有一次機會。
看準時機後的奮力一擊,水下鏡頭捕捉的衝擊感,大浪、風聲再配上激昂的鼓點音樂,一部美食紀錄片乾脆拍出動作大片的效果與視覺。
時隔一年有餘,《風味人間》第二季終於姍姍歸來。
這一季的開篇,鏡頭首先來到了尼泊爾米亞格迪地區的一處懸崖峭壁之上。人們深入險境,只為尋得一種甜蜜的古老食材,蜂蜜。
搖搖欲墜的藤梯懸空而置,身處於上的“蜂蜜獵人”不僅要適應高空作業的難度,還要與來自大自然的力量搏鬥。
與“甜蜜”這種滋味有關的故事,就這樣驚心動魄地開始了。
有趣的是,之後的故事雖然沒有如大自然中那般兇險,卻同樣波濤洶湧。
一位來自揚州的點心師傅,特寫下,只見一雙樸素的黑布鞋在地上踮了踮,以加速使勁,手旋借力按壓麪糰。“麪糰充分發酵,鬆軟不易成形,只有功力深厚的內家高手,才能駕馭自如。”
這哪裏是廚師日常,分明是武林中人的招式——不過倒也沒錯,只有長年累月跟麪粉打交道的高手,才能掌握這麪糰的奧義。
發酵多一分嫌酸,少一分嫌硬,按壓的力道和時機也要剛好合適,才能使麪筋蛋白與水、空氣達成平衡,得到蓬鬆適當的麪糰。只見師傅將手中的麪糰一甩,擀麪杖一滾,麪糰便撲面而來滾成了薄片。
整套動作行雲流水,一氣呵成,這是師傅多年累積的經驗和技藝,施展到了麪糰上,每一個動作都是精準的拿捏。
酣暢淋漓的動作和畫面,背景裏鼓點激盪的中式配樂也恰到好處。短短30秒,盡顯一股東方武俠的獨有韻味。

可是一部美食紀錄片,有必要用到武俠電影的拍攝手法嗎?
《風味人間》的總製片張平解釋道,這種“武俠片”的風格,是導演根據不同食物和人的特質,所選擇的拍攝方式。有些故事適合用武俠風格呈現,接下來也有一些內容,更適合用黑幫片的手法。
不過這位“武林高手”,做的到底是什麼呢?熱氣騰騰的鍋蓋掀開,謎底揭曉——是一塊不起眼的白色糕團。
它呈半透明的芙蓉色,吃起來卻異常綿潤甜軟,小小一塊油糕,竟能達到驚人的64層。這便是揚州早茶裏的常見點心,並稱為“揚州雙絕”的千層油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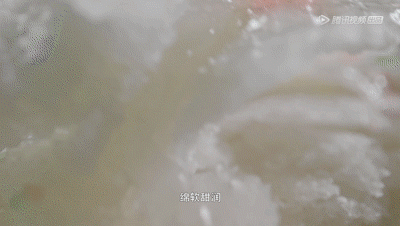
大隱隱於市,看客一品,也能咂摸出《食神》《中華小當家》的意味。
緊接着,影片轉而講述另一種國外甜點,土耳其甜點皇冠上的明珠——“巴克拉瓦”(果仁蜜餅)。
它被認為是世界上最甜的食物,飽含糖分的層層酥皮,包裹着開心果等堅果碎,出鍋前還要淋上滿滿一大勺的糖液,幾乎將甜發揮到了極致。

兩種東西方甜點的銜接與對比,背後折射出的是不同的審美與文化,以及人的處世哲學。
東方甜點口味上往往含蓄,不那麼激烈,就像我們中國人喜歡春風化雨、不動聲色。但西方甜點卻不同,它是張揚外放的,民族個性也是如此。從食物中,你很容易能體會到這種差異。
這樣的例子,在這一季《風味人間》裏還有很多。比如日本人吃螃蟹,要把螃蟹處理得精緻到變態:而美國人吃螃蟹,則是隻取其中幾塊肉,剩下的都不要,其中就包括中國人最不能忍的膏和黃,聽着就可惜。
再比如,同樣是蛋與肉泥的結合,英國人用肉裹上蛋油炸,罪惡美好;而在武夷山區,主婦卻能快速地將肉放到蛋黃的內部,看着是蛋,咬開又肉香四溢。
難怪《風味人間》的總導演陳曉卿感嘆:“這是多麼有趣的南轅北轍。它不僅代表着人們的食物智慧,也暗含着他們各自的生活哲理,對人生,對天地認知的不同。”
02.
回甘是最悠長的甜味
第一集的主題雖然是“甜”,50分鐘裏,卻並不只執着於直白地勾起觀眾對甜的味覺,而是盡力呈現甜的春風化雨、浸潤如絲,只覺“糖消弭於無形,蹤跡縹緲”。
開篇就先從人類獲取糖分最古老的方式開始,講懸崖取蜜、講甘蔗製糖。

原來,糖和甜並不如我們想象中那樣唾手可得。曾經一度因產量稀少、難以獲得,而成為一種權力和地位的象徵。
那人們為何還執着於甜的尋覓?
糖分容易吸收,在食材資源相對匱乏的古代來説,是一種極好的能量來源。甜味與糖分,還能促使人腦分泌大量多巴胺,帶來幸福和愉悦。
當然,發展至今的糖不再僅僅是一種能量的補充。如今她不僅能為甜食注入靈魂,進入烹調的江湖,更是大展身手。
在許多常見的菜餚中,糖都是無比重要的存在。而對於糖的用量、時機及火候掌握,中國不同地區千差萬別。

有意思的是,《風味人間》這一集裏並沒有過多討論我們印象裏偏“甜口”的菜系,比如江浙菜和粵菜,而是選擇了川菜作為切入。
當人們對於川菜的印象早已固化為麻、辣和重口,誰能想到,糖與甜才是其中最畫龍點睛的一筆——
無論是“小荔枝口兒”的宮保雞丁,還是魚香肉絲,酸甜、鮮香,配料只有簡單的糖、醋、姜、蒜、泡椒,卻能調和出近似荔枝和魚的味道。這便是川菜的精髓,複合味,而糖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味調料。
但最精妙的設計,其實在結尾。
誰能想到,整整一集甜的結束,是用苦瓜收尾。
最後一種甜,是為“回甘”。
很多中國食材,入口的第一感覺並不能算是“好吃”。比如苦瓜、橄欖、油柑和陳皮,它們含有一些苦味物質,直接吃起來苦澀難耐。

但經過中國人的巧思處理,再加上時間的沉澱,苦瓜排骨湯、醃橄欖、醃油柑……在苦味的表層之下,綿長的後味裏,總能品出一絲絲甜味,這種感覺常被稱為“回甘”。
英國茶往往靠大量的香料來進行調味,而評判中國茶的一個重要標準,則是回甘。好茶初入口時略顯苦澀,但隨着時間推移,甘甜滋味慢慢佔滿整個口腔,口齒生津。
大概只有中國人,才能真正理解“回甘”的意味。
張平説,“‘回甘’是東方文化語境下才有的概念,西方沒有這個説法,在翻譯時,我們甚至都找不到對應的英文單詞。
回甘到底是什麼作用機理產生的,還沒有被完全弄懂。這究竟是一種幻覺,還是一種真實存在。可能這就是我們東方人對甜的更高一層次的理解吧。”
03.
不變的,是我們對美食殊途同歸的熱愛
這幾年的美食紀錄片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但多數類型往往像命題作文,選擇一種情感或是場景作為主題,由此來選擇食物。
八年前《舌尖上的中國》曾讓人驚豔,對食物的光影特寫,飽含情感的解説詞,挖掘人文歷史,小人物的情感故事,這種美食與人文的固定結合,也幾乎成了現在美食紀錄片的一種“政治正確”。
然而有些卻過猶不及,只一心想着充沛感情,反而忽視了食物本身,美食紀錄片多了幾分説教和乏味。
如何平衡人的故事與食物之間的比重,一直是美食紀錄片面臨的巨大難題。
在《風味人間》第二季開播前的5個小時,陳曉卿發表了一篇自述。
他坦言,在當下美食紀錄片怎樣還能給觀眾帶來驚喜,如何擁抱新事物,對他來説確實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伴隨着無數糾結,在新的一期節目裏,我們在製作手段上做了一些新的嘗試,但我覺得這不值一提”。他沒有講鏡頭和畫面的提升,也沒有講那些驚心動魄畫面背後的艱辛和不易,而是強調“我更在意的是不變的部分”。
不變的是什麼?第一集中“甜燒白”的故事,或許就是對這個問題的解答。
甜燒白是四川傳統的“九鬥碗”之一,也是宴席上的壓軸大菜。故事就從鄉廚夏偉準備一次鄉間婚宴的菜餚開始。
比起那些高級餐廳裏的主廚,鄉廚顯然更粗獷、更顯“野路子”。夏偉準備一道菜,要從食材處理的最源頭,殺豬開始。捉豬、放血、殺豬、拔毛、處理乾淨,再挑選出最合適的部位。
燙淨豬皮,豬肉切成連刀薄片,九分肥一分瘦;夾好紅糖片,澆上糖油,拌入糯米,蒸制後出鍋。一碗熱氣騰騰的甜燒白出爐了,白肉油脂盡處,與清甜的糯米融為一體,口感又沙又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種“無肉不歡”的罪惡快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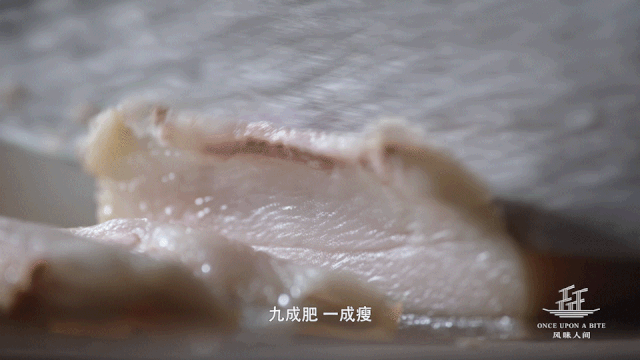
待鄉宴“流水席”接近尾聲,喜慶而美味的甜燒白作為壓軸,終於被端上餐桌。
杯盤盡掃,主客言歡過後,鏡頭特寫對準了夏偉的面龐,緊繃了幾天的他終於鬆了一口氣,露出幾分笑意。一位鄉廚的志得意滿,莫過於此。
甜燒白的故事結束了,但即便不是四川人,也能在其中看到很多熟悉的影子,中西混雜的婚禮習俗,“掌聲鼓起——”一口鄉音、接地氣的司儀,露天灶台,鄉土社會里緊密的親緣關係,現代與傳統的碰撞……
這是當下真實的鄉村生活,不是單純田園牧歌式的歌頌,沒有過於刻意的煽情,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陳曉卿曾在採訪裏説:“美食背後總有故事不斷髮生,透過美食你能看到歷史、社羣、情感。我們不應該因為走得太快,就忘了曾經打碎的東西。”
沈宏非在陳曉卿的隨筆集《至味在人間》的序言裏寫到,(陳曉卿總是能)在城市裏發現鄉村,在鋼筋混凝土裏翻出泥土。
這或許正是《風味人間》能夠打動人的原因。
裏面不乏各種新奇高端的食材,技藝精湛的大廚,保留着傳統習俗的少數族羣,各種讓我們大開眼界的內容。但裏面總會用不少的篇幅,去講述那些尋常而平淡,熟悉卻又難以察覺的日常生活,並透過美食,去發掘背後的地理、歷史、人情、社會……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説,“文化是依賴象徵體系和個人的記憶而維護着的社會共同經驗。每個人的‘當前’,都是整個民族的‘過去’的投影。”這些共通的生活、情感和記憶,組合起來,便構成了我們的文化。
《風味人間》又往前走了一步,把這種對生活、對人情、對文化的包容和理解,擴展到了全世界。
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普通勞動者、廚藝大師,都成了《風味人間》的拍攝對象。
總製片張平説:“家常食物有家常食物的温暖;珍貴的食材,也凝結了很多人的心力和智慧,它也有自己的價值和美好。從這個角度來看,普通人和大師我們都是一視同仁的尊重。只不過普通人我們往往會講他的偉大,而大師卻選擇去講述他的平凡。”
尼泊爾昌泰爾族的“蜂蜜獵人”,需要冒着生命危險從懸崖上採摘崖蜜,這是世界上獲取難度最高的蜂蜜,片子卻沒有過多渲染驚險和獵奇。
鏡頭只是轉向了這一家人的晚餐,剛剛獵取的甜香蜂蜜,被塗抹在了古隆麪包上,甜香醇厚,只需一勺,平常食物便煥發光彩。糖分給了這家人慰藉,小女孩咬着麪包,手背抹了抹沾在臉龐的蜂蜜,一臉滿足。
這種愉悦在影片中還有很多,甜點製作升級的伊斯坦布爾小哥,捕撈海膽的馬來西亞巴瑤族人,香港燒豬作坊的師傅……人種和族羣不同,在辛勤過後品味美食,他們臉上卻都洋溢着相似的笑容和幸福。
這便是陳曉卿所説的“不變的東西”,除了對專業主義精神的仰視,“在參差多態的生活方式中,尋找人類對美食殊途同歸的熱愛,依舊是我們紀錄片的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