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原則的寬容:E2A的建築戰略性方法論_風聞
全球知识雷锋-以雷锋的名义,全世界无知者联合起来!2020-04-29 17:22
譯者:孫天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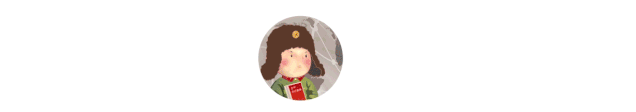

當你既學建築、又做建築、又教建築的時候,你能看到這個學科的許多面,不同程度的壓力、安逸和自由,當然還有限制。
我們喜歡這個方案是因為它是一個能使控制(control)和容差(tolerance)共存的系統。
想象一下,一幢90米的高層,大部分的樓層我們無法做出實質性的創新,就順其自然,選擇其中架空的兩層成為設計發揮的重點。依舊是那個問題:究竟哪些地方更適合我們大膽地揮灑想法,哪些地方不那麼適合。
E2A合夥人:Piet Eckert 和 Wim Eckert 兄弟
推薦語
本篇講座由瑞士中國建築師和藝術家協會主席孫慕蘭推薦
2018年5月忽然接到Piet Eckert的一個電話,開門見山問我有沒有興趣合作一個在深圳的競賽。聽他興奮地描述了競賽的大概情況後我心裏雖然默默地接受了這個邀請,但也有很多疑問,首先兩個月以後就是交標日,這種“速度”不像是瑞士一般的建築事務所能做出的舉動,巨大的好奇心使我馬上答應了轉天和E2A事務所兩位兄弟合夥人Piet Eckert和Wim Eckert的第一次見面。E2A事務所位於蘇黎世Altstetten工業區的Deaconry Bethanien新建築頂樓,這是一座包含辦公、餐飲、酒店、報告廳、託兒所、臨終關懷療護所等的超級混合功能大樓,建築設計、室內設計和景觀設計(部分)都是E2A的作品。事務所是一個80米的長條空間,像跑道一樣筆直地串聯起所有員工的辦公桌、打印室、模型室,跑道的一頭是廚房和會議室,另一頭則是Piet和Wim Eckert的開放辦公室。我從沒有見過如此“直接”單一路線的辦公佈局。
E2A事務所辦公佈局
兩個月合作競賽的節奏非常緊張,6月初Piet和我還有團隊另外一名助理建築師一起飛深圳,與當地設計院進行了三天極高密度的項目合作會。我們的方案是一個結合建築熱力學的節能設計,Piet和我的設計思路都非常“瑞士”——在設計階段就已經開始考慮建築設計、建築物理、結構與施工的配合問題了。我記得在談到一級混凝土主結構可以在中國現澆並且不一定那麼精準的時候,Piet興奮地從椅子上站起來説:“現澆混凝土的那天我一定要再飛到深圳來看!”我這才意識到,在瑞士預製混凝土精準工藝的背後也許是把建築師很多原始的、未打磨的甚至模糊的想象力捆綁住了。很可惜我們的項目雖然最終入圍前五卻沒能摘得頭甲,他或許因為不能親眼看到現澆混凝土而沮喪,這個in situ的夢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實現。然而我相信挫折更能激勵他,因為Piet有一種特殊的能力,就是可以毫無心理阻礙地直面困難,迅速找出問題所在,並且積極地將其視為新的挑戰,最終有效地轉成一套成功的建築戰略措施。我曾經問過他為何做事如此“運動型”(德文:sportlich),他説:“因為我就是運動員。” 在我震驚之時,他向我展示了一連串賽績,1992年奧林匹克帆船比賽全世界總成績第八名,四次瑞士國內帆船比賽冠軍……原來他真的是一名如假包換的運動員,“贏”是畢生目標。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國際設計學院競賽,E2A
和很多具有強大控制慾和強迫症的瑞士建築師不同,在E2A很多的項目中,都能讓人感覺到他們在嘗試衝出瑞士這個“精密機器”的牢籠,挑戰現代主義的傳統。他們把熱情和精力都集中投入到創造建築“獨特性“(specifity)的那一部分,也是項目中最昂貴最精準的那一部分,而永遠給模糊和靈活也留下空間,並且在此處節省了造價。最終建成結果卻能把二者澆築成一個整體。比如Bethanien Deaconry混合功能大樓這個項目的立面設計,其實因為造價限制全樓只有不到二分之一採用了昂貴的電動空氣壓力窗,其餘的二分之一隻是普通窗,然而建築立面的狀態因為使用者的參與,使得“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形成引人入勝的建築外觀。Piet和Wim Eckert在設計過程中已經能夠極其清楚地界定,哪裏必須嚴格干預,哪裏可以自由放任。不僅是建築師,其他行業亦是,關鍵不是在有限的條件和資源下只把事情的一部分做好,而是把能做好的那一部分做到最好。
Bethanien Deaconry,E2A
講座正文
Piet Eckert在庫珀聯盟學院
感謝邀請我們到這裏來講述我們的作品。我被要求不僅要講解我們的實踐成果,還要談談我們的教學感想。這兩者當然互相影響。我們將在實踐中發現的東西經過提煉帶到教學戰略中去。這將是接下來的內容。
我用一張圖片開場。我總覺得這張圖片十分迷人。這當然是哈里·胡迪尼(Harry Houdini)*,他發明了一種禁錮的藝術:他被層層鐵鏈纏身,數次被拋到水中仍然能奇蹟生還。胡迪尼晚年是自然死亡,而不是因為溺水。作為一個隱喻我覺得這個人物很有趣,因為當你既學建築、又做建築、又教建築的時候,你能看到這個學科的許多面,不同程度的壓力、安逸和自由,當然還有限制。
注:哈里·胡迪尼,1874年3月24日出生在匈牙利布達佩斯,曾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魔術師及逃生魔術表演者。而且,他還是一名反偽科學的鬥士,致力於揭穿“靈媒”等偽科學的假面目。
也許我們這一代建築師的工作和大家對當代瑞士建築的刻板印象並不一樣。因為,這麼講吧,我們的老師仍然能夠依靠於一種不會干涉建築師著作權的設計模式。但是今天的市場經濟非常蠻橫,我們經常要處理很多和學科原則相沖突的問題。我們如何生存,以及我們如何思考這樣的限制是我們這一代人建築實踐的重點。這裏有另外一張我認為迷人的圖片。這是電影Fountainhead中的一幕。甲方和學院派對現代建築的抵制正好在這個特別的一個瞬間顯露出來——“你需要根據我們的意見這樣改方案。”你可以認為這正是破壞建築的一幕,它顯示了甲方有着多大的權力、建築又有多脆弱。我甚至覺得近乎拼貼的圖像質感很有趣,有些後現代的介入的感覺:本質上完全不同的東西如何發生碰撞?我們又怎麼處理這樣的衝突?
在這個情境下非常切題的一個圖片我覺得是Hugh Ferriss*在回應紐約區劃法(Zoning Laws)*第二階段所做的最大體量研究。最終建築因為最大化體積問題而產生的不同形式表達讓我非常着迷,在傾斜和後退的表達裏面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已經找到了調和不同體量的方法,使之成為一個統一的系統。這就是我和我哥哥工作的興趣所在。
注:Hugh Ferriss(1889-1962),美國著名繪圖師和建築師。
注:紐約的1916年分區法(The 1916 Zoning Resolution)意在限制高層建築的體量,保證臨近街道享有足夠的日光和新鮮空氣。
以下三個論點能總結我們工作室的目標。1. 一種戰略性(strategic)的建築能混合建築元素,價值體系和行動策略。它能開啓一系列的最本質的先行要素(priorities)。戰略性建築的目標即是調和矛盾價值觀的共存。處理並不具備相同目標的多個元素對我們尤其重要。2. 多個建築狀況合併成一個系統的過程在本質上對傳統意義上的建築特性(Building Identity)和獨立建築類型(autonomous type)發起挑戰。它可以被看作一個用來處理特定功能、結構和類型組合以系統化其差異性(systemize discrepancies)的工具。顯然如果你把兩個東西融合在一起,它既不是這個也不是那個,那它究竟是什麼呢?3. 混合、組裝、整理併合成不同建築特性以得到一個新的個性,使得其組成部分都能被察覺,卻不能被還原。
我們倆都對建築的這個課題感興趣。現在放映的是我們在教學時用的一個例子,是希臘藝術家Haris Jusovic的一個作品。它通過煙斗和高跟鞋極為相似的橫截面將兩個物體融和在一起。因為這是藝術而不是建築,它並沒有生產新個性和新功能性的義務。但是它顯然產生了一種新的解讀,混合了一種常常屬於女性氣質的優雅和常常被標榜為男性氣質的一種習慣。當多個物體的聯合使他們再也無法分離併產生一種新的維度時,事情就有意思起來了。我們可以想象——當然現在只是一個假設,稍後我會用我們的作品證明——面對一個內含悖論或者局部之間有矛盾的任務書時,我們也許可以找到一種藝術性的方式將其統一起來。
這是我們在門德里西奧學院*的學生作品。學生們對於物體之間的連接並沒有很嫺熟,但是這兩個完全不同的物體——一個用來裝果醬的玻璃瓶和一個沐浴花灑——的結合卻模擬了一種新的功能性,好像真的是一個手持花灑一樣。我們覺得這個概念或者操作方式就很有啓發意義,值得探索。當然這也能被一種更加建築的語言來表現,比如多個樓板融和成一一個被壓縮的塔樓。這些元素着實為我們在門德里西奧學院的教學打下了基礎。
注:門德里西奧建築學院(Accademia di Architettura of Mendrisio創建於1996年,隸屬於提契諾大學,坐落於瑞士南部提契諾州最大的城市盧加諾,是瑞士12所公立大學之一,也是瑞士意大利語區唯一的公立大學。
事務所剛建立不久時,我和我哥哥開始嘗試以不同方式重組建築元素以得到更大尺度的建築。密斯的建築被選為組件,這樣讓我們更能專注於重組的過程,而非迫不及待地表達組件的設計本身(express immediately an architectural making)。因此密斯的建築對我們來説是種解放,能讓我們更關注物體之間如何組合或者疊加,或者説他們之間的關係(勝於他們本身)。
Heinrich Boell基金會
我們將這個興趣帶入2006年事務所的首次國際競賽,Heinrich Boell基金會的總部大樓,進一步地探索這種疊加的策略。我們在位於柏林的場地設計的這幢建築基本上是西格拉姆大廈(Seagram Building)和範斯沃斯住宅(Farnsworth House)的一個拼貼(montage)。大家都知道,西格拉姆代表的是一類非常緊湊、經濟高效的重複體系空間。而範斯沃斯正好相反,它是一個獨特的、富有情趣而優雅的房子。所以兩個完全不同的建築個體和類型在交融的同時交鋒。
我們的想法自然是重複性的空間會成為辦公空間,而獨特的空間則會成為會議中心。我們同時將這個快速生成的想法轉譯成了一個“白模(white model)”,在我們看來這是一種對於設計策略的三維抽象表達。可以看到,一個同質化、序列存在的體量被另一個獨特的體量截斷。這個模型某種程度上總結了這個策略的兩個方面,所以其實是一個發展拼貼思考的重要步驟和細節建模的基礎。這個項目的任務書飽受爭議,因為甲方在需求方面躊躇滿志,但是預算卻又囊中羞澀。在預算和需求幾乎完全不對口的情況下,我們的想法自然是在建築的一部分省錢,以保證在另一部分能花足夠的錢。圖示的這個模型和之前那個模型完全是同一個,只不過一個是數學模型,而另一個是建築模型。你可以看到各部分花費相對於這個紅色的水平線變化。這個令所有建築師都捏冷汗的紅線,則是標準花費水平(standard cost horizon),這是你每部分相對整體的平均開銷(total average)。所有花費最終都和這條線平齊——當然——或者比它更低。
我們引入一個包括紅點和綠點的標記系統,紅點代表我們認為非常有趣,非常重要,也很貴的元素,但是他們在建築中只出現一次,而綠點代表非常廉價,但是不斷重複的元素。這個策略的一部分非常小心謹慎,也非常很精確,為的就是另一部分能夠放鬆一些,有更多表達的空間。最終項目在競賽開始兩年之後,也就是2008年落成了,對我們來説也是一個成就。開幕儀式之後反響都還不錯。
沉默的形式
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我們最近剛剛發表了一本書,是Park Book出版的。德文的標題是“Leise Formen”,意思是“沉默的形式”(Silent Forms)。這基本上是一份目錄,記錄着類似一系列源於策略的建築構成和提案。
書(中的模型)賦予每一個策略一種形式。記錄這些模型的是我們的一位好友,Jon Naiman,一位移居瑞士的美國攝影家,他已關注我們的項目多達15年。這個項目集合詮釋着一個故事、一個發現或是一個悖論是怎麼和造型的想法(aspiration of form)聯繫起來的。它深入當今建築的討論,雖然是一個非常開放的系統,但是和我們剛剛解釋的那種戰略方法論(strategic methodology)有很深的聯繫。它和建築結構、表面建構(surface tectonics)都有關係;它有時候和建築的剪影、截面、以及內部劃分也都有關。所有這本書表達了我們的建構項目的框架,就像是我們用來探索發現的工具一樣,而不是在製造工具的同時做探索發現,那樣一時半會難有成效。
門德里西奧的教學成果
這和我們在門德里西奧建築學院的教學也相關。這是期末評圖的前天晚上。學院按傳統會在這個時段開放全校所有區域給學生做模型。因為學校不大,在學生基數很大的情況下,不是每個學生都有機會做模型,教授甚至也不會這麼要求。現在回看,學校的環境讓我們有機會將研究和時間更緊密地連在一起,將不同的東西通過圖像、模型和平面融和起來。這是個很好的開始。
這是僅六個小時之後,我們在同樣的空間裏進行評圖。我們採用了四個基本元素引導評圖的開展。
這其中有 1. 和場地整合的問題:如何處理現存的都市環境?2. 建築概念的問題:什麼想法、什麼發現超越回應場地本身?什麼能突破錶面問題,深化成為一個建築概念,成為一個戰略模型(即之前所講的白模型)?3. 現象體驗的問題:如何用拼貼這個介質將建築的抽象戰略轉譯成感官體驗?4. 方案敲定的問題:如何將之前的考慮總結成一張平面?
這張平面基本上就成了空間的組織方式,設計技巧秩序嚴謹,但我們在其中的發現是非常靈活開放的,所以我們將這個方法用在學校的教學話語體系中。當然,因為時間有限,我沒法給大家詳細講解學生項目,但是你能從我即將放映的一系列圖片中看到學生們如何操控他們發展出來的項目。
這個項目在柏林,對城市的街區(block)上做文章,學生的想法是將一個集體住宅平面和一個公共大廳(Hall)介入這個街區。通常兩者的共存並不常見:一般住宅是基於街區的,而大廳則是獨立的物體,因此這是類型的融合。可以看到,街區中央的負空間(void)像是例外,所以學生單獨做了一個模型來推敲這部分空間,其中小尺度的元素生長成街區結構,而大尺度元素則被包含其中。我們通過前景、中景、背景的疊加展現拼貼的場景美學和感官體驗,發展公共空間的邊界和通道等等,最終敲定出一個平面。
這個平面精準地控制了住房和內院的關係,或者説家庭尺度和大型公共空間尺度的關係,比如包括一個公共通道和一個容納萬人的空間。就像學生項目展現的一樣,即使設計過程的框架或學生提交的作業類型總是一樣的,但每個學生每次的發現應當都不一樣。這就是我們在(門德里西奧)學院排列分析模型的樣子,有些時候很大的突破可能歸功於一個小模型,有時另一個模型在之後的過程中可能就不太被重視了,這都是設計學校的家常便飯。這個關於類型融合的想法還有一些例子:不同的尺度如何互相協調運作?例如一個集市大廳怎麼和摩天樓合併?或者這個既簡單又複雜的問題——怎麼將幾座高塔合併起來使其落在同一個地基上?或者説如何遵循結構的邏輯,介入已有的結構或者創造新結構來賦予它新附加價值並且不顯累贅?就像增加這個大廳(shed)的結構跨度,隨之增加其高度,這樣就在固定面積之內就能減少柱子的數量,這是很基本的操作,但是它對功能組織(program)有着很有趣的影響。所以我們在(門德里西奧)學院基本就是在做這些鋪墊性的研究,即幾個東西如何組合,這個過程好像總是很相似,但卻又不一樣。
這種方法或許有點教條主義,但這對我們篩選真正必要的元素、做出重要探索很關鍵。比如在這個學生作業裏,建築的輪廓生長成為兩種不同的空間, 即單個展廳和公共空間,前者經過在截面上的變化成為後者,解決了兩者結合的問題。
貝塔尼恩教會總部
Deaconry Bethanien
在這裏我要做個轉折,接下來我將會講一系列我和我哥哥最近做的一些項目,這些實踐項目*越多,我們在(門德里西奧)學院的教學目標也就越明朗,互相的交流也越深入。這是蘇黎世,蘇黎世是一座小城,只有45萬人口。這個項目在城西,甲方是教會的執事機構(deaconry),在蘇黎世投身健康保障事業已經一個半世紀了,他們想在一個工業非常興旺的地方建一座新總部大樓。
注:講座原文中稱實踐項目為“繪圖桌上的項目(the drawing table)”,譯者認為是工作室文化的一種隱喻。
這是一些初步的場地圖片,這在蘇黎世其實並不尋常,對於瞭解中歐的觀眾來説,蘇黎世的城市風光一向比較優美,幾乎沒有醜陋的地方,所以這個場地也是出乎意料。
這個總部的功能非常複雜,包括執事機構的行政中心,一個健康保障療養院,一個臨終關懷療養院(palliative clinic),一個至少能容納85個孩子的日託所,一個商務酒店,一個會議中心,還有其他的辦公空間,員工食堂和廚房以及公共餐廳等等。多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我們就想還有什麼功能不包含的嗎?有趣的是,在這種混合功能的體系下,功能本身的相關度就很低了。
我們的問題則變成:如何設計一種獨立於功能的建築,因為按照任務書的方向,也許需要在這裏加一個髮廊,那裏還會加其它東西。於是我們的設計基於非常嚴格的網格體系,由承重的外牆和偏離中心的核心筒組成,這樣就造成了(核心筒和外牆)之間兩個不同的跨度,這是模型的幾個不同角度的照片。樓板非常薄,長85米、寬15米,這算是我們的第一個委託項目。
這是建成之後的內部照片。
外牆的每一個零件採用了預製混凝土,在工廠裏統一澆灌好之後被運送至場地,進行精準的組裝。這個過程非常振奮人心,因為施工非常之快,整棟樓就像是搭樂高積木一樣。每個稜角處理得都很乾脆利落,這就是預製的好處了。
我們同時加入了一個自動化的窗户系統,它採用電力開關,並且氣壓也控制地恰到好處,就像是公交車門一樣,關閉的時候它將部分空氣吸進內部,以保持緊實。我們以此達到瑞士的生態環保標準,因為一般的滑動式的窗户已經不能達標了。
這個系統的初衷來源於利用每層不同的用户的開窗決定對外立面產生干擾。某一時刻可能這個用户打開了窗户,那個用户卻沒有,這樣的時間差就使外立面時刻自然地變換,自成一個系統(its own game)。
從某個角度來講也折射出了不同使用者的不同需求,在這張照片中,整幢建築平靜地坐落在周遭略顯喧鬧的氣氛中。它雖然非常拘謹甚至死板,但它也可以非常值得玩味。
這是房子側面——即樓板短邊一側——的照片。也有一些景觀的介入。
我們接受委託的第一輪的工作範圍基本上就是這樣,只有設計外殼和核心筒,也就是框架部分。因為我們和甲方的關係還不錯,於是就幸運地也做了室內設計。第一輪設計的確是為了相對自由的室內設計而準備的,我們也就大膽地試驗了我們的室內方案。這個平面就展示了辦公空間和臨終關懷療養院的共存,這些功能都在核心筒和外殼之間的空間做了整合。
每次你看到這些看似一成不變的混凝土元素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受用户的影響)卻總有着完全不一樣的表達,或者説是用户的理解。內裝材料都不會覆蓋混凝土牆面,而是在部分表面添加,所以材料的表達上原汁原味。隔斷牆(partition walls)都是木製的,外牆和天花自然都是混凝土的。可以看到,基本的框架相似,但是不同空間所用材質,布料都獨具一格。
之後我們也把我們的工作室開在了裏面,所以説這幢樓裏面也能包含一個建築工作室,就像其他多重的功能一樣。這就好比是在一套(既定的)規則裏面做遊戲。
從這張照片上可以看到人們作息的時間差(time lag)造就的多彩景象。一成不變的建築與多彩多姿的景象共存。
倫敦高層住宅
相關的還有這個項目,這是一個位於倫敦的高層住宅,我們也使用了相同的設計原則。我覺得這個例子很好地説明了如何把握住宅設計中的既定元素,因為住房(housing)這類的任務書仍然需要所謂的“全面設計(total design)”,既需要想象一種先入為主的生活方式(preconceived model of life)。預定房間的功能、傢俱等等似乎是一種現代主義的傳統(tradition of modernity)。我們想要突破這個想法,並且對核心設施和外圍空間的等距關係提出質疑。事實上我們利用不同的核心筒之間樓板生成“外圍“空間,它的形狀便像是被做過減法(residue),原先清晰的幾何輪廓失真了。
**我們喜歡這個方案是因為它是一個能使控制(control)和容差(tolerance)共存的系統。**這裏面有非常較真,非常精準的元素——比如平面裏面的那些核心筒,都是經過嚴格測算和優化的;但是這些元素之間的空間非常自由,允許不同的居住方式和生活風格。你完全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在裏面佈置生活,不需要和任何其他人的一樣。可以看到,和上一個項目的共同點就是在基本設施上做文章以支持並促進室內生活的多樣性。
可以看到這幢建築有多直白,所有的衞生間都上下對齊地疊在一起,所有廚房也是。這張渲染圖中,我們想象這個建築一部分原始、未經加工而另一部分精緻、經過細心打磨。
你可以在這種模糊的二元(ambiguity)環境中生活,當然你也可以完全顛覆它的樣貌,使每層的生活都不同,對住房的觀點、態度也不同。
我們介入這個系統的方式並不是想要直接成就某些東西,而是為他們提供可能性。因為到頭來,一個有着不同想法的住户不可能對先入為主的設定完全滿意。
這張照片表述了樓和周遭環境的關係,有點軸測的感覺,你也能看到一列的廚房和它們旁邊的陽台。
德意志製造聯盟住宅
Werkbundstadt
這是我們另外一個項目,照片裏面有我哥哥和我的老師。這對我們來説的確是一個奇特的經歷,因為我們收到了德意志製造聯盟(Deutsche Werkbund)*的邀請。
注:講座原文中講者提到德意志製造聯盟不再依賴於Siedlung類型,即獨棟、水平排布的批量住宅類型了,轉換為更常見的公寓式的豎直排布。
如果大家還記得這個組織的話——在1920年代,它聯合密斯和柯布西耶等人在德國斯圖加特(Stuttgart)設計了製造聯盟的樣板住房項目(Werkbund Siedlung)。百年之後德意志製造聯盟希望重新啓動這個項目,希望使城中心的一角建起更合時宜的住宅原型,以此探討歐洲嚴重住房短缺問題的解決方案。獨特的是,我們必須和44個同僚協作。這個模型不是一個甲方出任務書,一個建築師出方案,然後甲方向建築師支付設計費這麼簡單了。而是我們和44個其他的同僚都需要在總平面圖上達成共識。這很有趣,因為合作包括了兩代人,我們的老師是其中的一員,也有比我們稍微年輕一些、和我們同時求學的同僚。這個實驗很有趣,讓每個建築師都能達成共識着實困難,你不能把總平面圖一個一個發給他們,而是大家在一起當場畫一張草圖才能心服口服。
這是場地的黑白平面圖(black plan)*,項目位於柏林市夏洛滕堡地區(Charlottenburg in Berlin),臨近“柏林之河”——施普雷河(Der Spree)。這張平面也許不夠大膽,但是我們的設計過程確實很大膽的。參與者抽籤選擇地塊,我們就選到了這一塊,並不是非常特別,其實非常簡單,包含一個轉角,而且不是高層。但是這都沒關係,因為比場地有趣得多的問題是,如何從製造聯盟的角度出發設計出一種公寓住房的原型。
注:講座原文為Black Plan, 應為德文Schwarzplan的直譯,指將建築塗成黑色,而其餘留白或者採用線稿的城市平面圖繪製方法,英文中常用的對應詞彙為figure-ground plan。
這就是我們的方案,仍然是非常嚴謹的網格系統。我們分析了現代公寓的演進,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現代公寓總是和“極小(minimal)”*尺度的概念有關,比如客廳的最小面積,父母需要的最小面積,孩子需要的最小面積等等。
注:Minimal也指極簡、極少。極簡主義(Minimalist)也是在現代主義興起時誕生。
這套系統裏的一切都是一套空間大小的階級系統。我們的操作反其道而行之:我們放大這個“極小”的面積到一個19平米的正方形,這個大小對於覆蓋基本的需求來講恰好大了些;這些方形經過組合,促進不同的居住方式發生的可能。
我們不太希望在兩個核心筒的前提下讓建築面向所謂的“典型住户”,而是希望每個公寓都能被住户個性化地使用,雖然廚房和衞生間是固定的。空間排布的結果就是以巴洛克式的縱射形佈局(enfilade)*,每個房間都直接和其他的房間聯繫起來。你可以將房間關閉起來,只用一個作卧室,你也可以多用幾個,甚至大家都在廚房睡覺都沒關係。所以你究竟是有三個小孩、一個小孩、還是沒有小孩,以及你需不需要琴房這樣的問題都不那麼要緊了。
注:縱射(Enfilade),指房間與房間由門直接連接,省卻走廊的平面佈局方式。美國建築學者羅賓 · 埃文斯(Robin Evans)曾在《人物、門與通道(Figures, Doors and Passages)》 一文中詳述了縱射到走廊的演變。從時間軸上來看,巴洛克時代走廊在住宅建築中慢慢出現。
我們覺得這樣的混合居住,這種在城市環境裏不同的參與者、不同的住户在一個屋檐下同住非常有意義。因為當前的現實是恰好相反的,開發商或者説是項目的作者們總是希望找到一種典型的住户作為模型,就好像住户都差不多——甚至他們銀行賬户的存款也差不多一樣。我們的方案算是有趣多了。這張圖片上你可以看到住宅之間的距離,總是讓我聯想起一個我在西班牙見過的地方,環境非常緊湊密集,我們把它當作一個參考。
Hofacker校園擴建
公共建築對我們來説非常重要,因為你總是需要考慮關於教育的問題,或者説應該如何構想一個學校、一個大學的問題。這個項目正在施工階段,場地十分微妙。左邊是一個受歷史遺蹟保護的現代主義建築,右邊的房子則是那種19世紀所謂的“民族風格”。這是場地模型其他角度的照片,可以看到這兩個房子中間就是我們的方案,是一所學校的拓建。項目的體量相對扁平,不在豎直方向上和臨近的歷史遺蹟爭鳴,而是融入周遭的環境。
我們的概念是將一個三層通高的風雨操場和教學空間合併起來。有趣的是,這樣一來,兩個空間就需要互相服務。這是建築裏很基本的相互依存的關係,但是你也可以將其發展成一個嚴謹而有活力的系統,我們就對此非常着迷。
這裏你可以看到下面的室內操場,九米通高,頂上的結構必須要覆蓋它的水平跨度。南面有主入口,教師區域和圖書館。上樓則是一整層的教學區,充分利用了這個進深過大的空間類型。我們是怎麼做的呢?通常教室的長邊總是平行於建築外立面的長邊,我們將教室旋轉90度,以短邊對齊立面的長邊。
這樣一來教室距離側面光源的距離增加了,我們便需要設計一套天窗採光系統,就是我正在放映的這個模型,同時也是一個結構元素。
教學區之上是一套縝密的採光系統,這是模型,它有點像是斜鋪頂棚的一種變式,允許兩種光線的進入。一方面將光線導入教室,另一方面導入走廊(aisle)。
這個剖面表現了斜坡屋頂根據採光需求所進行的變化。屋頂的形式和周圍的老建築產生共鳴。充足的光線讓屋檐下的教室顯得更像藝術工作室(atelier)。
另一個剖面顯示了一系列緊密的房間是如何共存的。整個項目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構成,即一個將有不同需求、不同高度、不同進深的兩個類型放在一起的設想。
制帽者之家
Hutmacher Haus
這是一個我們最近在柏林贏得的競賽方案,有時候我們自己都很驚訝,因為每次我們研究出自己的方法論,下一步總是在國外的項目中實施,而不是在瑞士,有點煩人,好像命運在捉弄我們——不過畢竟你也不能決定在哪裏贏得競賽。
這個競賽提案位於一個非常微妙的綜合社區,名叫比基尼綜合社區(ensemble),位於柏林西部。柏林牆倒塌之前,這裏是西柏林非常重要的地段,在1954年到58年,二戰戰後他們興建了這棟樓。
它叫比基尼是因為比基尼就是在這發明的,所以嚴格意義上來講不是辦公建築,而是和紡織工業有關。1958年的時候他們不僅發明了比基尼,還發明瞭很多東西。
這些發明之一就是照片上的這個空樓層。我長這麼大第一次見到一棟建築的中間有一個架空樓層。這就是他們試穿比基尼的場地,模特可以在平台上走動。這是一種早期的一種特殊的住宅,當然現在都歸為歷史遺蹟保護名列。這些照片提醒了我們當時柏林西部的密度。這個區域也和一個劇院區(cinema area)臨近。
這個地圖上你能看到整個綜合社區,上面兩處黑色的方塊就是所謂的“制帽者之家(Huthmacher Haus)”。當時是生產帽子的工坊,它們中間狹長的房子是就是“比基尼”,如今已經是一個25小時酒店(25 Hours Hotel)*。今天在右下角的黑色方塊則是“歐洲中心”,而區域中心則是威廉皇帝紀念教堂(德:Gedächtniskirche/英:Kaiser Wilhelm Memorial Church)*,是大師埃貢 · 艾爾曼(Egon Eiermann)*的作品。
注:25小時酒店(25 Hours Hotel),一個德國新興連鎖酒店品牌。
注:威廉皇帝紀念教堂最早建成並開放於1895年,為羅馬復興風格。在1943年,柏林遭到轟炸,教堂大部分結構倒塌,無法修復。1963年由埃貢 · 埃爾曼設計的新教堂羣組在原有遺蹟周圍竣工,為現代主義風格。
注:埃貢 · 埃爾曼是二十世紀後半葉德國最重要的建築師之一。
在場地模型上也能看到它們。
大家會看到,現代主義(modernity)零散地坐落在這個區域內,不像後現代建築一樣成羣結隊。這是“制帽者之家”目前的情況,我們覺得很是失望:因為它的修復採用的立面有誤,同時它的結構性能也大不如前了。因此在2020年12月之前,整棟建築都需要清空,無藥可救。在重建的競賽方案裏面,我們提出也引入一層“比基尼”架空層,因為它實在很有魅力,我們也希望順水推舟,促成整一層都市公共空間。這便有了開闊的底層和中間這一層共兩層的架空。
街景的視角也十分引人注目,前景的後現代的高層起到了框景的作用,像是一個大門一樣,而位於背景的則是埃貢 · 埃爾曼的傑作。在兩景之中的便是我們的方案,一個全新的高層,緊湊的體量中間有一道縫。
這是它在平面上的位置。
這是和剛剛一樣的視角,這次是一張渲染,在前景你可以看到動物園車站(Bahnhof Zoo),在德國也有一個同名的電影*非常有名。畫面中間是我們的方案,在40的高空介入了這樣一個架空層。
注:指《Chrisiane F. Wir Kinder vom Bahnhof Zoo》, 中譯《墮落街》,直譯為《克里斯蒂安娜. F, 我們來自動物園車站的孩子》。電影據真實人物改編,講述了一位身處離異家庭的未成年少女開始吸食致幻劑的故事,在歐洲各國引起轟動,獲獎無數,直指70-80年代歐洲青少年毒品成癮問題。
對於我們如何介入以及在哪介入這個架空層這個問題,結構起了重要作用。從剖面上講,我們所做的是在架空層引入一對X形柱。
有趣的是,邊緣的兩個柱子所承受的壓力是靠內部的兩個柱子所承受壓力的一半。利用X形柱可以將壓力的流向在中間交換,這樣一來,架空層上方承重較低的一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