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在雲端》譯者序:社交媒體中的交往與想象_風聞
新传研读社-新传研读社官方账号-用有趣推倒学术的墙,让传播学得以传播。2020-05-09 19:53
**《交往在雲端:**數字時代的人際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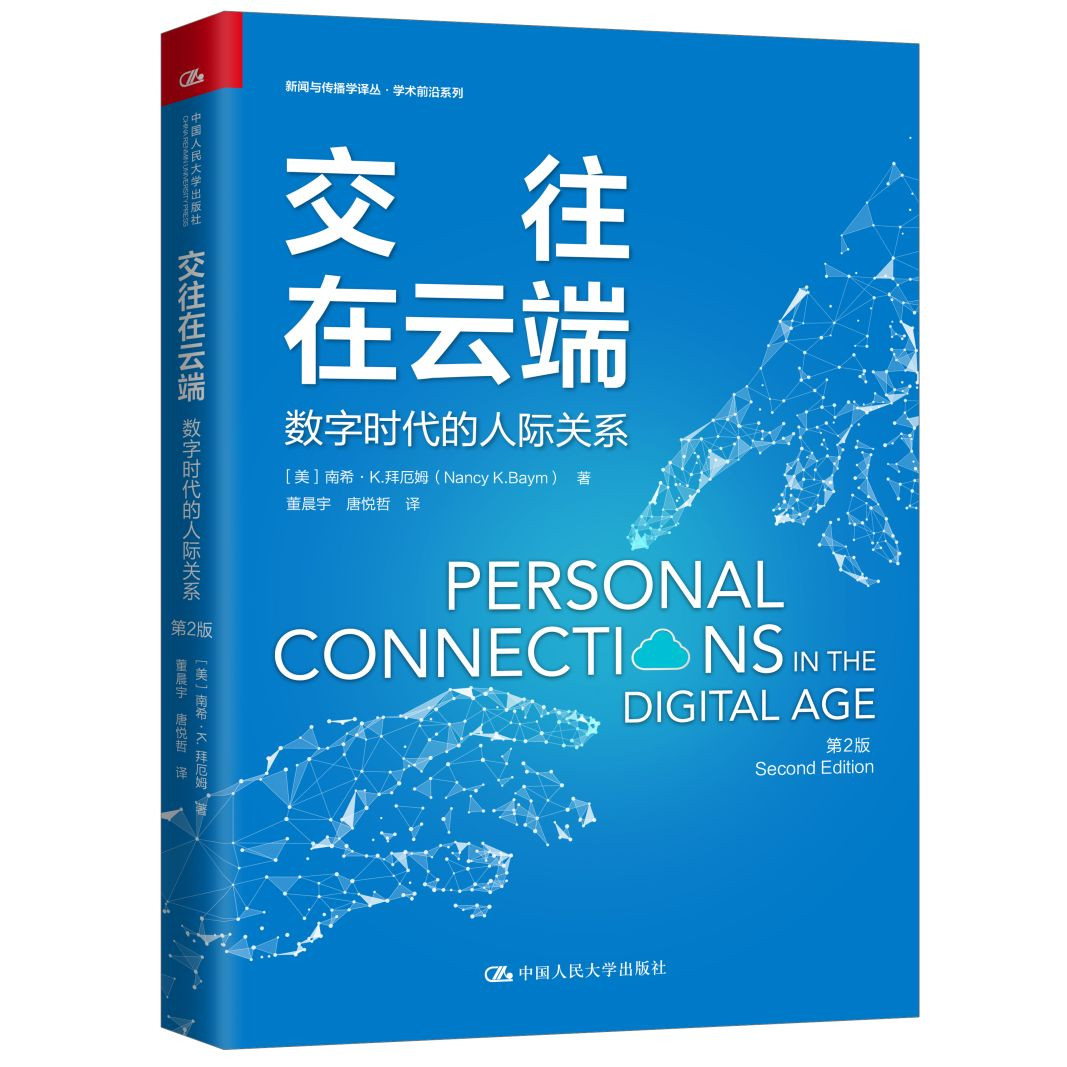
譯者序 社交媒體中的交往與想象
董晨宇 唐悦哲
我們先來講兩個故事。
1949年10月,33歲的美國作家海蓮·漢芙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售賣舊書的廣告,這家來自倫敦的書店宣稱自己收藏了不少舊書珍本。貧窮的漢芙猶豫再三,還是給書店老闆寄去一封信。她在信中寫道:“先生……我只不過是位對書籍有着‘古老’胃口的窮作家。在我住的地方,總買不到我想讀的書。隨信附上一份清單,上面列出我目前最想讀而又遍尋不着的作品。如果您那裏有這些書,而每本又不高於五美元的話,可否將此函視為訂購單,並將書寄給我呢?”
漢芙在落筆時絕不會想到,這封信會成為她與書店老闆弗蘭克·德爾長達20年友誼的開端。在最初幾封信中,漢芙還尊稱對方為先生,但從第五封信開始,她就直呼其名,如同與一位相知已久的老友談天,購書甚至已經不再是那麼重要的事情。更有好事者發現,德爾曾悄悄將信頭“漢芙小姐”改稱為“親愛的海蓮”,信件落款的時間是1952年2月14日情人節。
然而,漢芙與德爾的通信並沒有換來哪怕一次的見面。直到德爾去世的消息傳來,在漢芙心中,這個男人仍舊是一封封短信中的隻言片語。之後的日子裏,德爾的後人無心經營這家賺不到錢的書店,漢芙也久久不願踏上英國的土地懷念舊人,她乾脆將二人來往的信件編成了一本薄薄的小書,名叫《查令十字街84號》。

我們把時間再向前追溯幾百年,來到中國宋朝,講第二個故事。
宋代傳奇小説《流紅記》中寫過這樣一件事。書生於祐在宮門外散步,拾落葉一片,上有四句情詩:“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這首詩把宮女的生活寫得太幽怨了,於祐讀罷,便觸動了憐香惜玉的心絃,別取紅葉,回詩兩句:“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他將紅葉置於水上,看它漂入宮內。朋友聽聞後,莫不笑他痴情。
於祐數年趕考,都沒能取得什麼功名,於是便來到一位姓韓的人家做教書先生。韓家的老爺見於祐生性淳樸,又未娶妻,便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婚後,一日妻子整理房間時,發現於祐所藏紅葉,正是自己做宮女時所寫,於是潸然淚下,隨即取出自己當年撿到的紅葉,冥冥之中,“方知紅葉是良媒”。
試想一下,如果不是信件,漢芙與德爾恐怕永遠無法跨越遙遠的大西洋,在等待與書寫的交錯間傳遞着理想的温情。如果不是紅葉,書生與宮女又怎能跨越幽閉的宮門,在冥冥中埋下這段緣分的伏筆?當然,在我們生活的21世紀,恐怕不會有太多人願意承受等待的煎熬或將緣分寄託給天意,選擇通過信件或紅葉與他人產生交集。不過,似乎我們在做的事情與漢芙等人的所為沒什麼本質上的區別。我們不如打個有點冒險的比喻:這一封封往復的信件,不就是漢芙與德爾那個時代的電子郵件嗎?這一片片紅葉,不就是書生與宮女那個時代的QQ漂流瓶嗎?
前互聯網時代中的社交媒體

這當然不止是在感性層面上開個腦洞而已。我希望表達的是,《查令十字街84號》中温情的書信,《流紅記》中寄託愛意的紅葉,和我們在互聯網中親暱的交談,也許並沒有太多本質的區別,至少,它們都屬於所謂的中介化交往(mediated communication)。這樣一來,我們自然會產生一個疑問,當我們將微信與臉書(Facebook)視作數字傳播的革命,稱它們為“社交媒體”(social media)時,對書信和紅葉來講,是否有些不公呢?難道是因為書信和紅葉不夠社交嗎?
2015年出現了一本專門研究社交媒體的英文學術期刊,名叫《社交媒體+社會》(Social Media+Society)。這本期刊的主編齊齊·帕帕奇拉斯(Zizi Papacharissi)算得上是互聯網研究界的領軍人物。不過,她卻在創刊詞中給“社交媒體”這四個字潑了盆冷水。她説自己第一次接到邀請時,看了這個期刊的名字,就有點猶豫。她非常討厭“社交媒體”這個説法,既因為它體現出一種言過其實的暗示——社交媒體在社交性上是獨一無二的,也因為它本身存在着同義反復——當我們説起“社交媒體”時,難道在暗示,還有其他一些媒體不是用來“社交”的嗎(Papacharissi,2015)?如果從字面的意思來講,無論是《查令十字街84號》中的書信,還是《流紅記》中的紅葉,其實都是社交媒體。我們在讀中學時,給偷偷喜歡的人傳小紙條,現在想來,也是在使用社交媒體。只不過,隨着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更多時候,我們似乎更願意在深夜打開微信,對自己暗戀的人説一句:“在嗎?”

如果社交媒體僅僅突出媒體的社交本質,那麼,湯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還要走得更遠一些。在談論人類社交媒體的起源時,他直接指向了古羅馬。斯丹迪奇是《經濟學人》的記者,特別鍾情於通過古今傳播技術的對比,來理解當下的現實問題。他寫了許多傳播技術史方面的暢銷書,其中一本叫作《從莎草紙到互聯網》(Writing On the Wall)(Standage,2015)。這裏的“Wall”其實是一個雙關語,不僅指臉書上的留言板,同時也指古羅馬龐貝古城的殘垣斷壁。在那裏,考古學家發現了一萬多條塗鴉。塗鴉的內容可以説五花八門,有人在上面求愛,有人在上面發表政治觀點,還有人在上面“出櫃”。比如有一條塗鴉寫道:“賽昆杜斯想念普里瑪。”底下緊接着,普里瑪就回復説,自己也向賽昆杜斯問好。想想看,這些牆上的塗鴉,與我們在臉書留言板上書寫的對話,又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呢?
按照斯丹迪奇的描述,在古羅馬人的社交盛宴上,其實這些塗鴉還只是前菜,他們最經常使用的社交媒體,是蠟板和莎草紙。蠟板就是塗上蠟的木板,形狀和我們今天的平板電腦十分相似。蠟板比較沉,適合短途傳遞消息。如果是長途通信,古羅馬人更喜歡使用莎草紙,這是一種用尼羅河邊生長的草稈製作的紙張,價格相對貴了一些,但十分輕巧,便於攜帶。作者説,蠟板和莎草紙就是古羅馬時期的社交媒體,而幫助貴族傳遞這些信件的奴隸們,就是古羅馬時期的寬帶,他們將貴族們發送的信息連成網絡。
在古羅馬時期,著名的演説家馬庫斯·西塞羅就是個社交媒體迷。即便沒什麼事兒,他也要和朋友通個信,問候一下近況。朋友們接到西塞羅的蠟板,就直接在空白的地方回覆他,這不就是現代社交媒體的回帖功能嗎?如果通信的內容特別有價值,收信人還會讓奴隸抄寫下來,轉給其他朋友閲讀,激發進一步的討論,這簡直就是轉推功能。
從技術發展的高度上,莎草紙與微信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一方面,微信潛在地消滅了社會交往的時間和空間障礙,實現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的人類願景;另一方面,我們同樣可以發現,社交媒體在發展歷程中不斷地接近面對面的交流:信件可以還原語言,電話可以還原聲音,視頻通話可以還原樣貌。如今,虛擬現實技術則可以還原場景(Bolter & Grusin,2000)。不過,即便如此,技術的精進不會改變的是人類的社交本能。不管是古羅馬時期的蠟板和莎草紙,還是我們如今使用的微信、微博,都是人類社交需求的實現途徑。因此,在社交需求方面,不管是古羅馬人,還是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其實都是一樣的,並沒有貴賤之分。
《聖經》中説,太陽底下無新事。同樣,社交媒體中的中介化交往,也並不是什麼21世紀的新發明,甚至我們可以説,一切媒體其實都是廣義上的社交媒體。區別書信與微信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但如果我們想要理解社交媒體的意義,便需要從人類的社交本能與慾望出發,理解書信與微信之間若隱若現的延續性。
讓陌生之事變得熟悉

理解社交媒體歷史暗線的意義,在於幫我們抽身而出,更為理性地思考技術的社會影響,為社交媒體祛魅。按照本書作者南希·拜厄姆教授的話來講,便是逃離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技術決定論思維(Baym,2015)。
回顧人類歷史,幾乎每一種全新的社交媒體(或更廣義的傳播技術)出現在人們生活中時,我們都難免會產生極端化的應激反應,要麼認為它是洪水猛獸,要麼認為它是救世靈藥。人們憎惡王者榮耀、抖音、今日頭條會毀掉青年一代;人們讚美人工智能會帶來美好的未來。這些簡單粗暴的憎惡與讚美,都在人類歷史上不斷上演,同時也反覆被證偽。我們可以來試着讀讀這兩段話:(1)“這將是一座沒有屋頂的教室,教室的牆壁建立在整個地球上,每個家庭都是對哈佛大學的延伸”;(2)“新技術的卓越功能,將會把那些視覺化的手段和技術引入教育過程,對全世界的學生們來説,這將使得教育更加具有娛樂性和吸引力”。我在課堂上詢問學生,這兩段話讓你想起了什麼,很多人告訴我,這不就是在説在線教育嗎?不過實際上,前一句是20世紀20年代對於廣播的評論,後一句是20世紀40年代對於電視的評論(莫斯可,2010:121,124)。
對於傳播技術的烏托邦和反烏托邦想象,還有更多的例證,如今看來,這些判斷都難免讓人笑場:“20世紀90年代,權威專家一致預測,互聯網將開啓一個文化民主的新時代,自主的消費者將要發號施令,舊的媒體寡頭將要腐爛和死亡。互聯網將振興民主。在世界各地,弱者和邊緣人將被賦予力量,迫使獨裁者下台,並使權力關係重組。互聯網將會使宇宙收縮,促進國家間的對話和全球理解。”(Curran,2012)“在美國,人們擔心汽車會使青少年與家人產生隔閡,還指控書籍、漫畫、電影和電視會導致青少年早熟或成為少年犯。在美國歷史上,人們同樣會擔心19世紀中葉特別流行的廉價小説會損害其讀者的智力發展、增加他們潛在的反社會行為和犯罪概率。”(Baym,2015)
在研究者的世界中,這種烏托邦和反烏托邦思考邏輯也並不罕見。20世紀80年代,研究者基於媒體反饋速度、多線索溝通能力、語言使用能力和情感傳遞能力四個指標,將媒體分為貧媒體與富媒體(Daft & Lengel,1984)。這一區分的目的,在於通過媒體的“貧富差距”,確定它們的實際用途。例如有研究就發現,貧媒體更適合傳遞功能性的信息,富媒體更適合傳遞相對複雜的信息(Kiesler & Sproull,1992)。比如我可以通過即時通信工具和朋友約定聚會的時間和地點,但我們之間的情感關係,還是要依靠面對面的相遇來表達和增進。由此,我們似乎推演出這樣一個結論:社交媒體中的人際交往,註定是線索貧瘠的,社交媒體中的人際關係,也難免是相對膚淺和單薄的,這有些類似於雪莉·特克爾(2014)所説的“羣體性孤獨”。
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技術並不能完全決定人們的使用行為,它也許可以決定使用的起點,但卻不能決定使用的終點。在整個過程中,人們進行情感交流的本能,永遠是推動“情感補償”行為的原動力。
情感補償的第一種策略是標點符號的創意性使用,這要從20世紀70年代談起。1972年,也就是阿帕網問世後的第三年,卡內基·梅隆大學的教授斯科特·法爾曼(Scott Fahlman)提出,由標點組成的 :-)可以用來表示微笑。這種字符表情其實就是繪文字(emoji)的前身。有趣的是,這種創造性表達看似簡單,但卻可以反映出一些文化上的特質。比如在日本,人們使用的微笑字符是在平直的嘴巴上方畫上一對眯起的笑眼(^_^),這反映出的正是日本人在公共場合不能肆無忌憚地表達情感的禮儀。因此,注重用眼部來展露情感的文化特徵反映在了微笑字符之中(Yuki,Maddux & Masuda,2007)。在中介化交流中,標點符號被賦予了新的意義。比如,省略號在中介化傳播中,更多會表達“為難”,而不是像書面語一樣表達省略。

其次是文字的創意性使用。拜厄姆教授在本書中舉過一個例子,在英語世界中,表達我很繁忙,可以直接説“I am so busy”,但如果用户想在中介化交往中強調自己的情緒,便可以把這句話的副詞大寫(I am SO busy)、修改副詞的形式(I am sooooooo busy)或重複性、非正規地添加標點符號(I am so busy!!!!!!)(Baym,2015)。在漢語世界中,人們也會使用文字、字母、數字的組合來表達情感。比如在幾年前,年輕人經常會把“你是不是傻”寫作“你4不4灑”,來表達無惡意的戲謔和調侃。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更具文化色彩的情感補償方式,即所謂的“視覺方言”(eye dialect)(Haas et al,2011)。視覺方言是一種故意的、不標準的拼寫方式,用以表示文字的讀音和地域特色。這種方式在英文中分為兩種,即詞彙視覺方言和聲音視覺方言。比如,用k表示ok,gonna表示going to都屬於詞彙視覺方言;而hmmm……(呃呃呃,表示猶豫),hahaha(哈哈哈)則屬於聲音視覺方言。這種互聯網中的“方言”還可以用於增進親密感、建立文化身份的認同感。例如推特上的黑人用户經常會使用一種被稱為“黑人推特”(black twitter)的語言來表達彼此之間的熟悉與親密,例如他們會用wit代替with、用tryna代替trying to、用you代替your,還喜歡在形容詞後添加ass來表達更加強烈的情感,例如“stupid ass”(Florini,2014)。
讓熟悉之事變得陌生

當我們談到“讓陌生之事變得熟悉”時,想要傳達的是這樣一個觀點:不論是普通讀者還是研究者,在面對新媒體時,需要把新生之事放進歷史的脈絡中,才能更為清晰地洞察到它的真正意義。或者説,只有在經歷資本的瘋狂之後,一種新媒體變成我們身邊熟悉的事情,我們對其社會意義才能獲得更為冷靜的思考和判斷。丹尼爾·米勒(Miller,2011)的這段話完美地佐證了這種因熱情而生的偏狹:“每當一種新媒體興起時,總會出現一模一樣的觀點。舉例來説,菲律賓的EDSA革命能把總統趕下台,就被歸功於移動電話的出現,因為人們是通過發短信來協調政治抗爭的。不過,更加清醒的分析卻表明,移動電話的影響被誇大了。今天的人們已經不再認為,移動電話在政治方面具有特別的革命性,部分原因在於這種熱情已經被轉移到了社交網站上。”
“讓陌生之事變得熟悉”,是社交媒體研究者需要進行的“祛魅”;相反,“讓熟悉之事變得陌生”,則是社交媒體研究者需要進行的另一項工作。社會學家克莉絲汀·海恩提出了一個説法很有意思:因為這些社交媒體對我們來説太熟悉了,普通人也不難形成一些觀點,這就帶來了一種“平庸化”(banalization)的危險(Hine,2015:9),甚至會讓人覺得,這些司空見慣的事情有什麼可以研究的?此時,研究者要做的事情,就是“重新前置平庸的事物”(Reforeground the banal)。換句話講,就是藉助專業的方法性工具,把平常無奇的事物,重新擺在顯耀的位置上,賦予它們新的意義與解讀。
為了解釋這個觀點,我們不如從社交媒體研究中最為基礎的概念談起(把更為精彩的洞見,留到拜厄姆教授的正文中吧)。如果我們暫不考慮斯丹迪奇對古羅馬的召喚,僅僅聚焦以互聯網為基礎的社交媒體,那麼,何謂社交媒體呢?這似乎是一個“幼稚”的問題,因為社交媒體離我們太近了。不過,正因為這種接近,讓我們甚至不願多花時間來思考社交媒體究竟是什麼,甚至一時慌了手腳:“這……很難一句話説得清吧。”那麼,不如我們再把問題縮小一些:推特(Twitter)是社交媒體嗎?
我想大概沒人會否認,Twitter是社交媒體,因為人們會在上面相互“關注”。不過,在2010年,計算機研究領域中就出現了一篇“挑刺兒”的論文,提出了這樣一個挑戰常識的研究問題:Twitter究竟是什麼,是社交媒體還是新聞媒體?(Kwak,Park &Moon,2010)。三位作者抓取了4100萬名Twitter用户的好友關係,發現了這樣三個有趣的結論。第一,被關注人數超過100萬的用户總共有40位,要麼是布蘭妮·斯皮爾斯這樣的公眾人物,要麼是《紐約時報》這樣的媒體賬號,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賬號幾乎不會反向“關注”那些關注他們的人。第二,只有22.1%的用户的關注關係是雙向的,和其他社交媒體比起來,這個數字是非常低的,比如在圖片分享網站Flicker上,互粉關係佔到了68%。第三,67.6%的Twitter用户是沒有被任何人關注的。綜合這三個結論,Twitter的主要功能究竟是獲取信息,還是建立關係,本身就要打個問號了。倘若真如結論所言,Twitter的信息功能壓倒了關係功能,那麼,它究竟是新聞媒體還是社交媒體呢?

當然,一種解釋是,按照亨利·詹金斯(Jenkins, 2005)的説法,我們生活在一個“融合文化”的時代中,很難找到一個純粹專注一件事的平台。換句話講,我們不能要求Twitter只做社交,也不能禁止Facebook推送新聞。當我們談到社交媒體時,其實面對的是功能側重性千差萬別的互聯網平台。對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商學院的研究中獲得一些啓發,例如,簡·基茨曼等人的研究就展示了不同社交媒體平台之間的差異(Kietzmann et al,2011)。他們提出了社交媒體的七個功能塊,分別是分享、在場、關係、身份、對話、羣組與聲譽。比如,職場社交平台LinkedIn更加重視幫助用户建立“身份”,位置打卡平台Foursquare更加聚焦於用户的“在場”感,視頻分享平台YouTube更加突出“分享”,臉書則更加強調用户之間的“關係”。這樣一來,社交媒體就像是一把巨大的陽傘,把這些形態各異又鬆散相連的媒介平台罩在下面,並給它們取了一個看似整齊的名稱:社交媒體。
這種策略一方面讓“社交媒體”這一稱謂充滿了想象的張力,另一方面,卻讓定義它的嘗試變得越發難以實現。當這些平台都被我們統稱為社交媒體時,接下來一個殘酷的問題便是,什麼不是社交媒體呢?畢竟,社交元素已經越來越成為手機App中的標準配置,Apple Watch等可穿戴設備在強調社交,鼓勵人們分享自己的健身數據(你的朋友中是否有這麼一個人,為了爭取行走步數第一,每天晚上硬着頭皮在馬路上晃悠?);網易雲音樂鼓勵用户把自己喜歡的歌曲分享到微信中,讓朋友們聽到(除此之外,我曾經真的在網易雲音樂App上發私信和朋友約過一起吃飯……);就連滴滴順風車的廣告也告訴消費者“粉色星期三,你有短裙,我有暖風”(此處省略一百字不便印刷的評論)。如果我們把具有社交性的互聯網媒體都稱為社交媒體的話,那麼,整個互聯網中,恐怕剩不下幾個媒體不是社交媒體了。
因此,社交媒體這一稱謂總在時不時被過度使用。隨着社交媒體的流行,社交媒體這把傘的面積簡直要遮住整個互聯網世界。當然,這也許不過是“知識的商品化”的軌跡:社交媒體帶有資本紅利,資本就會貼標籤,反過來,社交媒體的概念外延也便愈加蔓延和模糊,創造了一些新的詞語。這樣一來,學術概念成為一種商業產品。“這種商品化的趨勢愈演愈烈,幾乎發生於所有的科學和藝術創造之中”(蓋恩,比爾,2015:4)。
畢竟,這是一個你管鄰居借個電鑽,都可以稱為共享經濟的年代。
《交往在雲端》的一種讀法

以上幾千字的自言自語,並非希望喧賓奪主,而是想要藉助以上兩種邏輯,為讀者提供一種閲讀這本書的方法。
不如我們把閲讀看作一場旅行,如此一來,本書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便是旅行前來打包一些行李。第一章重點落在互聯網技術可供性(affordances)上,這也許是我這樣的文科生最大的軟肋。當我們談論互聯網時,多數在聚焦關係與文化,少數在關注技術本身。拜厄姆教授為此提供了七個理解互聯網的關鍵概念:交互性(interactivity)、時間結構(temporal structure)、社交線索(social cues)、存儲(storage)、可複製性(replicability)、可及性(reach)和移動性(mobility)。第二章重點落在對待技術的不同想象上,即技術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技術的社會構建論(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技術的社會形成論(social shaping perspective)與馴化(domestication)。這也呼應了譯者序中我們談到的“祛魅”問題。我們當然需要正視“技術決定論”的價值,尤其是在這樣一個技術更新飛速的時代,技術的社會影響是我們無法逃避的關鍵詞;不過,我們更應該理性地考慮到這一過程的“互動性”,從社會因素出發,考慮社交媒體使用的“意外可能”——沒人想到美國社交網站Orkut會迅速被巴西人和印度人佔領;App的開發者也不會料到,人們以一種反社交的方式使用社交媒體。例如有人會使用地理位置打卡的App,避免遇到剛剛分手的前任。
打包好我們的行李,在之後的章節中,讀者也許會發現,拜厄姆教授在表達自己的觀點時,存在一條暗線,也就是通過分析人們對於技術可供性“不可預料”的使用方式,來駁斥技術決定論。
本書第三章聚焦數字空間中的傳播“線索”(cues),拜厄姆拒絕了技術決定論的線性思維方式,而是關注用户如何在這些社交媒體上重塑了媒體本身。按照拜厄姆的話來講:“人們並沒有就此放棄,也沒有甘於接受貧乏的社交線索,僅僅進行沒有感情和關懷的中介化互動。相反,交流的必要性激勵人們創造性地使用這些線索,以便能夠表達感受、開展遊戲、進行表演,並創造身份、關係和羣體語境。”第四章聚焦網絡“社羣”(community)。同樣,拜厄姆拒絕了技術決定論的線性思維方式,不認為線上社羣一定能夠解決美國人“獨自打保齡球”的困境。她採取社會建構論的視角,關注“那些影響線上和線下社區的社會力量,其中包括參與者的社會身份、激發線上行為的不同動機,以及圍繞如何在線上行事、哪些技能必不可少所發展出來的社會規範”。第五章聚焦互聯網中的“自我”(self)。同樣,拜厄姆也拒絕了“線上關係一定更加膚淺”“線上自我一定更傾向於欺騙”的技術決定論思維方式。她援引了不少近年來的研究,證明“技術可供性能夠影響自我呈現,但並不決定它”。第六章聚焦“交往”(interaction),技術決定論再次成為拜厄姆教授批判的對象,因為“媒介對於不同時間內、不同關係中的不同的人,都具有不同的含義”。除此之外,社會、文化、年齡、性別、個體人格特質等因素,同樣會影響用户對於社交媒體的具體使用方式。
一本譯著最大的受益者,往往是譯者本人。因為恐怕沒人會像譯者一樣,和書中的每一個字反覆較勁兒。一年前,出於對本書的喜愛,我將它推薦給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翟江虹老師,一年之中,我與唐悦哲一起,把這本英文書變成了“方塊字”。我相信,無論是社交媒體的普通使用者,還是社交媒體的專業研究者,拜厄姆教授都為之提供了值得關注的洞見。當然,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們雖然盡心盡力,但因為水平有限,難免有不妥之處,敬請讀者不吝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