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怡這一跳,是華語片20年最高峯_風聞
Sir电影-Sir电影官方账号-2020-05-16 22:18
作者 | 毒Sir
本文由公眾號「Sir電影」(ID:dushetv)原創。
魔幻現實主義再次上演。
原定5月12日開幕的戛納電影節,受疫情影響,“貢獻”給影迷這樣一幅又好笑又好氣的畫面。
一隻特立獨行的豬出現在戛納街頭。
72歲的戛納,中國電影有過無數高光時刻。
1993年,《霸王別姬》獲金棕櫚獎
2000年,姜文的《鬼子來了》獲得評委會大獎
同年,梁朝偉憑《花樣年華》獲得最佳男演員,楊德昌憑藉《一一》獲得最佳導演
但要説到真正在藝術和商業兩手開花,乃至文化影響力綿延不斷的,或許只有它。
5月16日,是它在戛納首映20週年。
當年導演李安,攜主演周潤發、楊紫瓊、章子怡引爆全場。
次年2月,第73屆奧斯卡獲得包括最佳攝影獎、最佳原創音樂、最佳藝術指導等在內的四項大獎。
奧斯卡第一次授予華語電影最佳外語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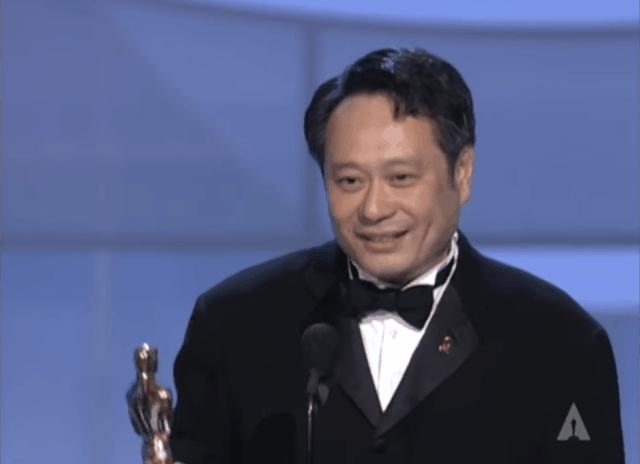
直到今天,豆瓣8.3分,爛番茄新鮮度97%,好評率86%。
你應該猜到了。
它是《卧虎藏龍》。
《卧虎藏龍》的二十年,是華語電影走向多元,也走向焦灼的二十年。
今天説它。
不單是看到荒誕的野豬奔跑,背後全球電影人的困惑與焦慮;更是反思“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青冥劍”的真正內涵:
什麼才叫入道?
不為外物虛幻之表象所遮掩,唯有舍我,才能入道。
西方
20年前。
戛納電影節上,觀眾們對將要放映的電影議論紛紛。
“這部電影的片名有點怪”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這是什麼電影?”
“好像是一部中國科幻片。”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即《卧虎藏龍》。
在老外眼中,《卧虎藏龍》,這片名聽上去像科幻片??

先別急着笑。
一部來自東方的古裝武打片,對當時的西方觀眾來説,就像90年代的中國觀眾,接觸到《星球大戰》一樣。
在它身上,西方觀眾差不多滿足了他們對於神秘東方的全部想象。
怡然自得,水墨畫般的江南建築。
△ 安徽黃山市宏村鎮,至今對遊客宣傳的最大賣點,就是《卧虎藏龍》拍攝地
隱藏在人間,雲霧繚繞的宗教聖地(道觀),觀眾們相信這裏住着“神仙”,煉着不老的“藥”。
當然少不了神乎其神的功夫。
尤其是輕功。
竹林上彈跳自如、綠湖面如履平地。
除了從未見過的視覺衝擊,聽覺上也是針灸般的迷離、刺激。
譚盾與華裔大提琴家馬友友共同合作,既融合西方古典音樂的渾厚、工整,又加上東方味道的鼓點、民樂器。
一切的一切,像極了李慕白口口聲聲的意境:
意境是什麼?
五個字。
很深的寂靜。
當然了,單單是感官上的饕餮,西方觀眾也只會停留在獵奇層面。
真正從情感甚至價值觀上將這部作品捧上經典的,還在於李安的故事,情感,以及突破東方語境的價值觀。
《卧虎藏龍》的內核,其實任何一個西方觀眾都瞭然於心。
理智與情感。
是的,你沒有看錯。
當年改編自英國作家簡·奧斯汀原著,李安説,我想拍女主角面前一望無垠、被風吹拂的草地,一直延續到地平線。
攝影師説,你不可能拍到。
李安説,不,我要拍到。
“不,你不可能。”
“我做得到。”
於是,執拗的李安把這份念想,一直延續到《卧虎藏龍》。
電影開篇就是極其漂亮的邊疆壯景。

它,就是片中所有人物理智與情感鬥爭的“牀”。
電影裏,理智派是俞秀蓮、李慕白、王爺,玉嬌龍的父母,甚至碧眼狐(理智到冷血)。
情感派則是玉嬌龍、羅小虎。
但這兩派並非涇渭分明。
它們互相滲透,互相影響。
比如面對李慕白,俞秀蓮不就是充滿情感,喪失判斷,從女俠還原成女人。
比如面對羅小虎,玉嬌龍拒絕回新疆,她識破“私奔”並不能真正解決人間的功利鬥爭,於是,毅然決然地帶着青冥劍跳下山崖。


所以,看《卧虎藏龍》。
你第一眼看的是東方,是功夫。
但你再咂摸,你看到的情感,是李慕白&俞秀蓮&玉嬌龍&羅小虎的四角糾葛。
但你再再再咂摸,他們的選擇,真的是“我愛你你不愛我”那麼簡單嘛?
不是的。
他們最後的選擇,都是因為對過去的自我有了更深刻的認知。
理智派開始有了不能克服感情的軟弱。
情感派開始有了不能承受理智的算計。
而後,理智與感情一起赴湯蹈火。
《卧虎藏龍》是把功夫當愛情,把愛情當哲學命題拍。
不信。
聽聽李慕白的獨白。
你品,你細品:
我並沒有得到的喜悦,相反地,卻被一種寂滅的悲哀環繞。這悲哀纏繞了我很久,使得我無法再繼續……
從眼睛到耳朵再到心靈。
西方觀眾受用於李安這種電影魔術全方位的按摩,既熟悉又新奇、既認同又驚訝。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青冥劍。
東方
但誰也沒想到。
戛納引爆後的《卧虎藏龍》,兩個月後內地公映,打了啞炮。
口碑遇冷,票房遇冷。
時至今日你還能在網上搜到類似問題:
這種“牆內開花牆外香”的反差是怎麼回事?
是期待值的落差,也是傳統觀念遭遇挑戰。
在《卧虎藏龍》之前,我們熟悉的主流功夫片長這樣:
《少林寺》,1982年內地公映,一毛錢的電影票價創造的是1.6億票房。功夫皇帝李連杰從這裏走出來。

然後就是成龍的《蛇形刁手》《醉拳》等片,硬橋硬馬。
然後就是徐克的黃飛鴻、方世玉、令狐沖等等,飛天遁地、寫意過癮。


概括起來就是:
不論你是柔是剛,是寫實是寫意,最最起碼,打得好看,就是精彩,就是刺激。
但李安偏偏捨棄了“刺激”。
最經典的竹林戲,周潤發扮演的李慕白,與章子怡扮演的玉嬌龍,與其説在打鬥,不如説是一場坐而論道的“奇葩説”。
主流的功夫家甄子丹、袁和平都抱怨過,李安這場戲動作欠佳。
——李安本意就不是去渲染動作的力度、速度。
對峙雙方表面上的情節是試探功夫實力,實則試探心意。
李慕白要玉嬌龍歸順他,拜他為師;
玉嬌龍不服,要用青冥劍證明自己可以。
李慕白偏要,打着打着,實際上就已經開始闡述他對人生的看法。
是兩種慾望的較量。
李慕白是情慾、是對青春生命的控制慾;玉嬌龍是女性意識的自省、反抗。
後輩導演徐浩峯看出這一層,在自己的影評集《刀與星辰》,直接用“巨大的彈簧牀”比喻竹林這場調情。
調皮,但意思是對的。
“劍法即心法,一切都是人心。”
有韌性竹子前後搖曳,讓李慕白和玉嬌龍兩人若即若離。

象徵着彼此內心的距離。
每一次進攻性的揮劍,都是在拉近心理距離。
慢鏡頭,特寫,電影忽然切換為李慕白的主觀視角。
四目交投中,流淌着難以言喻的情愫。

玉嬌龍顯然不是李慕白的對手,面對她氣急敗壞地胡亂抖動,李慕白氣定神閒。
玉嬌龍稱他做“老江湖”,類似“老司機”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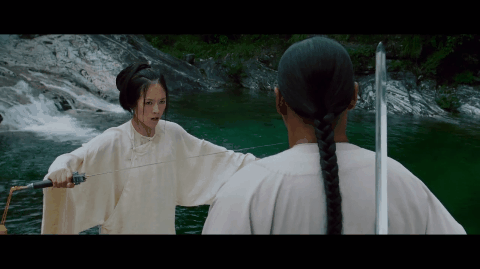
李安放棄了傳統功夫片的硬朗審美。
誰説輕功就是狂風大作,人體翻飛。
他更傾向於在力道中加入更多陰柔、更多纏綿。
她把武戲當文戲。
再看這場戲。
玉嬌龍與俞秀蓮的打戲。
像什麼?
像是情敵之間的較量。
比如這一幕——

俞秀蓮拿起月牙鏟,向玉嬌龍砸去。
但因為兵器過重,沒能揮舞起來。
此刻,俞秀蓮對於李慕白求而不得,又不敢主動告白的焦慮,化成對玉嬌龍微妙的嫉妒,惱羞成怒。
而玉嬌龍呢,則有後浪的桀驁不服,管你是誰,擋我道者,殺。
但她何嘗不也在發泄不能與羅小虎團聚,被父親逼婚的憤懣。
所有這一切的趣味,由於過於“叛逆”,東方觀眾的錯愕可想而知。
第一反應幾乎都是失望。
直到第二年春季,該片又在奧斯卡上大放異彩,越來越多的人放下執念,重新回顧才覺得它的好,它的妙。
管它西方東方
好在哪?妙在哪?
Sir想提影片最後的死亡。
很多觀眾都不理解,玉嬌龍為什麼自殺?
她不是可以逃離婚姻,與小虎瀟灑人間嗎?
原著中,玉嬌龍確實沒有死。
但。
李安改造原著文本的能力是一流的,他總能看到隱藏在情節裏,人性的疑點。
原著裏,玉嬌龍跳崖是假死,是為避開身為朝廷命官的父親玉大人,成全他的名望,此後玉嬌龍縱情縱性,浪跡江湖。
但到了李安手上,玉嬌龍非死不可。
為什麼?
因為一生醉心江湖的她,看破了江湖的不自由。
更殘酷點説:不存在**。**
玉嬌龍不想成為父母那樣的人,這點很好理解。
玉嬌龍也不想成為師傅那樣的人,因為師傅道行太淺,她的悟性,功夫早就超過師傅了。
那當俞秀蓮這樣的大師呢?
一生也不快樂。
羅小虎的“新疆”,像是“自由”的應許之地。
但那種目無法規的作風,當真能被江湖長久接納?
不是。
説白了,她苦苦尋找的江湖,不過是另一個朝廷。
玉嬌龍應該最愛李慕白。
李慕白的死,也成為她人生的幻滅。
愛上一個不存在的人,一個不存在的世界,這份無處寄託的情感,只能反過來囚禁自己。
她的跳崖可以理解為追隨李慕白死去的腳步。
同時,也可視為,她實現自由的方式。
借用李慕白的話:“當你握緊拳頭,手中什麼也沒有,鬆開雙手,你擁有的是一切。”
握緊拳頭是執着於“有”,而“生”就是一種“有”。
鬆開雙手隨從了“無”,但**“無”能生“有”。**
某種程度,玉嬌龍的死並不是逃避。
她,只是選擇了“無”。
這種改編,無疑是李安的自我表達。
這正是李安了不起的地方。
這個長相儒雅的男人,在他天真的笑容背後,其實藏着華語電影人罕見的反骨。
《喜宴》中同性戀與傳統孝道的兩難、《卧虎藏龍》的朝廷與江湖的兩難、《色,戒》中兒女情長與國家大義的兩難…….
傳統or現代,東方or西方,信仰or慾望,擅於製造衝突的李安,其實一直在述説“理智與情感”。
李安一直在面對自己。
這也是之後“跟風”的中國武俠大片都不能企及《卧虎藏龍》高度的原因。
2002年的《英雄》,掀開了內地的大片時代。
投資3000萬美元,全球票房1.77億美元。
這當然是一筆成功的買賣。
但《英雄》説的是什麼?
是“江湖(自我)本不該存在”。
張藝謀很委屈:
其實《英雄》還有一個隱藏結局。
無名死後。
秦王説“厚葬”。
眾大臣哈哈大笑”吾王萬歲,又躲過一劫”。
秦王再次不動聲色:“厚葬!”。
這樣做就深刻?
可能有一點點。
——諷刺了權力的虛偽。
但不能改變《英雄》那種士大夫式渴望被權力垂青,乃至變成權力的軟弱。
同理還有陳凱歌的《無極》。
今天,你能讀出層出不窮的“神預言"。
但“預言”的死結也在於它的空洞。
它不過利用那些“説了等於沒説”的話術。
馮小剛的《夜宴》就更不用説。
連他自己都不想多談。
李安的電影讓人剝皮,也讓自己剝皮。
易先生和王佳芝的牀戲,是整部片的節拍器。
身經百戰的梁朝偉一開始不以為然。
但一上手,李安就發飆了。
他覺得易先生的性愛,跟王家衞那種風騷不一樣。
他的性是發泄。
是一個亂世惶恐特務的暴虐和絕望。
梁朝偉至今忘不了李安發火的樣子:
李安不會轉彎抹角,誰都不給面子,直指要害。譁,讓他一句一句地擲過來。
最後翻來覆去拍了13條,拍到梁朝偉崩潰,李安才罷手。
最後李安也哭了。
二十年過去了。
Sir今天重提《卧虎藏龍》,其實更想説——
華語電影又到了沉重的時刻,看似二元對立的選擇又出現了。
疫情,是致命打擊還是催化升級?
院線電影退出主流,還是加大網絡電影開發?
甚至,堅持還是妥協,理智還是情感?
……
這時候,Sir總想起李安關於在電影院裏看電影的比喻。
他説:
電影不是把大家帶到黑暗裏,而是帶過黑暗,在黑暗裏檢驗一遍,再回到光明。
原本以為這是李安説給觀眾的話,是對電影的情書。
但再咂摸咂摸。
Sir以為。
這更像他對電影的要求。
電影,是有信仰的。
所謂信仰。
請先把自己完完全全裸露出來,我信什麼,我懷疑什麼?
我不能假裝自己從沒面對過。
本文由公眾號「Sir電影」(ID:dushetv)原創,點擊閲讀往期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