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向東 施展: 當下我們的內外困境, 無不源於一種“精神分裂”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0-05-18 23:20
CSSCI核心期刊**《文化縱橫》2020徵訂火熱進行中**
✪ 於向東 | 上海世界觀察研究院
✪ 施展 | 外交學院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導讀】**2012至2014年,《文化縱橫》曾約請上海世界觀察研究院《大觀》雜誌的編委於向東、施展多次對談中國外交哲學,對世界格局在現代和前現代的變動,以及中國外交所面對的處境,做了深入解讀。本次對談中,兩位學者討論了現有世界秩序(清教歷史觀和世界觀)運作的思想內核、浪漫式民族主義精神的心理內驅力、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英美兩國相繼成為世界秩序制定者的原因、中國國民認同中的內在張力等問題。他們認為:
“近代化”從“民族意識”產生,而“現代化”從“民族精神”產生。“近代化目標”與“現代化目標”之間的衝突造成了一場“精神危機”,甚至可以説是一種“精神分裂”,中國今天所面臨的很多內政外交的困境都與此相關。今天,沒有人否認中國已然強大,但我們並沒感受到想象中的地位和榮耀,相反,我們不停地感受到普遍主義世界秩序對我們的約束,而這被解讀為西方列強秩序下的羞辱。這就進入一個不斷地自我證成的邏輯:越是追求列強意義上的強大感,越是獲得挫折感;於是追求進一步的強大感,又感覺陷入更深的圍堵中,惡性循環,彷彿周邊世界充滿惡意,彷彿我們不是龐然大物,而是待宰羔羊。這意味着最強的國家理由,它幾乎可以正當化任何內政和外交上的行為,卻不僅帶來外部的反彈,也帶來內部深刻的不滿。他們指出,只有實現民族的精神轉向,從封閉的“民族意識”躍遷到勾連世界、構建世界的“民族精神”,中國才能徹底消除民族精神分裂和精神內戰的所有可能性,從而成為一個精神飽滿的民族,一個自我實現了的民族。如今讀來,這些思考不僅沒有過時,而且在今天世界秩序接連巨震的時局之下,反而更具現實意義。
本文原發表於《文化縱橫》2014年2月刊,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思考。**
從“民族意識”到“民族精神”
——外交哲學對談之六
(本文原發表於《文化縱橫》2014年2月刊)
▍從民族意識到民族精神
施展**:**所謂外交哲學,其根本還在於國家的自我意識,這決定了它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世界,以及如何看待自己與世界的關係。對談進行到現在,該回到對於我們來説最根本的問題了,中國的自我意識是什麼?它是如何生成的,又是如何演化的,今天該是什麼樣子?
於向東**:**民族的自我意識,可以細緻地勾勒為一個精神現象學的過程,我稱之為從“民族意識”到“民族精神”的歷程。以“民族”作為意識主體,對中國人來講,是很晚近才有的。在此之前,我們有天下意識,有地區意識,但沒有作為一個民族的“中國人”的明確意識。在傳統的天下觀裏,外部世界以各種方式被編織進我們所構想出來的天下秩序當中,沒有“他者”的地位,從而也就沒有“自我”。宋元明清之際的華夷衝突,並沒有否定天下觀,而只不過是在爭辯據有天下者是否必須中原出身。到西方人來的時候,一種更強的國際秩序替換了“天下秩序”,周邊世界頃刻成為“他者”,而且是強有力的“他者”,形成對中國的全面壓制,於是強烈的“自我”意識產生了,民族意識也才開始生成。
**施展:**民族意識在政治上表現為民族主義,是一種對特定區域內民眾的動員和治理方式。在歐洲,民族主義的起源有漫長的歷史,但它的興起和流行,和工業革命以及工業技術推動的軍事變革聯繫在一起:民族主義在政治上的動員效率與新的軍事體系結合起來,在國家之間的戰爭中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競爭能力。戰爭極大地推動了民族主義的擴張,並在戰爭中,逐步形成了基於民族國家的國際秩序,即關於國家間戰爭與和平的規則體系。隨着西方擴張,這種國際秩序伴隨着軍事勝利而強行推行到中國。
**於向東:**軍事的失敗,天下秩序觀念的瓦解,使得中國的自我意識籠罩在被打成弱者的氣氛下。所以我們的民族意識是從對自我的“否定性”意識開始的。它首先是一種歷史經驗,即在對抗西方人的擴張時,傳統的政治方式都失敗了,那隻好學習對方的政治形式,期間做過各種嘗試,包括革命。這個過程中遇到很多困難,新設立的政治制度似乎也沒有馬上見效,甚至相反,還帶來了更多的問題,對這更多問題的解釋乃至解決就走向了兩個路向:一是認為傳統桎梏過強導致學習西方還不夠,於是走上了激進主義;一是認為失敗證明了學習的無益,便走上了復古主義。
**施展:**更麻煩的是,當瞭解到西方也有自己的難題甚至發生危機的時候,或者是在自己取得某些成果從而改變了與西方的力量對比時,各種形式的反西方主義、傳統主義等等又成為潮流。民族意識發展過程中所依賴的歷史經驗相當不穩定。
**於向東:**這裏還有一些極其微妙的羣體心理現象:失敗會產生自我懷疑,持續的失敗卻可能會引發自我肯定,這是韋伯曾經分析過的一種猶太式心理結構。當民族主義浪潮湧到非歐區域,它往往變成複雜的不穩定的歷史湍流,一個微小的擾動就可能引起宏大的歷史變遷,讓人猝不及防。
施展:由於外在壓力而興起的民族主義案例,大部分都轉化為建制性過程,通過一系列的民族--國家體制表達民族的自我確認。有些案例,積極面相較強,它們通過一些對外戰爭或擴張來表達民族的自我確認;另一些案例,可能就消極、安靜一些,通過文化、貿易等,來表達民族的存在感。這類案例很常見,其目標通常內斂、有限。雖則這些國家有時會面臨很激烈的內部衝突,但最終都可以在特定範圍內的內部政治議程中取得妥協,或遲或早地變成安靜的國際成員。但有少量很特別的案例,吸引了歷史觀察家的大部分眼光。在這類案例中,民族主義不僅僅滿足於民族——國家的建制性過程,它還追求一種浪漫主義目標,即自我超越、自我神化的民族意識。這種民族意識的目標不再是內斂有限的,而是無限的,有極強的擴張性,是大部分現代戰爭的來源。
**於向東:**這種無限目標一定會被構思為某種帝國體制,它要麼替代外部世界,要麼並立於外部世界。這樣浪漫主義的超民族意識的產生,大概有兩個根源,一方面它苦於無法取得安靜的民族——國家那樣內外兩個面相上的政治妥協,另一方面,似乎也根源於它激活了某種古老的心理習慣,即唯我獨尊的絕對存在感。
**施展:**這種絕對存在感會反映在對應的帝國體制中各種差序——等級化結構中。這是傲慢的、瀆神的思想意識,是對諸他者的根本冒犯,它要挑戰、乃至瓦解幾乎所有行之有效的國際秩序。此時的戰爭便不再是國家間戰爭,而成為世界大戰。
**於向東:**這類民族主義最終也都走向了自我瓦解,我們可以更細緻地做一番解析。民族意識在自我與他者的對峙關係的變化中走過自己的歷程,它從“自我否定”的意識逐步走到“自我肯定”的意識,經歷了辯證的歷史過程。這中間的故事豐富多彩。當它達到“自我肯定”的意識狀態時,民族意識就進入岔路口。在大部分案例中,民族的規模不大,稟賦尋常,其內部政治議程往往同國際社會衝突不大,其民族主體性也就直接以現存的國際社會作為自我實現的外部條件,最終將自己轉化為一種文化的而非政治的存在。
在這種情況下,民族主體以“他者”為媒介,獲得對“自我”的確認,自我與他者在意識層面的共生關係使其可以將自己的主體性融為周邊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少數擁有非常稟賦條件的民族,則走上另一個方向,它的“自我肯定”是以對外部世界的“全面否定”為前提的,它拒絕了自我與他者的共生關係,將兩者的差異絕對化,並構造為“敵我”關係。它們的國內政治議程往往與國際社會完全衝突;同時,國際社會又不存在一個前置的、有足夠智慧的協調機制以控制衝突。於是,它們的民族訴求動搖着那些正在運行中的國際規則,引起國際社會的疑慮和全面抵制,卻又無處説理。一種怨恨、一種自尊感被抽空的感覺就扼制住了民族的精神發展,那種追求唯我獨尊的絕對存在感的慾望油然而生。原來是“他者”定義“自我”,現在則變為“自我”定義“他者”,就形成剛才説的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我稱之為民族的“精神危機”,它導向了無限的民族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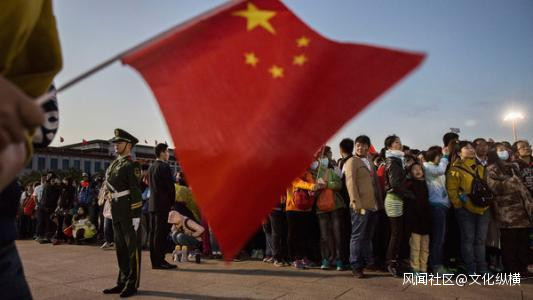
(訂閲《文化縱橫》2020年雜誌,享半年免費暢讀所有已出版雜誌電子版VIP,僅剩最後200席)
**施展:**這種民族意識所面對的國際社會,足夠清晰,你可以時時處處感受到它的存在的確證;但它卻又不足夠智慧,總是無法協調它面臨的各種衝突,最終常常以戰爭解決衝突,結果它就顯得既兇惡又虛偽,反過來強化民族主義的激進化。
**於向東:**民族意識的抽象化能力非常強大,以至於看上去它可以先於歷史而存在。民族主義的激進化往往不用等到那些羞辱、失敗、對抗和血戰的歷史發生或是完全展開,就早早地藉助觀念的力量而直接完成了。當民族走向自我肯定的意識狀態時,如果你的目標仍然是有限的民族主義的,那麼,你可能有明確的具體的敵人,就會有國家間戰爭,勝負皆有可能。當你的目標超越那種內斂、有限的民族主義,那麼你的敵人是你的民族意識構建出來的那個外部世界,此時無論是其他民族還是作為整體的外部世界,都被理解為緻密體般的“他者”,彷彿不可進入不可更改,於是便無法定義具體的敵人,只能全面與“他者”為敵,從而你打算發動的戰爭就會本能地滑向全面戰爭。這種戰爭在本質上是虛無主義的,敵人並不真實存在,它只是被某種觀念純粹地建構出來,並在某種政治圖謀下,推到極致。這種喪失了真實的敵我關係,喪失了真實的“自我”與“他者”關係的民族意識,當然也就自我瓦解,戰爭也就喪失了民族性,變成某個人或小團伙的戰爭。
**施展:**民族意識的自我瓦解,意味着政治動員手段的喪失。這注定是不可能取勝的。從虛幻的“敵我”意識上講,這種戰爭其實也無所謂“勝負”,它只不過是一種“精神現象”而已。
**於向東:**緻密體説到底只不過是觀念塑造的世界,不論它有多少存在的確證,在觀念變化時,也都雲流星散了。緻密體意識本身不斷瓦解民族主義的政治動員功能,從而也就不斷地證明了它所產生以及它由此產生的那些觀念的非歷史性。實際的世界處於不斷的生成過程中,是一個歷史的而非觀念的世界。這是一個隨着工業技術和貿易網絡的出現而出現的新世界,伴隨着技術和貿易的發展而發展,是不斷變化、不斷生成新內容的歷史過程。它有無限的擴張性以吞噬吸納各種各樣的“自我”主體性,將它們納入進程當中,你是這個進程的變量,有時可能還是最重要的變量,但也只是這個進程的一個構成性部分。這是一個多種主體性普遍聯繫的世界,在普遍聯繫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演化出各種規則和網絡,並且不斷地把這些規則積累為經驗。沒有隻存在於觀念中的虛幻的主體性,只有存在於普遍聯繫當中的主體性。民族的精神性存在正是生長於這種普遍聯繫之中。對這個生成中的世界的理解,就打破了那個穩定固化的“他者”的幻像,那個“自我”與“他者”絕對對立的世界消失了,從而那種基於“自我”與“他者”關係的民族意識也就被超越。在這種世界進程中,民族的自我認識就恢復了它的歷史主體性,它不是在對峙關係中確定自我的觀念,而是在世界的生成過程中實現民族的主體性。它把世界理解為民族的自我實現,把民族理解為世界的普遍聯繫。
**施展:**這樣一種對於世界的理解,便完成了從“觀念的世界”到“歷史的世界”的躍遷,這是民族精神發展中最為深刻的轉向,也是克服民族“精神危機”的起點。
**於向東:**所謂“精神危機”,一方面是指“自我肯定”意識發展到對“他者”的全面否定,從而在觀念上消滅了自我實現所憑藉的條件,民族的主體性陷入虛空,混亂和瘋狂開始侵入民族的精神領域;另一方面,它試圖尋找或是創造“民族神話”來克服主體性的非歷史性,各種各樣的歷史“神話敍事”層出不窮,輔之以色彩斑斕的藝術形式,製造出震撼人心的“民族狂歡”。
施展:“精神危機”的這些臨牀症候很容易類型化地加以診斷,從希特勒的《意志的勝利》到其後我們熟悉的種種。這些民族常常已經是世界歷史的生成過程當中的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因素了,但其精神層面對此茫然無知,反倒是仍在觀念性地界定它的外部敵人,並以民族主義作為動員手段,以征服這個包括它自己在內的世界,這當然既無法取勝也無法自圓其説,最終會帶來自己乃至世界的災難。
**於向東:**能夠超越“民族意識”,克服“民族精神危機”的民族,可能有能力進一步推動世界的普遍聯繫,我把它們稱為“世界歷史民族”,只有“世界歷史民族”才能達到“民族精神”階段並完成它的精神歷程。
▍世界歷史民族的歷史經驗
**施展:**到今天能夠數得出來的具有世界歷史民族潛能也就那麼幾個,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德意志民族、法蘭西民族、俄羅斯民族,日本也算一個。今天的中國當然也是,全看我們在精神層面能否從“民族意識”躍升到“民族精神”了。
**於向東:**就“世界的普遍聯繫”而言,有兩種不同的世界主義。一種是共產主義運動和伊斯蘭復興運動。這種世界主義從“世界的普遍聯繫”出發,有一個關於未來世界的詳細構造,以觀念形態先於歷史存在,隨後的歷史運動只是用來印證實現這個觀念。這種世界主義從一開始就排斥民族主體性,訴諸於人的本質要求。這種方案不存在民族主義的空間,是反民族主義的,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內。另一種世界主義,可以叫做歷史性的世界主義,在這種世界主義眼中,世界每天都是新的,都是在創造中,它沒有允諾一個未來世界的框架,它也沒有關於這個未來世界構造的知識,而是認為任何歷史主體的經驗都構成這個生成中的世界的組成部分,它的全部知識都只是藴含在生成的歷史經驗中。它排斥脱離歷史經驗的觀念規劃,它既不認為世界是可以規劃的,也不認為觀念具有規劃功能。換句話説,觀念只能作為道德戒律,而不能作為歷史的引導。
**施展:**現代世界從古典的普遍帝國時代脱出,實際上形成了三種世界秩序觀,一種是基於民族主義的,另外則分別是你所説的那兩種世界主義。民族主義擬製出“民族”實體,作為個體效忠的對象,任何具體的政治活動都要以此先驗實體為前提來獲取正當性。共產主義則構造出一個先驗的具有普遍性的歷史目的,將其視為政治活動的正當性標準。這兩種秩序觀雖則一個特殊主義一個普遍主義,但共享着政治上的先驗論,其政治觀念都內在地包含着某種緻密體觀念。你説的那種歷史性的世界主義,來自清教的倫理觀念。我們此前都談到過清教倫理的政治後果。清教的命運前定論裏面包含了兩個內容,一是人類理性的脆弱,另一是對上帝全知全能的絕對意志的信奉。這兩個內容都意味着,人類依憑理性構造或發現的、連上帝的絕對意志都無法對其有所改變的先驗緻密體——無論是所謂的超越於個體之上的“民族”還是所謂的終極歷史目的——都是根本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個個謹秉神意的道德主體,他們為了實踐上帝所加於自己的道德責任,自我立法、自我治理。國家被視作純粹的工具。作為道德主體的個人在無盡的互動中形成了動態演化的規則框架,國家的功能只在於維護這個規則框架的有效性。規則框架和國家本身,並不具備獨立於個體面向上帝的道德責任之外的意義。這樣,清教世界觀也就放棄了在世俗層面上對實質正義的追求,實質正義只存在於上帝對於個體的前定恩典,世俗層面只應追求一種形式正義。而那種緻密體式的秩序觀,恰是要追求世俗層面的實質正義,這也是當下國人在討論國際問題時往往不自覺地帶入的觀念前提,需要破除。
**於向東:**清教歷史觀和世界觀不是很容易理解,它認為諸主體性,個人的或民族的,相互關聯的實踐活動構成歷史,而那些作為神義論的諸主體的命運或本質,與這個歷史並無關係。前者直接呈現為歷史本身,不會也不可能被後者構建出來作為神義論的明證。形式性的公正、正義以及諸如此類,只在諸主體的相互聯繫的實踐活動中存在,並且也只是隨着這個實踐歷史的發展而不斷地湧現。任何一個主體既沒有義務也沒有可能在這個普遍聯繫的世界中提供實質道德的源泉。世界歷史不是某個主體性的,而是主體間性的。在主體間性中,沒有一個“他者”可以當然地被譴責,也沒有一個“自我”可以自誇自憐,想要獲得正義,只有參與到主體間的互動實踐當中。不參與,沒有正義;不締約,沒有公正;不交易,沒有利益。
我提過一個例子,冷戰時期,美國在與蘇聯的武裝對峙的情況下,逐步積累了全球秩序的知識、人才和經驗,甚至它的全球意識也是在“冷戰”的你來我往的交鋒中漸漸生長的,其中,各種各樣的算計、失誤、出醜露乖不計其數。所謂“美國治下的和平”是作為一個歷史過程被認識的,而不是作為一個規劃被落實的。考察大英帝國史,它的擴張、停滯、收縮及至消亡,整個過程沒有那種“自我”與“他者”“二分對立”的敵我界定,它承認各種民族部落的歷史主體性,它從這些歷史主體性的普遍聯繫中謀取利益,雖然在漫長的過程中戰爭、殺戮、背信棄義等等層出不窮,但細細分析就會發現,它的決策前提總歸還是回到那種“斤斤計算”的貿易商立場。它絕對不會像歐陸國家那樣,為浪漫主義的使命或追求付賬,除非這有更多的未來利益可以算到。二戰之後,雖然戀戀不捨,但它還是發覺帝國統治已無利可圖,勉強維持得不償失,在經歷了外人眼中那些丟人、羞恥、狼狽和無可奈何等等後,它收縮為一個普通國家,但依然還是全球普遍聯繫的樞紐之一,並以此證明民族的存在。
**施展:**對英國人來講,抽象觀念上民族的主體性從來不能凌駕於多樣化的歷史主體性之上。這些多樣化的主體性的歷史經驗才構成真實的世界,只有在真實的世界裏人才能兑現人的主體性。所以英國很少見那種浪漫派的思想家,也少見那種蠱惑人心的“人間神”。如果我們注意一下英美的議會辯論的話,會看到其辯論內容往往是具體化在一些瑣碎的物質過程當中,斤斤計較地爭來爭去,而少見基於宏大道德敍事的爭執。正是這種瑣碎的論辯,在反映着真實的物質世界的動態演化過程。這樣一種政治體,其憲政架構預設着一種過程性的、多孔化的政治觀,或者説,它將自己視作世界秩序的某種全息縮影,政治體的內部與外部是貫通的;而不是像民族國家那樣先驗(緻密)實體式的政治觀,將自身對立於外部。
**於向東:**人們常常把如今的世界秩序稱為“美英主導的世界”,倒也不失恰切。如果把“美英主導”理解為經驗世界的歷史,那麼它的經驗主義特徵,是我們必須時時注意的。
**施展:**沒錯。美英的過程性政治觀,其議會辯論中各種利益都在充分地表達自己,各種各樣的院外遊説集團也在施展各自絕技。這些院外集團不僅是受僱於本國的利益團體,同樣也受僱於外國的利益團體。這在緻密體式的政治觀看來,無法想象!但是在美英的政治觀中,國家利益是無法預先定義的,它只能在各種利益團體互相博弈的過程當中逐漸地浮現出來。受僱於本國、外國的各種各樣院外集團的遊説努力,都會反映在議會辯論過程當中,從而使得美國的政策形成過程,可以內在地包涉其他國家的利益,其內政與外政(如果可以這麼説的話)的契合度,遠高於那些緻密體式理解政治的國家。前者更容易構建並操作一個超國家的國際社會網絡架構,使後者深陷其中,有力使不出,受到柔性節制。每當後者想要朝向某個方向用力,以擺脱節制,則前者所支撐的網絡架構自然地就會變形以應對後者的努力,因為該網絡架構的運作與生成,也內在地包含着後者活動的影響。後者的民族意識被這種國際網絡纏繞,被以柔克剛,便試圖採取終極手段——戰爭,從中掙脱出來。
**於向東:**這樣一種視野下,再來看看那些經歷曲折的國家的戰爭史會很有意思,它們都曾處在向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挑戰的地位,到頭來,發覺自己最終是在向整個世界作戰,無一例外都失敗了。德國是最典型的案例。從拿破崙戰爭開始,到1871年第二帝國建立,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經歷了一個異常成功炫目的民族主義成長曆史。19世紀末,作為歐陸頭號強國,德國實際上已成功地終結了束縛德意志民族主義的大陸列強體制,隨後它就陷入民族的精神危機,它一方面不再滿足於俾斯麥設定的那些限於歐陸,特別是中歐地區的有限目標;另一方面,德國面對自己出乎意料的巨大物質生產能力,產生了激情澎湃的民族衝動。它借用德國思想當中各種觀念和修辭手段構思了一幅雜亂無章的新世界圖景,從中推定出所謂“民族的敵人”。
**施展:**俾斯麥執政時倒是一直恪守民族主義目標,但我想如果他在世紀之交仍然領導第二帝國,面對德國的巨大物質能力——這至少出乎他當年的預期,他是否仍然執行審慎的帝國政策?畢竟,人們似乎很容易被那些雄壯的艦隊、威武的陣列所激動。
**於向東:**這樣的羣體激情來得快,去得也快。當激情消退後,所有那些雄壯威武都只不過是民族的負擔而已。
**施展:**也有很多歷史研究者認為,本來英法美有可能預防兩次世界大戰,避免後來的災難……
**於向東:**這是膚淺的見識。德國要挑戰的那個世界,是由各種各樣歷史經驗構成、並且還在不斷生成的世界。這個世界無法理解更無法預測德國那種浪漫主義世界觀支配下的挑戰。它沒有這種事先的知識,它甚至排斥這種類型的知識,它無法信任這種預防措施所依據的那套推演模式。它只能被動地在挑戰來臨時,緩慢而又堅定地漸次進行抵抗,你所説的那個柔性網絡的以柔克剛,在這裏也能看到,只不過其應對節奏不像戰爭進展的節奏那麼快。以至於我們看到,在兩次世界大戰的前期,英國人都是狼狽不堪;但是作為普遍聯繫的世界,這個抵抗早早晚晚會變成世界範圍內的抵抗,重要的是,它把德意志民族也包括在抵抗之中。因為,德國物質力量的強大,在經濟上,是在這個普遍聯繫的世界中運行的。而德國民族主義的政治動員力附着於它的物質生產體系,當這個生產體系被隔絕時,作為政治動員的民族主義就開始瓦解了。這個過程相當快,也就三四年時間,挑戰就衰竭了,與歐洲歷史上冗長的國家間戰爭不能比。
**施展:**第一次《大觀》會議討論科耶夫時,就注意到他説無論8000萬德國人多麼優秀,也無法支撐希特勒允諾給他們的那個千年帝國,很快戰爭就從德意志帝國事務變成希特勒的個人事務,他臨死時説德國人背叛了他,其實一點沒錯。
於向東:****民族主義的動員魔力在於明確的“敵我意識”,當大戰一開,卻發現你無法固定住你的“敵人”,這倒不是説人人都是你的敵人——這本來也是題中之義,而是説此時你和你的民族分離了,你的民族也是你的敵人。希特勒的抱怨固然無賴,倒是揭示了這層真實的關係。日本軍國主義者在1945年叫嚷“一億玉碎”也是如此。歸結起來説,德國的這類挑戰是不可能取勝的,但也不可能預防,除非德意志民族克服了自身的精神危機。
**施展:**也就是説,德國必須認識到它所處的那個世界與德意志民族的精神追求的內在一致性,必須認識到一個德意志人共同參與創造的世界才是德意志精神的實現。
**於向東:**二戰後,德國人在阿登納以及一大批覺醒的歐洲政治家的引導下,徹底放棄了“德國人的歐洲”這個不切實際的民族追求,轉而致力於“歐洲的德國”的創建,即推動歐洲統一進程,完成德國與歐洲的精神與政治統一。當然這是在一系列可遇不可求的歷史境遇中完成的。當冷戰結束,德國統一時,我們在政治上看到科爾和他的同胞們如何精彩地證明了他們的智慧;等到歐債危機爆發之後,人們才發現,德國人正在完成遠比德國統一還要偉大的歷史進步,即一個嶄新的充滿世界主義精神的“德國的歐洲”正在形成中。德意志民族曾經有過的任何輝煌都不能與之相比,此時的歐洲對於這樣一個德國,不再是懼怕,而是信任。這是一個典型的“世界歷史民族”的歷史經驗。
**施展:**從這裏面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説,具有全局性影響力的大國的國家利益,無法通過民族主義方案而必須通過普遍主義方案來獲得。此前討論過民族主義與國家規模之間的關係,便是此意,德意志於此給了一個很好的例證。
**於向東:**如此説來,俾斯麥前期的德國,以民族主義的方案來統合國家迅速崛起,這條路大致還走得通,是因為當時的德國還只算箇中等規模國家。但是到後俾斯麥時代,德國已崛起為全局性大國,仍然堅持民族主義,便兩次將自己帶到幾欲亡國之境,從根本上違背民族利益原則。
**施展:**德國也有超越自身的宏闊的精神結構。康德、黑格爾的哲學都達到了這個高度,像我們現在用的“民族意識”、“民族精神”的概念也還是從黑格爾哲學中引申出來的。問題是其偉大的哲學只在觀念層面打轉,對實踐層面的影響很有限,而且往往是通過扭曲病態的方式來顯示,偉大的觀念不能與實踐形成共振,反倒是庸俗的觀念撩撥着民眾的心絃,瘋狂地引導着實踐。
**於向東:**這也應了韋伯的憂慮,彼時的德意志尚不是個政治民族,它沒有能力識別自身的長遠利益,無法將現實的物質過程——也就是德意志的物質強大——上升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秩序安排,無法體會到自身的世界歷史民族的意義。
**施展:**你説得很對,直到二戰,德意志都還是在“敵對意識”下來看待自身與世界的關係,世界政治在它看來就是緻密體之間的命運對抗。這種自我意識的表達是很容易激起感受着屈辱、身處困境的民眾的熱情的,但它卻將這個民族帶入更深的災難。
**於向東:**任何經濟的微觀基礎都是一個個的企業和個人的活動。這些活動本身不具有國別屬性,基於並且越來越基於世界的普遍聯繫。在實際的運行過程中,沒有一個國家是孤立出來獨自運行的,蘇東集團曾經做過這種嘗試,我們在改革開放前也曾做過這種嘗試,後果很糟糕。現實當中的世界運行,每個國家實際上都是一種多孔化結構,國和國之間有着深刻的相互依賴、相互穿透的關係。從商業史經驗上説,國家層面和全球層面的法律——經濟架構,有可通約性。單個國家的經濟政策,自然會有各種自利的經濟民族主義行為,但只要它立基於這種可通約性,則其自利行為都有外部溢出效應。這種微觀活動形成的經驗具有普遍主義傾向,傑出的政治人物,就在於能夠找到表達這種普遍性的宣傳方式,以此形成有實踐基礎的對民眾的動員。
**施展:**緻密體式的觀念,強行賦予微觀的經濟活動國別或民族屬性,無視基於普遍聯繫所帶來的潛在利益,最終在國民經濟的競賽中敗北。二戰前德國所謂的“雅利安物理學”,便是荒唐一例。
**於向東:**緻密體式的觀念不是發現出來的,而是發明出來的。它是野心家用來操控民眾的手段。
施展:“生成中的世界”這樣一種觀念,在精神氣質上與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普通法傳統有很大相似性,英美相繼成為世界霸主也不是純屬偶然。對於經驗的歷史,普通法傳統是最為有利的一種法權結構。普通法本身是司法主導的,它的性格在日積月累的各種各樣案例中形成。每一個案例都是微觀的、個案性的,它會在其中識別出具有普遍性的原則,進而將這些微觀層面的經驗在歷史積累中匯聚成一個宏觀的秩序。在普通法眼中,世界天然就是多孔化的,在不斷變化生成的過程中的。對英美而言,國家利益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具體的微觀利益匯聚而成;微觀利益引導着個體國民的好惡,國民好惡引導國家政策;隨着它逐漸走上世界霸主的地位,民族的理想也就在微觀行為的引領下轉向了普遍主義。其“民族意識”就這樣漸次地發展為“民族精神”。韋伯所豔羨的英國國民經受的政治教育,也是在這樣一種不斷累積的政法過程中完成的。英美民族的引領者的地位來自於一系列無法複製的稟賦條件,這些條件使他們可以從容自若,讓歷史先於觀念,讓物質引導精神。而其他的那些世界歷史民族,作為挑戰者,都是備嘗挑戰失敗的苦痛經驗後,才完成民族精神的世界主義轉向。對它們而言,需要有一種精神上的轉型,超越緻密體式的民族觀念,形成對真實的“生成中的世界”的認識,以此來引導物質。

(訂閲《文化縱橫》2020年雜誌,享半年免費暢讀所有已出版雜誌電子版VIP,僅剩最後200席)
▍近代化與現代化:民族的精神轉向
**於向東:**在和劉蘇里的談話中,我曾提到19世紀我們睜眼看世界,那個世界恰好是維也納和會之後確定的歐洲大陸列強體制。那時,還無法清楚地區分歐陸列強體制和英美體系的區別。況且,就其對中國的逼迫性交往而言,二者看上去也差不多。中國的民族意識及其政治形態——民族主義——在這個時期發展起來,並匯聚成民族的近代化目標:成為列強之一。這是相對於19世紀中國人感知到的那個世界的民族意識。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基本穩定下來,中國那時的危機是內部的,外部並不嚴重。走向近代化目標的努力,雖然差強人意,也還碩果累累。但19世紀末葉,日本在近代化競賽中取得領先,隨即侵害中國,大大地破壞了中國與外部的關係,也破壞了正在穩定形成中的關於外部世界的知識積累,很快,日本侵害帶來的痛感就擴散為我們關於外部世界的知識重組。
**施展:**列強秩序是列強主導的集體安全體系和國際法體系,它並不是純粹的弱肉強食,其中包含指向正義秩序的國際規則。以丁韙良所譯的《萬國公法》為中介,晚清的中國人就是如此理解國際秩序的,並依此而定義了“自強”的目標。這個時候中國人還是以平和、雍容的心態對待列強秩序的,他們試圖將它與傳統帝國秩序相調和,並通過自強而有機會參與到列強秩序的構造當中去。但日本的侵害,破壞了這種平和雍容的心態。一種怨恨的情緒蔓延開來。
**於向東:**歐陸列強體制本來就是作為區域內部衝突的避險機制,是很脆弱的。波蘭尼在《大轉型》中曾對此做過細緻分析。由於國際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這個秩序在20世紀初崩潰,引發了一戰。一戰後的巴黎和會讓中國對列強秩序的公正性產生了強烈質疑。作為對列強秩序所代表的西方世界的整體否定性認識,各種激進主義和普遍主義的政治主張在中國流行起來,代替了自19世紀中葉以來的關於西方的知識積累。
**施展:**其實,這個知識重組,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因素扭曲了我們相對於外部世界的民族意識。對非工業國家來講,列寧主義表達的那種普遍主義本來很難是民族主義的對手。但恰恰中國的民族主義在政治上處於瓦解狀態,列寧主義才有可能勝出。
**於向東:**列寧主義對當時普羅大眾並沒有什麼吸引力,但從這個觀念推演出來的政治功能設計,卻有非凡的社會民眾動員效能,填補了民族主義動員功能的缺失。列寧主義主要是作為政治功能,而非觀念體系應用於中國。儘管它在觀念上排斥民族主義,卻不期然經由毛澤東的政治實踐,成為民族主義外設的政治動員功能,而與中國的民族主義話語攜手共進,並幫助民族主義政治走出困境。但列寧主義和民族主義並存,使國家目標產生內在緊張,國家利益難以確定。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採用了巧妙的修辭策略,調適二者的緊張關係。
**施展:**列寧主義的成功,統一了民族-國家,使中國的民族意識重新回到一個統一的實體上,使民族主義的發展重新成為可能,這恰恰是鄧小平時代的國家轉向的一個條件。民族主義的失敗,為列寧主義的成功創造了條件;列寧主義的成功,為民族主義的復甦提供了基礎。
**於向東:**無論如何,列寧主義的消退,為民族意識的發展騰出空間,於是近代化目標又回到中國政治生活的中心,其中的接續關係,還使一些學者做出努力,試圖把這段歷史放到一個一致的民族精神歷程敍事框架當中。
**施展:**這是有疑問的,因為民族主義話語、近代化目標的迴歸,是建立在列寧主義政治動員功能基礎上的。這種關係下,民族主義目標的成功無法完全用民族主義來解釋,這裏仍然有某種內在緊張。當時就有爭論。
**於向東:**這都是小浪花,很快被更大的浪潮淹沒了。從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經濟起飛,民族主義的政治動員功能逐漸恢復,民族復興成為主流政治語言。新的話語一方面在內部與列寧主義政治動員功能發生緊張關係,並對後者形成壓制;另一方面,在外部為開放的經濟系統提供了正當性。民族主義政治語彙不斷從經濟成功中得到正向激勵,迅速成為主要的政治意識形態,舊的政治動員體制收縮為工具性變量,從民族的目標方程中消失了。國家目標成為純粹的民族意識的產物。
**施展:**也就是説,民族主義在離開了很長一段時間以後,又回到了民族精神發展的原有軌道。
**於向東:**在這個軌道上,民族主義獲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似乎這種成功來得太快,它還未及確認它的目標是否已實現,也未及把自己的政治語彙合理化,它就喪失了目標確定性。而目標確定性正是民族意識的主要政治功能。
**施展:**或者用我們在前面的説法,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還只是箇中等規模國家,民族主義在此時有凝聚人心形成動員力的作用,它帶來了中國的蓬勃生氣。但是到21世紀初期,中國已成長為全局性大國了,此時它便無法在民族主義下確認國家目標和國家利益。
**於向東:**我在《大觀》武漢會議上談到民族的“近代化目標”與“現代化目標”的區別。這實際上對應着前面我們講的“民族意識”和“民族精神”兩個不同的階段。“近代化”指的是與“列強”這個“他者”相對而生的民族的自我意識,它是以對對方的肯定,即成為列強之一作為民族的“自我”實現,由此確定“近代化目標”。而“現代化”則意味着民族“自我”處於世界歷史的內部變動過程之中,並且也只能在這個過程之中達成民族的“自我實現”。它把變動中的世界視為民族精神的實現條件,從中確定把“世界歷史民族”作為民族的“現代化目標”。這兩個目標之間存在緊張的關係。
**施展:**一戰結束了列強體制,巴黎和會開啓了一種普遍主義的國際治理。在持續了幾百年的全球貿易之後,一種新的世界政治開始出現了,這肯定會是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你講的這個“現代化目標”,就對應着相應的歷史意識。新的秩序,新的規則,新的利益,從這個不斷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湧現出來,那種“自我”與“他者”的對立關係,需要逐漸被二者的普遍聯繫所替代,如何從這個普遍聯繫中實現民族自我,是民族的現代化所面臨的挑戰,也是它要達成的目標。
於向東:“近代化”從“民族意識”產生,“現代化”從“民族精神”產生。但“近代化”的成功,特別是近年的持續成功,強化了緻密體思維,變成一道“南牆”阻擋“民族精神”的發展。
**施展:****“近代化目標”與“現代化目標”的衝突,這是一場“精神危機”,甚至可以説是一種“精神分裂”,中國今天所面臨的很多內政外交的困境都與此相關。**今天,沒有人否認中國已然強大,但我們並沒感受到我們想象中的地位和榮耀,相反,我們不停地感受到普遍主義世界秩序對我們的約束,而這被解讀為列強秩序下的羞辱。這就進入一個不斷地自我證成的邏輯:越是追求列強意義上的強大感,越是獲得挫折感;於是追求進一步的強大感,又感覺陷入更深的圍堵中,惡性循環,彷彿周邊世界充滿惡意,彷彿我們不是龐然大物,而是待宰羔羊。這意味着最強的國家理由,它幾乎可以正當化任何內政和外交上的行為,卻不僅帶來外部的反彈,也帶來內部深刻的不滿。惡性循環便進一步由外而內地彌散開來。
**於向東:**中國的經濟成功建立在經濟全球化基礎上,它不但依賴全球貿易網絡,而且事實上也重新塑造了這個網絡的大模樣。這個形塑的過程還在繼續,我們用“全球貿易雙循環結構”來刻畫這個過程。這也相當清楚地印證了我們常説的一句話“未來世界秩序是中國加入這個秩序的過程所定義的”。很多貿易結構,中國不是創始者,卻是定義者。這種“世界歷史民族”的地位和功能,還遠遠沒有在民族的精神層面得到反映,我們還停留在“自我”與“他者”的“二分對立”的世界圖景和歷史記憶中。這當然是民族的“精神危機”。所以,必須實現民族的精神轉向,將民族的目標確定性建立在“世界歷史民族”的意識覺醒的過程之中,並以這個全新的“現代化”觀念完成民族的精神統一。
**施展:**中國經濟崛起對世界秩序的衝擊以及對中國自身的改造,帶來了終結列強秩序的可能性,我們在第四講當中提到的傳統現代化範式的終結以及全球"中心-外圍”體系的終結,或許預示着生成中的世界正漸漸進入高潮。
**於向東:**這籲求着我們精神格局的轉型,要從“民族意識”躍遷到“民族精神”,這個過程中,中國與整個世界歷史進程逐漸融合在一起。當我們達到這個轉變的時候,就像今天的歐洲人一樣,我們就徹底消除了民族精神分裂和精神內戰的所有可能性,從而成為一個精神飽滿的民族,一個自我實現了的民族。在這樣一個過程中,也只有在這樣一個過程中,這個民族內部的自我立法和自我治理,才有可能最終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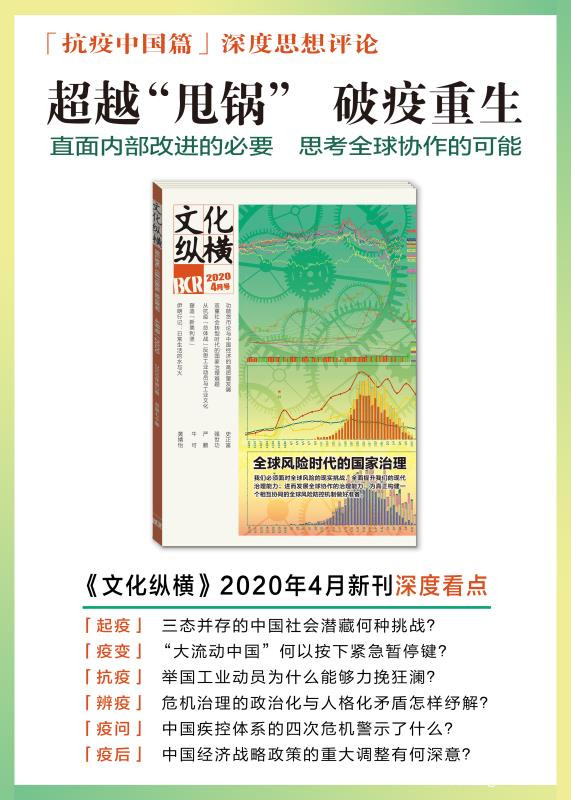
本文原發表於《文化縱橫》2014年2月********刊,原題為《從“民族意識”到“民族精神”——外交哲學對談之六》,****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