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分鐘就可封神,她絕對是最被低估的華語女演員!_風聞
影探-影探官方账号-美日韩剧资深鉴赏员,电影专业老司机2020-05-21 14:14
作者| booka
來源| 影探
從去年開始,我就在等一部國產電影。
光看製作團隊,它就可以秒殺眾多國產大片。
主演郝蕾,從《圓明園》(沒寫錯,你懂的)一路走來,她是最被忽略、最被低估的華語女演員。
“配角天后”金燕玲,4屆金像獎、2屆金馬獎最佳女配角得主;
監製廖慶松(代表作《風櫃來的人》《刺客聶隱娘》《踏血尋梅》),與侯孝賢合作四十多年,有“台灣新電影保姆”之稱;
監製市山尚三(出品過《山河故人》《站台》《海上花》),是賈樟柯、侯孝賢的御用合作伙伴;
攝影師包軒鳴(Jake Pollock),近幾年最有風格的攝影師,拍攝過《風中有朵雨做的雲》《七月與安生》《艋舺》…
導演楊荔鈉,中國獨立電影女導演,曾在賈樟柯《站台》裏飾演鍾萍一角。
《春潮》部分主創在上海國際電影節
它串聯起了第六代電影、台灣電影新浪潮,彙集了大陸、香港、台灣三地最優秀的製作陣容。
這樣的片子,只需要二個字:必看。
觀影的過程中,它就像一個漩渦,把人狂吸進去、筋骨不留。
讓你忽略了東北語境下金燕玲的港台腔,不再追究敍事的碎片感,不再考慮角色行為動機的合理性。
但,當聽到**“我來例假的時候…”這句重新配音的台詞**的時候,所有人都會立馬被打醒。
例假?月經?這個粗糲的改動嫌疑,總是帶有一絲絲獨特的荒誕感。
《春潮》
Spring Tide
2020.5.17
01 三個女人一台戲
>>>無聲自毀的我,憤怒咒罵的她
“童年時期受到父母強烈攻擊的人,終其一生都將陷入沮喪和不斷掙扎中。”
郭建波(郝蕾 飾)就是一位飽受原生家庭之殤的受害者。
她是一名報社記者,懷着不合時宜的新聞理想,在江河日下的紙媒裏固守着職業操守。
即便昔日搭檔升為了主編,傲氣冷漠的她也沒有一絲妥協。
她未婚生育、大齡單身,在母親家、集體宿舍、音樂家男友之間來回遷徙。
居無定所、一事無成、吊兒郎當的形象是她給母親的報復。

母親紀明嵐(金燕玲 飾)是一位社區幹部。
集體感榮譽爆棚的她,為了給社區爭成績,帶着合唱隊去自己家裏排練。
深入宣傳第一線,她帶着媒體進社區,表現社區羣眾和諧美滿的好日子。
閨蜜自殺,她一邊憤怒哀傷,一邊擔心這是負面新聞,有損於社區形象。
在親情、婚姻上的受挫,她在信仰上尋找了依靠。
無論是領袖,還是菩薩,都是她傾訴的窗口。
她整天信佛吃素,本應該仁慈心腸。
對外人一派和善,對自家人卻換了一張嘴臉。
看到在家吸煙的女兒,她會叱責,“有毛病”。
當看到閨蜜自殺的新聞登上報,她二話不説就質問女兒。
“這新聞是不是你爆料的?是不是你寫的?”
一家人圍着飯桌吃飯,本來和和氣氣,説翻臉就翻臉。
“你們都是白眼狼。”
“我老了還要看你的臉色嗎?我不欠你們姓郭的。”

面對母親的咄咄逼人、憤怒咒罵,女兒總是一言不發、冷漠無聲。
如果實在忍受不了,她就會走向廚房,打開水龍頭。
讓噪音淹沒了咒罵,遮擋一切聲響。

她內心裏清楚,質問和反擊只會讓矛盾加劇,讓母親更加肆無忌憚地賣慘和抱怨。
她乾脆把自己放在一個真空罩裏,眼瞅着母親在裂眥嚼齒。
母親越憤怒,她越麻木、越無感。

正面不剛,暗地裏互相較真。
給屋子放水、把煙蒂戳到蘿蔔乾上,女兒的這些陰招屢試不爽。

有一次,她還特地找一個相親對象,當着母親的面,自我羞辱。
母親客氣地介紹,“家裏就一個女兒,一個孫女,沒有男人。”
她就當場給男方發短信,“男人都死亡了。”
母親説,“男的在小孩剛出世就出車禍去世了。”
她就回復,“我也不知道孩子他爸爸是誰。”
母親在那滔滔不絕,十分殷勤。
她就説,“你對面的兩個女人只有一個乳房,你猜在誰的身上。”
這樣的舉動,直接把男方給嚇跑了。
這種自我羞辱,不是鬥氣,這是一種自毀。
任何人都重視自己的形象,更何況是一個未出嫁的女人。
她讓自己塑造成一個浪蕩女,對自己沒有任何好處。
之所以這麼做,就是報復母親多年來的咒罵。
她想讓別人知道,這個家多麼噁心、多麼病態。
一邊是無聲自毀的媽媽,一邊是憤怒咒罵的姥姥。
中間就是夾縫裏的孫女郭婉婷。
婉婷不是女人關係緩和的助推器,而是女人戰爭的工具。
姥姥一直給她灌輸仇母思想。
“這個世界上真的沒有什麼人能夠相信,但是你要知道,姥姥是愛你的。”
“媽媽不疼你,她曾經要殺死你。”
早熟的她,用機靈的話題來試圖調節家庭的關係。
她可以沒大沒小地戲謔姥姥,
“你總跟外人這麼説你丈夫好嗎?你翻臉比孫悟空還快,就你這樣的人還有人喜歡你。”
但她明白,媽媽與姥姥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
每每當姥姥發火的時候,她會善意地提醒媽媽,
“你該走了。你走了,她就好了。”
長此以往,孫女將是這個家庭的下一個受害者。
>>>缺席的男人
《春潮》和其他的女性電影一樣,有意去營造一個男性功能缺席的失語語境。
在郭建波與紀明嵐這對母女的生活裏,一個過世的男人總是陰魂不散。
他就是女兒的父親,母親的前夫。
殘缺的照片是父親唯一的畫面
在母親的口中,他是一個臭流氓。
喜歡在戲院露自己的身體,喜歡在菜市場隨便摸人家女人的屁股 。
又一次,還把一個小姐帶回家搞,因為錢給少了,還被人家報警強姦。
不過,在女兒的心中,爸爸是一個性格好、脾氣好的人。
她總是記得,小時候去動物園看長頸鹿。
爸爸總會給她買麪包、汽水,讓她在動物園待一整天。
關於“父親”這個形象的認知偏差,讓這對母女變成了敵人。
母親把因他而遭受的苦,全部反彈給了女兒。
從小到大,弱勢的女兒成為了被報復的對象。
缺少親情關懷的女兒努力保護父親的完美形象,彌補殘缺的母愛。
久而久之,她變得麻木了。
她不會大哭大叫,不會表達內心的情感。
正如同赫塔米勒説的那句話,
“我幾乎不哭。比起那些淚水漣漣的人,我不是更堅強,而是更軟弱。他們敢於哭出來。一旦人只剩下皮和骨頭,表達感情就是一種勇氣。”
她會擁抱仙人掌,用刺痛和流血來感受自我的存在。


用仙人掌扎手的場景,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藍白紅三部曲之藍》裏朱麗葉·比諾什的表演**。
她在電影裏就用自己的手在石牆上滑出一道道的血痕。


《藍》
>>>長達7分鐘的獨白
至始至終,《春潮》沒有歇斯底里的爆發戲。
但是,它在剋制隱忍的氛圍之下,呈現出一片暗潮洶湧之勢。
這段長達7分鐘的對白就是一個發泄式的出口。
“你安靜了,這個世界就安靜了,就讓我們這樣安靜地待一會吧。”
“如果你醒來一定會罵我,用骯髒惡毒的語言來咒罵我。”
“你總是説我會遭報應。哪有媽媽這樣對自己女兒説的?你期待我遭到什麼樣的報應?貧窮孤獨、孤兒寡母、疾病纏身…差不多都實現了,還有什麼都説出來吧。”
這是女兒對母親的第一次傾訴。
這是讓人心疼的一次吶喊,一次積攢多年的情緒。
40年的咒罵,40年的順從,40年的不得安寧。母親變成了一個貶義詞,變成了仇恨的代名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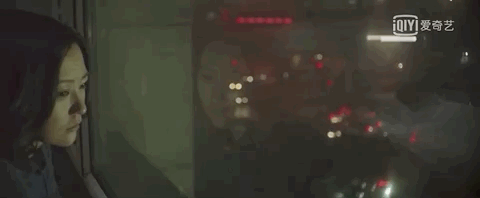
“還有我的父親,一個死去的人都要遭受你的咒罵。
如果不幸,我更同情他。
他是你所有生活的謀殺犯,所有的錯誤責任你都推給他。你就那麼清白無辜嗎?
寫檢舉信,去領導家告狀。
每一個咒罵,我就憎恨你一次,摧毀了母親在我心中的形象。”
從這段對白裏,我們知道了母親曾對父親做過的事情,知道了女兒對母親憤怒的原因。
這段7分鐘的獨角戲,如同海嘯來臨前的一次暗湧。
值得注意的是,女兒沒有直接在媽媽旁邊傾訴,而是對着窗外傾倒苦水。
這就給我們一個多樣解讀的角度。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女兒面對母親的一次傾訴。
你也可以理解成,這是女兒的內心戲,它是女兒在內心排演過一遍又一遍的獨白,現實中根本沒有發生。
就像是郝蕾對這段戲的理解。
“我覺得不能直接對着媽媽説出來。這段話有一種空間感。
這可能是郭建波日記的內容,也可能説了無數遍,如果她青春期的時候能説給媽媽聽,有對話的語境,那最後郭建波可能不會一無所有。”
02 歷史的幽靈
《春潮》一方面側重在描寫備受原生家庭傷害的母女關係;
另一方面,保留了現實主義的視角,串起了性侵、暴力拆遷、移民、記者困境等社會話題。
值得留心的是,除了當下的社會話題之外,它在文本深處還隱藏了一個歷史的幽靈。
雖然沒有明説,但是在細節之處還是有所體現的。
郭建波去拜訪同學的父親,他剛好是一位小有名氣的作家。
在兩人的交流之中,我們就能品味出那段動盪不安的時空裏的故事。
“我想上吊,我把尼龍繩撿回來,搓成4米的繩子,藏在牀板底下。”
“我在工作台的鋪板上找來兩根銅線,插入電插座裏,橫下心的我用手捏住兩根銅線,啪的一聲,手背麻了一下根本沒有被擊倒,周圍一片漆黑,是電閘跳了。面對死神,我還是站在原地。”
不用直白的挑明,觀眾就可以體會出這段故事的背景。
母親與父親的婚姻,母親對父親的檢舉,也是那段特定時期發生的故事。
從這個角度來看,《春潮》是在給這個原生家庭找一個原因。
這就是第五代、第六代電影里老生常談的命題——
特殊時代的後遺症。
03 私人化的意象夢境
《春潮》是一部充滿多種意象和夢境的電影。
意象是多義的,夢境是私人化的。
導演楊荔鈉在寫給《春潮》的信裏也提到,
“你身上也有夢痕,雖然留下的不多,都是日夜纏綿的果實。現實和夢境我更喜歡在夜裏遨遊,夢境比現實更有穿透力,我靠夢活。有一天夢沒了,我的肉身也離死亡不遠了。”
在夢中,女兒發現一羣穿着防疫服的醫生敲開了家門。
他們尋找一番之後,在桌子底下發現了一隻被捆着蹄子的黑山羊。
慘叫的叫聲如同哭泣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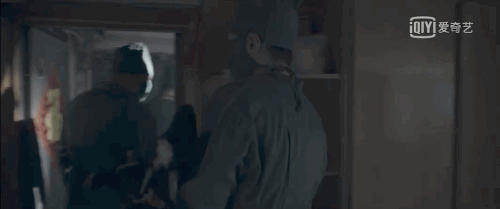
醫生與她進行短暫的眼神交流之後,抱着山羊,走出家門。
此時,這隻山羊瞬間變成了母親。
母親努力掙扎着,試圖擺脱醫生的控制,而她在一旁無動於衷。

在某些情境下,黑山羊可以指惡魔。
或許,在女兒心中,母親就是一個惡魔,這剛好是母女疏離的體現。
此外,醫生的形象,也與母親昏迷住院的場景相契合。
紅衣女人,這個意象出現過兩次。
一次是,在公交車上,她朝着女兒招手;另一次是,在傾倒骨灰時候,她在湖裏輕撫秀髮。

在我的理解中,紅衣女人是女兒潛意識裏的另一個自己。
紅色象徵着生命與熱情。
對於飽受原生家庭之殤的女兒,冷色調的自己沒有了熱情,只有與東北寒冷氣候相適應的冰冷和悽清。

談到電影裏的意象,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電影詩意般的結尾。
從屋裏流溢而出的水,如同被賦予了生命,其勢之猛,漫向街頭。
它流過了母親的病房、缺少母親的舞台、流向了女兒的學校…


它匯流山河,引導着女兒走向山間,在河水裏嬉戲。
這春潮是子宮裏的羊水,是一家三代人的牽絆。


流淌在三個女性之間的春潮,沒有團圓和美好,只有切割和決裂。
似乎,原生家庭的深淵,無法找到一個出口。
它沒有和解,只有溝通的不可能。
一個心懷憤怒,另一個只能無聲自滅。
最終,這股超現實的春潮只是鏡中月,水中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