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 很多人痛批“閲讀不自由”, 卻忽略了另一深入骨髓的毛病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0-05-22 18:06
CSSCI核心期刊**《文化縱橫》2020徵訂火熱進行中**
✪ 潘光旦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導讀】**讀書是每個人明理閲世、昇華自我的重要途徑,但這條路並不總是通暢順達。當下的一個典型現象是:一邊是書籍和知識海量增長,一邊是很多人認為讀書不自由。潘光旦先生在1948年寫下這篇文章,認為造成閲讀窄化乃至堵塞的原因有二:一是外部的限制,二是自我的設限。外部限禁的影響自然是明顯的,無庸多説。更嚴重且隱蔽的問題,是自發的好惡或忌諱,惟其是自發,表面看來不像限制,而不成其為限制;惟其不像,所以無人理會;惟其無人理會,問題就更見得嚴重。這主要表現在,人們常常囿於新舊、中西、左右之爭,在不自覺中讓自己陷入自閉自賞的窠臼之中,由於主觀成見的作祟,錯過了更多有價值的知識和有洞見的思想。潘先生認為,這種內發的、自我設定的不自由,其範圍之廣,影響之深,以及解脱之不易,甚至超過了外部限制所帶來的不自由。對於閲讀者來説,來自外部的限制固然莫能奈何,但在紛紛擾擾的思想爭論中,如能打破自我設限的困籠,在自己能主宰的空間裏,超越對立之爭、放寬閲讀視野,更有可能形成獨立而開放的思想空間。
文章選自《潘光旦:守住靈魂的底線(潘光旦選集)》,轉自“學人Scholar”,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思考。
半年多以前,我寫過一篇《救救圖書》的短稿,為坊間行將“還魂”的大批書籍呼籲。呼籲的效果如何,我不得而知。但轉眼一想,即使有些效果,又怎麼樣?當代的人根本沒有讀書的自由,留下書來,也無非束諸高閣,最好也不過為典藏而典藏而已。有人説過,天下的圖書館,十之八九是“藏書樓”,十之一二是“尊經閣”。這話很對,因為在讀書不自由的情況之下,少數人儘管藏,少數人儘管尊,絕大多數的人,包括藏的與尊的人在內,也包括以讀書為業務的青年在內,不感興趣,不來問津。
(潘光旦先生)
▍“禁”與“忌”的學問
不過我們先得把題目的意思弄弄清楚。一兩天以前,和一位朋友閒話,朋友説起,某一個都市經某方攻佔以後,某國的外僑向本國政府報告,説是情形還不錯,不錯就是“對”,那外僑確乎用了一個“對”字,意思是説——這是朋友自己的註腳了——外僑們還可以“自由行動”。我趕快插嘴説,該是行動自由,不是自由行動吧。這位朋友和其它一二參加閒話的人都首肯的笑了。行動自由與自由行動很有幾分不同,我想誰都瞭解,用不着解釋。好比戀愛自由與自由戀愛也有很大的分別而不煩解釋一樣。如今閲讀自由與自由閲讀之間也有類似的情形。其實所謂自由這個、自由那個的“自由”並不是我們所瞭解而能接受的“自由”:“自由行動”可以包括殺人放火,“自由戀愛”意在廢止婚姻制度,“自由思想”志在排斥所有的宗教信仰,至少一部分自由思想者是如此,“自由閲讀”或“自由讀書”,准此,可能引起搶書、偷書以至把公家書籍割裂、塗毀等等的行為。那就成為自放自肆了,自放自肆的人與完全不放不肆的人是同樣的不自由的。
自由是禁忌的反面。爭取自由等於排除禁忌。對於生活的其它面的禁忌,我們是知道得比較清楚的;對於讀書的禁忌,一則大概因為愛好而能夠讀書的人究屬少數,再則即在能夠讀書的人也未必真有多讀的毅力與機會,我們卻不甚理會,在大家忙於衣食奔走的今日,自更無暇理會了。一切禁忌,包括讀書的禁忌在內,又有外鑠與內發的兩個來源,大抵對於外鑠的來源,我們在這叫喊民主的時代,是理會得比較清楚的;**至於內發的來源,我們卻又不大理會,以至於全不理會,即使被指點出來,怕也還有人否認。**其實這內外兩路的禁忌,我們從禁忌一名詞裏就可以辨別出來。
“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禁忌原是一個籠統的名詞,指着行動思維的一切限制,初不問這限制的由來。但若我們稍加分析,可知禁是外鑠的,而忌是內發的。禁的所以為外鑠也是比較容易瞭解的。“入國問禁”,“懸為厲禁”,禁止吸煙、吐痰、閒人出入之類的禁,很清楚的是由外而來的。“禁”字的下半字是“示”字,無論是上帝的啓示、官廳的告示,總是外來的。“忌”字卻不然,它的下半截是“心”字,上半截是“己”字,“己”字可能只供給了“忌”字的讀音,也可能是“台”字的假借,而又供給了“忌”字的意義,那就等於説,忌者,我心之所忌耳。其實要坐實內發的一層意思,下半截的“心”字已經是足夠了,初不必問上半截“己”字的源流。
從社會與文化的立場看,一切忌諱也未嘗不可以説是外鑠的,一切行為上的限制,最初可能都是“禁”,日久才習慣成自然的變而為“忌”,換言之,起初是人家不容許你做,後來你也就自然而然的不做,以至於覺得不應當做了。但從生理與心理的立場看,至少有一部分的限制,原先可能是一些“忌”;有一類行為,你做了之後,或做過火之後,也許妨礙了你自己的健康,或至少會教你感覺到不舒服、不自在,而別人既同是人也,也往往有同似的感覺,日久經過一番社會化與形式化之後,就成為“禁”了。兩方面大概都有話可説。但無論如何,一種行為的限制,要成為“忌”,總得先經過你內心的接受,方才有效,才有限制的力量,而這種效力才能維持得比較長久,初不論這接受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
▍被套上“緊箍咒”的閲讀
**讀書的不自由,一部分是由於外來的禁止,另一部分卻是由於內發的忌諱。**外來的限制或禁止是最明顯的,可以無庸多説。圖書的缺乏,藏書的過分的限於某一專行、某一方面,書報的寫作、印刷與流通受到阻礙,等等,不論是由於不可避免的情勢,或由於人為的因素,有如社會的風尚或政府的功令,都是外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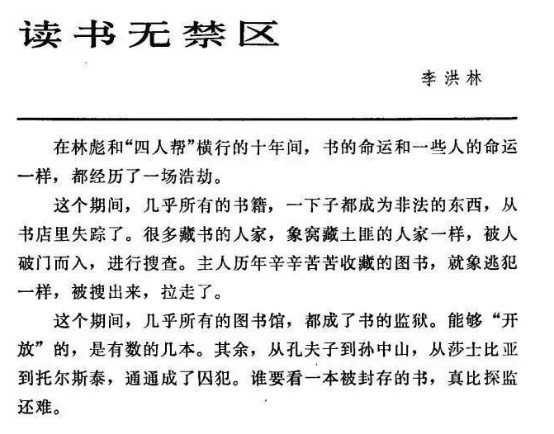
(李洪林:《讀書無禁區》,載《讀書》1979年1期)
**不過更嚴重的問題是內發的限制或忌諱。惟其是內發,所以表面看來不像限制,不成其為限制;惟其不像,所以不受人理會;惟其不受人理會,問題就更見得嚴重了。**我近年來因為職務上的關係,與圖書出納的接觸較多,對於青年人讀書的習慣,也就多得了幾分瞭解。我發見他們的忌諱是不一而足的。歸納起來,這忌諱大都跳不出三個範疇:一是新舊之間,二是中西之間,三是左右之間。
**青年人愛讀新書,不愛讀舊書,愛讀洋裝白話文之書,而不愛讀線裝文言文之書,愛好討論現實問題與宣傳當代思想的書,而不愛讀關於人格修養、文化演變、比較通盤而基本的書——是誰都知道的。**但為什麼有些愛與不愛,有此愛憎,説法就不同了。普通的説法總是從興趣出發,説青年對前者有興趣,而對後者沒有興趣,青年自己的答覆也復如此。其實這只是一種冠冕的説法。試究其實,則所謂興趣的後面,必有一番成見,而成見一深,對所愛悦的便成迷信,對所憎惡的便成忌諱,所迷信的趨之唯恐不速,所忌諱的避之若將浼焉。從社會的立場説,這種愛憎當然也有其來歷,就是“現代化”或“進步”的要求,但青年既接受了這種要求,並且拳拳服膺於此種要求,此種要求的見諸意向行事,便成為內發的,成為成見的一種表示,而其對於“不現代化”、“不進步”的一路事物的不表示,以至於反表示,也未嘗不是一種表示,那就是有所忌諱的表示了。
**中西之間我們所看到的成見大致與此相同,但比較的複雜。大體上是對“西”是積極的信賴,對“中”是消極的忌諱。**讀書人一般的態度如此,讀書時的態度尤其如此。不過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這便是中西之間比新舊之間更為複雜之所在了:一是讀書人對於所謂“西”的對象的接受是不一致的。甲有甲的西,乙有乙的西。所謂西,本身原不是一件單純的東西,英美是西,蘇俄也是西。一個人究竟接受那一個西,就要看他過去的訓練與平時的接觸了。不過訓練與接觸,如果太片面,或太不經心,太無抉擇,結果也就成成見,而對未經訓練未經接觸的事物的態度便成忌諱。二是精通西文的人畢竟不多,讀書的人雖愛讀舶來之書,卻大都不能讀原本,只好讀譯本。原本與譯本,可能一個圖書館都具備,但譯本往往摺皺爛熟,而原本可以幾年無人過問。這不用説,讀者表面上閲讀的是“中”,實際上欣賞與嚮往的還是“西”。
(訂閲《文化縱橫》2020年雜誌,享半年免費暢讀所有已出版雜誌電子版VIP,僅剩最後200席)
**左右之間所表現的愛憎也是一樣的,不過因為目前國際與國內的冷戰、熱戰特別劇烈,此種愛憎,或信賴與忌諱,而表現的範圍與程度似乎是遠在新舊之間與中西之間之上。**近年來此種範圍之廣、程度之深,更若變本加厲,至於有把新舊與中西吞並進去的趨勢,成為左的就是新的、西的,右的就是舊的、中的。青年人一般的態度之中,大體説來,對於左的、新的、西的的信賴和對於右的、舊的、中的的忌諱要大於它們的反面。一般的態度如此,讀書時的不免分些畛域,也就如此了。
有人替青年讀書人辯護説,這一類對於讀物的取捨並不由於成見與忌諱,而是由於能力與訓練的多寡。許多青年對於文言文了解得不夠,讀去不通暢,因而就不感興趣,對於西文也是如此。至於左右之間,因為名詞、習語、命意、遣辭的不同,彼此也就發生了扞格,起初的“看不慣”終於成為後來的“慣不看”,倒不是故意拒絕不讀。這是對的,我不否認這其間有一個能力與訓練的問題存在。不過我們如果作進一步的推敲,便可以發見此種能力之所以差,訓練之所以少,還是由於成見與忌諱的心理在後面作祟,青年自己有此種心理,而五四以來出身做教師的人也未嘗無此心理。
一個人存心厭惡一種事物,第一自然不趨向於此種事物的學習,第二學習了也決不會有長足的進步,原是我們的常識,初不待精神分析派的上場。
總之,由於上文所論對於“三間”的成見與忌諱,我們的讀書是不自由的。此種內發的不自由,其範圍之廣,影響之深,與解脱之不易,要遠在政令法律所能給我們的不自由之上。
一樣爭取閲讀的自由,向環境爭取總還容易,而向自我爭取則大難,因為,上文已經一度説過,這在閲讀的人自己大都並不覺察,而並不感覺到有什麼取捨的必要。
這種不自由的局面,覺察得比較清楚的怕還是一部分負圖書守藏之責的人。國內公私圖書館也還不少,多則百餘萬冊,少亦數萬冊,但除了十分之一,以至於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洋裝、白話、譯文與白報紙的書籍借閲得爛熟而外,看來其餘只好供太平時的點綴裝潢、離亂時的咸陽一炬而已。我們看果子可以知道樹,看書庫的冷落便可以知道讀書的不自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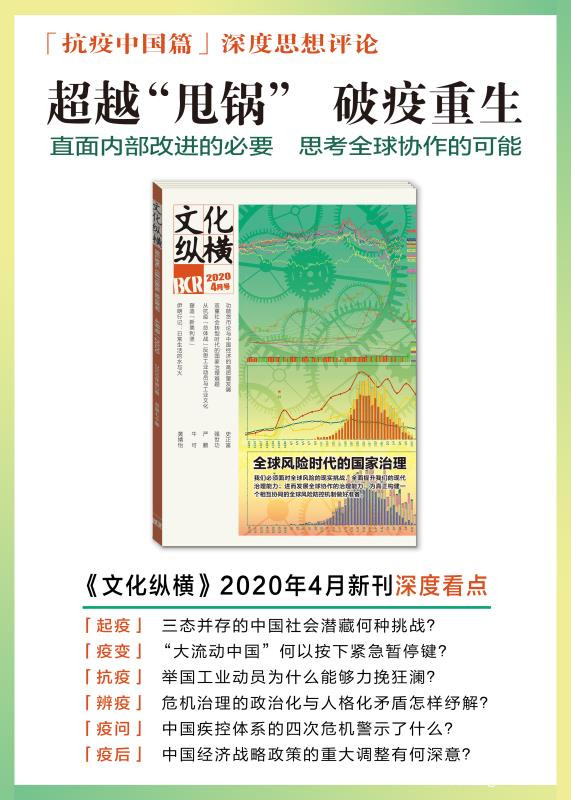
**本文選自《潘光旦:守住靈魂的底線(潘先旦選集)》,原標題為《讀書的自由》,轉自“學人Scholar”****。**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