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拉鋸:美國醫保值得中國借鑑嗎?_風聞
饭统戴老板-饭统戴老板官方账号-有趣且深度的硬核财经2020-05-28 07:55
作者:高翼
編輯:李墨天/戴老闆
支持:遠川研究所醫藥組
2017年7月28日晚上,特朗普在白宮橢圓辦公室裏緊盯着C-SPAN頻道,觀看一場正在美國參議院進行的投票直播。
這次投票,是特朗普上台後推動的第一項重大立法,目的是用一項新法案來替代和推翻前任奧巴馬政府最大的政治遺產:《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也就是俗稱的奧巴馬醫改法案(ObamaCare)。特朗普為此籌謀已久,並派副總統彭斯親臨現場監督,志在必得。
ObamaCare如果用一句來總結就是:強制建立全民醫療保障體系。這項法案從一開始就提倡“小政府”的共和黨視為眼中釘。但要想廢除法案,需要兩院通過以及總統批准,因此奧巴馬時代共和黨無能為力。直到特朗普上台,他們才等來了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機會。
此時特朗普所在的共和黨是參議院多數黨,擁有52個席位。不過因為有兩名共和黨參議員明確表示“叛變”,因此100張選票最終結果可能會是50:50。但加上副總統彭斯(副總統通常兼任參議院議長,在投票平局時可以親自下場投票)的一票,法案就可僥倖通過。
要想達到這個局面,就需要所有共和黨參議員一個不拉地全部出席。而恰在此時,曾在2008年跟奧巴馬角逐總統寶座的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剛動完腫瘤手術,本來要在家休養。但為了湊足該有的票數,共和黨特意把投票推遲到他回華盛頓的那一天。
為了保證他贊同廢除ObamaCare,特朗普在投票特意給麥凱恩打了一個電話。左眼上方剛被手術刀割開過的麥凱恩已經知道自己患了腦部惡性膠質瘤,他走到更衣室接了特朗普的電話,回來後就一直靜靜地坐在大廳的角落裏,等着統計票數的工作人員喊出他的名字。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輪到他投票時,他走上主席台前,伸出右臂,拇指向下,平靜地説出:我反對。説完便轉身就走。
投票大廳當場炸了鍋,民主黨人喜極而泣,共和黨人則是一臉懵逼。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趙小蘭的老公)臉上一片陰沉,抱胸站在計票員的旁邊一言不發,這意味着共和黨6個月的謀劃全部白費了,而ObamaCare則被49:51的投票結果給驚險地保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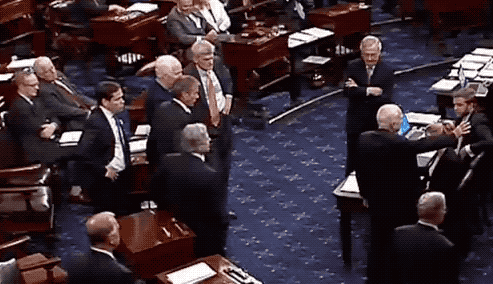
麥凱恩的經典投票鏡頭,2017年
正盯着電視機準備歡呼勝利的特朗普,自然也是惱羞成怒,迅速掏出他最擅長的武器——twitter,連發數條內容指責共和黨建制派的無能。而對於麥凱恩,特朗普更是懷恨在心。一年後麥凱恩去世,葬禮雲集了華盛頓政要,而特朗普故意選在這一天去打高爾夫球。
麥凱恩為何會特立獨行,違背共和黨和特朗普的意願?他自己沒有過多解釋,但人們普遍認為跟他自己患病就醫的經歷有關。而他在深夜投出的這一反對票,從某種程度上挽救了美國人的全民醫保,兩年半後新冠疫情在美國大爆發,無數擁有醫保的底層美國人因此受益。
而2017年7月28日深夜的這場投票,其實是自ObamaCare在2010年通過以來從,共和黨第69次試圖通過國會來廢除奧巴馬的全民醫保。而放到更長的時間維度上,圍繞着“全民醫保”這項議題,民主黨和共和黨從1910年代就開始糾纏,發生過數千次的拉鋸和對決。
一百年間,美國全民醫保的支持者和反對者輪番登場,一個打着“平等”的旗號出師,一個打着“自由”的名義反對,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最後催生了美國醫療體系的“獨特風景”——既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醫療技術,但同時也擁有難以克服的制度頑疾。
雖然千言萬語可以匯成一句話:我大美利堅自有國情在此,但美國醫保拉鋸中的很多細節,值得中國借鑑,也值得中國警醒。
01. 設計師:兩個羅斯福的未竟事業
19世紀80年代,鐵血宰相俾斯麥在德國創造了被後世稱作“俾斯麥模式“的社會保障體系,其核心是僱主、僱員與政府三方共同承擔社保與醫保資金的籌集。大西洋的另一邊,俾斯麥的改革方案深深打動了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他此時正被尖鋭階級矛盾所困擾。
1901年,老羅斯福一上任便籌劃全民醫療保障體系,思路和現在一樣:政府強制平時個人和僱主多出錢,而生病時就能病有所醫。但在當時自由主義的語境下,全民醫保是不折不扣的“進步主義思潮“,不但華爾街的資本家不理解,就連共和黨內的建制派也反對。
八年任期裏,老羅的醫保構想幾乎沒有任何進展。卸任後,他把賭注壓在了他的得力干將——國防部長塔夫脱(William Taft)身上。結果當選總統的塔夫脱立刻化身資本家代言人,對全民醫保不感興趣,氣的老羅在1911年重新競選總統,最終敗給了威爾遜。
**在美國人眼裏,全民醫保縱有無數好處,最終都離不開“強制“二字。**對於自由主義立國的美國來説,搞全民醫保等於壞了老祖宗的規矩,傑斐遜的棺材板恐怕都要摁不住了。在長期拉鋸中,醫保陣營開始形成了民主黨支持、共和黨反對的格局,一直貫穿至今。
威爾遜執政期間(1913年-1921年),兩方的衝突迎來第一次高潮。
支持方由經濟學家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坐鎮,四處宣揚複製德國經驗,推進全民醫保。費雪的勁敵則是代表美國醫療體系的美國醫學會(AMA),他們認為一旦政府成了買單方,自然而然的會用行政手段來約束服務價格,因此旗幟鮮明的跟費雪唱反調。
正當費雪以德國為範本推進全民醫保時,一戰爆發了。1917年美國對德宣戰,國內隨即掀起一股反德浪潮。反對派笑納大禮,直接把費雪的醫改方案印成小冊子,在封面加上一句:Made In Germany,發給不喜歡給德國人遞刀子的美國羣眾,全民醫保方案隨之夭折。
經歷了20年代的繁榮後,接踵而至的大蕭條席捲美國,老羅斯福的遠房侄子,民主黨候選人富蘭克林·羅斯福在一片悲鳴聲中扛起了美國大旗,沉寂了十年的全民醫保再次被提上日程。上任不久後,小羅斯福便迫不及待地起草了《社會保障法案》,其中的重頭戲就是醫改。
為了保障醫改的順利進行,小羅斯福專門成立了一個醫療衞生戰術委員會,用來協調各方利益關係。如臨大敵的AMA果斷出手:1934年,AMA在全國醫學大會上通過了十項反對醫改的戒律,而其中的第二條就是:嚴禁第三方力量介入醫生和患者之間的關係。
翻譯過來就是:怎麼看病,收多少錢,全部是我説了算。
兩方焦灼之際,德國再次為反對派送上神助攻:1939年,希特勒閃電襲擊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打。此時,國會山上爭論的議題從全民醫保,變成了美國要不要參與戰爭。為了建立各民族抗德統一戰線,小羅斯福不得不在醫保方案上示弱,暫停了改革進程。
隨後,一些原本就不堅定的民主黨人徹底失去了進行醫改的信心,於是在美國有史以來離全民醫保最近的年代,小羅斯福因為二戰的突然打響錯過了寶貴機遇。陰差陽錯的是,商業醫療保險在20世紀40年代迅猛發展,成為了日後攔在醫保面前的另一個大敵。
二戰後,美國迎來了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繁榮,按理説,各項社會保障也應該緊鑼密鼓的推行。然而,醫保的反對派卻找到了新的萬金油藉口:蘇聯。
02. 接力棒:民主黨人的第一次勝利
反對美國搞全民醫保的理論大本營,是美國醫學會創辦的《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
JAMA在醫學圈大名鼎鼎,跟NEJM(新英格蘭醫學期刊)、Lancet(柳葉刀)和BMJ(英國醫學雜誌)並稱全球四大頂級醫學期刊。但JAMA除了發表醫學論文之外,政治、經濟、哲學、倫理方面也常常涉獵,可以説是醫保反對派維護自己利益的主要陣地。
1924年至1950年擔任《美國醫學會雜誌》主編的Morris Fishbein,便是醫保反對派的代表人物。他曾經撰文痛批醫保就是搞共產主義,並聲稱“任何形式的社會保障或強制保險,都意味着國家侵犯個人私生活的開始,毫無疑問是導致國家邁向極權主義的第一步。”
而在另一邊,小羅斯福去世後杜魯門接任總統,也接過了民主黨醫改大業的光榮傳統。杜魯門出身底層,經歷過因為貧困輟學,因此他比所有前任都更有動力推行全民醫保,其半生精力都放在了醫改問題上,因此也得了個稱號:“美國全民醫保的政治教父”。
1945年11月19日,上任不到一年的杜魯門動手了。
他向國會提出通過扣薪的辦法,來實行國民健康強制保險。整套方案有四個要點:一是醫療費用由強制保險和國家總收入中支付;二是因病因傷的工資損失由政府補助;三是醫院和醫療機構由地方政府興辦;四是醫藥教育和醫藥研究由聯邦政府給予補助。
方案本身沒什麼問題,甚至可以説準確命中了美國醫療體系的所有缺陷,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方案跟當時蘇聯的“公費醫療”有些過於相似了。
AMA經驗豐富,立刻募集了3500萬美元,聘請公關公司抓着“社會主義“這個點窮追猛打,甚至直接引用列寧導師的話:“社會主義醫療是通往社會主義國家的基石”。在AMA的精確打擊下,杜魯門通過援歐抗蘇立起來的反共人設瞬間崩塌,醫改計劃自然不了了之。
同一時間,美國開始了戰後經濟大繁榮,企業利潤增加的同時,工會勢力也節節高升,為工人福利待遇提高奠定了基礎,商業醫保趁機以“員工享受、企業買單”的方式在工薪階層中迅速普及,連工會都喪失了推進全民醫保的動力,杜魯門自然是獨木難支。
民主黨人毫不氣餒,屢敗屢戰,下一位接過革命火炬的是民主黨總統約翰·肯尼迪。
1960年,肯尼迪在大選結果出爐的第一天,便任命一個小組負責推動全民醫保。此時的肯尼迪遇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老齡化。由於保險公司對老年人不感興趣,使老年人錯過了之前的商業醫保普及。到了肯尼迪執政時,老年人看病難成為輿論焦點。
杜魯門失利的殷鑑不遠,深諳失敗教訓的肯尼迪決定順勢先從醫療需求最高的老年人下手,強制由政府收取員工一定工資,來全面保障65歲以上的人能夠得到免費的救治。1962年5月,肯尼迪在紐約發表全國電視直播的演説,試圖説服選民支持自己的醫保政策。
這一次,為反對派吹響衝鋒號的不是AMA,而是還在美國演員協會當公務員的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
1962年,厭倦好萊塢生活的里根決定進入政壇,正式加入了共和黨,也走向了反對全民醫保的前線。演員出身的他親自錄製了一段反對全民醫保的演講,並錄製成唱片公開發行。唱片中里根義正言辭的呼籲:“自由距離滅絕只有一代人,我們必須捍衞它。”
里根的反對全民醫保專輯封面,1961年
里根的自幹五行為讓AMA喜不自勝,他們立刻將里根同志極具煽動性的演講分發給各個會員,並鼓勵他們向國會寫信,以阻止醫改方案的通過。然而就在這個關鍵時刻,肯尼迪總統在一次競選演説途中遇刺身亡,這顆子彈,也決定了肯尼迪醫保法案的命運。
肯尼迪遇刺後,副總統約翰遜臨危受命,並打出了一張情懷牌——“對肯尼迪最好的懷念,就是通過他的社會改革法案”。藉着美國民眾對肯尼迪的懷念,約翰遜在第二年大選中實現了碾壓式的勝利,眾議院和參議院中民主黨人數也超過共和黨兩倍之多。
有了這樣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約翰遜開始全力推進老年醫保法案的改革。雖然AMA仍花巨資遊説,但在民主黨佔據兩院2/3投票數的絕對優勢下收效甚微。1965年7月30日,《社會保障法案修訂案》正式通過,美國有史以來首部社會性醫療保險得以正式誕生。
為了紀念杜魯門對全民醫保做出的努力,約翰遜專門邀請了81歲高齡的杜魯門親自出席儀式。儀式上,約翰遜用了72支簽字筆簽署了這部老年醫保法案,並將這些筆發給了國會中為推動醫改做出過貢獻的人,接着將美國第一張聯邦醫療保險卡,贈送給了老同志杜魯門。
杜魯門和約翰遜(左)簽署法案,1965年
在三代民主黨總統的不懈努力下,帶着“集權色彩”的全民醫保總算在美國取得了局部勝利,65歲以上的老年人成為了第一批受益者。但問題是,會生病的可不只有老年人。
03. 叛變者:大社會與小政府的爭論
在美國,大部分出身貧寒的總統都在民主黨,比如上不起學的克利夫蘭、得過閲讀障礙症的威爾遜和“農民的兒子”吉米·卡特。但中間也有例外——尼克松。
還在小學時,尼克松兩位兄長便因肺結核去世。被哈佛錄取又因為掏不出路費而放棄[3],這些經歷讓身為共和黨人的尼克松開始關心起了全民醫保的事宜。1971年,尼克松正式向美國國會遞交了一份醫改報告,指出要確保每位美國人都能平等地獲得醫療衞生服務。
尼克松的提案頓時讓民主黨非常尷尬,也不知道該支持還是反對,AMA也被尼克松的騷操作搞得措手不及,居然沒有第一時間跳出來反對。最終,民主黨的靈魂人物愛德華·肯尼迪發現了尼克松醫改不對勁的地方:法案並不是簡單粗暴的“政府買單”,而是引入了商業保險。
尼克松的原意是引入商業保險從而形成一種競爭機制,來避免全民免費看病下,公共醫療服務的效率低下。而共和黨主動搞醫保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彼時美國醫療費用日益高漲,社會福利制度的建設成為全民共識,連任在即的尼克松也不得不做出讓步。
愛德華·肯尼迪本想揪住“利益集團的代言人”這一點攻擊尼克松,但後者在1972年成功連任,民主黨也逐漸對這個注了水的全民醫保法案採取妥協態度,兩黨歷史上第一次就全民醫保達成了一致,就連《時代》也感嘆道[5]:“美國全民醫保的時代即將來臨”。
尼克松與幕僚討論醫改,1972年
然而,歷史再次和美國的醫保改革開了次玩笑。就在美國兩黨就醫改問題逐漸達成一致的時候,水門事件讓尼克松轟然倒台,民主黨為了重新掌權,把友誼的小船直接鑿翻,開始加大力度抨擊尼克松的醫保方案。於是距成功只有一步之遙全民醫保,最終宣告流產。
1976年,出身農場主家庭的民主黨人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當選總統,老實人卡特寄希望用一種“漸進式”的改革逐步解決美國醫療問題。但還沒等共和黨和AMA出手,民主黨內部先起了內訌,肯尼迪帶頭反對自家總統,稱只有快速革命式的改革才能改變狀況。
在民主黨無休止的內訌中,曾經的好萊塢肅反領導者、反醫改先鋒里根1981年坐進白宮的辦公室,醫改的結局不言自明。
然後再提全民醫保,已經是12年後了。1992年民主黨人克林頓當選美國第42任總統,就任第五天,充滿激情的克林頓就宣佈成立“國家醫改總統特別工作組”,並且拉着第一夫人希拉里親自掛帥,牽頭醫改法案的起草工作,這在整個美國歷史上都是沒有先例的。
克林頓要求特別工作組在100天內給出醫改法案的草案。希拉里不負所托,法案在11月份正式頒佈,有1300多頁之多,足足兩本新華字典那麼厚。
闡述醫改法案的希拉里,1993年
克林頓醫改思路和前幾任總統類似,但除了保障全民就醫,還加入了降低醫療服務和藥品價格的機制。這種矛頭直接對準利益集團的改革自然引起了反對派的極力反抗,美國醫學會、保險協會和各大製藥公司聯合起來,打出“增加政府開支”和“公民選擇權喪失”兩張牌。
美國醫療保險協會花費近2000萬美元,拍了一則短片在各大黃金頻道不間斷的投放,片中説道:“政府的健康聯盟給我們提供我們不喜歡的醫療保險方案,根本沒有選擇的機會。他們替我們選擇,但吃苦的卻是我們。”
美國保險協會會長Bill Gradison親自參與廣告的策劃,出演這則廣告的主人公叫Harry和Louise,他們在片尾敦促大眾向各自選區的議員聯繫,希望反對克林頓醫改。希拉里對此火冒三丈,痛批美國保險行業貪婪成性[2],反而把這則廣告帶火了。
反希拉里的Harry&Louise廣告,1992年
而且麻煩的是,美國的熱搜不是説撤就能撤的。
與此同時,民主黨自己也不爭氣。克林頓的年輕氣盛給了民主黨內部“革命形勢一片大好”的假象,黨內同志普遍覺得總統的醫改不夠堅決、不夠徹底,紛紛另起爐灶單幹。克林頓上任一年不到,27個版本的法案相繼出爐,大大分散了凝聚力,最終在共和黨反對派的攻勢下不堪一擊。
1995年國會換屆時,民眾對克林頓虎頭蛇尾醫改方案的不滿也發泄到了選票上,共和黨重新佔據兩院的人數優勢。失去了政治基礎,全民醫保法案再一次的胎死腹中。到共和黨人小布什入主白宮那一年,美國的醫療保健遊説總支出達到2.37億美元,可以在美國最頂級的梅奧診所做4000次心血管手術。
這還是在經濟繁榮的時期,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幾乎每隔30秒就有一個美國人因醫療費用而破產[3]。
04. 掘墓人:從奧巴馬的立,到特朗普的破
2009年6月1日,剛剛過完百年慶典的通用汽車向紐約法院遞交了破產申請,最終拿了政府301億美元援助。人們覆盤發現,高昂的醫療保險福利支出是壓死通用的最後一根稻草:2008年,通用汽車每年給員工醫療支出高達450億美元,足足佔到營業收入的三分之一。
在對經濟一片哀怨聲中,發誓要成為 “最後一屆致力於醫改的總統”的奧巴馬走馬上任,醫改是其競選的核心主張。2009年3月,上任伊始的奧巴馬在白宮召開醫療衞生峯會,主動邀請了醫生、保險公司和製藥企業加入到此次談判中,甚至委任來自利益集團的人。
比起死在沙灘上的醫改前浪,奧巴馬最大的創新在於拿出了一套飽含紅頭文件哲學的改革路線:僅僅提出了降費、高質量和自由選擇三點基本改革精神,至於具體的條款,可以邊改邊議,先行先試,摸着石頭過河。
鐵桿反對派AMA很吃這一套,在看到民主黨如日中天下也放棄抵抗,轉而支持奧巴馬全民醫改,只是在法案中去謀求更多利好自己的法律條目。有了AMA的帶頭表率作用,社會各界都對奧巴馬醫改由觀望轉向了支持,整個全民醫保方案的反對者就只剩一方勢力:共和黨。
共和黨繼續拿“政府過多幹涉”這點做文章,甚至搬出憲法來指責全民醫改的“強制性”。此時,奧巴馬再度使出了東方智慧:主動邀請共和黨人一起來討論美國的醫改問題,加上各大媒體紛紛帶節奏,美國民眾普遍覺得共和黨只知道唱反調,而奧巴馬才是一心為人民服務的好總統。
2010年3月,奧巴馬來到國會山打情懷牌,他在演講中講到:“我崇尚我們的自由主義,但我相信作為一個美國人,我們要有一顆仁愛之心和社區精神,我們要幫助那些暫時不走運的人們。”奧巴馬也相信口號的力量,他在演講中不斷重複着那句口頭禪:Yes we can!
奧巴馬確實做到了。那年3月21日,聯邦眾議院和參議院就奧巴馬醫改法案進行最終投票,法案最終以微弱優勢通過(參議院219:212,眾議院220:211)。在簽署法案的當天,副總統拜登抑制不住激動心情,在全美的電視台和記者面前脱口説到:
這真他媽的是個大法案!(This is a Big Fucking deal)
作為美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民醫保法案。奧巴馬醫改主要解決三個問題:1.通過強制購買保險來覆蓋剩餘1/6的未參保羣體;2. 嚴禁保險公司拒絕和歧視參保人羣從而保障公平性;3. 加大中高產階級税收從而提高聯邦政府的醫療保障。
和我國去年年底開啓的醫保談判引起的藥品大幅降價情況類似,奧巴馬原意也是希望通過政府的力量介入到醫療費用中去,從而影響醫療服務和藥品價格(這也是利益集團反對全民醫改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這種控費需要時間來發酵,而中產階級税負加重和保險公司支出增加,卻是短期的問題。
更多的參保人意味着更高的賠付金額,保險公司只能將保費壓力轉嫁到平時的保險費用上,以至於出現男性必須購買乳腺癌和宮頸癌保險項目的亂象。而對於中產階級來講:一邊是更高的税收,一邊是不斷提高的保險費用。到最後出現戲劇性一幕:很多健康人羣寧願交罰金也要拒絕參加醫療保險。
不過儘管如此,ObamaCare還是讓很多平時沒有醫保的人擁有了醫保。根據數據顯示,美國未參保人數從2010年的4650萬,降低到了2018年的2790萬。
但美國沒有大洋彼岸的那套公立醫院體系,強制約束醫療服務價格無異是臣妾做不到的,而製藥公司不斷創新的基礎,又恰恰是高昂的醫療費用。所以看似堅實的醫改法案,其實只有“提高醫療保險的覆蓋率和賠付率”這一條路,這無法解決日益高漲的醫療費用問題。
當然,即使這樣的全民醫保法案,也仍然會不斷遭遇共和黨的攻擊。2016年特朗普上台後第一件事情就是籌劃廢除全民醫保,這便有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而在2017年那場深夜投票之後,特朗普自知無法通過立法來廢除ObamaCare,便逐漸用行政手段來四處破壞。
導致的結果就是美國未參保人數停留在2600~2700萬的水平上,無法進一步下降。所以用Bernie Sanders的話來説就是:美國依然是唯一沒有全民醫保的發達國家。
05. 尾聲
在任何國家,全民醫保的體系建立都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世界上沒有完美的醫療體系。廣受讚譽的英國NHS系統,也飽受着效率極其低下、資源分配不合理等批評,中國台灣的“政府監管+市場供給”模式,一度也被奉為圭臬,如今卻面臨醫保資金見底的難題。
中國大陸自然也不例外,漫長的醫改牽扯着諸多博弈,衞健委、人社部、發改委和財政部各有各的訴求,市場機制派和政府主導派又陷於長久的路線之爭,但無論有多少波折,全民醫保依舊在爭議聲中覆蓋了99%的中國人,這也是醫改十七年來最為實打實的成績。
但光有全民覆蓋的醫保還不夠,繩子的另一頭是“物美價廉”的公立醫院。沒有後者,再充沛的醫保資金也會捉襟見肘。從某種程度上來説,中國老百姓目前的醫療滿意度,一方面取決於財政資金調配和全民醫保覆蓋,另一方面取決於對公立醫院的壓強式“成本管理”。
而在“小政府”的觀念下,到底是建立以税收為基礎的全民醫療,還是讓沒有保險的人自找出路,主導美國精英們永遠會選擇後者。這在發達國家中也算異類:根據統計,從1970年到2014年,在經合組織成員中,美國的醫療費用長的最快,但人均壽命卻增長最慢。
這裏面的本質原因,其實用2008年麥凱恩同奧巴馬競選總統時説的一句話便可以解釋。那會兒他尚未患病,極力反對全民醫保,更想不到有一天會挽救民主黨的方案。在那年,他對奧巴馬的醫保計劃不屑一顧,並給出了自己的理由:“健康是一種責任,而非權利”。
讀懂這句話,你才能理解大洋兩岸醫保體系的核心差異,更能明白為什麼在這次新冠疫情之下,不同政府和民眾會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