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國聲優的強大,在100年前就埋下了種子_風聞
影探-影探官方账号-美日韩剧资深鉴赏员,电影专业老司机2020-06-28 13:26
作者| 錢老闆
來源| 影探
我們都知道,電影誕生之初是沒有聲音的。
也知道全世界各個國家基本都經歷過無聲片的時代。
然而,日本電影卻很神奇地沒有這個階段。
因為早在電影最初傳入日本的時候,上映期間就已有解説員在旁講解。
這類解説者被稱為**“活動辯士”**(活動弁士,かつどうべんし),地位可與明星比肩。
幾十年後,隨着有聲電影時代的來臨,辯士一職才漸漸消失。
日本電影的這個現象不僅在亞洲,甚至在全世界也可以説是絕無僅有。
而那些辯士,也代表了日本電影的那段曾經——
《默片解説員》

1915年。
村裏的俊太郎和梅子是兩個愛電影的孩子。
因為沒錢,他們常常偷拆掉劇場的門板,逃票觀影。
兩人也因此結緣。


字幕出自豬豬日劇字幕組,下同
俊太郎的夢想是做一名人人皆知的大辯士,就像他崇拜的偶像山岡秋聲一樣。
梅子的夢想則是當一名默片演員。
一內一外,堪稱天生一對。
後來劇場門板被封了,俊太郎就常常憑着記憶,手舞足蹈地把電影解説給梅子聽。
風格自然是學他的偶像山岡秋聲。
大概是天賦加熱愛的關係,儘管無人指導,俊太郎竟也學得惟妙惟肖。
這天,俊太郎正準備給梅子講解法國電影《怪盜吉格瑪》。
講到興起時,説要去商店偷一盒奶糖來助興,讓梅子在原地等他。
可惜在商店行竊時被抓了現行,扣押了。
殊不知梅子明日就要隨母親搬去他鄉,此行原本是來道別。
卻終於沒了機會。

一別十年。
俊太郎長大了,也的確做了辯士,輾轉於各個鄉鎮演出。
可這並非如他所願。

成田凌 飾 俊太郎
其實是有個盜賊團伙看上了他模仿山岡秋聲很厲害,便騙了他加入。
之後又威逼着俊太郎,協助他們去到處行竊——
假扮成擁有王牌辯士山岡秋聲的放映團隊,上山下鄉去放電影。
趁着村民們一窩蜂地去觀影,他們便悄悄潛入村民家盜走財物。
俊太郎雖心有不甘,卻也不敢貿然逃離。
警察當然也注意到了他們。
在一次逃脱追捕時,俊太郎被意外從車上甩了下來。
一起被甩下來的還有盜賊團伙的小金庫。
俊太郎就這麼順勢離開了盜賊團伙,另謀生路。
後來,他來到一個快倒閉的劇場當起了夥計。
劇場名叫**青木館,**原本大概是很紅的,連山岡秋聲都是他們的常駐辯士。
這也是俊太郎願意留在此地的原因。
但他曾經的偶像山岡秋聲,如今已然無心業務,成了個頹廢酒鬼。

有次,山岡秋聲喝到不省人事,俊太郎主動請纓替他上場。
不料,一戰成名。
又嘗試用自己的風格進行解説,添進些幽默詼諧的元素。
依然大受歡迎。
已經出落成黑島結菜的梅子,也在偶然的一次觀影中聽出了他是俊太郎。
如今的梅子也當過演員。
但能不能繼續當,能當到什麼程度,在那個年代,女性沒有話語權。
黑島結菜 飾 梅子
這突如其來的名氣,讓俊太郎贏得了作為辯士的榮耀。
也讓他陷入了接踵而至的麻煩。
盜賊團伙、青木館的競爭對手、警察等皆聞訊而來,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
一場場讓人啼笑皆非的大亂鬥就這麼在青木館輪番上演…
片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辯士這一職業。
在日本評論家四方犬文彥所著的《日本電影110年》中,有幾章寫到過辯士。
雖説不算什麼詳細的專項研究,但其起源,發展,衰落的大致脈絡已經介紹得很清楚。
而電影內容和書中內容基本都對得上。
用現在的理解來看,辯士的作用大概就像是旁白者,照理應居於幕後。
但在當時,辯士往往身着西式禮服,頭戴禮帽,作為表演者站在台前。

辯士解説電影,也並非完全遵循其原本的劇情。
在電影開始前,他們往往就會對影片的內容及主題做一個概括。
電影開始後,他們也往往會在解説中加入自己對故事的看法或者提示。
又或者興之所至,直接搞些即興創作,篡改劇情。

比如電影開頭,俊太郎和梅子誤入片場,被拍了進去。
後來上映時,辯士順口就把兩人説成了片中的龍套角色,替他們加了台詞。
只要畫面和解説詞對得上,辯士的解説情緒又足夠到位,觀眾一樣會看得津津有味。
並且,那些會借電影"開車" alt=“500” />
也正因為如此,觀眾對一部電影的感受有時會帶有即興性。
他們選擇去哪家電影院,看哪一部電影,往往取決於辯士是誰。
影院也常常根據辯士的節奏來調整電影的放映速度。
某些大腕辯士甚至還有權力讓導演為了配合他而刪改內容。
堪稱頂流待遇。
現在咱們可以很容易想到,辯士的這種解説實際上屬於二次創作。
他們的存在,掩蓋並削弱了電影本身的魅力。
但當時人們對電影還未進入探索的階段,再加上觀眾喜歡,辯士自然很火。
儘管也有些人主張廢除辯士制度,試圖引入歐美電影的字幕欣賞方式,但屢屢受挫。
甚至在有聲電影初入日本時,由於大多數觀眾不懂外語,辯士的作用反而更被凸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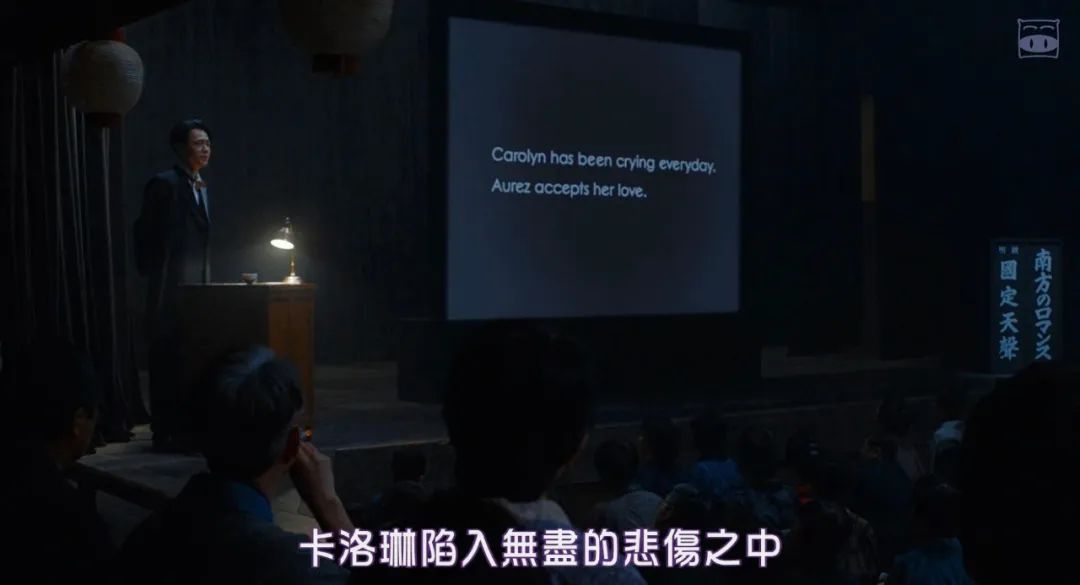
日本電影的有聲時代來得比其他國家更晚一些(除了辯士制度,還有設備投資的原因)。
但,總歸也是來了。
1931年,約瑟夫·馮·斯登堡的《摩洛哥》在日本公映時,在拷貝里就已加印了字幕。
這一事件代表着,理論上辯士繼續存在的意義已經沒有了。
就像片中山岡秋聲説的:
電影能脱離辯士存在,辯士卻不能脱離電影存在。
他先一步認識到了辯士對於電影的制約性,也察覺到了辯士終將走向沒落。
所以他才終日渾渾噩噩,解説時也越來越傾向於不説話,讓觀眾自己去看。

不過,電影並沒有提及辯士制度的發起源與結局。
其實也很簡單,無非是辯士制度因襲了大眾文藝的歷史傳統。
自江户時代以來,落語、講談、説經祭文、音頭等各種形式的口傳文藝已經深入人心。
日本的觀眾已經習慣了將舞台中央的表演**(視覺)和舞台一旁的演唱、彈奏部分(聽覺)**結合起來欣賞。
所以當他們第一次接觸電影時,很自然就接受了旁白的存在。

而辯士們的結局雖然是衰亡。
但他們在日本的電影裏仍然以某種方式留存至今。
比如日本電影中常見的全景鏡頭和長鏡頭,原本是為辯士拿手的冗長對白而預留的;
感傷的結論性旁白則是辯士解説的遺留痕跡。
本片由日本導演周防正行執導。老人家已經6年沒有拍過長片電影了。
他最為人所熟知的作品應該是《談談情跳跳舞》。
一個講述中年男人最後的倔強的故事。
片中竹中直人那淡黃的襯衣,那蓬鬆的假髮,那銷魂的舞姿,都一直讓我念念難忘。
他彷彿不是在跳舞,而是在燃燒。

《談談情跳跳舞》
如果你看過這部電影就知道,周防正行十分擅長用幽默+感傷的方式拍故事。
這部《默片解説員》也不例外,而且似乎更適合這樣的方式。
電影裏的場面多是鬧騰着的,但它有個核心。
表面一層,是緬懷逝去的默片時代和辯士制度。
其實不瞭解那段時期的觀眾,對裏面出現的各式各樣的致敬啊什麼的很難領會到。
但內裏的那一層,我想只要是影迷,大概都能感受得到——
導演通過講述辯士的故事,在片中所表現出來的對電影的熱愛。

如果你拿着這個主題去重新審視影片的一些情節和場景,就會很有意思。
比如在影片的高潮部分,青木館遭競爭對手搗亂,庫存膠捲被損壞得所剩無幾。
館主別無他法,只能把還能用的膠捲拼在一起,試圖做最後的掙扎。

而此時的俊太郎,正處在身份暴露、多方追捕的危急關頭。
還有梅子在車站等着他一起遠走高飛。

但俊太郎還是堅持回去解説完了這場特別的**“混剪電影” alt=“500” />**
片中的理由是他不能對收留了他的青木館忘恩負義,要回去救場。
但放在戲外來看,
這個情節其實也像是導演借俊太郎一角,與默片、辯士時代好好作了別。
否則,大概也不會設計出讓俊太郎解説混剪電影的情節。
不同的默片被放在一起,由辯士俊太郎憑才能將其現場口述成一個連貫的故事。
這根本就是赤裸裸的緬懷與告別。
又比如之後,百年劇場青木館在大火中毀於一旦。
幸好俊太郎提前把盜賊團伙的錢藏在了鐵盒裏,青木館才有了重振的希望。
這不正是代表着作別之後的釋然?
舊的時代已經過去,新的時代即將來臨。
所以導演也順便安排了山岡秋聲一言不發地離開。
因為他已不再沉溺於過去。
還有導演兩次安排的男女主同時出現在銀幕與現實。
這種讓銀幕中平行世界(我認為好故事的本質就是如此)與現實世界交匯的騷操作。
不是死忠影迷根本幹不出來這種事兒。
有句話説得挺恰當的:電影不是站台,是列車。
電影不等人,它一直在前進。
黑白變彩色、無聲變有聲、實拍到特效、膠片到數碼、2D到3D、攝影機到手機…
每一次新技術的誕生,都會讓很多人惶恐。
電影公司只想安穩賺錢,電影人則擔心電影淪為技術的附庸品。
因為新技術的誕生,意味着變,也總是會催生出大批借技術為噱頭的粗製濫造之作。
但結局怎麼樣?
電影還是活過來了。
它怎麼會死呢?
雖然電影一直在變。
但無數影迷、電影人對於電影的愛卻未曾變過。
他們是電影得以不滅的火與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