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前夕,日本曾出版過一部聯蘇抗美的漫畫_風聞
瘟疫公司搬砖部-最近在看《宋案重审》2020-07-08 15:37
文|李青嵐
1987 年 12 月 7 日,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抵達華盛頓,開始了對美國的首次國事訪問。在他前往白宮會見里根總統途中,大批市民向戈爾巴喬夫尖叫歡呼,他當場下車走進人羣,與激動的人們握手留念。
蘇聯領導人在美國擁有如此聲望人氣堪稱空前絕後,即使二戰時期成為美國最重要盟友的斯大林都難以相比。在世界其他地方,人們心中的天平似乎也在向蘇聯傾斜。
1980 年代以來,巴黎、波恩、海牙等歐洲政治中心城市接連爆發大規模反戰、反核示威,矛頭直指華盛頓;美國對核裁軍、反導的積極態度,又令西歐各國堅定反蘇防蘇的黨派、政客感到不安和幻滅。
1983 年 10 月 29 日,荷蘭海牙 50 萬人上街遊行示威,抗議北約即將在西歐部署潘興 Ⅱ 導彈

1987 年,西德政府邀請東德領導人昂納克訪問波恩,重啓 1970 年代左派政府的「東方政策」,向蘇東陣營伸出橄欖枝。作為冷戰中西方陣營的最前線陣地,西德與北約的關係還是否穩定,一時間都成為了美國決策者揮之不去的烏雲。
1988 年 12 月,戈爾巴喬夫再接再厲,在第 43 屆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歷史性講話,將蘇聯的國際聲望推升到了新的高度:他將進一步主動裁減東歐駐軍 50 萬,不再堅持傳統「勢力範圍」,不干涉東歐國家自主選擇的內部變革,以貫徹其國際關係民主化與人道化的主張。
「共同歐洲家園」
戈爾巴喬夫上台後,並未如後世想象得向西方「卑躬屈膝」,而是力圖在國際上重塑蘇聯的和平形象,在美蘇爭奪道義制高點的角逐中超越對手。
蘇聯首先高舉和平旗幟,積極運作核裁軍議題,戈爾巴喬夫甚至在 1986 年的雷克雅未克峯會中大膽向里根提出,美蘇 10 年內銷燬全部核武器,儼然人類和平天使。
更雄心勃勃的謀劃,則是戈爾巴喬夫重提的蘇聯所謂「共同歐洲家園」構想,倡議與西歐各國攜手建設以「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歐安會)為基石的泛歐洲共同體,將華約、北約這兩大對立集團轉化為歐洲內部的集體安全體系。
為推動這一設想,戈爾巴喬夫不斷提出宣揚歐洲和平的説法,1988 年西德總理科爾訪問蘇聯時,他表示:「我們歐洲人至少應當按照新時代的邏輯行事:不要準備打仗,不要勒逼彼此,不要比拼更完美的武器,也不要只去避免戰爭,而要學會締造和平。」
對於西歐社會而言,這是二戰結束以來,蘇聯領導人第一次提出具有真實號召力的驅美設想 ——「歐安會」框架下的新歐洲,顯然沒有美國的位置。
蘇聯領導人的和平論調,也與同時期大幅擴充軍備的美國里根政府形成鮮明對比,而且戈爾巴喬夫本人在國內發動「公開化」「新思維」改革運動,不像前幾代蘇聯領導人身負布達佩斯、布拉格的血債,似乎正適宜充當和平新歐洲的總設計師。
這種一時間令美國人感到不易招架的「和平攻勢」(Peace offensive),最初是 1980 年代初美蘇間國勢消長、蘇聯居於劣勢下的無奈選擇。
1970 年代「東攻西守」的冷戰競爭態勢,在里根總統上任後得以扭轉,美國大幅增加國防開支,加快美軍裝備更新換代步伐,國防戰略上也凸顯強硬作風,在西歐部署中程導彈,對華約陣營的局部戰爭優勢,乃至全面戰爭能力,都形成了巨大威脅。
反觀蘇聯,由於 1980 年代國際油價長期低迷,蘇聯高度依賴的油氣貿易硬通貨收入嚴重受損,無論是向衞星國陣營輸血,還是介入第三世界熱點地區所需的投入,都越來越不易承受。
蘇聯以數量對質量的軍備競賽風格,在美國新一代軍事裝備的效能飛躍面前,也處於棄之可惜留之無用的兩難困境。
一言以蔽之,蘇聯 1970 年代的戰略擴張已過度透支其能力,敗相畢露而面臨收縮調整。
在此背景下登場的蘇聯「和平攻勢」,最初以外宣統戰工作為重點,通過西歐各國進步羣眾發動規模宏大的反戰反核抗議浪潮,試圖阻止美軍中程導彈在西德等東道國實際部署。
· 1981 年德國波恩羣眾示威,反對部署潘興 Ⅱ 導彈

然而,蘇聯的這一波出擊並不成功。1983 年 3 月,里根總統推出「戰略防禦倡議」(又名「星球大戰」計劃),不但大方接過了反對核武器的旗幟,甚至把它舉得更高。
里根宣佈,由於核戰爭極為恐怖,美國將發揮其在航空航天、半導體、新材料、高能物理等領域的科技優勢,研究和部署能夠對抗大規模核導彈進攻的防禦系統,使戰略武器領域的「共同確保摧毀」,轉變為美國所領導下的「共同確保存活」。
面對「星球大戰」,蘇聯的戰略處境不但未有改善,反而可能進一步惡化 —— 一旦美國建成其聲稱的全面防禦體系,蘇聯的核武庫就可能失去對美國及其盟國的威懾作用,再難與美國作對等抗衡。
如此一來,蘇聯將勢必從美蘇兩極格局的一級,淪落為諸多次等列強的一員。
正在這一近乎弄巧成拙的危急時刻,戈爾巴喬夫成為了蘇聯的最高領導者。
下一盤和平的大棋
戈爾巴喬夫的內外施政,可以被視為蘇聯的「第二代和平攻勢」。
新的攻勢中,既然核武器的傳統教條已經被「星球大戰」打破,蘇聯的戰略收縮難以避免,那麼不妨因勢利導,主動管理收縮的節奏和側重,尤其是在蘇聯自身難免喪失霸權的前景下,爭取將美國也拖下超級大國寶座。
戈爾巴喬夫向里根提出「 10 年銷燬全部核武」,其算計便在於,如果美國戰略防禦設想最終成真,蘇聯若能以終將無用的核武庫捆綁美國、換取共同裁減,也不失為不利形勢下的最優結果。
與此同時,蘇聯又提出國際關係領域的種種新倡議,高風亮節地卸下超級大國的冠冕,將事實上的戰略收縮表現成蘇聯對「民主平等多極化的國際關係新格局」的倡議和追求,以消解美國霸權,樹立蘇聯道義形象,推動向多極世界體系過渡的戰略目標。
除了「歐安會」框架外,蘇聯還大力支持聯合國加強其全球干預能力,取代任何單一國家(即美國)的海外行動。例如在兩伊戰爭中的襲船戰期間,蘇聯即提議美蘇干預艦隊統一懸掛聯合國軍旗幟。
在戈爾巴喬夫的遠景規劃中,聯合國將在蘇中法德日等兼具實力與意願的有力成員主導下,掙脱美國的操控,以其「理想」形態發揮作用,迴歸 1947 年冷戰揭幕之前的「初心」,建立真正有力的聯合國直屬常備軍,成為維護國際社會多元和平共處的「世界警察」。、、
· 籌備之初,聯合國總部曾計劃設立於中美洲的尼加拉瓜,並規劃建立以 3 艘戰列艦,6 艘航母為核心的常備海軍艦隊

在這一有利的國際環境下,蘇聯將得以藉助西方世界的資金、市場與技術,逐步實現經濟改革的目標,為其未來複興奠基。
戈爾巴喬夫的新一輪和平攻勢,一時間令美國及其領導下的北約體系倍感尷尬,有北約官員直言:「現在我們只能説,我們是因為喜歡核武器才想擁核的,而沒法再説是因為蘇聯也有核武器了。」
在地處冷戰前線、直接承擔大戰風險,且因歷史原因而極端盛行和平主義思潮的西德,戈爾巴喬夫更是迅速成為政壇偶像,以至於總理科爾私下裏羨慕嫉妒恨地指控他「花了一大筆錢」來操控西德輿論,其聯合政府更是在輿論衝擊中岌岌可危,不時向東方陣營搖擺。
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弗萊德 · 伊克萊牽頭,彙集基辛格、布熱津斯基、亨廷頓等美國傑出戰略家的整合長期戰略委員會,則於 1988 年公佈其第一份正式報告,對美國戰略環境的前景作出了灰暗的分析:蘇聯的戰略收縮並不能實質解決戰略武器對峙壓力,而德日與中國的崛起又將使美國面臨新的挑戰,美國國力相對優勢將進一步被削弱、稀釋,維持霸權的難度將日益加劇。
同樣體現這種時代氛圍的,是日本 1988 年 10 月開始連載的長篇漫畫《沉默的艦隊》:

有理想有思考的日本少壯軍官劫持「大和號」核潛艇,響應國際關係民主化、多極化的歷史潮流,叛離美軍第七艦隊序列,與軍工複合體幕後控制的美國一路苦戰,擊沉包括中途島號航母、新澤西號戰列艦在內的美艦逾 20 萬噸。最終,中、蘇、印等東方大國的核潛艇會師紐約曼哈頓海灣,為聯合國大會助威,迫使美國總統不得不反思其霸權主義理念。
這種多極化思維,在和平攻勢影響下的西方輿論場上愈演愈烈:既然蘇聯業已主動摒棄「冷戰思維」,美國形單影隻的超級大國姿態顯得頗為另類,似乎已經被某種浩蕩的歷史大潮拋在了一邊。
失去的機會?
1987 年,精研國際關係大戰略的美國學者保羅·肯尼迪出版了代表作《大國的興衰》,通過對過去五個世紀的歐洲文明圈霸權更替研究,提出美國正在衰落的重大論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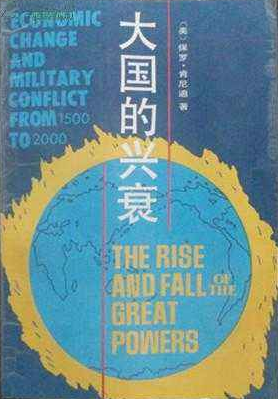
此書的出版,標誌着國際關係學術界的「美國衰落」大辯論達到高潮,在這場辯論中,持「衰落」觀點的學者佔據主流地位,基歐漢、吉爾平、金德爾伯格等大家均在其列,至於如何應對美國的衰落,多數學者建議應直面現實,積極順應多極化潮流,卸下不合時宜的超級大國擔子。
也有如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等學者,提出美國效仿大英帝國故智,在霸權晚期主動選擇與培植其接替者,具體來説就是接納崛起勢頭最迅猛的日本分享其霸權地位,優勢互補,從而實現兩國「合霸」(Bigemony),代替美國力不從心的「獨霸」(Hegemony),與其本人 20 年後提出的中美 G2 概念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對於這一邀約,日本政界並不感興趣,認為這是把日本放在火上烤。
倒是盛田昭夫和石原慎太郎兩人在同期出版的《日本可以説不》一書中,反而熱情暢想日本憑藉其先端技術,在美蘇之間扮演調解人的角色,進口蘇聯軍用發動機用於國產新型戰機,擺脱美國鉗制,也向蘇聯供應洲際導彈所用的芯片,幫助其維持與美國的軍力平衡。

1988 年 12 月戈氏發表聯大講話,將蘇聯的國際聲望推升到新高度之後,連美國保守主義陣營最傑出的「筆桿子」克勞薩默都極不情願地作出了高度評價,視之為戈爾巴喬夫作為政治家的「天才」展現,能夠將最堂皇靚麗鼓舞人心的理念與蘇聯的現實利益有機結合,不愧為這一時代最強悍的政治人物。
此時的克勞薩默恐怕做夢也不會想到,短短幾個月後他就將見證蘇東陣營的劇變,並將親手發明「單極時刻」一詞以彰顯美國的勝利。
今時今日回顧,戈爾巴喬夫和平攻勢從輝煌成功到慘烈失敗的戲劇性轉折,既非這一對外戰略設計本身有何缺陷,亦非西方陣營此時有何對抗性回應,問題還是出在己方陣營內部。
戈氏在改革進程中,強力壓迫東歐兄弟黨開啓轉型進程,並對其進程堅決不予以任何強力干預,甚至堅決制止其本國政府以武力保衞政權,使其轉型幅度迅速超出預期,也為蘇聯內部各加盟共和國地方勢力釋放了信號:作為國家實體的蘇維埃,並無行使其合法壟斷暴力權的意志。
隨着各地方大膽截留財政收入,蘇聯財政能力驟然瓦解,驚人規模的赤字貨幣化立即引起宏觀經濟動盪。原本成功的西方外交,也不得不從高舉高打的理想感召,轉換為四處乞討緊急援助。
蘇聯的外部威信與談判地位蕩然無存,其最初的對外戰略也已失去意義,走向最終解體的惡性循環就此成型,並以每週、每月為單位不斷加速。
因此也可以認為,「和平攻勢」的最終失算源於這一戰略的真誠:蘇聯並非只是高唱「國際共同體」的高調與美國爭奪各國好感,而是確實在大力削減軍備,坐視波蘭、捷克、南斯拉夫等國的親美政客奪取政權而束手無策,甚至接受了立陶宛、拉脱維亞、愛沙尼亞等自治共和國的徹底獨立而無所作為,從而導致美國的精英集團最終還是選擇了不收斂、不收手,堅持走上打造單極化世界的不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