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BBC會玩,兇殺、桃色、潛規則,一集一個爆點_風聞
影探-影探官方账号-美日韩剧资深鉴赏员,电影专业老司机2020-07-10 13:10
作者| 香蕉姐
來源| 影探
試想,在黑漆漆的電影院。
銀幕上的演員,突然轉過頭對着你説話。
瘮不瘮人?
這種“打破第四堵牆”的方式,在最近一部新劇裏被廣泛運用。
驚悚的配樂下,朱迪·科默(《殺死伊芙》小變態),一雙明亮的眼睛盯着你,臉部暗黃色的陰影,提示着危險。
“我上週射殺了一個男人”。
語氣輕鬆得好像只是吃了一頓晚餐而已。
講着講着,她抖漏出一個又一個秘密:
女演員被潛規則,懵懵懂懂拍了色情片……
一箇中年婦女愛上了她的繼子?
一個女人長期遭受性虐待?
還有多少骯髒和慾望,藏在體面之下,等待被撕碎——
《新喋喋人生》
Alan Bennett’s Talking Heads
2020.6.23 英國

準確來説,這是一部重啓劇。
脱胎自阿蘭·本奈特在1988年、1998年創作的兩季《喋喋人生》。
兩季在IMDb上分別獲得了8.6、8.7的成績,口碑不俗。
新版在豆瓣上也有9.1的高分。
如果沒有疫情,這部劇大概也不會重啓。
因為它是一部獨白劇——
發生在室內,從頭到尾只有主角一個人,對着鏡頭,喋喋不休地給你講故事。
特別適合疫情期間,保持社交距離的需求。

形式的單調,決定了內容必須有趣。
如何在40分鐘內,牢牢抓住觀眾的注意力?
當然必須有爆點。
每個故事的開場,都是一顆炸彈,炸得你七葷八素。
第四集,開場就是朱迪·科默冷漠得談論殺人,讓人瞬間夢迴《殺死伊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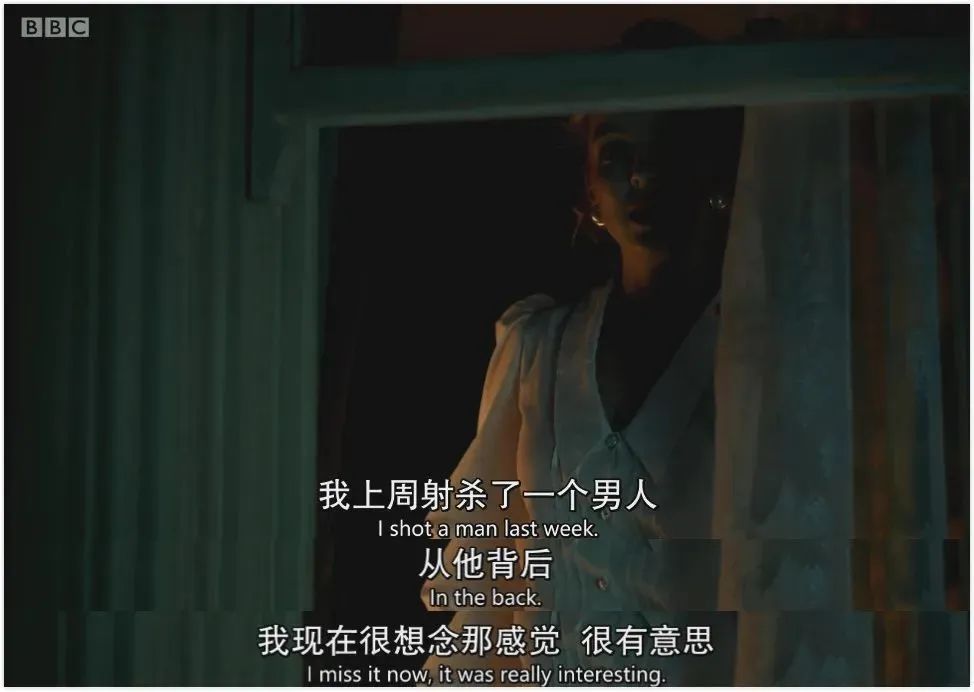
不過,這次她不再是《殺死伊芙》裏那個全能女殺手,
而是一位被潛規則的女演員萊斯利。
她周旋在四個男人之間,每個男人都對她提出不同的要求。
一號男,薯哥。
她在宴會上認識薯哥,兩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
薯哥馬上提出給她介紹個角色,但卻説:
“試鏡的地方太遠了,不如今晚住我家吧?”
為了證明自己是正人君子,薯哥説,自己家裏有兒子、有女兒、有弟媳。
可萊斯利進門後發現,哪兒有弟媳?
都是鬼扯。
**二號男,西蒙,**他是面試萊斯利的人。
為了準備面試,萊斯利專門讀了關於面試技巧的書,
她談了一堆電影,願意為角色去學習滑冰和象棋,
西蒙卻只提了一個問題:
“我能只看你穿內褲和內衣的樣子麼?”
就這樣,萊斯利脱了個衣服,通過了所謂的外形測試。
萊斯利以為自己是對角色理解獨到,才被導演選中,
三號男奈傑,甩給她一句話:
“那是因為你的胸圍有38寸。”
到了現場實拍,萊斯利為角色設計了很多有趣的小細節。
比如手邊拿着書,戴眼鏡,或擺着公文包。
可導演卻只需要她做一件事——
坐在甲板上,穿着比基尼,在性感的胴體上塗抹防曬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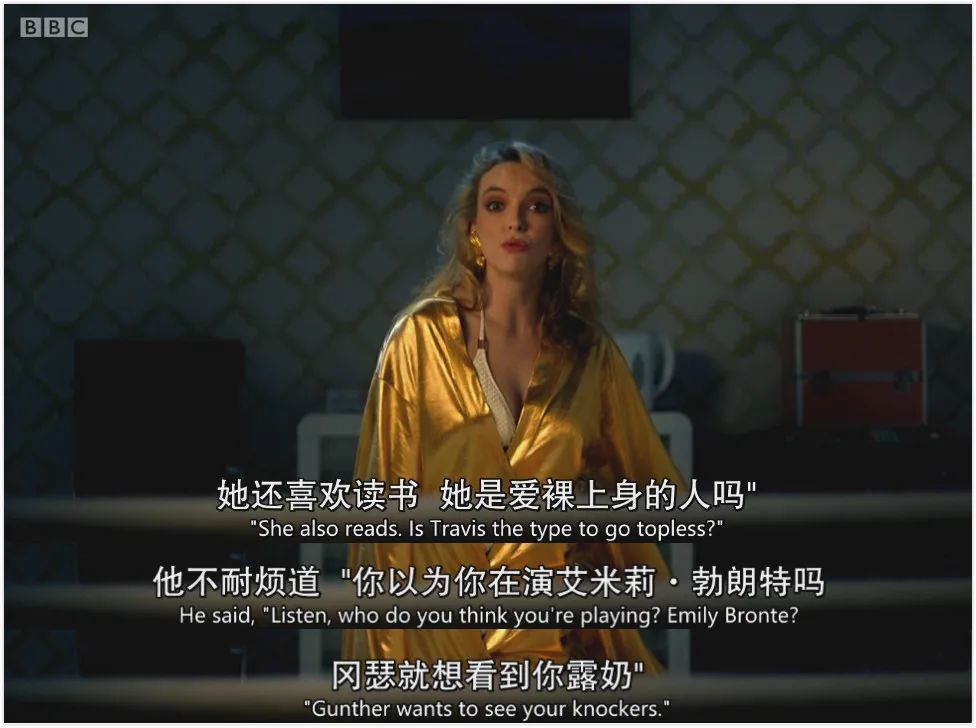
其實萊斯利是誤入了色情片劇組。
整體的故事結構像一個隱喻——
暗示着心懷理想抱負,內心又不太堅定的女演員,
在利益驅使下,不得不淪為展示肉體的背景板。
最後導演打來電話,告訴她電影上映後,你會爆紅。
朱迪·科默眼含熱淚,説出那句**“藝術即奉獻”,**極具諷刺與悲哀意味。

(⚠️劇透預警)
除了演藝圈的秘聞,鄰居的秘密有時候更可怕。
麥先生死了。
他沒穿褲子,躺在地上,腦袋開花。
霍太太問要不要報警。
麥太太卻説:“不用,是我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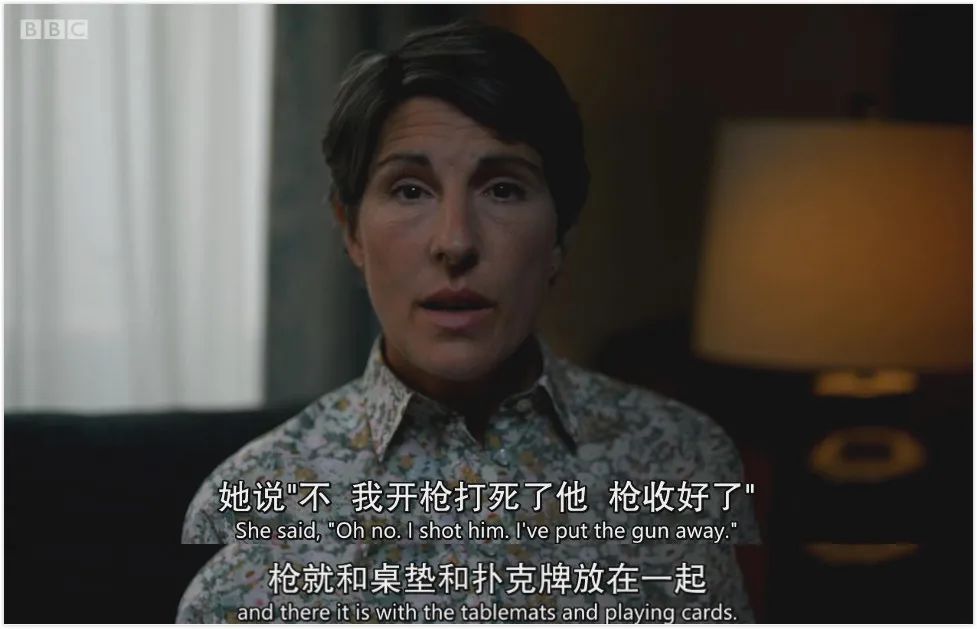
現場情況並不簡單。
沒有警察來過,可水槽裏卻有一副手銬;
而且,麥太太的亞麻連衣裙下,什麼都沒穿。
法庭上,麥太太證明,自己長期遭受性虐待。
被打、被恐嚇,戴項圈、拴繩子,被像狗一樣對待。
麥先生還把麥太太的頭蒙上,讓朋友們一起侮辱她。
麥太太雖然看不見,但她記得,有一個人的呼吸裏,帶有哨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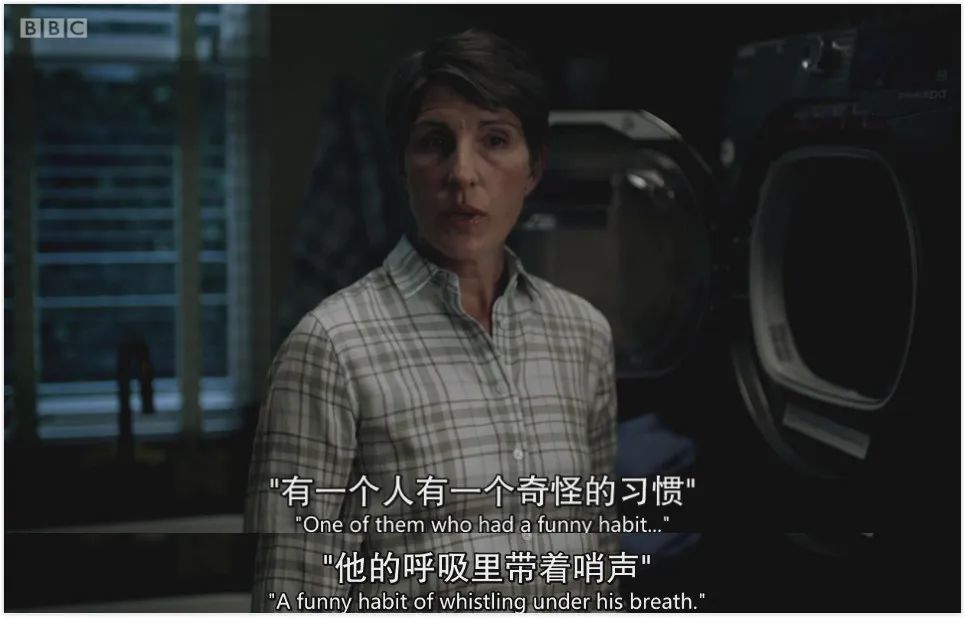
霍太太慌了。
因為,她丈夫亨利的呼吸,恰好帶着哨聲。
一樁兇殺案像光一樣,照進她婚姻中的陰暗角落。
她開始思考自己的婚姻。
亨利對她毫不關心,她去體檢那天,亨利去看了高爾夫錦標賽。

他們已經多年不同牀了。
她甚至帶着自嘲,一邊暗罵亨利是衣冠禽獸,一邊又願意這樣取悦他。

她沒有閨蜜,沒有朋友,沒有孩子,她的生命中只有亨利。
自己這樣,和帶着項圈的狗有什麼分別?
她第一次覺得,生活竟然如此無趣,自己竟然如此孤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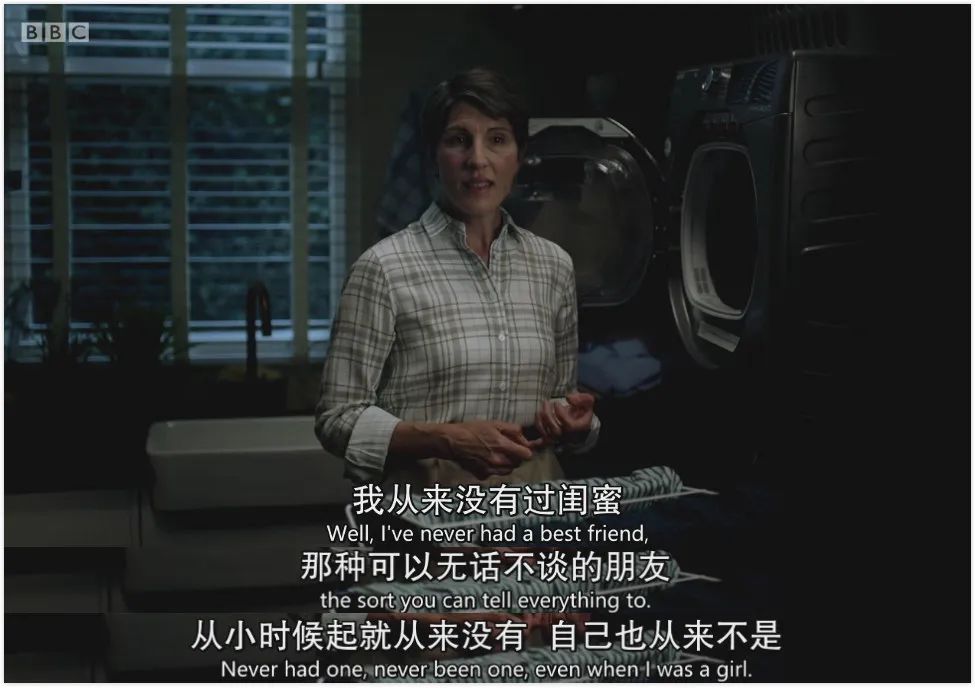
於是,她被那個殺夫的女人吸引了。
她們手挽手逛街,去教堂,照顧花園。
麥太太種出的番茄,她小心嗅着,貼在臉上,無比依戀。
看到這,有沒有覺得莫名熟悉,這不是高配版的“貝絲·安”(《致命女人》)。

開玩笑地説,如果不是疫情影響,這個故事拍成正兒八經的劇,完全可以放進《致命女人》第二季裏。
這部劇十二集,每集一個故事。
每個獵奇的故事背後,充滿悲劇的內核。
每棟不同的房子裏,上演的是不同的人生。
舉步維艱的女演員、內心掙扎的母親、精神病態的兒子、矛盾的主婦、一個可能是戀童癖的男人……
相同的是,每個人都失去了快樂的能力。

比如第一集的魯多克女士。
半遮半掩的小屋,魯多克女士警覺地觀察着窗外,嘴上喋喋不休,一臉憤世嫉俗。
她有太多的不滿,殯儀館有人抽煙,白金漢宮外的人行道有狗屎,她都會寫信投訴。
對面搬來一對夫妻,妻子早出晚歸,還不帶着孩子,
魯女士便惡毒地猜測人家妻子是妓女。
事實上,鄰居只是去醫院照顧得了白血病的孩子。
得知那孩子不幸去世了,魯女士上一秒還得理不饒人,下一秒卻兩眼含淚,雙唇微顫,像一隻鬥敗的雞。
懟天懟地背後,其實沒什麼惡意,不過是對變化的恐懼。
他們嘴裏嘮叨着以前有多好,現在有多糟。
不過是太怕被時代淘汰,太想和周圍的人建立聯繫。
他們只是太孤獨了。
魯女士的小屋只有她自己。
對窗外世界的窺探成了她跟外界唯一的聯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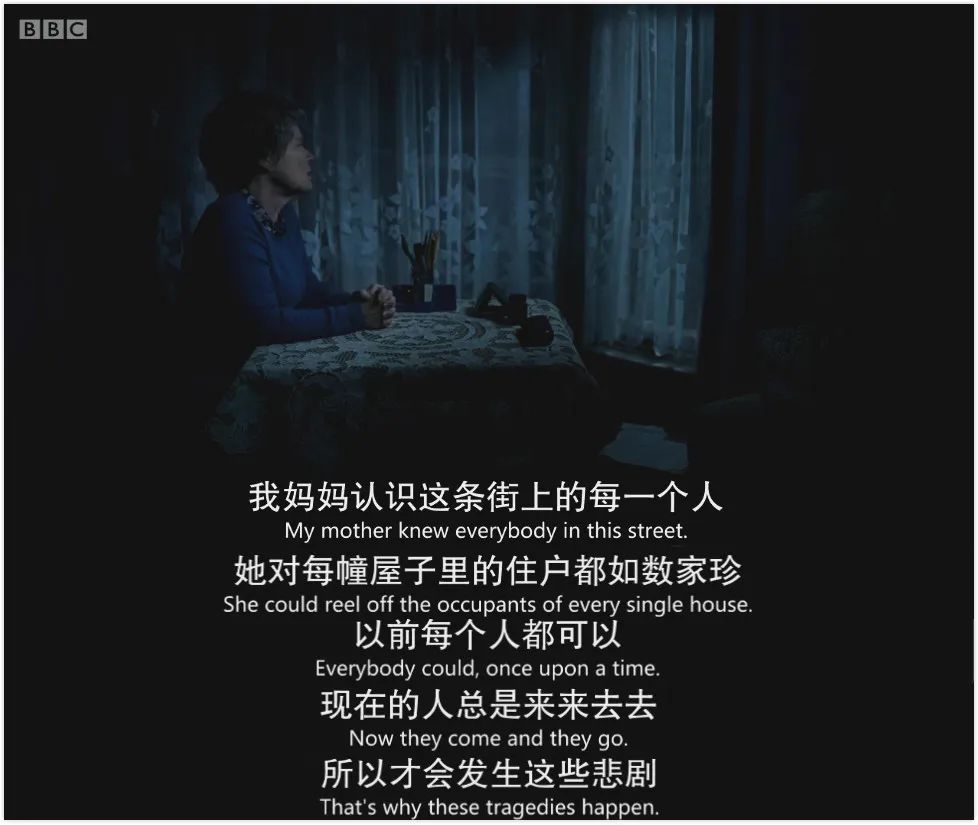
直到不切實際的舉報信,使魯女士入獄,她的生活才真正發生改變。
她的獄友是個真正的妓女,醉酒後失手殺了自己的孩子。
每天有做不完的手工活兒,放到以前,魯女士一定大翻白眼。
可此刻,她從沒笑得如此燦爛過。
再看光影變化。
在小屋時,不論黑白,屋裏好像永遠被陰影籠罩;可在監獄中,窗明几淨,世界大白。

沒有愛的小屋,才是真正的監獄。
而監獄裏,可以隨便寫日記、做手工,朋友的鼓勵、老師的肯定,這才是自由的滋味。
每晚,那個妓女會夢到死去的孩子,尖叫着驚醒,
魯女士會按時坐到她牀邊,拉着她的手。
這一刻,魯女士能聽到午夜時針轉動,風拂樹葉,雨聲沙沙。
她內心平靜,身處牢房,卻無比快樂。
這也許就是被需要的感覺。
影迷圈流行一句話:世界上有三種演員,男演員,女演員,和英國演員。
專業精英的表演訓練、本土戲劇的底藴深厚、演員本身的高素質和文化內涵,
都讓英國演員在影壇異軍突起,他們的演技也得到認可。
而這部重啓劇的參演者,幾乎都是“國寶級”的演員。

獨白劇的形式,對演員要求極高。
朱迪在採訪時就説,自己足足有二十頁的獨白台詞。
一個場景基本上都是**一鏡到底,**意味着演員要吧啦吧啦不間斷地説十幾分鍾。
巨長篇幅的台詞光背下來還不夠。
如何用別人的口吻説話,如何通過細微的表情變化表現出主角心裏的驚濤駭浪。
這都是難題。
比如第6集,馬丁·弗瑞曼模仿健忘症的母親剛和情人約會後的嬌羞。
第9集,霍太太明明心虛,卻還為丈夫辯解,解釋後乾笑了兩聲。
萊斯利談到表演即奉獻時,流下的一滴淚。
演員們彷彿成了劇中人,分享着他們的喜與悲,
也感染着屏幕外的我們,相信這一切真的存在。
但不得不説,這種形式的表演,對觀眾的要求也極高。
大密度的台詞,宛如雅思聽力。
劇情更像一篇篇短篇小説。
所有情節的展開都不是大開大合,而是如冰湖上的裂紋,緩慢蔓延。
初時無法察覺,最後卻能讓整座冰山倒塌。
這就要求觀眾必須全情投入,稍有走神,就可能錯過關鍵信息,看不懂劇情。
疫情之下,電影院關門,新劇新片難拍。
導演和演員們做出種種嘗試,給觀眾產出劇集,無論如何都是應該受到誇獎的。

獨白劇的形式,像是一場圍爐夜話。
爐中燃着的,我們藉以取暖的,正是別人的故事。
從故事裏,我們體驗着未曾經歷過的生活。
借別人的故事,流自己的眼淚;
借我們在故事裏讀到的死亡,來温暖冷得發抖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