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歲的許巍,變了:曾經愛聽許少年,再聽人已到中年……_風聞
最人物-最人物官方账号-记录最真实的人物,品味最温暖的人间2020-07-22 13:23
許巍再也不會追求大紅大紫了。
穿過幽暗的歲月才發現,別人的掌聲會成為牢籠,外界的讚美會成為枷鎖。而所謂的夢想和遠方,跟真實的幸福,永隔一江水。
原來,平淡無奇、不成功、不成名、不抑鬱、不遍體鱗傷,哪怕一無所獲地度過一生,挺好的。
何必仗劍走天涯,天涯就在腳下。
何必追尋詩和遠方,人生的最後一程,總是要回家。

1990年,崔健在西安唱了一首歌,叫《一無所有》。
“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
那是激情又充滿詩意的年代,人們熱愛知識與藝術創作,音樂更是人們表達自我的方式。
中國的搖滾樂,在這樣的環境下應運而生。

嚴肅板着面孔的時代,崔健的陣陣嘶吼讓台下的觀眾陷入了瘋狂中,這其中便有許巍。
他站在人羣中,聽到崔健的一聲吶喊,瞬間戰慄不已,心想:原來歌還能這麼唱!
吶喊過後,有些不可名狀的東西已在少年的內心發生着改變。
22歲這年,許巍感覺生命有股狂熱洶湧而來,當看熱鬧的人羣遠去,他決定用一生的時間去玩搖滾樂。
許巍 現場版《藍蓮花》,燃爆全場

2019年夏天,合肥濱湖國際會展中心場館內,人頭攢動,座無虛席。
上萬人的到來只為一人,他的名字叫許巍。
人羣的嘈雜很快停止,燈光暗了下來,聽眾們都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舞台中央的巨大藍蓮花開始旋轉上升,氣氛靜謐,彷彿大家都在屏住呼吸期待着什麼。
許巍出來了。
眼前的這個男人,看上去平和而淡定。放大的現場鏡頭裏,他的皮膚有些粗糙。
“當我平靜時,我發現這才是正常的狀態。我作為普通人,所有的東西跟別人都是一樣的。”
舞台上,他多數時候彈着吉他淺淺吟唱,唱到盡興處會跑到吉他手李延亮身邊,對彈一段solo,氣氛明媚温暖。
《無盡光芒》中包含10首歌曲,詞曲創作都由許巍一手打造,“有感而發”是他做該專輯的初心,專輯沒有主打歌。
願所有的悲傷
都化成喜悦的力量
就像你愛這世界
你無盡的光芒
當最後一首歌唱完,舞台背景顯示出《無盡光芒》的專輯封面,一輪紅日懸掛在地平線上。

全場大合唱的時候,鏡頭隨機給觀眾特寫。很多人的穿着都“不夠搖滾”,甚至有些普通,從高處看去,一片光海。
沒有人站起來,沒有人説許巍牛逼,沒有人喊搖滾不死……
一切都在靜靜流淌着,回韻悠長。
其實2012年到2018年這六年時間裏,許巍並沒有閒着,創作無時無刻都在進行。
新專輯裏10首歌的靈感出現在車上、飛機上、火車上……只要有感覺,任何時候他都可以創作。
曾夢想仗劍走天涯的少年,如今也行盡天涯靜默山水間,歸順於平淡的生活,追尋着那道屬於自己的光芒。
他像毛姆筆下的查爾斯,“滿地都是六便士,他卻抬頭看見了月亮。”


可33年前的許巍,並未如此平和。
“我覺得我一定要做崔健這樣的音樂,我要像他一樣,我不知道我有沒有這個能力,但我想嘗試。”
18歲之前的許巍,是反叛的。他拒絕生活在父母的期望裏,考上大學,進中科院是父母給他定下的目標。
可許巍只想一心做音樂,和所有想要表達自我的年輕人一樣,他也買了一把吉他。
在高考前,他揹着吉他離家出走了,開始了走穴演出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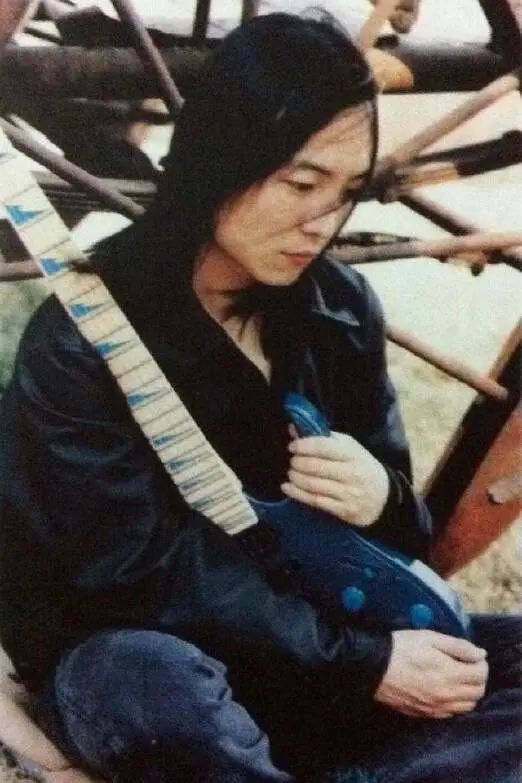
從福建到廣州,許巍跟着搬運工人一起坐大卡車,又要幫着搬樂器。
從晚上八點到凌晨四點,當天演出完連夜拆台,再坐大卡車去下一個縣城搭台。
選擇夢想像是選擇了一種困窘,餓的時候一天吃一頓。那年他18歲,不曾覺得痛苦。
許巍把那段日子,看成是動盪的歲月。
之後的他在西安組建了自己的樂隊,取名叫“飛”。同年12月,他們舉行了首次公演,獲得不錯的反響。

飛樂隊 許巍(左2)
遺憾的是,儘管人們對這個年輕的樂隊一度充滿了期待,他們還是解散了。
解散的原因很現實,連飯都吃不上了,還談什麼音樂與夢想。
原本五人的樂隊,最後就剩許巍一人。他陷入苦悶之中,在一種極度無奈和近乎絕望的心境下,寫出兩首作品《兩天》和《青鳥》。
“我只有兩天,我從沒有把握
一天用來出生,一天用來死亡
我只有兩天,我從沒有把握
一天用來希望,一天用來絕望”
粗糲的躁動中,是迷茫與不甘。
1994年,許巍帶着這兩首歌的小樣,去往北京,他相信自己可以成為崔健那樣的搖滾歌手。
很快,紅星音樂生產社簽下了許巍。
他的《兩天》與崔健的《一無所有》一起被收入《中國當代詩歌文選》。

正在他意氣風發,紅星音樂的老闆陳健添,跑過來跟他説:“你形象一般,你不像鄭鈞那麼偶像,想要把你捧紅太難,而且你的音樂太另類了。”
這一年,竇唯、張楚和何勇作為魔巖三傑,在香港紅磡鬧出了大動靜。
黑豹的“穿刺行動”也開始巡演,崔健早已遠赴柏林,大談《一塊紅布》時説:“藝術沒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責任。”
而彼時的許巍,還是一個寄人籬下的北漂。
1997年,在北京西郊一個6平米的宿舍裏,他寫出了第一張正式專輯《在別處》。
在這張專輯的名單中,我們能看到許多響亮的名字:製作人張亞東,吉他手李延亮,鼓手趙牧陽……
當時竇唯、高曉松都在錄音棚外頭看:這哥們太牛逼了。
樂評人李皖將《在別處》視為當時最吵鬧的中國猛樂,又厚又重的噪音流,足以把中國土搖青年震成傻逼。

可這終究是少數人的狂歡,這張專輯並沒有掀起多大的浪花。
對許巍來説,生存仍是一個無法迴避的難題。
那年,他29歲。

許巍在重重的打擊與壓力之下,得了抑鬱症。每晚都失眠,要靠安眠藥度日。
走在唱片店裏,看着一百塊錢的原版CD,他非常想聽,可是根本買不起。
最慘的時候,他為了付房租,將自己最心愛的電吉他賣了,一轉身就淚如雨下。吃了上頓沒下頓的生活,折騰下來,讓許巍徹底迷失。
在生存面前那純潔的理想,原來是那麼脆弱不堪。
那段日子,鄭鈞和葉蓓常常給他打電話:“你需要錢嗎?”許巍總説不要。
2000年,他靠吃藥錄製了第二張專輯《那一年》,反響依舊平平。

許巍和紅星社最終解約,頭也不回地回到了故鄉西安。
這麼多年,搖滾歌手的理想,推着他不斷往前走,突然就消失不見,人生的全部支撐都崩塌了。
在最為抑鬱的日子裏,他多次想從樓上跳下去,結束一切。
“你每天要和一萬個要自殺的念頭去作鬥爭,再用一萬零一個念頭去戰勝它”。
他總是忍不住和父母交代後事,那時候許巍對生活失去了信心,以為真的過不去了。

還好在最低迷的時候,有家人的陪伴。
一天,許巍獨自走在西安的街上,突然聽到天橋下的流浪歌手在唱自己的歌,深情而真摯。
他聽完,紅着眼睛走了。
也是在那個時候,他開始反思自己:為什麼我就不能老老實實過日子?為什麼我從小到大,就一定要成為一個什麼什麼人?
許巍開始學習傳統文化,研讀歷史,每天準時起牀,堅持鍛鍊。
他嘗試在創作裏滲透禪意,後來又從論語、中庸、道德經一直到佛經、佛法,認真研究。
最終,佛教的信仰給他帶去深刻的轉變,“它讓我走過去,三十歲,我會反思自己,看到太多問題,就開始自省了。”
許巍自我救贖後,放下成功的執念,決定做個普通人,挺好。

放過自己後,他聽披頭士,感受到音樂的力量不再是之前的鋒利與控訴。音樂是可以救人的,它成為一種救贖,它救了他。
2000年,宋柯給他打電話,讓他回來幫葉蓓的新專輯《雙魚》做製作。
許巍輕鬆地重回北京,也在2002年出了自己的第三張專輯《時光漫步》。
彼時的他紮起長髮,穿着牛仔褲,臉上有了温暖的笑。
“沒有什麼能夠阻擋,你對自由的嚮往
天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無牽掛
穿過幽暗的歲月,也曾感到彷徨
當你低頭的瞬間,才發覺腳下的路”
《時光漫步》這張專輯一經發行,讓許巍火得一塌糊塗。

那首《藍蓮花》傳唱度極高,成為了經典。
在外人看來,一度頹敗的許巍,終於迎來了事業的巔峯。
在鄭鈞、老狼、朴樹、葉蓓等民謠和搖滾歌手都還在賣力做唱片的年代,許巍不僅沒被市場淹沒,反而站穩了腳跟。
他不需要佶屈聱牙的字句,用平實無華的歌詞與曲調就能將聽眾們吸引。
最終能幫到許巍的,還是音樂。
他那顆對音樂赤誠的心,從來不曾改變過。


2005年8月13日,北京工人體育館。
這是許巍首次大型個人演唱會,台上的人露着靦腆的微笑,台下的人等了十年。
當揹着吉他的許巍望向萬人的場地座無虛席的時候,笑得像孩子一樣開心,他在26首歌裏唱完了自己過去的十年。
“我覺得跟做夢一樣。”

那晚,崔健也在現場。
很多年以來,許巍都在埋頭做自己的事情,不管喜怒哀樂都是自己在折騰。
突然有一天他要開演唱會了,才反應過來,原來有那麼多的人在和他一起成長。
那一刻,他不覺得孤獨了。
後來,他説:
“很多東西突然在改變是因為從原來一個文藝青年或者説覺得自己是藝術家什麼的,突然心態有改變,就是其實我是一個老百姓,我就是一普通人。”
七年後,許巍活得更為透徹了,他寫了一首《空谷幽蘭》,字裏行間滿是禪意。
在對生活有了深刻感受後,許巍開始歌唱外界萬物,詞曲裏少了偏執,多了些對過往歲月回望的赤誠。
唱歌的人釋懷了,可搖滾青年們的臉上露出失望的神情,甚至有人開始罵他是搖滾叛徒。
他們覺得許巍變了,不再吶喊的作品變得像背景音樂。
對此,許巍説:
“一個人連生活都成問題了,你還指望他去聽搖滾?背景音樂挺好的,可以讓我的心靈變得很舒緩,同時讓我很放鬆,我可以安心做自己的事情。”

時至今日,外界對他的音樂“是否搖滾”仍在爭辯。
爭議還在繼續着,而許巍已默默走到了更遠的地方。
那個地方,是自己的內心,他不再向外界索取。
2014年,許巍開啓了英倫之行。
也是在那年,他將一個刻有“許巍xuwei”字樣的磚頭,鑲在利物浦洞窟酒吧的名人牆上。
這個酒吧,是披頭士樂隊的成名之地。而許巍,成為了這面名人牆上的第一位中國音樂人。



2013年高曉松創作了一首歌,名叫《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他寫完後,覺得只有許巍可以將這首歌唱出它應有的味道,然後把稿子放在一邊。
高曉松覺得作品寫完之後,如果過了一年還能再想起來,就證明這首歌還不錯。
2016年初,高曉松想起了那首歌,最終由許巍演唱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這是他第一次唱由其他人創作的音樂作品。
有聽眾聽這首歌時,一直期待着高潮,聽到最後才發現沒有高音。
生活本就是平淡,雖不止眼前的苟且,但也要默默追逐自己耀眼的瞬間。
這年,有人問了許巍一個問題:假如穿越回二十年前,會對那時候的自己説什麼?
許巍回答:“玩開心點,愛誰誰。”
如今的他在北京西郊農村,租了一個果園,住在裏面專心做自己的音樂。
他越來越喜歡清靜了,鮮少去人多的地方。每天在家中寫歌,讀書,不再輕易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聽眾們早已放棄捕捉許巍的日常生活,他不用微博,也不參加綜藝,不領獎,不接受羣訪。
在真人秀場,前輩們被請去綜藝裏重新發光發熱,為鮮肉保駕護航。大師出山,既搶手又場面。
這些他都明白,卻依然拒絕。

吉他手李延亮説:“這是種精神潔癖,他覺得不好的東西,會選擇躲避。”
有些事,不是不會做,是不願意。
一個能把全場幾萬人唱得熱血沸騰的男人,卻無法在鏡頭前流暢地講幾句場面話,這是許巍的選擇。
面對如此平淡悠然的日子,他很滿足:
人生三大悲,少年得志,中年失業,晚年入花叢。還好,我都沒有。

這幾年,他反覆觀看《我在故宮修文物》這部紀錄片,裏面的師傅在離開工作之後就過着平淡的日子。
這類似他當下的狀態,不疾不徐。
許巍每天看日出、喝茶、彈琴,研究佛家文化。他以一個音樂人,而不是流行歌手或搖滾明星的身份,認真生活着。
生活中的許巍比普通人還普通。
個子不高,長相平平,板正的寸頭,面對鏡頭緊張到不行。把這樣的許巍丟進人海,真的會瞬間“悄然無蹤影”。
可是這樣一個人,拿起來吉他,就像變了一個人,他的身上有光。

“所有人在年輕時最好有點理想,而年紀大一點的時候也要保持一顆少年的心,不要到了年紀就老氣橫秋。”
2020年7月21日這天,許巍52歲了。和二十多歲的時候一樣,他唱的還是自己。
只不過他早已從過去的悲傷,轉變成了現在的平靜,詮釋出自己的慈悲。
在一些許巍的鐵粉看來,許巍依舊是個少年,他們稱他為“許少年”,覺得他還有一顆赤子之心。
其實暌違已久歸來,許巍不再是少年,卻也不是庸常的中年人。


2019年,許巍出了新專輯《無盡光芒》。
唱片封面寫着:這個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那就是認清了生活的真相後依然熱愛生活。
這或許也是彼時,他的心境。
經歷了青年到中年,如今的許巍大隱隱於市,沉浸在充滿禪意的音樂世界裏,褪去了《在別處》裏的迷茫,迎來了《無盡光芒》裏的温暖。

不知他是否還會想到1991年,自己拒絕了第四軍醫大學的保送名額。
那時,他找領導們解釋:“我要做崔健那樣的人,崔健特別棒,很厲害,是中國最牛逼的……”
他們當然不會理解,且反問他:“你確定你能成為崔健嗎?”
30年時間匆匆而過,讓人猝不及防。在嘗過苦樂悲歡後,他沒有成為崔健,穿過幽暗的歲月,他成為了自己。
在曠野,那些惶然與不甘都已遠離,剩下的只有靜謐,許巍終於可以睡得好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