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邊芹唯一專訪,觀察者網獨家發放_風聞
西昌学院南校区学生时评-2020-08-18 22:18
受訪人/邊芹 採訪人/燕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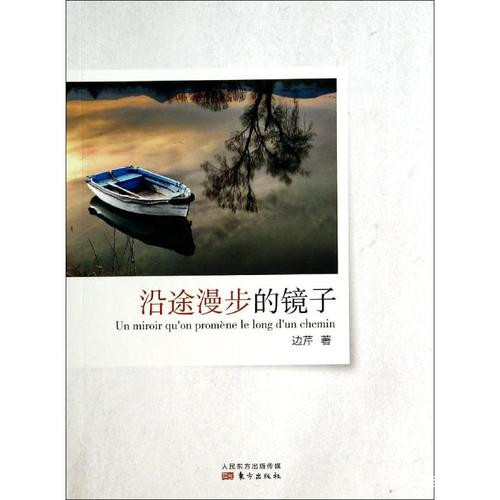
2005年7月上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了旅法作家邊芹女士的《一面沿途漫步的鏡子》。這個化用自司湯達(他曾有言“小説是一面沿途漫步的鏡子”)的書名,在中法文化年如火如荼應時書籍眼花繚亂的背景下,卻以異乎尋常的魔力抓住了筆者挑剔而疲憊的眼睛。早在邊芹的隨筆在上海一家雜誌以專欄形式刊發時,筆者就為其獨到的人文眼光而吸引。這部隨筆並不亞於林達夫婦當年炙手可熱的《帶一本書去巴黎》和“近距離看美國”系列,但審慎的出版社還是把該書列入長銷書計劃。
邊芹既是作家,也是翻譯家。由於去國多年,讀過她翻譯的《直布羅陀水手》和《廣島之戀》(同屬春風文藝出版社版《杜拉斯文集》)的國內讀者,還在上海譯文出版社的網絡談論裏討論着“誰是邊芹”。
藉着邊芹新書出版的機會,筆者通過電子郵件採訪了遠在巴黎的邊芹。由於邊芹太過低調,筆者在聯繫採訪的郵件裏只好懇切地慫恿她:“我以讀者的名義請教您”,沒想到她愉快地接受了訪問,“不管你以什麼身份提上述問題,我既然答覆你,就是認真的,也希望你能把我的思想完整表達出來,避免‘斷章取義’。這是我唯一的要求”,“看得出你是一個像海綿一樣吸食這個世界的青年,不回答你,是殘忍的。”雖然未曾謀面,但就《一面沿途漫步的鏡子》本身和中國人對法國、巴黎文化的想像以及法國文學的翻譯等話題的交流短暫而愉快。讓筆者感動的是,回答“您相信‘宿命’”的問題時,邊芹告訴我“這個問題本身就是要讓人流淚的”,她的真誠讓我確信這個訪談是有趣的。我一直避免“相信”這個詞。
問:斷斷續續拜讀您《一面沿途漫步的鏡子》中的文字,我容易把您和《帶一本書去巴黎》的作者林達夫婦對比(而且他們帶的那本《九三年》的譯者正好也是您的公公鄭永慧先生),也會聯想起上海作家餘秋雨早年讓我喜歡的《文化苦旅》。如果將您的大作冠以“人文隨筆”或“歷史文化散文”一類的稱謂,您介意麼【也許您的回答是“稱謂並不重要,重要的是……”】?
邊芹:我不介意你給我的文字什麼稱謂,我想最終它們還是文學範疇的。
問:如果您讀過林達、餘秋雨,我也想聽聽您對他們文本本身的看法。
邊芹:你説的“文本本身”是指什麼?思想性?文學性?林達的東西屬於隨筆外殼下的政治,你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在某一歷史時期同意,在另一歷史時期不同意。餘秋雨則屬於文學範疇,那就是對文字喜歡或不喜歡的問題了。
問:《一面沿途漫步的鏡子》的序言中,您感慨“人的演變常常是徒勞無功的”,這種告別進化論崇拜的“保守”和人到中年後的心態有關係麼?“三十歲前不是激進派沒出息,三十歲後還是激進派照樣沒有出息”,幾乎成為我們理解所謂“保守”和“平和”的陳詞濫調,您也是這樣認為的麼?
邊芹:我個人認為這恐怕來自我對歷史的觀察,不是五十年或一百年的歷史,而是更長。 但年齡有沒有起作用,則是一個問題: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在這個問題上永遠達不成一致的意見。何況不激進並不意味着保守,保守也不意味着不激進。如果你曾試着改變一個人,你便明白我説的“徒勞無功”是指什麼。我們中國人凡事都是不切實際的,喜歡從大處着眼,永遠認為問題在上面。
問:冒昧地問,您相信“宿命”麼?
邊芹:你問我相信不相信“宿命”,這個問題本身就是要讓人流淚的。我一直避免“相信”這個詞,在後面的名詞沒有説出來之前,單前面這個動詞,就是很多偏見的開始。清醒不一定是宿命論者,宿命論者也不一定清醒。但清醒是命運的懲罰,這是逃不掉的。是夢,遲早都要破碎。
問:遊走於東西方之間,談談東西方(中法)文化異同的觀感總是難免的?五年前您在《人民日報》的專欄《人情之別》中談到:“總的來説,生活在中國,人情太累。生活在法國,總有一種孤零零的感覺。”五年後是不是有更新更深的體會,能否在“人情”之外的角度談談這種文化差異(當然歡迎您的舉例了)?
邊芹:《人情之別》寫得很早,屬於浮光掠影的觀察,不值一提。但的確可以作為思考東西文化之別的一個切入點。文化來自哪裏?來自我們的天性。中國人是多情善感的,喜歡被人感動,也喜歡感動別人,這是我們文化的根脈,很難斬斷,除非全民換血,或與另一人種雜交。
問:國人往往容易陷入盲目的文化自卑。而您在《鏡子》序言中也説過,“那時候,歐洲人想罵政府或罵教會,有什麼不便或不敢説的話,便借中國人來説。可見‘借刀殺人’每個民族都在行。伏爾泰是藉此路走得最遠的。比如他對天主教不滿,便搬出中國人來反。”這種文化平視的自信是如何得來的,是不是因為身臨其境的和對歷史的整體觀照所致?
邊芹:我只是很遺憾地發現沒有神話,既然沒有神話,失去分寸地堅信,就使你相信的東西變成了宗教,而這是危險的。中國人習慣於不黑即白的思維方式,好幻想,這不是幾場革命,幾次流血可以改變的。如果我提前打碎了很多人的夢,只是我沒有把握好時機。是夢,遲早都要破碎。文化有雅俗,有進化的早與晚,但沒有優劣,因為人説到底是同一種動物。
問:在不侵犯您隱私的情況下我想請問,您選擇居住巴黎的原因是,您和您先生這一代人是不是受1960年代的那種“革命”記憶影響很大?具體的説,您來巴黎是哪一年,除了偶爾回國探親是不是長期定居巴黎?
邊芹:不是故意擺架子,是實在不想存活在文字之外,我只是我思想的影子,除此之外,我與無我,沒有什麼兩樣。揭開私生活的一角,和全面揭開,也沒什麼兩樣。西方人只認“征服”這兩個字。
問:“浪漫”幾乎是國人提到巴黎和法國的第一印象,這想必是不全面的,您覺得巴黎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特質?
邊芹:每一種文化傳統都大致能提供一兩個這類概括性的名詞,既然是概括性的名詞,就很難是全面的。但旅遊文化需要這種“明信片”。關於巴黎的氣質,我在本書《尋找海明威》和《詩人的夢想》兩文中,試圖擺脱“明信片”效果解釋一番,不知做到了多少。三言兩語説不清,在此不細説了。
問:在巴黎,文化和藝術是不是比別的國家和城市更密切地融入日常生活中?瞭解原汁原味兒的巴黎有哪些可靠的途徑,比如咖啡館或者……?中法文化年如火如荼地進行,國內一些論者就認為中國政府行為式的文化輸出和交流缺乏生命力,您能同意嗎?
邊芹:我只能把我看到的一面告訴你。我在外看到的是,中國人在這次難得的文化輸出中,商業算計和意識形態宣傳的痕跡,遠不如法國人走得遠。法國人並不孜孜以求地把最好的東西拿給你看,因為他不需要你的承認;而是把他認為應該拿給你看的東西拿過來,來影響你。歸根到底,他要的是你的市場。理解西方人,有一個詞不可忽略,那就是“征服”,西方人只認這兩個字。中國人則喜歡送“禮”,在很多事上其實都是這種操作方式。中國人現在看世界(主要是看西方)都戴着玫瑰色放大鏡,所以法國的過氣人物全都想往東方跑,以重拾往日的輝煌。中法文化年,我們是把最好的拿去,法國人可不是這樣,他們是把想給你看的東西拿來。而且拿什麼來不是國家行為,全靠想來的人的鑽營本領。前不久作為文化年項目在紫禁城搞音樂會的讓-米歇爾·雅爾就是個過氣人物,靠乃父的名聲搞現代音樂一度紅過,才華不大全靠製造花邊新聞的本事充填,在法國文化界名聲不説“臭”,至少也是不“香”。文化年全送出這種項目,歸根到底是法國人的文化自大,“送去更好的,你們欣賞得了嗎?”法國人連向中國輸出香水,都強調先要教育中國人學會欣賞香水。這是他們內心不説出的話,但做起來都以這個為標準。至於哪一種輸出方式更有生命力,目前還很難判斷,文化演變得自於一盤菜還是一場音樂會,還真難説。最後是善打小算盤的贏,還是不打算盤的贏,也很難説。只能走着看。看,不等於看見。
問: 法國文化對中國知識分子應該是影響最大的異域文化,上海學者朱學勤在其博士論文《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中多有反思,您結合您切身的體驗認為有哪些需要反思的地方?
邊芹:很遺憾沒有讀過朱先生的這本書,沒有發言權。要説反思,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就時斷時續地開始了反思,多半是歇斯底里的,因為被列強打得抬不起頭。歇斯底里的結果,是各種觀點在水面上打來打去,而且只在上面打。比如為要不要民主打,好像你只要要,拿來就行了。從不先想想民主究竟是什麼。單把“德先生”譯成“民主”,誤解就開始了。殊不知“democracy”在西方從來就是上層精英階層極其聰明的統治術,有一整套的避免走極端的控制系統,遠不是我們在譯成“民主”後,以我們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加進去的“平民主義”、“平等主義”和“造反有理”之類的東西。單從這一點講,我就是悲觀的,我認為文化交流的終點站是誤會。
問: 大作中《尋找海明威》、《先賢祠裏的兩個死對頭》、《蒙莫朗希和一個人的影子》及《聖夏芒的死亡火車站》等篇目是我格外喜歡的。您在《尋找海明威》中提出“一個人與一座城市分手後的結果”的問題,還想像“海明威時代,也就是20年代初,這裏每天早上都有牧羊人趕着羊羣經過。住在擁擠的小樓裏的房客,會拿着杯子下樓,拉住一頭羊擠上一杯奶,再放幾個生丁在牧羊人的手裏。這是海明威每天早上打開74號四樓的窗户即可看到的景象。”這種引人入勝的“合理想像”是為了配合“發思古之幽情”的麼?行走就真的如此有效地提升了作家的思考層面嗎,還是這些耐人尋味的話題更多是您閲讀的結果?
邊芹:請允許我首先強調,這並非“合理想像”,而是確有其事,海明威自己回憶過。在這系列文章中,我不允許自己為“發思古之幽情”而“合理想像”。這畢竟不是小説創作,除了我的議論,記實部分均有出處。行走可能能讓我們丟掉一些框框和偏見,但提升不了思考層面。看,不等於看見。閲讀的確是逃避自身煩惱的一個辦法。但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因此而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堅持獨立人格才是關鍵,但難於上青天,因為這意味着巨大犧牲:作永遠的遲到者;靈魂死亡三次;可能從此斷氣。麼?行走就真的如此有效地提升了作家的思考層面嗎,還是這些耐人尋味的話題更多是您閲讀的結果?
問:您説“在產生情感那一刻真誠與否,文字是掩飾不住的,在其前或在其後則是另外一回事。”我拜讀您的文字,往往感覺有人到中年的徹悟或者説準徹悟或者一點點的哀傷或者將要看破紅塵的豁達、不屑,是這樣麼?
邊芹:我用帕斯卡爾在他的《思想錄》裏説過的一句話回答你:“我會讓那些我使之產生慾望的人上當的。”我早已決定不再翻譯。
問:春風文藝出版社的《杜拉斯文集》中,您翻譯的《直布羅陀水手》和《廣島之戀》的主題都和“愛情”有關,能否説“愛情”是您文學翻譯中的一個重心,是您觀照這個世界的一個重要的維度?
邊芹:翻譯有關愛情的書,只是偶然。翻譯選材上我並沒有多大發言權,我只是出版社聘用的工具。至於是否以“愛情”來觀照這個世界,這可能是文人逃避不了的。文人都是精神病患者,情感世界的缺失者。他們尋找最美的東西,大概只有愛情能提供一點點幻覺。
問:在您翻譯的《植物之美》的序言中您説:“我們最多一百年的生命,與壽命達幾千年、幾百年的植物,不可同日而語。加利福尼亞松樹活了將近五千年;最新發現的羽扁豆種子已有一萬年的歷史,居然發了芽;而鈴蘭幾乎是永生的。它們才是地球歷史的真正的見證人。”這種敬畏之心和反人類中心主義的自覺也和年歲漸長有關麼?
邊芹:《植物之美》是別人翻譯的,我只是寫了一個序。我無意反人類中心主義,我沒有力量反,人類已經不可避免地成為這顆星球的主子,不知恐龍作主子的時代,地球是不是幸運一點。我只是希望人能時不時地換一個視角看問題,在別的物種面前謙卑一點。比如砍掉一棵樹的時候,自然不必經過樹的點頭,但至少問一問自己的良心。
問:您的翻譯作品粗粗分了兩大類,一類是文學作品,一類是《謠言》、《虛偽者的狂歡節》這樣的學術作品,是不是更偏愛文學作品的翻譯一點?《植物之美》劃分到學術類中合適嗎? 又提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請講講您的“翻譯觀”。翻譯《一個陌生人的畫像》時您説,“但譯這本書,你絲毫得不到這種宣泄,因為你走進了人的精神世界的迷宮”,這種痛苦體驗在您的翻譯中應該比較少見吧?一個您和先生、公公組成的翻譯世家的書香氣息是不是足以讓您感受到平淡生活的幸福?
邊芹:我的翻譯作品不多,真正屬於我獨自翻譯的更少。《直布羅陀水手》是我最滿意的,也是我的封筆之作。我早已決定不再翻譯,因為我們已經進入了翻譯的魚龍混珠時代。至於你問我“來自翻譯世家”是否“足以讓我感到平淡生活的幸福”?我直接了當回答你:這個世界沒有一處地方足以讓我感到平淡生活的幸福。平淡意味着生與死是一條直線,那樣等待將是無窮無盡的。
問:在國內偶爾看到您和您先生就嘎那電影節或者龔古爾文學獎發表看法,電影是您寫作和翻譯生活外的一個重要調劑?
邊芹:你能看到的那些電影稿,都是應景之作,不值一提。電影的確是我偶爾“逃學”的一個去處。何況電影在這個時代已經部分取代了文學。謝謝你的誠懇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