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頑童」李安的困惑_風聞
娱乐产业-娱乐产业官方账号-带你了解行业的“热点”“盲点”“痛点”2020-08-27 07:33
作者 / 耿凌波
第十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大師班”開講時,美國已經臨近午夜,頂着12小時時差,李安如約上線,屏幕上的他穿着舊的藍襯衫,頭髮已經花白了,顯得有些憔悴,儘管如此,面對現場頻頻拋出的“一個導演應該具備怎樣的專業知識?”“你對自己作品中的父親有什麼新解讀嗎?”等基礎問題,他依然耐心、認真作答。
這是北京電影節首次開設大師班,也恰好是李安從影第三十個年頭。受到新冠疫情影響,李安只能通過線上連線的方式與觀眾交流,但現場依然人頭竄動,還有更多影迷聚集在網絡上,實時關注着這場分享會的進程。兩個小時的交流中,李安圍繞“東方表達與數字技術”的主題,講述了他執導筒多年的創作體悟,分享了他理解的技術形式與藝術表達的關係,同時也回應了對電影改革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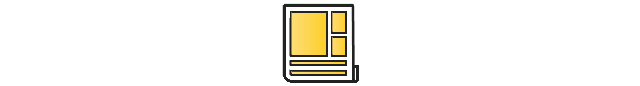
疫情加速行業變革
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讓全球電影業都受到不小衝擊,在李安看來,電影業要恢復,局勢上非常困難,生意上也是。
他所在的製作端,也能感受到拍攝受到影響,“我們拍片的話,幾百個人要到處跑來跑去,但是現在這變成一件非常困難的事”。而放映端承受的打擊則是分層的,“高端的影院可能會有生意,就是説你有特別好的銀幕,特別好的放映條件,這樣的還可以生存,一般的影院就比較困難。”
同時大家還普遍面對的一個衝擊,就是流媒體對觀眾的分流,“疫情期間觀眾一直在家裏看電影,他養成習慣以後,再回去影院是很扭轉的”,李安坦言。
正因如此,他表示,疫情或許會加速電影改革時代的到來。“毫無疑問(流媒體)看電影的方式更方便,也會更流行”,但電影從業者也沒必要恐慌,李安建議大家放平心態、接受挑戰。“誰也做不到,逼着觀眾進入電影院,你只能給他誘因,讓他感覺值得進電影院。”
“如果你做的東西和他在家裏看的一樣,甚至還沒有那個好的話,你就不能怪觀眾宅在家裏。創作者只有自己努力,努力創造新的影像、新的故事,創造在平台、在家裏沒辦法體驗的內容,當電影可以做到比真的東西還真的時候,那可能它的這種方式就會被革命性的改變”,而觀眾也可能重回電影院。
現場他提出假設,“未來很多年輕朋友再拍電影,可能就不是現在這樣,一個一個景這麼拍,可能要接近動畫,又可能會更真實。”而這樣的行業背景下,也更顯得李安一直以來在技術上的探索已然迫在眉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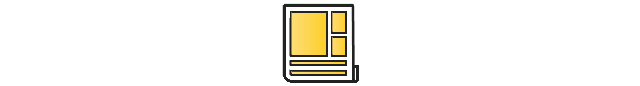
技術讓電影表達更自由
從《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開始嘗試3D技術,到《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雙子殺手》首次應用4K、120幀,李安就被貼上了“技術控”的標籤,但在他自己看來,“我其實對科技一點都不熟,電話我只會打出去,其它的什麼都不會”,他將自己定義為“老式電影拍攝者”,追求新技術,只是為了讓電影在表達上更自由。
比如拍攝《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李安遇到哲學上的思考不知如何突破,於是就有想到了利用3D來增加一個視角空間,突破想要表達的題材,“我知道電影必須要靠媒體才能把內心世界將心比心地傳達給觀眾,不管這個媒體是繪畫、文字、膠片、數碼,立體的還是平面的,直接的還是間接的,它就是你的依靠”。
電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劇照
技術提供了新的可能,讓觀眾看到更多。用李安的話來説,新技術的應用催生了新的電影美學標準的建立。與傳統影像相比,應用了新技術的影像會更加清晰,觀眾對信息的要求也會更加豐厚,隨之,對演員的表演、藝術的層次、拍攝的方式等也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比如,過去遵循西方戲劇所誕生的“三幕戲”的敍事方式下,演員的表演會相對誇張一些,立體感的呈現,是依靠燈光、攝影、道具、化妝等外在形式綜合作用下呈現出來的;
而應用的新技術的銀幕,觀眾看得更真切,則要求演員的表演方式也必須更精緻、更含蓄,光有一個故事去表達出來還不夠。角色的內心世界、他的衝突,都要能夠一層一層透過表演表達出來,甚至是演員在無意識的狀態裏透露一種捉摸不定的東西,也需要攝影師捕捉下來。
但當主持人問道:未來拍電影是否會優先考慮技術?李安當即給出了否定的回覆,“還是看我想表達什麼,不管你用什麼樣的藝術形式,數碼也好、影視也好,它都是一種媒介。你怎麼表達內心的景觀,你要跟大家分享什麼,這才是重要的。”
同時,李安也坦言,對於新技術的探索,整個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我自從接觸數碼和3D以後,我整個人對世界影像的解析,整個心理過程需要一個調試。開始的時候很難做,過程中也曾受過很多的打擊。”
大師班現場,李安提到拍攝《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他第一次接觸到“立體”的感覺,“拍到一半的時候,我發現很糟糕,因為我依靠的媒體,等於是我的信仰,突然之間好像瓦解了”,他形容當時的自己“和少年派沒有什麼差別,和一個老虎在小舟上漂流,很恐懼的感覺。”
而除卻這些拍攝過程中特別具象的困難,李安還要面對來自電影工業界和觀影文化的阻力,“電影工業是一個固定的形態,要顛覆非常困難,一個人是扭不過機器的,胳膊是擰不過大腿的,所以有時候吃了很多暗虧,很多血淚往肚子裏裝,很難和人家講為什麼走不通,為什麼會拍攝變成那個樣子”。
儘管如此,他表示依然會堅持下去,“現在,等於是在摸着石頭過河,我用10年拍了兩部,後面還有計劃,我覺得我還在一個初步的學習階段。我會繼續努力,繼續去研發這種東西,因為現在,從我腦子裏面的影像來看,(應用新技術的)電影已經是這麼回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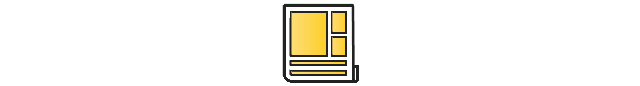
電影越拍越困惑才越有意思
眾所周知,李安是一個將東西方文化融合地特別好的導演,現場他也分享了對東西方文化的看法,“我個人感覺在東方,尤其是東亞這一塊,之前是幾千年農業社會的文化形態,敬畏天地、尊重團體,人會思考怎樣能融入這樣的社會,怎樣能有序地生存,是大家關心的問題…東方是非常講意境的,在有意和無意之間有一個似有似無的東西”。
“而西方可能和他們的遊牧民族有關,征服性、侵略性比較強,個人想決定怎麼改變世界。尤其是美國,是一個新大陸,在建國的時候,就把個人的意志放在很前面”。
因此,在拍電影的時候,“我們會吃一點虧,因為他們的故事有衝突,結構有一定起承轉合,全世界也看得非常習慣。現在講我們東方要怎麼樣融入或者改變它,我覺得新技術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怎麼把我們習慣的、我們擅長的東西,比如意境、似有似無的結構,還有崇敬天地的感覺表達出來,我覺得是蠻有機會的”。
但在面向全球市場的同時,李安也曾面對着無數挑戰:
我開始拍片的時候,資金都不大,雖然是美國片、英國片,但也算不上特別好萊塢,所以自由度也還可以。但在我拍完《卧虎藏龍》以後,算真的進入了好萊塢。這個時候就會面對比較多觀眾,而他的觀影習慣、觀影特點,也都需要去注意,常常會出現,跟你心裏想表達的東西不太一樣的情況,你要去調和,但那個過程不太容易。
電影《卧虎藏龍》劇照
尤其現在好萊塢的工業體系越來越成熟,觀眾會給你很多意見,這個真的很難應付。關於你應該怎麼樣拍電影這件事,常常會有外行領導內行的情況,那個對我來講是蠻大的困惑。
儘管,像李安這樣,用西方的電影語言講述東方哲學意味的故事,實現起來非常困難。但他卻總能成功,用他自己的話來説,或許是因為,做電影的人都有一個“殺手本能”,“我也常常會膽怯,只是那個害怕程度沒有那個渴望去做、放手去做的那種心理那麼強烈”。
因此,李安逐漸領會了在好萊塢工業體系下的生存法則,“你身處這個電影工業當中,不用類型根本沒辦法和人家溝通。畢竟電影工業已經存在了100年的時間,各方面都已經很成熟了,包括類型、表達,它都有一個格式在裏面,你的電影也很容易歸納到這個格式裏面”。
除此之外,還要學會考慮觀眾的觀影習慣,他們對各種類型有不同的體會,心理活動也會有不同的軌道,在電影的兩個小時裏面,你要保證只有一個敍事性,把旁邊不相干的東西除掉,讓它單純一點,這樣觀眾才能夠跟隨你的故事,去做一個情感的啓發。
這正應了李安自己對電影的理解,“電影不是在説人生該怎麼樣,而是把這些東西用電影的形式誠懇地表達出來,讓大家共同體驗、共同交流、啓發思路。”正因如此,李安覺得:“我的電影越拍越困惑,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