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座談為何請鄭永年: “假裝100%中立不可能, 做智庫關鍵是説真話”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0-08-30 18:45
《文化縱橫》2020年8月新刊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 鄭永年
✪ 高淵(採訪)
(本文摘自2017年上觀新聞對鄭永年的採訪稿)
**【導讀】**近期,在中南海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等9位專家代表先後就中國“十四五”規劃編制等提出意見和建議。作為在中國頗有知名度和爭議性的學者,鄭永年近年來活躍於公共思想領域,和許多學者一樣,致力於推動中國社會科學的本土化和知識生產體系的創新。然而這並非易事。在這篇訪談稿中,鄭永年提出:
其一,不盲目相信教科書,因為中國的現實和書上説的東西,相差太大。其二,在學術研究中,即使沒有政治影響,也會有文化差異,假裝100%中立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儘量爭取價值中立。用西方理念發表作品是很容易,但不能照本宣科,做學問還是要追求接近真理。更何況,向世界解釋中國是中國人的責任,不是西方的責任。其三,做智庫的關鍵是要説真話,否則就可能誤導決策,更重要的是自己不能是利益相關者,否則就會屁股指揮腦袋。其四,中國的大學有時比美國的還美國,我們的學術不能照搬西方,更不能比西方還西方,否則我們的學術研究就沒有自己的聲音了。其五,中國歸根到底最核心的問題還是政治問題,政治這一步走得好不好,決定着中國能不能成為一個新型大國。而事實上,探索好的政治體系,並不只有中國在做,西方也在探索制度重建。
**本文摘自2017年上觀新聞高淵對鄭永年的採訪稿,**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鄭永年教授是當前極具公眾性的學術人物。19歲那年,鄭永年走出餘姚山村,挑着扁擔到北京大學報到。當時村裏沒有電話,北大招生的老師找不到他,中學班主任就為他選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專業。1990年,他懷揣120美元遠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此後長期生活在國外。博士畢業後,他曾在哈佛大學、諾丁漢大學等學校工作,後來成為新加坡東亞研究所的“元老”成員,並於2008年開始擔任所長。
他雖然常居新加坡,但每個月至少來兩次中國,或參加論壇,或到各地考察,也會在媒體上露面。十九大召開前,在大型政論片《將改革進行到底》的第一集中,他便出鏡亮相,談改革必須啃硬骨頭的問題。
我和鄭永年聊了一下午,他有問必答,聊到高興時,還拿出口袋裏的身份證,説:“我到現在還是中國國籍,今年剛把户口放到了老家寧波餘姚鄭洋村。”對於自己的經歷,他表示:“我是越來越覺得做學問實在太幸福了,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其樂無窮。做學問不用冒犯任何人,自己跟自己較勁就行了。不過,我對自己寫的書從來沒有滿意過,好像永遠都只是剛剛開始。”
▍“中國的現實和書上説的東西,相差太大了”
高淵:農村生活對你的學術人生產生了什麼影響?
鄭永年:我現在想想,**農村生活對我影響太大了。**到現在我還是認為,我是作為一個農民在做研究,我從來不盲目相信教科書上的東****西,因為中國的現實和書上説的東西,相差太大了。
高淵:在北大期間,有什麼印象特別深的事?
鄭永年:**第一就是,我發現讀書太容易了,遠沒有務農辛苦。第二是圖書館裏居然有這麼多書,真是看不過來,讀了很多文學歷史方面的書。**剛進學校的時候,我不太自信。但一個學期後,我就考全班第一了,後面名次靠前的全是女生。所以,我真是覺得讀書沒那麼難。但也是因為對其它東西不會,也沒興趣。人家去跳舞了,我不會,人家去唱歌了,我也不會,只能讀書。那時候,我整天就待在圖書館和教室裏,有時候春節也不回家,就在學校裏看書。我們那代大學生可以説是思考的一代,當然有點過於理想主義,但不管怎麼樣,每個人都在思考。
高淵:研究中國問題是從普林斯頓開始的?
鄭永年:我主修政治哲學,還上一些別的課,像比較政治、國際關係等,普林斯頓的教授都蠻強的。後來,我從政治哲學轉向比較政治,這是因為對中國感興趣,我在中國的時候倒是不研究中國問題的。對於政治哲學,我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到現在為止,我一直覺得哲學是不可研究的。****每個人都可以是哲學家,但很難理解這個哲學家到底是怎麼想的。100個人心中有100個尼采,**哲學只能去體會、體驗,所以我從來不去研究他人的思想。
高淵:拿到博士學位後,是怎麼打算的?
鄭永年:我畢業時有兩個選擇,要麼工作,要麼做博士後。我正好申請到了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的經費,這個研究基金蠻好的,基本上可以去任何學校,我選了哈佛。申請經費的題目,就是後來我的第一本英文書,研究中國的民族主義,這實際上跟中央地方關係也有聯繫。
後來出版的時候,我把書名定為“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翻譯過來就是“在中國發現中國民族主義”。因為我覺得,**站在紐約或倫敦看中國民族主義,和站在中國看,是完全不一樣的,我不同意西方對中國民族主義的看法。**所以,我堅持要寫上“in China”。
高淵:因為常去新加坡,後來就決定加入東亞研究所?
鄭永年:那時候叫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他們正好在美國登廣告招人。哈佛大學的漢學家傅高義先生認識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的創始人吳慶瑞,他覺得這個地方挺好,建議我去申請。當時的研究所規模很小,但幾個月後就發生了變化,吳慶瑞先生退休了,進行了改組。我和王賡武教授同一年來到東亞所,他是從香港大學校長任上榮休後過來的,比我早幾個月。改組後,東亞所加入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更名為東亞研究所,王賡武教授當所長。一開始,整個研究所只有我們三四個人,我們繼續招人,所以,我剛來就成“元老”了。
高淵:在諾丁漢大學那三年有什麼收穫?
鄭永年:我在那裏當終身教授。因為由我主導中國政策研究所,我要考慮找什麼人、怎麼發展等,這種經驗以前是沒有的,以前都是在別人領導下工作。另外在學術上,我在英國寫了好幾本書。2005年去的時候,在英國研究中國政治的華人教授,我可能是第一個。所以,來找我諮詢的人很多,英國外交部、首相辦公室、議會也請我去參加討論。這使我學到了很多,也瞭解西方政界到底關注中國什麼方面。更重要的是,那三年讓我進一步瞭解政策諮詢和學術研究的差別,前者要更多從決策者出發,瞭解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假裝100%中立不可能,********************但可儘量爭取價值中立,**********做學問要追求接近真理”
高淵:我發現你每隔一兩週就要寫一個“週日徒步日誌”,每次都要走上三四十公里,你走馬拉松累不累,目的是什麼?
鄭永年:在我50歲之前,做什麼事基本都不累,但50歲以後,如果在辦公室寫一天東西,就會感覺累了。所以我就強迫自己,一週要休息一天。這一天如果待在家裏,估計就是看看書看看電視,我們男人又不愛逛街,最多去書店。
我想來想去,還是覺得走路比較好。因為我一直覺得,**男人需要三種感覺:飢****餓感、疲勞感和孤獨感。走路可以同時獲得這三種感覺。**如果每天吃得很飽,不僅不利於健康,而且不利於思考。現在,我一週有兩個晚上讓自己有點飢餓感,這樣身體就比較舒服。同時,疲勞感也是需要的。如果天天坐在辦公室裏,新加坡的空調又很厲害,這就是負能量。但走路的疲勞是正能量,睡一覺第二天就恢復了。而且,走路也是很孤獨的。這不僅能鍛鍊身體,也能更好地思考。
高淵:一個人走馬拉松,其實就是自己跟自己的賽跑?
鄭永年:對,走馬拉松和跑馬拉松不一樣,**走路就是自己走自己的,沒有目標,能走多少走多少。**我從來不喜歡比賽,也從不參加、拒絕參加學術論文評獎等。上世紀80年代,**讀薩特的存在主義,給我一個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人只能自我衡量,評判標準只能是自己,不是另外的人或物。**所以,我對薩特當年拒絕領諾貝爾文學獎特別佩服,他説人就是自己衡量自己。我的理解就是,自己跟自己競爭,絕不要跟別人競爭。
高淵:現在户口在哪裏?
鄭永年:我以前一直是北大的集體户口,今年我把户口放到我的老家餘姚市鄭洋村去了,辦了新的身份證。我現在是農民身份證,但沒有土地,因此是“失地農民”。
高淵:你打算一直保持中國國籍嗎?
鄭永年:**對我們這種人來説,要放棄中國國籍是比較難的決定。倒不是説有多麼抽象的愛國主義,就是覺得怪怪的。**我1990年就去美國,要放棄中國國籍早就放棄了。其實在國外將近30年,我一直用中國護照,也習慣了。這些年我不知道換了多少本護照,以前要求五年換一次,最近這些年才是十年一換,但因為經常出國,兩三年就用完護照頁了。我想以後寫一寫我的護照的故事。
高淵:準確地説,你是“常年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國學者”。這樣的雙重身份,對於你的學術研究有什麼利弊。
鄭永年:當然會有點困難,主要是認同上的。80年代我讀馬克斯·韋伯的書,他有個理論概念叫“價值中立”,至今影響我的學術態度。
當然,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你要完全中立是不可能,因為即使沒有政治上的影響,也會有文化上的影響。就像我們東方人看西方,和西方人看中國,因為文化上的差異,**要假裝100%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儘量爭取做到價值中立,**這是可能的。所以,我觀察政治,包括觀察中國、新加坡、美國的政治,儘量不把自己的情感加進去,這樣的學術態度雖然比較難,但還是有可能的。而且,中國本身也有這個傳統,司馬遷寫歷史,就是要公正、持中,這是目標,是價值觀。
實際上,對我們這些在海外的中國學者來説,用西方那一套理念發表作品,要容易多了,但我不能這樣,做學問還是要追求接近真理。更何況,向世界解釋中國是中國人的責任,不是西方的責任。
高淵:你領導的東亞所是個知名智庫,你認為什麼樣的智庫才是好智庫?
鄭永年:做智庫的關鍵是要説真話,只有説了真話,政府和領導人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沒有真話,哪裏能有好的決策?**像我們做智庫的人,上至總統部長,下至流氓地痞都要接觸。**更重要的是,自己不能是利益相關者,否則就不可能客觀,這是人的本性,屁股會指揮腦袋。
高淵:作為一個經常做政策諮詢的學者,你覺得應該和政府保持怎樣的關係?
鄭永年:我喜歡打一個比喻,我們學者跟社會的關係,就像醫生和病人。醫生憑自己的知識和經驗,給病人看病。如果沒治好,很多學者喜歡説病人的病生錯了,而不是説自己的知識經驗不夠了。而政府官員比學者更像醫生,他們必須要解決問題。所以我們要研究社會,也要了解政府的想法,底線是不要把病人治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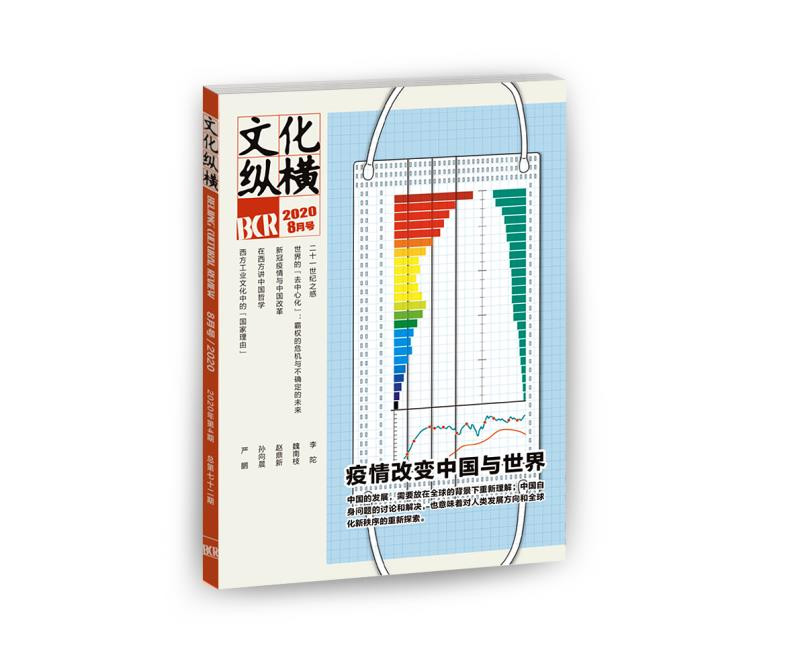
(《文化縱橫》8月新刊)
高淵:作為東亞所所長,你怎麼把握東亞所的研究選題?
鄭永年:**所裏的選題,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各個方面都會照顧到。**對我自己來説,當年去英國的時候,就規劃要寫“中國三部曲”,第一本是解釋中國共產黨,2010年已經出版了英文版,這花了我很多年心血。第二本書可能明年出版,解釋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第三本書現在開始寫了,解釋中國的國家形態。這三本書是互相關聯的。當然,現在又有很多題目出來了,反正是做不完的研究。
高淵:你在中國有很高的知名度,你對此有沒有感到過驚訝?
鄭永年:實際上,我大部分的學術著作都是用英文寫的,當然有幾本翻譯成中文了。我經常被人誤認為是專業的專欄作家,實際上我是寫書的,也編了很多書,當然專欄也在寫,但是業餘的。**寫一篇學術文章或一本學術著作,可能沒有多少人讀,因為太專業,但專欄文章的讀者多很多,這在任何國家都一樣,這就是大眾化。**這也符合我的價值觀,要寫普通人看得懂的文章。
高淵:這些年來,外界對你有不少評論,很多人很崇敬你,但也有些人會批評你,你在意那些批評的聲音嗎?
鄭永年:其實我自己也搞不清,我希望是實事求是、就事論事。我基本上會把中國現在所發生的事放到中國的歷史,放在東亞的歷史,放在世界的歷史來看,一定要把中國放在世界地圖上看,才能看清楚,所以很難説有什麼意識形態。
**這些年來,常有人批評我,説我是不是在投機?我對人家怎麼説我,都覺得跟我沒關係,文章只有寫的時候是屬於自己的,寫完了就不屬於自己了。其實,很多人所理解的鄭永年,和我自己所認為的鄭永年可能是兩個人。**説到底,還是要做自己的事,有態度地去做事,不參與那些無謂的爭論。我觀察政治,但我不參與政治。
▍**********“**********我們的學術不能比西方還西方,否則就沒有自己的聲音了”
高淵:你在美國、新加坡和英國的一流大學學習工作過,這些國家對中國的研究水平如何?
鄭永年:**美國人才很多,但現在對中國的研究有很大的不足,就是太過於微觀,太過於量化。**西方的社會科學有一個長期發展過程,在18世紀和19世紀,馬克思、馬克斯·韋伯等幾代人把宏觀的理論都建立起來了,到二戰前後,中觀理論建設得也差不多了,走向微觀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我上次去哈佛跟傅高義交流,他也蠻擔心的。像他這一代漢學家要花很多時間搞調研,但現在的年輕學者很少調研,就找一套統計數據或者民意資料,然後就閉門寫論文了。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的問題更大,美國還有錢,歐洲要少很多。
高淵:我們自己對中國的研究呢?
鄭永年:我覺得,中國的大學有時候比美國的還美國,比英國的還英國,我們的學術思想和評估系統,都比西方還西方。我們的學術不能照搬西方,更不能比西方還西方,特別不能被西方某一派的思想佔領。要是一直這樣下去,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就沒有自己的聲音了。我現在有點使命感,所以我從不參加爭論,要拿出時間做更多自己的研究。
高淵: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在提“中國模式”,你認為“中國模式”存在嗎?
鄭永年:我相信,“中國模式”是存在的。在我看來,“中國模式”是幾千年來一以貫之的,而現在走到了一個關鍵節點。中國歸根到底最核心的問題還是政治問題,政治這一步走好了,中國就真是一個新型的大國。現在西方遇到了很多問題,打着民主的旗號走不下去了。這200多年來,西方國家大部分時間都是精英民主,但現在在大眾民主的條件下,哪裏有忠誠的反對派?都是為了反對而反對,這是走不下去的。所以從這一點來説,探索好的政治體系,並不只是中國在做,西方也在探索制度重建。
我驚歎於中國這個制度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都能通過轉型,始終一以貫之,我相信中國政治也會是這樣。

—2020年8月新刊目錄—
▍域外
美國:重回“分裂之家”?
吳 雙
▍特稿
01.21世紀之惑——疫情危機與當代資本主義問答
李 陀
▍封面選題:疫情改變中國與世界
02.疫情危機與中國思想界的任務
柯貴福 鄭 濤
03.世界的“去中心化”:霸權的危機與不確定的未來
魏南枝
04.美國長期金融資本向何處去?
唐毅南
05.多難興盟?——新冠疫情與歐盟的秩序危機
章永樂
06.新冠疫情與中國改革
趙鼎新
07.上下聯動:全球化的“義烏模式”
錢霖亮
▍天下
08.在西方講中國哲學
孫向晨
▍公益理論與公益實踐
09.公益的“中國式合作”道路——陝西婦女研究會的實踐經驗
高小賢
10.本土傳統慈善文化的價值與反思——以汕頭存心善堂為例
韓俊魁
▍重述世界史
11.西方工業文化中的“國家理由”
嚴 鵬
▍城市政治經濟學
12.城市病是一種什麼病?
譚縱波
▍觀念
13.小康語義的歷史變遷與現代啓示
張 文
本文原為2017年上觀新聞對鄭永年的採訪稿,篇幅所限,內容有所刪編。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