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後直諫中央“大搞都市圈”, 但為何很多人莫名恐懼大城市?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0-09-01 2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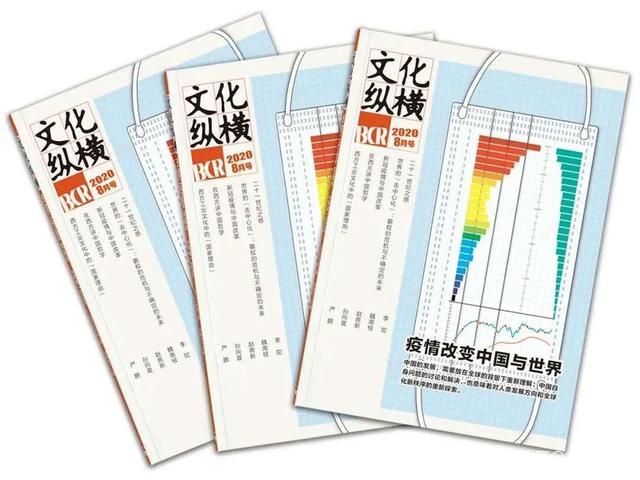
歡迎關注《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 譚縱波 |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
【導讀】8月24日,在中南海召開的專家座談會上,9位專家中最年輕的“70後”學者陸銘提出持續推動中心城市人口聚集、加強都市圈“增長極”作用、優化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供給、加大流動人口子女教育投資等建議,被輿論認為在一定程度上預示了中國城市未來方向。但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規模的擴大,也必然伴隨着對交通擁堵、住房緊張、環境污染、秩序混亂等“城市病“的憂慮。
本文發問:頗具批判意味的城市病,到底是什麼病?作者認為,城市病——更中性地説是城市問題,實為“成長的煩惱”。為什麼人類給自己創造了問題繁多的城市聚居形態呢?説到底還是為了效率,在人類不斷追求生產效率的自然演進過程中,城市問題是發展的必然代價。然而,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傳統社會卻對大城市有着天然的恐懼心理,往往憑直覺批判“城市病”,但沒有意識到城市本身就具有提供穩定生態系統的能力。
因而作者指出,解決城市問題之前,先要正視、撫平“城市恐懼症”,而非不加區分地籠統歸因;城市問題的解決不能僅靠規劃,而要建立在尊重城市發展客觀規律的基礎上。人口規模大、建築密集是城市宿命,也是其優勢。限制人口規模乃至強行疏解人口的方法,無助於從根本上消除城市問題,還可能適得其反。城市問題本身不是“病”,對城市與城市問題認知的誤區,以及城市治理能力的不足,才是“病”。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第4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城市病是一種什麼病?
▍所謂“城市病”
20世紀80年代後期,“城市病”(有時也被稱為“大城市病”)這個情緒化、擬人化的表達詞語出現後,就被廣泛應用到了媒體、專業論文乃至政府文件中,形成了漢語語境下的一種獨特表達方式。它指的是“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交通擁擠、住房緊張、供水不足、能源緊缺、環境污染、秩序混亂,以及物質流、能量流的輸入、輸出失去平衡,需求矛盾加劇等問題”。
學術界更傾向於把城市“人口膨脹”“交通擁堵”“環境污染”“城市貧困”等問題歸結為“城市病”。也有的將其歸結為“自然資源短缺”“生態環境惡化”“交通擁堵”“生活成本上升”“公共資源供給失衡”“公共安全事件頻發”等更加寬泛的範疇。部分社會學研究者也把“城市冷漠”“青少年問題”“乞丐”等也歸入“城市病”的範疇。更有甚者,有人把“狗患”“空巢青年”等現象也作為“城市病”一股腦都算在城市頭上。

本質上,“城市病”是伴隨城市化,城市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大城市的出現而產生的。西方國家對伴隨城市化所產生的城市中的一系列問題採用了一個更為中性的名詞——“城市問題”(Urban Problems)。它與我國“城市病”的話語有明顯差異:首先,針對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同階段所出現的城市問題進行論述,而不是籠統地作為一種抽象的問題,例如早期工業城市的城市問題主要集中在勞工階層生存環境、城市基礎設施不足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公共衞生等方面,而被我們稱為“城市病”的交通擁堵、空氣污染、房價上漲、公共服務不足等問題則是到20世紀80年代才作為主要城市問題提出來的;其次,城市問題的着眼點更多聚焦於生活在城市的社會問題上,如貧窮、暴力犯罪、無家可歸等,而“城市病”更多提及的是城市空間和設施問題。換言之,城市問題本質上是“人”的問題,而不是城市的問題。
從以上的區別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一個如何看待城市問題的基本思路:**其一,城市問題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不同的發展階段乃至不同城市的問題都有可能存在差異,討論問題須界定範圍,並具有針對性;**其二,城市問題源自人類的活動,通過城市中的某些表徵體現出來,所以解決城市問題歸根結底是要解決人的問題;其三,即使認識到城市問題是由人類活動而引起的,仍有必要區分達到城市問題程度的原因是否是由城市這種特定的空間形態所造成的,還是一種人類活動的普遍性問題。有了這個看待城市問題的基本框架,就可以具體來看一看城市問題是如何產生的,以及怎樣才能緩解這些問題。
▍“成長的煩惱”
如果一定要用“城市病”這種擬人化的方式來論述城市問題的話,筆者更願意將被稱為“城市病”的種種現象稱為“成長的煩惱”。事實上,即使一個健康的有機體在其成長過程中也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和煩惱。一個人在嬰兒時代大約只需要完成三種本能的行為:會吃、能睡、不無故哭鬧,就會被視為是完美的。但是好景不長,一旦他到了進幼兒園的年齡,也就意味着好日子結束,開始進入了被各種“問題”和“煩惱”包圍着的日子。入小學、小升初、中考、高考,一路下來,要求越來越多、越來越高,問題湧現,煩惱不斷。這還沒有完,大學畢業即便不考研也要步入社會,參加工作,戀愛、結婚、買房、生娃,沒有一件事是可以輕輕鬆鬆搞定的。所以,人的成長必然伴隨着煩惱,一定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正常的人絕不會因為出現問題而拒絕長大。
“城市問題”也與之類似。“城市問題”出現的根本原因是大量的人類活動聚集在一個異常狹小的空間中所產生的各種不適及其連鎖反應。“交通擁堵”“環境污染”“住房緊張”“公共服務不足”等問題皆是如此。隨着人類聚居點規模的逐漸擴大,從小型村落到集鎮,從城市發展為大城市,進一步成為特大城市、超大城市、都市連綿區,城市問題正是伴隨着城鎮規模的擴大而出現,並愈加多樣化和複雜化。
那麼,為什麼人類給自己創造了這麼一個問題繁多、看上去並不適合生存的聚居形態呢?**在筆者看來,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效率”。**城市產生了社會分工,帶來了生產的規模化效益,促進了技能和知識的傳遞、積累乃至創新,並使得開展大規模社會組織行為、實現共同目標成為可能,同時也使得個體生活的多樣化選擇成為可能。人類的城市史正是這樣一個不斷追求生產效率的自然演進過程,而城市問題則是發展的必然代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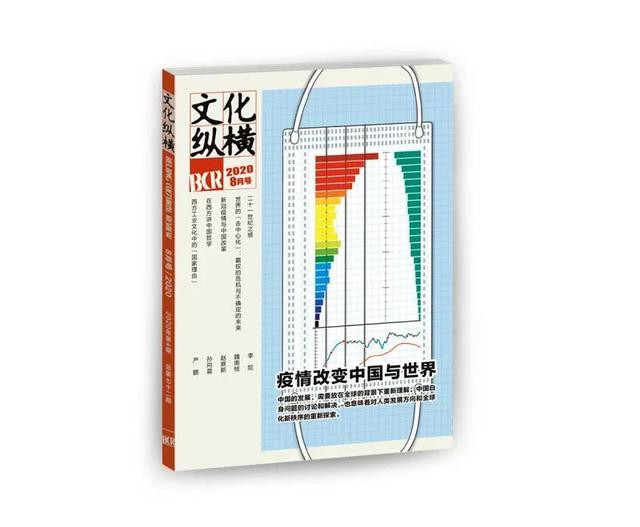
《文化縱橫》2020年8月新刊上市可在微店訂閲:https://k.ruyu.com/8T=90Hl8
▍“生態城市”的悖論
既然聚居規模的擴大會帶來負面效應,那麼有沒有辦法在聚居的正負效應之間取得某種平衡呢?20世紀70年代起,對現代城市的批判逐步演化出一系列“另闢蹊徑”的規劃理論,“生態城市”就是其中的代表。雖然“生態城市”也承認城市的資源和能源使用效率要遠比郊區或鄉村高,但其主導思想仍是希望城市可以融入自然。在“生態城市”之後,“綠色城市”“低碳城市”“景觀都市主義”“生態都市主義”等類似的概念不斷出現。
然而,這些理論通常存在三個致命的軟肋:第一,無法提供與其批判內容相對應的解決方案;第二,任何利用自然力量來解決城市問題的方法均需要付出佔用更多自然空間的代價;第三,缺少具有説服力的實踐案例支撐。
以“生態城市”為例,首先,“生態城市”的12項原則只是一些局部的改善和僅存於設想中的對策,仍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城市與生態系統間的衝突和矛盾;其次,這種過分依賴自然力的“生態城市”由於佔用了更多的空間,實際上對生態系統的破壞更大;最後,“生態城市”好像舉不出太多被實踐證明成功的案例。從阿布扎比的馬斯達,到上海崇明島上的東灘,理念可以很完美,規劃設計也可以很酷炫,但建設工程的停滯和項目流產反而證明了“生態城市”的理論是無法普遍付諸實踐的。
**那麼怎樣才有可能破解城市與生態系統的矛盾?其實答案很簡單,就在城市本身,或者説城市的發明和發展雖然在主觀上是為了追求效率,但在客觀上卻形成了有利於生態系統穩定的模式。**在城市人口規模一定的前提下,相較於“生態城市”所提倡的低密度、富綠色的空間模式,其實聖吉米尼亞諾(San Gimignano)那樣的中世紀歐洲城鎮和紐約等現代大都會才是更加“生態”的聚居模式。格萊澤的《城市的勝利》、陸銘的《大國大城》都在試圖證明這一點。

(類似聖吉米尼亞諾的中世紀城鎮是更“生態”的聚居模式?)
從個體角度看,人們看似悲慘地被侷限在擁擠的城市裏,忍受着諸多的“問題”,但無數個體選擇的集合卻在客觀上形成了較為合理的人類居住模式。與其他形態比較,城市在整體上仍然是解決人類生存與生態系統之間矛盾的最佳方案,可以説是一項**“有瑕疵的成就”**。
▍“城市恐懼症”
在演化史上,食物鏈高端的動物通常繁殖能力較弱,不同物種之間總是趨於相對平衡的狀態。但人類是一個例外。無論是數萬年前採集和狩獵時期對大型哺乳動物的滅絕式捕殺,還是刀耕火種的農業對原有生態的毀滅性破壞,直至工業革命開始大規模開採億萬年積累下來的化石能源,人類在不斷打破生態系統平衡的同時,種羣的數量也在持續增加,遠遠超過了維繫種羣延續所需的規模。城市正是為了容納這一物種的龐大人口而出現的。
雖然城市及其雛形已伴隨着人類存在了數千年,但是聚集了上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卻是工業革命之後的事情。人類面對從未經歷的現象和問題難免產生心理上的恐懼,進而加以否定和排斥。歷史上,空想社會主義者所提倡的“新協和村”(Village of New Harmony)就是面對工業革命後城市問題開出的一劑烏托邦式藥方。霍華德提倡的田園城市雖然在城市規劃理論界被奉為圭皋,但究其本質或多或少也透露着作者對大工業生產時代大城市的憂慮和逃避。
由於我國長期處於專制的農業社會,在近代既沒有經歷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也沒有發生工業革命這種原發性的社會變革,對城市這種聚居形態既無原生的現實需求,也缺少系統和全面的認知,潛意識裏仍將城市作為傳統社會的統治中心,與鄉村保持着若即若離的關係。即便是新中國成立後,對城市的認知依然停留在“消費”與“生產”相對立的觀念中。**“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適度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的城市發展原則一度被列入1989年頒佈的《城市規劃法》,直至2007年。**可見,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傳統社會對大城市有着天然的恐懼和由此而生的抗拒。
**事實上,“城市問題由城市規模過大而引起”這一判斷本身就存在爭議。**施益軍、陸銘等學者的研究發現:無論是“城市病指數”還是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均與城市的人口規模無明顯的相關關係。英國物理學家傑弗裏·韋斯特(Geoffrey West)更是基於對統計數據的分析告訴我們:在相似的社會背景下,城市的規模越大,其所創造出的人均財富和創新越多,所需要的人均基礎設施越少。當然,該研究也沒有迴避犯罪數量和傳染病傳播率也同樣是人口規模的1.15次冪。可見,人類出於對未知事物的本能恐懼,憑直覺判斷而得出的對“城市病”病因的診斷,事實上是不可靠的。在着手解決城市問題之前,人類首先要解決自身的“城市恐懼症”。
▍ 城市問題的對策
既然我們知道了形成城市問題的原因一部分與城市人口規模有關,而另外一些則關係不大,那麼解決城市問題就有可能對症下藥。首先,對於犯罪率和傳染病等與城市規模成正相關的問題,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降低城市人口的規模。理論上,限制甚至疏解城市人口就可以緩解這些問題。但是這種方法會帶來另外多個新問題,一是分散的人口對生態系統的影響更大;二是無法享受大城市所帶來的經濟、創新及基礎設施的高效。同時,還要承擔限制人口的道義負擔。
顯然,如果僅僅是為了解決犯罪率與傳染病傳播率這些問題而限制城市人口的話並不是一個理智的選擇,甚至可以説是一種本末倒置、因噎廢食的思維方式,或可稱為“城市病”的“休克療法”。與之相反,採用技術和管理上的手段將這一類的城市問題控制在最小範圍之內或許是一種更為明智和現實的“保守療法”。
另一方面,類似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已被證明與城市人口規模並非成明顯相關關係的問題則涉及另外一個與城市密切相關的話題——城市治理能力。雖然限於本文的主旨和篇幅不在此展開來論述,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就是對這一類的問題,單純依靠限制或強制疏解城市人口規模是無法解決的。
**城市規劃大概是社會治理工具箱裏面最容易、也最頻繁被想到用來應對城市問題的工具。**起源於公共衞生政策的近代城市規劃也的確扮演了緩解城市問題,幫助實現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角色。但在現實中,城市規劃的角色又時常扮演着“背鍋俠”和“萬能藥”的雙重角色,許多嚴肅的論文都會將城市問題的產生原因歸結為“規劃不合理”,但同時在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時,又將“合理規劃”作為重要的手段,彷彿只要規劃做好了一切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但事實上,城市規劃只是城市治理政策工具的一種,城市問題的解決,還取決於城市規劃之外的多種因素。**仍以城市的人口規模為例,雖然目標年限裏的城市人口規模通常是城市規劃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時還會為此開展專題研究論證,但有多少時候這個人口規模是由城市規劃專業人員客觀測算出來的,又有多少時候是由包括政治決策在內的其他因素所左右的呢?
城市的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它很大程度上遵循着市場規律。而由於市場不是萬能的,需要代表公權力的政府使用諸如城市規劃的政策工具對市場的失靈部分進行糾偏,因此城市規劃的基本態度應該是把握並順應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糾正明顯的“市場失靈”部分,而不是越俎代庖、想象着完成英雄主義的宏大敍事。
具體而言,城市規劃一方面為包括城市開發在內的各種利益的博弈提供了一個相對公正的平台,並監督、執行博弈的結果;另一方面,城市規劃是政府利用税收等財政收入為市民提供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引導城市發展的藍圖。由此可以看出,按照客觀規律合理編制的城市規劃在整體上一定是順應城市發展的需求,並通過對規則的執行和公共產品的提供,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部分城市問題的嚴重程度,而非主觀意願的強勢推進,也絕不是治療“城市病”的“萬能藥”。
現代城市中存在的問題,形式多樣,成因複雜,不宜籠統地將其稱為“城市病”。這種籠統的稱謂或許無意中掩蓋了某些因果關係,久而久之形成錯誤的思維定式。城市問題的緩解,需要建立在尊重城市發展與運行客觀規律的基礎之上。人口規模大、建築密度高是城市的宿命,也是城市的優勢。限制城市人口規模乃至疏解城市人口的方法無助於從根本上消除城市問題,甚至可能適得其反。或許,城市問題本身不是“病”,而對城市與城市問題認知的誤區,以及城市治理能力的不足才是“病”。

— 2020年8月新刊目錄 —
▍域外
美國:重回“分裂之家”?
吳 雙
▍特稿
01.21世紀之惑——疫情危機與當代資本主義問答
李 陀
▍封面選題:疫情改變中國與世界
02.疫情危機與中國思想界的任務
柯貴福 鄭 濤
03.世界的“去中心化”:霸權的危機與不確定的未來
魏南枝
04.美國長期金融資本向何處去?
唐毅南
05.多難興盟?——新冠疫情與歐盟的秩序危機
章永樂
06.新冠疫情與中國改革
趙鼎新
07.上下聯動:全球化的“義烏模式”
錢霖亮
▍天下
08.在西方講中國哲學
孫向晨
▍公益理論與公益實踐
09.公益的“中國式合作”道路——陝西婦女研究會的實踐經驗
高小賢
10.本土傳統慈善文化的價值與反思——以汕頭存心善堂為例
韓俊魁
▍重述世界史
11.西方工業文化中的“國家理由”
嚴 鵬
▍城市政治經濟學
12.城市病是一種什麼病?
譚縱波
▍觀念
13.小康語義的歷史變遷與現代啓示
張 文
本文原發表於《文化縱橫》2020年第4期,原標題為“城市病是一種什麼病?”,篇幅所限,內有有所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刊。

